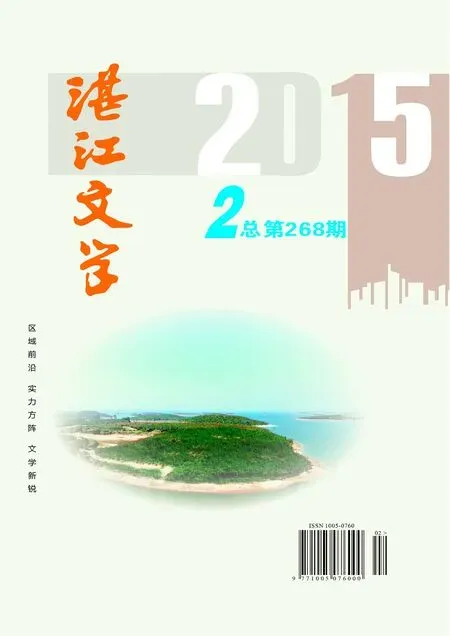郑老夫子
※ 龙 鸣
郑老夫子
※ 龙 鸣
一
生活在太平盛世,让人感情大起大落的事情极少。起码我和周围的人生活得都很平静。平静得乏味而又让人烦恼。神经常常处在松弛涣散的状态,像架弃置不用年久失修的破琴,渐渐变得暗哑麻木。不可思议的是,泪腺也跟着退化了。对我来说,哭泣成了一件很娘们很陌生的事儿。
走进火葬厂的告别大厅,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哭,而且绝大多数是男人。有的神色凝重,站着静静地流泪,有的压抑不住恸哭,肩膀一耸一耸的,身体也扭曲变形。他们都穿着整洁的深色衣服,胸前佩戴白花,一看就知道是些上层人士,用大牙的话说都人五人六的。有些人看着面善,大概是电视里常见。你想吧,一个正常人,听着上百人压抑的痛哭声在大厅里回荡,是个什么感觉?还有那首低沉的哀乐,像只庞大的蝙蝠张着黑色的翅膀到处飞翔。我有些不知所措,大牙回头冲我一笑,低声说:“都是些人物,还这么容易感情冲动。”
我俩傻帽似得东张西望了好一会,有人过来,接过我手里的花圈,安排我们站在队伍里,我这才看见隐在花丛中的郑老夫子,遗体上盖着党旗,瘦小得像个孩子。脸色煞白透明,和他的白色塑料眼镜浑然一体,如同蜡制。火葬厂烧人按个头收钱,恐怕最喜欢郑老师这样的顾客,省油!
郑老师的遗像挂在吊唁大厅正堂上。老夫子穿戴整齐,还像过去那样,极其清瘦。镜片后面眼神诚恳,直看到你心里去……我和老夫子对视着,心里翻腾着乱纷纷的往事,懊怼又揪着心弦袭上来,再加上周围的恸哭声、哀乐声造成的悲凄气氛,心里难受了半天,眼窝便有些潮。我用翻砂工人特有的黑乎乎的粗手指头擦了擦眼,回头看大牙,他也眼圈发红,眼皮眨巴得很快。
二
昨天打牌,大牙忽然楞住,抽出垫在底下的那张市报,看了会,说:“完了”也可能是“晚了”。递给我,指点着一则讣告。
“市政协常委、著名教授郑伯庸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时二十五分去世,终年六十二岁。今定于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北郊火葬场举行追悼会,特此讣告。”
从乡里回来,偶尔也想想过去。觉得饭也吃了,罪也受了,都这样,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比较突出的感觉就是深深地冒犯过郑老夫子,有些愧疚。说起这个话题,大牙也有同感。便商议着什么时候称二斤点心去看看他,说几句道歉的话,请他原谅我们年少无知干得蠢事。可平时除了上班,就是打扑克下象棋,一直没抽出空儿,——竟永远不能了。唯一补救的机会就是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去送送他。商议着,就去买了花圈,顶着风登车擎着来了。
一个人死了,能有这么多人伤心地哭,这辈子活得也值了。这种死简直让人羡慕,不,其实应该羡慕这种人的生。想想自己,如果死了,顶多父母妻子嚎几嗓子,我敢打赌,掉泪的顶多不会超过五个人。
三
1975年8月26日,是我们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由于成千上万的学生一齐转折,就成了重大社会事件,政府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仪式。那天,平时踢着石子在街巷里乱跑的学生一起被集中到马路中间来,穿着过于肥大的军装,腰里扎着武装带,两边是水壶饭包,交叉在胸前的带子上戴着一朵纸做的大红花,把我们十六七岁的年轻脸庞映得通红。锣鼓喧天闹地,鞭炮炸出团团青烟代表着我们的心情——心花怒放,香气四溢。我们心中充满欢乐,从家庭到社会,从城市到农村,我们马上就要冲破双重牢笼,奔向广阔天地啦。毛主席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是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上山下乡的。我们在队伍里兴奋得抓耳挠腮,前张后望。突然听到一个故意压低的喝止声:注意遵守纪律!吐吐舌头,我才发现每个方队前都有一个成年人带队。别的方队前面走着的大多是成年女性,而我们前面则是一个清瘦的老头。他带着啤酒瓶底似的眼镜,脚步和着鼓点,两臂来回摆动。不时回头监视一下他的部队。我们挺起胸膛,对路边欢送的人群招手、行注目礼,走向城门外停放着的敞蓬汽车。等带队干部进了驾驶室,汽车发动起来,我们几个男生互相看了一眼,掏出烟来,用衣服捂着点着火。彻底放松了,疾驰的车带起的风把我们狂野的笑声冲撒一路,惹得路边干活的农民楞楞地看半天。

刚开始学吸烟时,倒没觉得有什么快感,纯粹摹仿一种派。够派的人,比如打进敌营的地下党,运筹帷幄的决策者,必都吸烟。要不就临危不乱,要不就深思熟虑,显得风流倜傥。再就是坏蛋女特务什么的,显得帅。
在中学里就学会了吸烟,也真不容易。特别是头几盒,呛得蹲在墙角吐酸水,胃里翻腾得眼泪直往下掉。不少人没坚持住,被淘汰了。我和大牙,属于那种有毅力的人,经过长期不懈的苦练,终于有瘾了。敲烟、点烟、弹烟灰的姿势也很潇洒老道。中学生,吃老子的,吸烟干嘛的,有点地下党的意思。
当时听着顺耳的口号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猪圈里养不出千里马,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说得多好,长人志气。听着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便没头没脑地兴奋,站在堆得老高的麦秸垛上,挥舞着草叉子,也有一股豪气。役使几头牛,动不动就拿鞭子抽它,也有几分奴隶主般的快乐,不久便腻歪了,多少有些想家。
平时各村窜窜,发现别的知青组有干部领着,拿粮食换豆腐换鸡吃是常事,早晚还弄只羊杀了,熬肥肥的一锅汤,加上芫荽,鲜鲜地喝得满头大汗,多过瘾!实在不行就下套子偷老百姓的狗吃,队长也睁只眼闭只眼。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嘴里寡淡,脑子便往那方面想。到河里炸鱼,到野外抓野兔子,天上跑的,水里游的。藏在土里石头下的,都挖出来打牙祭。嗨,你看人家!
而我们的带队干部郑老师抱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宗旨,搞得成天清汤寡水。这还不算,下到乡里,本以为有了充分的资格,自由自在地抽烟谈吐了,没想到老夫子也管,比班主任的嘴还碎。领教了几回,只好又转入地下。
记得在一个云彩很好看的傍晚,我和大牙正躲在屋后面一丛矮墙下抽烟捉蛐蛐,一边东一句西一句谈着人生什么的。不提防老夫子端着盆走来。我俩都以看见他那一瞬间的姿势定住,不敢喘气。
让他看见可不是好玩的,肯定又是一番苦口婆心的教育,听他再给上一节课,还不如罚去掰两沟棒子。要知道,才刚刚从那里头毕业呐。万幸,他还没看见我们,就先摘下眼镜。我俩相互看了一眼,松了口气。剩下那两只眼加起来恐怕有一千六百度,如果能那样加的话。这样,离他七米之外,只要不吭声儿,就尽可能以放肆。
叼上烟抱着腿,我俩轻松地看着他。他堵在出口处,想走也走不了。再说,既然这么着,也不着急。
老夫子肯定以为这地方挺私密,便作出一些在人前少有的动作来,只见他扩扩胸甩甩手,动作怪异地做了几下原地跑,就摸到盆沿把双手醮了水,抹了肥皂,两只手叠起来,极快地在脸上转了几圈。这样洗脸真是怪,他脸的面积那样小,也只好这么洗。
洗过脸,他脱了衣服,呀,奇瘦!像吓鸟的稻草人蒙上张皮。没有腿肚子。我们街上有个瘸子,他那条残腿就是这样的,看着让人害怕。怪不得他经常坐的棉垫上有两个硬币大的洞,是尖锐的尾骨硌的!
明白了。为了这,他不敢到河里去洗澡。那可是条好河,夹岸生着树荫浓昏的洋槐林,河床上铺满雪白的细沙,河水拐来拐去在上面流,很清。劳累了一天,脱光了跳进去,洗去一天的汗腥、刺闹和疲惫,别提多痛快了!有时候夕阳很红,照得河水像流动的沸钢,人在里头,像一尊尊活动的红铜塑像。挥舞着手臂踢着水花跑,咋呼几嗓子,吓得归巢的鸟又飞起来。洗着,闹着,简直是人间少有的享受。
他猫儿捞鱼似得从盆里抓点水,马马虎虎地往身上撩,迅疾使劲来回搓。肋骨在半透明的黄皮肤下很整齐地滑动,嘴里发出压抑得很细的呻吟声:咦……
我看着自己牛犊子似的身躯,心里陡然升起一丝自豪感。这很难得。通常,被老夫子排在逻辑弹夹上的一发发追问逼得抬不起头。今天,终于在一个缝隙里挤出一丝优越感。心里快活,猛吸了一口烟,呛得差点咳出声来。
回去忍不住对大华和鸡屎说了,他俩在第二天的那个时辰也去看了一回,像是报复了老夫子,也快活的不行。
四
带队干部都兴叫队长,老夫子不让这么叫他,和我们商量,还是叫老师吧,不然就叫名字,名字起了就是给大家叫的嘛!我叫郑伯庸,出自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说着就摇头晃脑,古韵十足。
有老师,便有了学校。我们就不如别村的知青那么自在,讨厌的学还得接着上。
下地干活,社员想出许多古怪的问题问他,在我看那一半是揶揄。老夫子却很兴奋,两片眼镜在太阳下一闪一闪的,一边认真解答,一边仔细地低头寻见草,一根根挖掉。众人见他跟不上趟,把前面的都替锄了。他只得扛着锄跟着走,嘴里仍然絮絮叨叨,也累得气喘吁吁。
晚照里下了工,都下河去洗澡,他不去。回来时见他以床当桌,正伏在上面备课。本子上写得密密麻麻。
队里对我们真是没说的,动不动就置酒相待。社员喂的鸡,记几个工分就抓来炒上。老夫子的迂劲儿上来,每次都生硬地拒绝。弄得大队干部讪讪的无话可说。还不如我们世故,虚推一推,就跟着去了。后来干部请客也就不让他。不到中秋节,满街哑着嗓子叫的小公鸡都吃光了。大队干部真行,接着是羊!老夫子不去吃,也劝我们不要去。说为社员想想吧,工分多了有什么用?一年就那些收成,你们不去他们就没有借口了。这话我们听了也觉得天真。不知谁嘴快,没过夜便传进队干部的耳朵。便都烦他。说吃社员的社员都没意见,他多个鸟嘴。
更烦人的是,每周我们必须听他两个下午的课,课后作业逼得还很紧,像个债主。
五
到最后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教授。他好象什么都精通。你不能不佩服他知识的渊博。和他装得实实在在瘦小的脑袋相比,我的大脑袋整个儿就是一大南瓜。
他给我们开了语文、历史、政治和道德几门课。每一门又包括几个小门类,本子写得整整齐齐,成天翻着头头是道地讲,对我们讲得再好也是白费功夫。反抗精神不那么强,又不十分笨的女生,头年高考就呼拉拉考上好几个。这时候才悔得肠子发青,没想到突如其来的高考是那么容易,三百分就可以上重点,简直白送。可见机会都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那几个女生如今都到大城市去生活,嫁了好丈夫,住上大房子,回来特别喜欢召集我们聚会,这会子与过去需要我们保护的时候可不一样了,人家个个衣着光鲜,谈吐高雅,跟我们几个灰粒子浸进皮肤,怎么也洗不干净的翻砂工比,简直天下地下。此是后话。
有一天他给我们上道德教育课,看着他抑扬顿挫、一本正经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他衣服中藏着的瘦小身躯。和鸡屎对望一眼,便忍俊不禁。笑又不敢在嘴上释放,都憋在脖子里,直憋得血往脸上窜,实在忍不住,就装着咳嗽到外头去吐,泪都下来了。
那时我们只崇拜超人的武力。常怀着崇敬的心情谈论镇西郊。那小子路见不平,拨刀相助,出了人命,去刑场的路上,头昂得像浇铸在腔子上。眼睛贼亮。饿狠狠地再看这世界最后几眼,扫视得众人心里发毛。刑警使劲摁,摁得他屁股都撅起来,脖子也不弯。可惜了那身好拳脚,那身腱子肉,都让黄土沤烂了。
转过神来,老夫子还在诵经僧一样念一段解一段:“……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听不睹,恐惧其听不闻,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慎独也。“
慢慢也觉得明白了些,自讼,就是要挑唆自个和自个过不去。慎独,就是在人面前装模作样还不能算完,独处的时候还要自我管束。还有什么存天理,灭人欲,积学以储宝。终觉得和上级的精神不那么一致。
后来知识涨了价,据说像他这水平,讲一下午值几百上千元。有人写文章夸他,说郑教授在课堂上使讲课成为艺术,听课成为享受。用三寸舌攫住学生的神经,带他们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竟然使那些平日心猿意马的青年不子恨起下课铃声。
那时候如果能聪明起来,认真听他几堂课,这辈子就会换一种活法。说不定还能成为以身任天下,丹心照汗青的角色。那时候冥顽不灵,只觉得心情烦燥,时间难熬……懊悔也没有用了。
终于讲完了。老夫子拿出上回我们做的语文作业,满脸不客气地又数落开了。说比喻、拟人做得不沾边,统统重做!
这下子老夫子激起了“民愤”。他刚离开,都七嘴八舌地骂开了。
六
大牙悄悄扯我的衣服,我看他,他向旁边挤挤眼,顺着望过去,见大华也来了,一脸的哀凄。据我所知,大华先富起来了。
一块儿上来,他分的地儿最差劲——付食店。后来一承包,面貌大为改观。
他承包了一个猪肉零售摊点,操着一把风快的刀卖肉。猿腰轻舒,两臂挥洒自如,一身功夫不亚于疱丁。一年下来,便腰缠万贯,买辆本田摩托骑上,满城乱窜。
从礼堂出来,大华问,回来你们一直没见过老夫子?我点头。他极表愤慨,说你们差劲!旋即又轻松地说:“我算对得起他了,每星期我准给他送回肉,全是里脊。不要也得要。”
鸡屎呢?大牙问。
没看布告?进去啦。他先进了市歌舞团,红了一阵子,后来参加了流氓团伙。
七
社员在地里干活,男女间好开些粗俗的玩笑,先还避着我们,偶尔露出一句,也弄得我们心跳脸红。日子久了就打成一片,不再避讳。我们也觉得接受再教育很见成效,皮肤、感情和话都变得粗糙起来。觉得在太阳底下干活出汗,打情骂俏,开怀大笑,爽心得很!
最令人兴奋的时间是钻进蚁帐入睡前。玩着肚脐交流在四坡里听来的荤素。亮开嗓子大笑,打嗝,喷出一股地瓜味。气得隔壁女生呼呼砸墙,越发高兴。
老夫子便出来干涉。说抽出那两下午学习时间太少,既然睡不着,可以利用一下这个时间,正好男生的学习普遍是差,补补课。于是又开讲。
我看见挨着我的大华爬起来,指着老夫子的帐子,掐着腰,歪着头,脸上极尽各种表情,嘴大动,像是在激烈争吵,不出声而已。闹腾了半夜,账子里纷纷响起了鼾声,老夫子才停下。
再讲,一开始便鼾声四起,老夫子叹口气:等你们知道后悔,一切都晚了。
八
大牙有意于仕途经济,很注意研究官场的学问。那张脸已修炼得颇见功夫。他对我说过,脸上,要反映出对方的需要,不能展露自己内心的变化。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便是中庸之道,孔子毕生鼓吹,自不必说,庄子也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这一直是中国的为官之道。
刚下去不久,大牙就格外显示出要求进步的迫切来,看准行情,让他父亲给队里买了台拖拉机,很快就入了党。
不久,有风声传到大牙的耳朵里,发展他入党,曾征求过带队干部的意见,老夫子极表反对。慷慨道,我追随党已三十多年,入党是我心目中的神圣理想,要加入她,必须具备很高的政治素养,哪能那么容易?
虽然没能阻碍大牙顺利入党,大牙听了,还是觉得老夫子可恶。
九
鸡屎的父母都是搞艺术的。鸡屎人长得帅,还天生有副好嗓子。他歌唱得好,先还清新可听,常在联欢会上演唱,后来,就越唱越带股滑不拉叽的流氓味。
他和队里的一个老光棍十分要好,听了满肚子的《聊斋》故事。那些故事被老光棍去其精华,存其糟粕,净剩些神鬼魔怪和男女私情。鸡屎回来以这方面的专门家自居。央他半天才亮宝似的讲上一个,听得我们个个毛发倒竖或小肚子发热。真够刺激。老夫子找他谈话,也不知怎么说他了,从此结下梁子。背地里说:“人家老辈子是贫雇农,他算什么?本人阶级阵线还分得清!”
他可老辈儿不是光棍吧,要是光棍,如何有他?我顶他,鸡屎笑。
最为苦大贫深的是大华,这小子嘴特馋。夜里常去偷社员的瓜,还拿组里的玉米换豆腐。经常被老夫子当着众人的面说得灰溜溜的。
我那时也恨老夫子,现在想来自然是我毫无道理。但说别人行,我的那些丑事到现在还不好意思抖露,这也是人之常情。
十
骂了一通,还不解恨。大华提议,咱们就老夫子的光屁股打个比喻。谁要不写,不交,谁就是王八蛋,谁就是XXXX!他咬着牙骂了个很毒的誓。大家一至赞成。
鸡屎写:“郑老师的裸体像个剥掉皮的青蛙。”他昨天刚剥了青蛙和那老光棍喝酒,记忆犹新,信手拈来。
大华写:“……像个不足月的羊羔刚离开娘胎。”都觉得这太下作恶毒,迟疑一下,还是叫了好。
我写:“……像个剥掉皮的免子。”鸡屎嚷是抄袭他的。我说一时想不起别的,就这样吧。
大牙写:“……像我写的作文。”都不解。大牙解释:“老师的批语,干吧,没血肉。”还得要注解,都说不好。
不愿意再动脑子了,起着哄交了。
十一
第二天,老夫子不再提上课的事。蔫蔫的,面如死灰,坐在一块石头上发呆。
我心里老大不忍。不光觉得对不住他,觉得也亵渎了自己心里什么神圣的东西,也对不住自己。大牙也显得心事重重。
鸡屎很高兴,溜他一眼。说,在我们,这么治他最大合适。要是把他说的那些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话捅出去,就得把他那把骨头埋在垄沟里。
大华嚷,走哇!自由啦,出去打点野食吧。
既然无可补救,我也想把这事儿尽快忘掉。就跟着出去。鸡屎亮开嗓子唱歌,我们也都跟着对着红艳艳的高梁地高声长嚎。一群麻雀从里面窜出来,直射进村西的一片灰云里去。
十二
从那以后,老夫子成了知青组多余的人。常这里坐坐,那里站站,对什么都插不上手。知青组像一户农家,参加队里分配。领的各样粮食都有,堆满院子。踩来踩去。老夫子应是家长,但他全没有规划。看见谁先下工,就派人去打水、晒粮、或者打面摊煎饼。本来就累,叫谁去谁也不痛快。老夫子似乎不觉,仍絮絮叨叨地催促,一面摸索着带头干。其实,他干活远不如农家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诸事越忙越糟。阴天下雨,粮食混在泥水里,烂了许多,社员看着心疼,纷纷提出批评。支书来组里开会,排了值日。从此各负其责,样样井然。老夫子倒高兴,腾出时间备课,越发讲得多讲得细。
从交了那次作业,老夫子眼睛失了神,面色灰暗,常常发呆,又猛然醒悟急急去干点什么。走起路来飘飘荡荡,像只剩下一个魂灵。
据传,老夫子曾巴巴地找过支书,要求办个夜校什么的。说他能给社员补习点文化。讲点科学种田的知识,说不定在哪里就用得上。支书对着局促不安的老夫子吸了半晌烟,回他,怕不来。说书唱大鼓行。老夫子扭头走了。
吃饭时,值日生端一碗递给他,他像接受施舍,感恩似得接过去,坐在一旁细细地吃,像是咀嚼很苦的东西。他想帮着干点什么,常遇到阻拦。郑老师,您放着吧。郑老师,您歇着去吧。老夫子惨然一笑,躲在一旁。
有的女生心软,见他形销骨立,用体已钱买几个鸡蛋煮给他吃,却弄得他很惶恐。使不得使得。他推出去,连连摆手,弄得那位女生也下不来台。
有人问他问题,他眼睛会突然亮起来,清清喉咙,前因后果,讲起来没完。甚至节外枝,讲起别的。临了,还缠着住人家,央求道:有问题再来问我 ,来问我,呵?弄得人家再也不敢遭惹。
有天吃饭时,我觉得气氛有些点异常。鸡屎和大华老是忍不住捂着嘴笑。老夫子的碗放在石凳上,被另一只碗扣着,老夫子疑惑地揭开碗,呵了一声楞住。都凑过去瞧,碗里盛着几只血淋淋没皮的青蛙。大牙端过去,使劲摔在鸡屎面前,吼,你他妈欠揍!我忙去搀老夫子,发现他抖作一团,呵呵地干呕,泪流满面……
十三
一天,支书在门外招我出去。说,大队里有几斤肉,提了来,包顿饺子,送送老郑。喂,就说是知青组里买的。
怎么要走?
他自己要求的。公社给机关党委打了电话,上面同意了。
我提肉进了屋,正打扑克的众知青一阵欢呼。围上粗粗剁了,大个大个地包成饺子。
老夫子抖擞精神,和大家说笑,已经好长时间没沾荤腥,大家都忙着咽唾沫。饺子包好大家都催着赶紧下,拉风箱的连换了好几个,还嫌慢。锅一开,也不知生熟,立刻被围上,饿虎般舀了去。老夫子锈迹斑斑的搪瓷碗被挤在旁边冷冷空着。老夫子脸又灰了,站在一旁进退维谷,样子十分尴尬。等又下出来,忙给他盛上,他竟一个也没吃下去。
车来了,都吆喝着帮他搬行李。除了个简单的被褥卷,净是些捆扎得很整齐的书。
后来才听说,老夫子本在大学教书,大学里的工农兵学员,给伙食科提意见言词犀利,到了课堂上都木呆呆的,老夫子很失望,认为其不可教化,怀着一个宏伟的计划和献身精神,扶着病体主动要求下乡带知青……
支书急急走来,提着个大口袋,放到车上,回头握住老夫子的手:“郑老,农村就这样,蛮荒。您满腹经纶,日后定有用处。这一去,多多保重。这是点花生,我自己园里收的,您一定得收下。”老夫子眼睛湿润了,重重点头:“我收下我收下,鄙人无能,给您添麻烦了。”说着低头上了车,伏在靠背上。
我们望着开走的吉普车,一阵欢呼。
老夫子走了,我们多了些自由,也觉得少了些什么,时常心里发空。老夫子的床空着,我却时常看见他伏在上面备课,坐在小板凳上,姿势很不舒服。翻着书,把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或者极认真地剪剪贴贴,并且,按时吞下一大把白药片。
后来,这个形象在我脑子里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