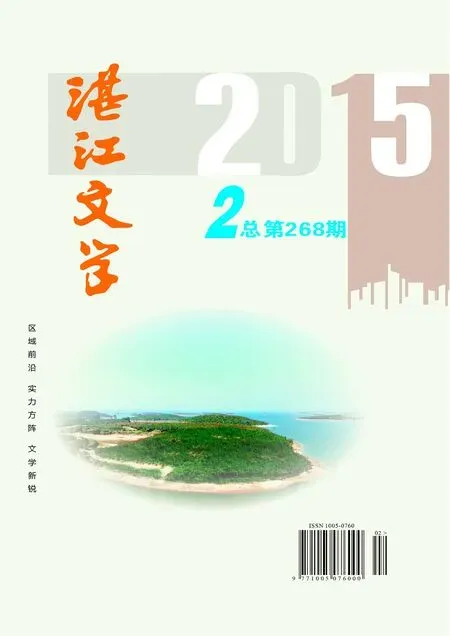存在与超越:梁永利海洋诗歌的生命意蕴
※ 张德明
存在与超越:梁永利海洋诗歌的生命意蕴
※ 张德明

梁永利是雷州半岛上出生并长大的,对于紧邻半岛的那片广漠的海域,他是再熟悉不过了,那里的沙滩、礁石、海风、海浪,那里的红树林、海椰树、相思林,那里的对虾、生蚝、巨蟹,都在他的视野中刻印着深刻的痕迹,留存下独特的身形和姿态。当其他海洋诗人都对这些海洋事物乐此不疲地加以细致描摹、热情礼赞的时候,梁永利却并不热衷于此,我很少在他的诗歌中发现直接描写这些海洋事物的作品。更多的时候,他会越过事物表面的视觉形象,而将思维的触须伸向更为深远的地方,以海洋为文学母题,呈现海洋背后所藏蕴的更有价值的深意。在《古渡遗址》中,诗人这样写道:
欲上岸的鲸 掠开一面坚硬
刺穿古船
在历史的梦境中漂流
看见蓑衣垂钓 孤舟横摆
众多的显贵也踏歌蛮荒
古渡风凄草瘦
叹逝川者是谁
两千年的世面太难见
唯有雷鸣电闪震荡古渡的神经
它的遗骸
为今人的欢颜复活
涨潮之时
鲸的眼睁得太大
远古的中国一直是以内陆文明为基本的文明形态的,海洋文明其实只是古老中华文明中一个极不重要的部分,甚至很可能是极为隐秘的部分。因为此,古代诗歌中的海洋书写是相对稀疏的,海洋远不是古诗中的重要意象和母题。当古代诗人写“渡口”之时,一般都是指河渡、江渡,而很少海渡。“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渡口水流急,回船不自由”(崔国辅《中流曲》),这些都是写河渡与江渡的好诗。相比而言,对海洋世界中的渡口写照,古典诗歌中很难得一见。梁永利的这首《古渡遗址》,从题材选择上说,就是富有新意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并没有停留于对古渡现状的直接描写之中,而是将现实与历史交织在一起,在对历史的缅怀与追忆之中,表露出有关光阴如梭、沧海桑田的感慨和叹惋。
梁永利的海洋诗歌,往往不是外在事物的简单陈列,而是将大海与人类联系在一起,描写海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人的在场,人是海洋景观的观察者和注视者,是海洋变化的记录者和沉思者;描写人的时候,常常将他们放置在海洋场景之中,让海洋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场域,海洋的惊涛骇浪、迷人风物,将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气度充分照亮。在这众多的人物之中,“我”是较为常见的在场者,以“我”为抒情主体和海洋观察者的诗歌作品是相对丰富的。《台风》即是其中一例:
东经117 ° 北纬17 °
这是一个海妖的世界
在陆地 我的耳朵
成了喇叭 海上的旋风
以每秒120公里的风速
前进在我们跳动的心脏
我从黑夜开始
从一棵棵大树开始
掩盖着许多不断动摇的植物
摸黑时刻
海妖毫无情面
把即将下卵的鱼摔死
所有的船舨都铺成她登陆的路
直至东经120 ° 北纬19 °
海妖便潜入到我的风信网
她带着怒气 寻找往年的萍踪
不过是与渔夫的誓言
不过是一次儿戏的情事
多少次葬身鱼腹了 风说
这渔夫 也经常对着海
作惊天动地的胃痛
天渐亮 我看到
海妖被一棵大树刮了胸膛
一条血路通往渔夫的小屋
毫无疑问,“台风”是大海带给海边人家的最为寻常的海上礼物。台风到来时,那巨大的风浪、如灌的雨水和此起彼伏的险情,是海边人早已惯见的充满残忍和暴力的重大海事。不过,由于台风巨大的杀伤力和摧毁性,所以每当其到来时,很多人都悄然躲藏在最安全的地方,用听觉在感受台风,而不是用视觉去直视台风,甚至用身体去亲历台风。因此,很多诗人的台风体验,往往停留在想象和虚拟的层面上,很少是视觉层面乃至身体层面上的。梁永利由于生于斯长于斯,对台风季候司空见惯,他熟视台风,也可能亲历过台风,他的台风书写中,便有了赫然的“我”之在场,“我”是台风中的亲历者,“我”在诗歌中的现身,将台风现象的可信度大大提升。“我”与海妖之间的机缘巧合,道出了台风妩媚而神秘的一面,“我”看到“海妖”被大树刮破胸膛的情景,将台风可怖的一面形象地刻绘出来。不难发现,诗歌中所着力表现的“海妖”意象,不过是对台风超越常人的肆虐状态和不可测度的存在景观所作的拟人化表述。诗人以“海妖”来喻指“台风”,为我们理解与认识台风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并赋予这一场自然灾害以某种神秘感和传奇性。
《台风》以“我”为抒情主体,生动呈现了海边人家的真实生存情态,《海边情事》、《海边渔女》、《老蟹肖力》则更多是站在客观述说的层面,对一些平实的海洋人生命境况的艺术写真。自然,梁永利不只是简单写出了海上人家、临海生命的存在样态,还常常能在描写之中渗透着有关人生和命运的更深层次思考,从而凸显出某种给人启迪的超越意识。这是我更看重诗人作品艺术价值的方面。在《波光一闪而过》里,我读到了这种超越现实的思想信息:
一排水杉 碎银落在空巢
我的小船开得飞快
真以为 鱼腥暖和的胃口
保留了秋莲的滋味
我追寻波光里的影子
我心中的苹果
留下蜻蜓飞过的声音
走过渔村 铁轨交叉前进
沿途的鱼骨贴近窗口
村庄的后面 海盐浸化了古船
我的脸孔苍白
一张海盗的地图
画着出海口 没有风标
没有地名 我发现一面铜镜
与波光一样闪亮
波光是一把刀
很快剥开我的双眼
一切的误会 交给海鸟
海鸟说 我心中的苹果
是天堂的粮食
海洋上的波光以其强烈的照明度和一闪而逝的飞越速度,常带给人莫名的惊悚和极大的不安,诗人也如实交代了面对“波光”时内心的恐惧与惶惑。不过,正所谓“不经历风雨,如何见彩虹”,波光闪过之后,会有希望和光芒的力量在人们内心珍藏。当诗人借海鸟的口说,“我心中的苹果/是天堂的粮食”,我们可以欣慰地发现他在经历波光之后的淡定,战胜惊恐后的升华。
在世界正朝着全球一体化大步迈进的当下,海洋已成为了各国异常看重的新的开发地带和争夺地盘,其地位将越来越重要,海洋书写必将成为未来几十年非常重要的文学形式。面对海洋题材,我觉得还有很多值得开垦的地方,比如其生态学内涵、交通和居住意义、矿藏与军事领属、国家社会力量的博弈等等,相信有这样开阔的书写空间作保障,梁永利的海洋诗歌会越写越出彩,会向我们呈现更多新颖而奇幻的海洋景观,会更为深入地展现其内心深处的存在体验与超越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