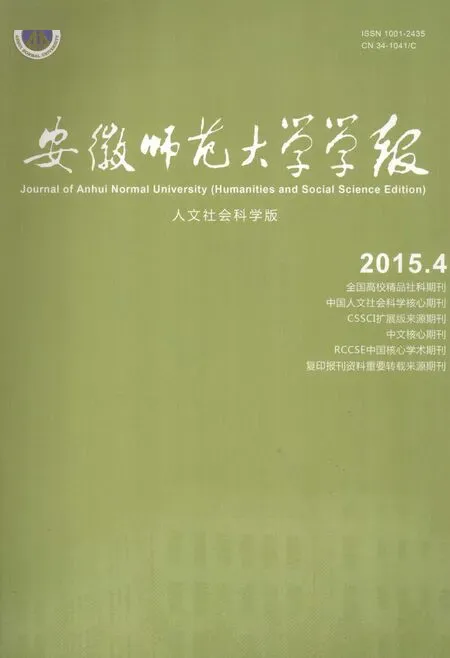《二程遗书》“昨日之会”节考释*
张新国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100084)
近年来,学界越来越重视对于二程语录的划分,即根据其门人记录、年谱考异以及思想特性等加以勘验。而划分程颢与程颐语录的繁难之处在于,门人学生各以自己的语汇记录,且散见于《二程集》中对于同一件事的记录多有理解的不同与思想侧重,这在卷二“昨日之会”节尤其突出。对此,学界尚未有专门的研究,本文拟作历史和义理考证与辨析。这一工作亦涉及书中多则材料的澄清,对理解明道思想及其发展乃至对当时文化实况的把握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缘起及研究价值
《二程遗书》卷一“端伯传师说”,为二程门人李端伯记录。李端伯先于伊川而逝,为伊川所重。在 《祭李端伯文》中,伊川尝道:“自予兄弟昌明道学,世方惊疑,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子与刘质夫为有力矣。”[1]634“刘质夫”指的是二程门人刘绚。刘绚与吕大临对“昨日之会”也均有记录,且较为可信。对于李端伯所记二程语录的可信性,伊川曾加以首肯道:“《语录》,只有李吁得其意,不拘言语,无错简者。”[1]1后来朱子编定 《二程遗书》亦说:“才经李端伯、吕与叔、刘质夫记,便是;至游定夫,便错,可惜端伯、与叔、质夫早丧。”[2]3261幸运的是,“昨日之会”各节分别为李端伯、吕与叔和刘质夫录,可信为真。“端伯传师说”第一节所录为明道与韩维之间的儒佛之辨:
伯淳先生尝语韩持国曰:“如说妄说幻为不好底性,则请别寻一个好底性来,换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圣贤论天德,盖谓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所以能使如旧者,盖为自家本质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义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义也;故常简易明白而易行。禅学者总是强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说,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犹患门人未能尽晓,故曰‘予欲无言’。如颜子,则便默识,其他未免疑问,故曰 ‘小子何述’,又曰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可谓明白矣。若能于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会禅,也非是未寻得,盖实是无去处说,此理本无二故也。”[1]1
李端伯与之后编定 《二程遗书》的朱子都将此条列为第一条,整节内容为明道阐发自己辟佛的重要思想。要之,明道此段语录重在阐发其“道即性”的道体论儒学思想。即在他看来,人性不是像佛家所言是空幻不实的,人性之善就在此浩浩不穷、生生不息的宇宙之道的化育过程中显现,否则就会认定人之善性须在此变动不居的世界之外索寻,而这在明道看来是荒谬和不可能的。这也显示了明道始终以生论性而不特别表彰极本穷源之善性的思想特质。正如陈来所说:“程颢所谓 ‘性’是指人生而具有的现实属性。”[3]程颢一向以温润和蔼见称于后学,而本节明道表述的语气显然偏重。加之,此节并未记录韩维的说法。也只有考定出二者之间在具体时空语境中交流往复的实情,二者尤其是明道思想的全貌方可加以准确衡定。余英时说:“如果想认真了解理学的根本取向,在纵的方面必须把它置于全部宋代儒学的历史动态之中做整体的观察;在横的方面则不但要研究理学家的种种言论而且更应该考察他们的实际行动。[4]920下文对于包含上述明道与韩持国论辩内容的“昨日之会”的考辩,亦即以此为方法论。
二、“昨日之会”考证:历史与义理
“昨日之会”节语出 《二程遗书》卷二上,此章上下两部分均为吕大临于元丰己未(1079)冬见二程后记录。对于包含明道所发儒佛之辨内容的“昨日之会”节语录的考证,在具体方法上分为历史事实考证和义理考证。相对于历史考证,即参考二程年谱,从义理上加以考证显得更为繁难和重要。而后者即“昨日之会”节的义理考证,笔者自觉自始至终将散见于 《二程集》的相关记录不仅考证为明道所言,同时在“昨日之会”节历史语境基础上从义理思想的相关性上加以连贯,希图还原当时的谈论语境。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认为程颢、韩维等人之间相关的学术集会只有一次。
(一)“昨日之会”时间考证
兹将“昨日之会”节录呈如下: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在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他。然据今日次第,便有数孟子,亦无如之何。只看孟子时,杨、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盖亦系时之污隆。清谈盛而晋室衰。然清谈为害,却只是闲言谈,又岂若今日之害道?今虽故人有一(初本无一字)为此学而陷溺其中者,则既不可回。今(初本无今字)只有望于诸君尔。直须置而不论,更休曰且待尝试。若尝试,则已化而自为之矣。要之,决无取。(初本无此上二十九字)其术(初本作佛学)大概且是绝伦类,(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会,大率谈禅’章内,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于此。异时有别锓版者,则当以此为正。”今从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已尔。又要得脱世网,至愚迷者也。毕竟学之者,不过至似佛。佛者一黠胡尔,他本是个自私独善,枯槁山林,自适而已。若只如是,亦不过世上少这一个人。又却要周遍,谓既得本,则不患不周遍。要之,决无此理。(一本此下云:“然为其学者,诘之,理虽有屈时,又却乱说,卒不可凭,考之。”)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执持?今彼言世网者,只为些秉彝又殄灭不得,故当忠考仁义之际,皆处于不得已,直欲和这些秉彝都消杀得尽,然后以为至道也。然而毕竟消杀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气,则须有此识;所见者色,所闻者声,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乐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强曰必尽绝,为得天真,是所谓丧天真也。持国之为此学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尽说得知有这道理,然至于“反身而诚”,却竟无得处。他有一个觉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然无“义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赞易,前后贯穿,都说得是有此道理,然须“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有德行字)处,是所谓自得也。谈禅者虽说得,盖未之有得。其徒(笔者按:暗指持国辈)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国家者,然又须道得本则可以周遍。[1]23
在“外书”之“传闻杂记”中,有记载道:“韩持国与伊川善。韩在颖昌,欲屈致伊川、明道。”[1]435余英时据叶梦得 《避暑录话》记录苏轼乌台诗案推证,“昨日之会”之事可能发生在元丰三年(1080):“二程初至颖昌为韩维上宾和范镇移居颖昌,适同在元丰三年。”[4]71按:据年谱,当为元丰四年(1081)。元丰三年,程颢仍知扶沟县,九月后才罢去。后二程兄弟寓居颖昌(今许昌),侍奉父亲程太中。韩持国所撰 《明道先生墓志铭》中即载:“先生之罢扶沟,贫无以家,至颖昌而寓止焉。大夫(太中公)以清德退居,弟颐正叔乐道不仕。先生与正叔,朝夕就养无违志。”(《宋文鉴》卷一百四十三)“只有望于诸君而”,一个“诸”字,说明明道此语,除指程颐,还说给韩维、范镇等与会多人,此与诸节多人对话相应,均可以拉入元丰四年(1081)四月的颖昌之会。此正与史事相符。
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到任,元丰七年(1084)五月离去(傅藻 《东坡纪年录·集注分类东坡诗》卷首)。余英时的叙述,似未注意颖昌之会是在元丰四年的四月。因为虽然苏轼被贬是在二月,颖昌之会发生在四月。范镇写信给被贬在外的苏轼请教得解老友韩维受佛禅影响之深的对策。但此年的四月为元丰三年,程颢还在知扶沟县,还未前往颖昌。余先生此误似系一时疏略,将年份与月份作同时考虑之过。
元丰四年四月,韩维知颍昌府,常同故友二程兄弟一起论学或游颖昌。此时,李端伯亲炙从学于二程(诸星杓 《程子年谱·明道先生》卷四),遂记有二程与韩维往复问答语,即 《程氏遗书》首篇 《端伯传师说》。程颢、韩维儒佛之辩诸事,程颢又写诗 《酬韩持国资政湖上独酌见赠》述怀:“对花酌酒公能乐,饭糗羹藜我自贫。若语至诚无内外,却应分别更迷真。”韩维也写了 《湖上独酌呈范彝叟朝散、程伯淳奉议》诗:“曲肱饮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愧我未能忘外乐,绿尊红芰对西曛。”[1]24而姚明达 《伊川先生年谱》引 《吕氏童蒙训》载韩维和诗为“闭门读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顾我未能忘世味,绿樽红妓对西曛”[5],有异字,且文不成意,当为误抄或窜改,不当取。
(二)“昨日之会”义理考证
“昨日之会”义理考证首先要求相关语录为明道语。《二程遗书》卷二上:有问:“若使天下尽为佛,可乎?”其徒言:“为其道则可,其迹则不可。”伯淳言:“若尽为佛,则是无伦类,天下却都没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国家为不足治,要逃世网,其说至于不可穷处,他又有一个鬼神为说。”[1]488此节中所问“若使天下尽为佛,可乎”,与“昨日之会”节文中“又却要周遍”所问之意同。“其徒言:‘为其道则可,其迹则不可。’”与卷一“佛学以生死恐动人”节文中“禅者曰:‘此迹也,何不论其心?’”意思相同。明道所答“若尽为佛,则是无伦类,天下却都没人去理”与“昨日之会”节文中“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与“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里去”,据话语理路,应判断均为二程中一人所言,此似可证。语汇字句不完全雷同,其原因在于语录为学生回忆并用自己的话记录。
癸亥八月,即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8月),刘质夫录明道先生语:“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一无老字)之害,甚于杨、墨……故孟子只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字)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1]138按:据以上语录分析,文中两个括号内注为真,现文为后人脱离语境以求话语完备所改。此节明道所言,与“昨日之会”节文中一段文字意同:“然据今日次第,便有数孟子,亦无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杨、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盖亦系时之污隆。清谈盛而晋室衰。然清谈为害,却只是闲言谈,又豈若今日之害道?”“其言近理”与“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意义相印证。由此可知,前三节虽录在文集不同处,但均可证为明道语。故牟宗三径直说“昨日之会”章节“自系明道语无疑”。[6]
韩维信佛笃实,未可以几句论辩可转换其信仰,下文可见韩维的疑惑和诘难:
先生尝论克己复礼。韩持国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错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说道也。克己复礼,乃所以为道也,更无别处。克己复礼之为道,亦何伤乎公之所谓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无可克者。若知道与己未尝相离,则若不克己复礼,何以体道?道在己,不是与己各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复礼,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实未尝离得,故曰 ‘可离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无真无假。”曰:“既无真,又无假,却是都无物也。到底须是是者为真,不是者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1]3
韩维的意思可表述为:道即是当行之道,只可言顺道而行,而不能说有以逆向修为的克己之道。明道所答之意为:克己复礼本身就是道,没有一种道超越日用营为。此意恰如李端伯首节所录明道语:“盖谓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所以能使如旧者,盖为自家本质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义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义也;故常简易明白而易行。”在另一处此节有重出,且明显可见明道的语气更重:“持国尝论克己复礼,以谓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国又言:‘道则不须克。’伯淳言:‘道则不消克,却不是持国事。在圣人,则无事可克;今日持国,须克得己便然后复礼。’”[1]28人物形象随生动的话语跃然纸上。明道后一句即露骨地说:“不消修治即依道而行,那是生知安行的圣人。但是今天的韩持国还没达到这样的境界,你也只有切实下克己功夫,始可言能复归礼义道体。”韩持国继续反驳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则岂不信?盖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见也。凡云为学者,皆为此以下论。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1]141明道一生因材施教,但始终以“必有事焉”的儒学精神接引朋友与门人。
至此,通过对“昨日之会”章的历史时间考证和义理考证,得出的结论为:此节儒佛之辨主要是在程颢和韩持国之间展开的,同时参加集会的人还有范镇和程颐等;程颢为学始曾“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故而明辨儒佛,且深谙以此接引朋友门人之方法。
三、“昨日之会”的其它议题
宋元丰四年四月,韩维知颍昌府,因此常约故友二程兄弟、范镇、范纯礼等一起论学,游颖昌。与会人员文化归宗不一,儒佛之辨也不是唯一的议题。其他人的思想观点,在 《二程集》中也有所反映,但囿于二程门人记录时没有记录具体时间,故而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如,周伯忱记录伊川先生语有曰:“韩公持国与范彝叟、程子为泛舟之游。典谒白有士人坚欲见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见之。’顷之,遽还。程子问:‘客何为者?’曰:‘尚书’。子曰:‘言何事?’曰:‘求荐而。’子曰:‘如斯人者,公(缺一字)无荐,夫为国荐贤,自当求人,岂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以子为不通。子曰:‘大抵今之大臣,好人求己,故人求之。如不好,人岂欲求怒邪?’韩公遂以为然。”[1]270此重申了“昨日之会”的与会人员以及可能触及的其它议题。关于伊川在“昨日之会”儒佛之辨的话题立场,吕大临在卷二记录二先生语有曰:
圣人之教,以所贵率人,释氏以所贱率人。(初本无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 ‘学佛者难吾言’章,一本章首有云云,下同,余见 ‘昨日之会’章。”)学佛者难吾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则无仆隶”。正叔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所愿也;其不为尧、舜,是所可贱也,故以为仆隶。”[1]37
韩持国的疑惑即:“若依照儒家所说 ‘人皆可以为尧舜’,那为什么还会有仆人奴隶这样不同的社会等级呢?”这实在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伊川所答与孟子答复性善之难同:“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即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一种普遍性的可能性,其本身不是充要条件、不具有必然性。可见,相对于伊川,明道更加偏重于从现实人性和佛教的社会文化影响立言。疑似“昨日之会”的话题,还比如:
先生曰:“范景仁论性曰:‘岂有生为此,死又却为彼’,尽似见得,后却云 ‘自有鬼神’,又却迷也。”(与会谈资:儒佛、人性论之外,亦有其它话题)[1]10
持国曰:“凡人志能使气者,能定其志,则气为吾使,志一则动气矣。”先生曰:“诚然矣,志一则动气。然亦不可不思气一则动志。非独趋蹶,药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动气者多,气动志者少。虽气亦能动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1]9
持国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则气住,气住则神住,此所谓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终食之顷未有不离者,其要只在收放心。”[1]10
虽从内容上看,可能为“昨日之会”的议题,由于不能确定此三则具体语境时间,今暂阙疑以备考证。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学术集会,可能触及的话题还不止这些。结合宋代政治文化史,相对于荆公新学,此次学术集会均为保守人士,在政治观点上与王安石壁垒分明。伊川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记此说:
时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进见,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神宗始疑其迂,而礼貌不衰。尝极陈治道。神宗曰:“此尧、舜之事,朕何敢当?”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说,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十余事。荆公与先生虽道不同,而尝谓先生忠信。先生每与论事,心平气和,荆公多为之动。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与言者为敌矣。[1]634
明道论列荆公新法为功利霸道之学,以人君不当取法施治国家。至此,程颢、韩维等人在元丰四年四月的“昨日之会”中,其深一层的议题极可能触及应对王安石变法的政论问题。这个论题的深入发掘,需要其它史料的佐证,另文再叙。质言之,“昨日之会”中明道与韩维之间的儒佛之辨等,集中彰显了明道穷究异学、修其本以胜之的儒学素养和论辩特色,这在时人和后人均有领会。韩持国在 《明道墓志铭》曰:“先生于书无所不至,自浮屠、老子、庄列,莫不思索穷机,以知其意。”[7]相对于韩维之论,朱子说得更透彻。朱子论道:“李端伯所记第一条,力辟释氏说出山河大地等语,历举而言之……今人多说辟异端,往往于其教中茫然不知其说,冯虚妄语,宜不足以服之。如明道诸先生尝深究其说,尽得其所以为虚诞怪癖之要领;故因言所及,各有所旨,未可以为苟徇其说也。”[2]3284明儒高攀龙亦曾说:“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禅书透,识得禅弊真。”[8]此论确然。
[1]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 陈来.宋明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9.
[4]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2011.
[5] 姚明达.伊川先生年谱[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85.
[6]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76.
[7] 王梓才,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明道先生学案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2:1203.
[8]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明道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