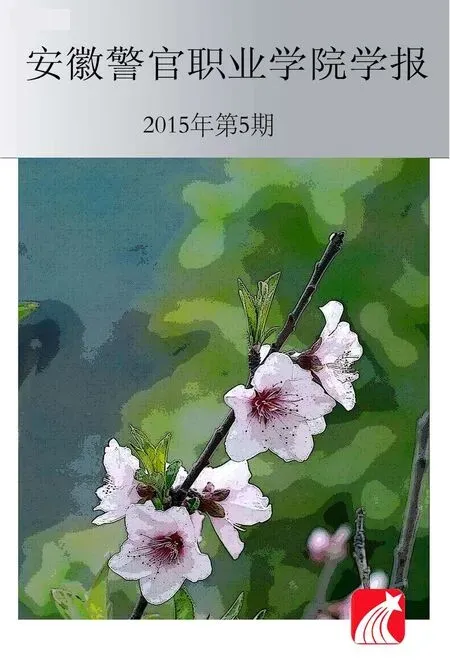论缓刑的法律性质
——兼评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成立累犯的合理性
李瑞阳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论缓刑的法律性质
——兼评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成立累犯的合理性
李瑞阳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缓刑在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所表现的主要特性是不同的,因而对其性质进行分阶段的界定也就有了现实的依据和合理性。从决定是否对犯罪分子宣告缓刑的意义上来说,缓刑有刑罚裁量的性质;从对犯罪分子具体适用缓刑的各项规定的意义上来说,缓刑又具有刑罚执行的性质。缓刑,兼具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两重性质。在明确缓刑具有刑罚执行的法律性质的前提下,认定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相应之罪的犯罪分子为累犯,就有了理论以及法律上的合理性。此种处置,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角度来看,既符合中国社会重视行为人主观意志的现实,又能更好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也是符合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的。
缓刑;法律性质;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累犯
“缓刑是当代刑罚制度的宠儿。”[1]作为一种集刑罚社会化、人道化、个别化等优点于一身并符合当代刑事政策的刑罚制度,缓刑自其诞生之时起就备受青睐,在世界范围内被演绎成多种形式而为各国广泛采用。大体而言,缓刑是指对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在一定的法定条件下,暂不执行宣告刑罚或者暂不执行原判刑罚,以促其悔过自新的一种刑罚制度。[2]从世界各国的缓刑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大致有缓宣告缓刑、缓执行缓刑(又称“缓执行主义”或者“执行犹豫主义”)、不执行余刑的缓刑(有学者称之为“休克型的缓刑”[3]、“震击缓刑”[4])和缓予起诉(又称“缓起诉主义”或“起诉犹豫主义”)等四种缓刑种类。透过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可知,我国采第二种缓刑类型即缓执行缓刑,并细分为普通缓刑和战时缓刑两种具体制度。由于战时缓刑在适用时间、对象以及结果上的特殊性,其与普通公民的联系不大,故此处仅就普通缓刑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
根据我国《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八)》的有关规定,所谓普通缓刑,就是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不予关押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的情况下,可以暂缓关押,并规定一定的考验期限,对其实行社区矫正,如果考验期内没有发生应当撤销缓刑的法定事由,那么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5]然而对于《刑法修正案(八)》第13条规定里“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具体理解,理论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也就因此在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是否构成累犯的问题上有了不同的立场。第一种观点认为,缓刑只不过是刑罚执行的一种变通方式,即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分子不予以关押,通过社区矫正的方法执行刑罚,以避免短期自由刑所固有的弊端,因此,缓刑考验期满就视为刑罚已经执行完毕,而非免于执行。而第二种观点则正好与其相反,其认为“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实际上就是没有执行,也就是说在符合条件时免于执行,当然也就更不存在“刑罚执行完毕”问题了。可见,缓刑的法律性质为何?不仅涉及制度自身在刑事领域的定位,也直接影响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是否成立累犯。
一、缓刑法律性质既有观点的分析
关于我国缓刑的法律性质,理论上有多种不同的见解,主要的观点有:(1)刑罚裁量制度说。该说认为,缓刑属于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而“刑罚的裁量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犯罪人是否需要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并决定是否适用某种刑罚制度的审判活动”[6]。既然决定是否适用某种刑罚制度属于量刑活动的一种,那么宣告缓刑当然也就属于刑罚裁量制度了。(2)刑罚执行制度说。该说认为,缓刑属于一种特殊的刑罚执行方式,是人民法院在确定了犯罪分子的刑种、刑期之后,在综合犯罪分子的特殊预防的必要性等因素的基础上,对于刑罚具体的执行方式所作出的选择。(3)刑罚裁量兼刑罚执行制度说。该说认为,“从裁量是否执行所判刑罚的意义上说,缓刑属于一种量刑制度;从刑罚执行的意义上说,缓刑也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7]。虽然对于缓刑法律性质的争论还有独立刑种说和有条件赦免说等观点,但根据我国缓刑的立法实际我国学者对于此问题的争论,大体上还是以上述三种观点为主。
然而,学术上的研究是自由且无限发展的,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对上述的三种关于缓刑法律性质的观点也提出了异议,并形成了自己具有独到见解的观点:(1)刑罚消灭制度说。该说从三个方面来论证缓刑属于刑罚消灭制度:根据排中律,在刑罚诸项制度中,缓刑只能归入刑罚消灭制度之中;从具体内容来分析,在刑罚的诸项制度中,只有刑罚消灭制度与缓刑的属概念最相符合;宣告缓刑后未立即导致刑罚消灭并不影响缓刑是一种刑罚消灭制度。[8](2)缓刑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该说认为,在我国刑法规定的前提下,缓刑应当定位为介于刑罚措施与传统的非刑罚措施之间的一种中间措施:它是以刑罚的判处为前提、以刑罚的执行为背景的非刑罚措施。[9]
就上述两种新兴观点来说,其理论中虽各有合理成分,但其不足之处也不应该忽视。首先,就刑罚消灭制度说来看,其虽然运用了科学的分析方法来论证其观点的正确,但基础性结论的谬误则直接导致了建立在其上的结论也是错误的。其谬误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提出自有观点之前,该说首先对传统的关于缓刑法律性质的三种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不可取,故而在运用排中律时就直接将缓刑排除出刑罚裁量制度和刑罚执行制度之外,而对上述刑罚裁量兼刑罚执行制度说的否定,则是建立在既然刑罚裁量制度说、刑罚执行制度说都是错误的,那么兼顾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的刑罚裁量兼刑罚执行制度说就必然错误的简单逻辑之上,显然,这种轻率地罔顾缓刑法律性质阶段性的结论是不足取的;另一方面,该说对排中律的运用是建立在“刑罚制度由刑种制度、刑罚裁量制度、刑罚执行制度和刑罚消灭制度组成已经为刑法理论界所公认,亦即在这一判断中刑罚制度这一概念是周延的并已经得到公认”[10]的基础之上的,对于刑罚制度概念是否周延仅用一个“公认”来论证,缺乏严密性,并且,即使这一论断是正确的,那种认为缓刑必须属于四种刑罚制度中的单一一种而默认不能兼顾两种制度的逻辑也是错误的。其次,就认为缓刑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的观点来看,显然不可避免地拔高了缓刑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刑事责任是承担刑法规定的惩罚——主要是刑罚惩罚,也包括非刑罚处理方法的惩罚;同时也包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单纯的否定法律评价,即免予处罚和免予起诉。[11]而将缓刑定位于刑罚措施与传统的非刑罚措施之间的一种中间措施,显然将缓刑提高到了刑种制度、刑罚裁量制度、刑罚执行制度和刑罚消灭制度等刑罚制度之上,不符合实际。并且,“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只是对犯罪分子因其犯罪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而接受国家何种刑事法律制裁的概括性说法,对外只具有将其与一般的民事、行政制裁区别开来的作用,而在刑法理论内部对于分析某种制度的法律性质而言则毫无作用,仅用此说明缓刑的法律性质,缺乏说服力且有逃避问题的嫌疑,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将刑罚执行所涉及的所有制度都冠以“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法律性质,显然,这是毫无意义的。综上,新兴的两种关于缓刑法律性质的观点不具有可取性,因此,探究缓刑的法律性质还是要从传统的三种观点中来寻找。
二、缓刑法律性质的确定
对事物性质的分析,应当建立在全面客观的基础之上,不能盲人摸象般地只看到事物整体中的一部分就妄下结论。况且,由于所处的阶段不同,事物也完全可能以不同的状态存在。因此,对于缓刑法律性质的分析应该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的指导下,全面审慎的进行。通过对缓刑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研究,传统的第三种观点,即刑罚裁量兼顾刑罚执行制度说是比较可取的。一般情况下,学者们在对该观点进行批判时,往往都是以“上文已论证缓刑既不属于刑罚裁量制度,也不属于刑罚执行制度,因此将刑罚裁量制度说与刑罚执行制度说论者的理由相结合来论证缓刑属于刑罚裁量兼刑罚执行也是不成立的”[12]这种逻辑来推论的。因为缺乏对该观点更为深刻的理论挖掘,也就忽视了其所具有的合理性。
实际上,根据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缓刑是处于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阶段的制度,具有宣告和执行这两个阶段。缓刑宣告是指在对犯罪分子定罪判刑的前提下,根据其自身情况是否符合《刑法修正案(八)》第11条的规定,进而决定是否对其宣告缓刑。此阶段,人民法院所履行的职责主要是在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运用法律赋予其的裁量权,决定是否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以及缓刑的考验期。也即此阶段主要解决的是在具体案件的刑事处罚中缓刑是否可以存在的问题。而缓刑执行则是指在缓刑考验期内,犯罪分子须遵守法律规定进行社区矫正,并严格遵守法律对其在考验期内进行某些活动或进入某些区域的限制,如果缓刑考验期满,没有发生法定事由,则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否则,就撤销缓刑,或数罪并罚,或执行原判刑罚。此阶段,主要是由有关部门根据法律规定赋予的职权执行人民法院做出的缓刑判决,并且在缓刑考验期内,犯罪分子随时面临着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而被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的危险。也即此阶段解决的是缓刑的具体执行问题。
诚然,自由刑和生命刑在法院判决是否适用时也存在刑罚裁量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缓刑的适用,刑法特别规定了 “在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不予关押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等考量因素,而这些是其他刑罚所不具备的。也就是说,就刑罚裁量的角度来看,是否适用缓刑所需要裁量的程度要远远大于其他刑罚,并且此种裁量已使缓刑在刑事判决阶段具有了与其他刑罚方式所不同的法律性质。根据事物的某些方面性质所表现的程度不同,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在性质的描述上做出明确的区分。虽然这种程度不同的分界线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标准,但是就已有的两样事物在此种性质的程度差异方面,我们还是可以进行正确判断的。
另外,缓刑的考验期内,刑罚的严厉性并不表现在直接对犯罪分子的惩罚,而是重在对犯罪分子的威慑,以及那种因犯罪分子若不遵守缓刑的相关规定,原判刑罚就会存在立即执行的危险。相对于自由刑直接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和死刑直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而言,缓刑表现出的是对犯罪分子一定时期内意志安定和部分人身自由的剥夺。毕竟,一个合法公民是可以自由出入那些特定机关以外的任何场所的,并且不必担忧被执行刑罚。虽然暂缓执行所判刑罚,但并不就是对犯罪分子就像普通公民那样给予其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其所表现的对犯罪分子在刑法上的否定性评价和对其部分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及意志安定的影响,也足以表明缓刑在执行中具有区别于一般民事和行政制裁措施的严厉性。
既然缓刑在刑事案件相关联的两个阶段,所表现的主要特性是不一致的,那么将缓刑的法律性质按阶段分情况来进行界定也就有了事实上的依据和必要。因此,采刑罚裁量兼顾刑罚执行制度说,认为“缓刑是两个阶段的结合,在法律性质上,缓刑既是刑罚裁量制度,又是刑罚执行制度”[13]的观点是科学而且合理的。所以,虽然缓刑在实际上可能并未执行原判刑罚,但是根据其内含的刑罚执行的法律性质,更应该将在执行阶段的缓刑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刑罚执行方式。“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并不是免除了刑罚,更不是取消了原判刑罚,而是通过缓刑的方式执行完毕。
三、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成立累犯的合理性
累犯,是指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一定时间内又犯应当被判处一定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14]理论上通常认为,国家法律之所以要对累犯进行从重处罚,主要是因为这类罪犯先前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但是在刑罚执行完毕后又犯较为严重的犯罪,表明其主观恶性大,具有特殊预防的必要性。虽然,理论界一直有人认为我国关于累犯制度的规定,有重复评价的嫌疑,对累犯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15]但是累犯作为一项我国刑法的既有规定,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要对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问题进行研究,以确保现行法律正确实施的同时,最大限度保全公民的合法权益。
我国《刑法》第65条第1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从这一规定来看,构成累犯的起始时间应是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否则,就应当按数罪理论中或合并或并罚的规定进行处理。而对于符合条件的缓刑犯在考验期满后再犯一定之罪时是否构成累犯的争论,也主要集中在其是否满足构成累犯的起始时间条件。也即此争论的症结,就是如果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遵守了法律的各项规定,缓刑考验期满是否为“刑罚执行完毕”。
由前述可知,缓刑的法律性质因其在刑事处置过程中的阶段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法律性质:从决定是否对犯罪分子宣告缓刑的意义上来说,缓刑有刑罚裁量的性质;从对犯罪分子具体适用缓刑的各项规定的意义上来说,缓刑又具有刑罚执行的性质。因此,认为缓刑考验期满的犯罪分子再犯较严重的犯罪因不符合构成累犯的起始时间条件而不构成累犯的观点,由于其实际上否定了缓刑所具有的刑罚执行的法律性质,故其合理性就值得商榷。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满后,虽然其原判刑罚不再执行,但也改变不了其犯罪行为的法律性质,以及因为犯罪而受到国家刑事法律否定性评价的事实,是属于有前科的人。况且,缓刑并不具有消灭原判刑罚的特性,其只是对原判刑罚的一种特殊执行方法,主要目的是避免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因短期自由刑而受到交叉感染,避免过分强调对犯罪分子的惩罚而忽略预防犯罪的现实问题。缓刑是在综合考虑了犯罪分子个人的人身危险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刑罚的消极影响等因素后,所设置的一种特殊的刑罚执行方式。其所具有的不同于民事和行政制裁的严厉性也是无可置疑的。明确了缓刑的执行具有刑罚执行的性质,也就明确了缓刑犯考验期满后再犯罪的应该构成累犯这一结论的合理性。
从刑罚特殊预防的角度来看,既然缓刑犯在考验期满后又犯了一定之罪,就表明其主观恶性大,从重处罚是合情合理。虽然先前的缓刑宣告是基于其在罪行较轻、有悔罪表现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较小的人身危险性,但是缓刑犯再次犯罪就表明了先前的缓刑并没有达到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作为一个自古就强调以“德主刑辅”来规制社会的重视行为人主观意志的国家,在现时代,虽然我们可以在禁止主观归罪的原则指导下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评判标准,但也改变不了中国社会重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现实。所以,对这样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从重处罚,既是对其藐视法律的回应,也是对社会公众情感的回应,更是刑事法律规范社会行为的应有之义。
从刑罚一般预防的角度来看,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一定之罪成立累犯,表明了国家对犯罪现象零容忍的态度,是对社会上潜在的危险分子的震慑,也是对已经存在的或将来存在的那些受到过缓刑判决的人的一种警示。虽然刑罚的功能在预防犯罪方面的效果有限,但也不能否认相对加重的刑事处罚会对选择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分子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在预防犯罪方面收到一些实效。康德虽说“一个人永远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服从他人的目的手段”[16],但其也只是强调人是目的,而没有绝对否定人作为一种手段而去实现他人或社会的目的。由此来看,刑罚的一般预防的功能,不能仅仅就用人不能作为手段就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累犯制度有助于刑罚一般预防功能的发挥,而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构成累犯,则是对现有累犯制度的合理诠释,以助于其发挥制度优势而优化刑罚执行效果。
四、结语
对事物性质的正确认识,往往会有定纷止争的效用。而对事物性质的分析,则一定要立足于全面客观的分析这一基础之上。缓刑在解决刑事案件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因其侧重点不同而导致了其法律性质的差异。我们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对缓刑的法律性质做出正确的界定。正因为缓刑在执行阶段具有刑罚执行的性质,所以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原判刑罚不再执行的,就应当认为刑罚已通过缓刑这一特殊执行方式执行完毕。如果再在一定时间之内犯一定之罪的,就应当构成累犯,从重处罚。支持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能够成累犯,并不是迷信刑罚功能的重刑主义,而是在对犯罪分子主观恶性大、特殊预防必要性大的理性判断之下,基于社会一般预防的必要而做出的慎重选择,其定罪量刑的基础仍然是犯罪分子依据法律所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缓刑考验期满后故意犯罪构成累犯,符合累犯制度的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应该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达成共识。
[1]甘雨沛.比较刑法学大全(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1137.
[2]顾肖荣.体系刑法学——刑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164.
[3]朱华荣.各国刑法比较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264.
[4]储槐植.美国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36.
[5][8]左坚卫.缓刑制度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7,20-21.
[6]赵秉志.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76.
[7]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41.
[9][10]冯全.中国缓刑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13,22.
[11]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8.
[12]屈耀伦.我国缓刑制度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109.
[13]王炳宽.缓刑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9.
[14]刘宪权.刑法学(第三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02.
[15]周光权.论量刑上的禁止不利评价原则[J].政治与法律, 2013(1):109-116.
[16]邱兴隆.罪与罚讲演录[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61.
On Legal Nature of Probation——Comment on Rationality of Recidivism Caused by Criminals after Expiration of Probation
Li Ruiya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42)
Probation has different featur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riminal proceedings,which thereby provides the realistic basis and rationality to the nature of its definition.From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the criminal on a sense, the nature of probation have penalty discretion;from the provisions of the applicable probation in a specific sense, probation has the nature of punishment execution.Under the premise of making clear the legal nature of penalty execution of probation,recidivism has the theory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law.This kind of treatmen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prevention and special prevention,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reality of Chinese society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erpetrators subjective will,and can better develop the function of punishment to prevent crime,also conforms to our country current criminal policy and the law.
probation;legal nature;measurement of crime punishmen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nalty; recidivism
DF613
A
1671-5101(2015)05-0001-05
(责任编辑:孙雯)
2015-06-28
李瑞阳(1991-),男,河南洛阳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2014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