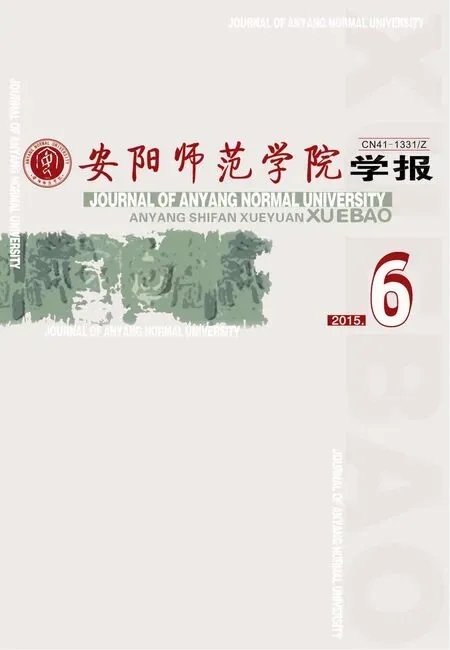中国新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李兴阳,朱 华
(1.湖北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2.湖北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中国新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李兴阳1,朱 华2
(1.湖北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2.湖北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中国形象是晚清以来中国新文艺现代性建构的重要内容。晚清至民国初期,以报章小说为主的中国文艺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可概括为“过去之国”、“未来之国”和“新生之国”三大类型;“五四”至1949年,中国各类新文艺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可以概括为“病态中国”、“青春中国”、“革命中国”、“都市中国”、“乡土中国”和“战时中国”等六个类型;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各类新文艺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文革中国”、“改革开放之中国”、“现代中国”、“世俗中国”和“东方化中国”等六个类型。中国新文艺在不同历史时期塑造出的中国形象,具有不同的国家形态与时代精神,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国家形象历史演变的现实投射与新文艺家们主观想象的艺术之果。
中国新文艺;民族国家想象;中国形象
中国形象是晚清以来中国新文艺现代性建构的重要内容。这里所谓的中国新文艺,是指晚清至今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报章小说、戏剧、诗歌、散文、舞蹈、音乐、电影、电视、绘画、雕塑、摄影、书法和建筑艺术,等等。中国自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在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与鸦片毒品的夹攻下走向衰亡开始,历经近代、现代和当代的百年沧桑巨变,由一个传统的王朝国家逐渐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国家形象在百年历史演变的每个阶段都有新的变化,都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特征。与之相应的,中国新文艺在不同历史时期塑造出具有不同国家形态与时代精神的中国形象,即如有论者所说:“中国形象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作家和诗人们总是从不同角度去想象中国。”[1]
一、清末民初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晚清至民国初期,是中国由封建王朝国家被迫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大变革与过渡时期。在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里[2],晚清至民初的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3]。以报章小说为主的中国新文艺及传媒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可概括为三大类型:
其一,“过去之国”[4],指正渐趋衰亡的晚清王朝。鸦片战争之后,曾经的“中华帝国”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无论是整体的综合国力还是国家的客观形象,都一落千丈。刘鹗的《老残游记》把贪污腐败、苛政如虎的晚清王朝喻为航行在太平洋上即将沉没的“危船”;曾朴的《孽海花》也把昏庸无能、积贫积弱的晚清王朝喻为“陆沉奴隶国”和“陆沉奴乐岛”;陈天华《狮子吼》把朝廷昏庸国人浑噩备受外敌欺凌赔款割地的晚清中国比作“混沌国”,这“混沌国”曾经轰轰烈烈做过,辉煌过,后来为自古流传下来的忠君邪说所害,衰败了,被蚕食国、鲸吞国、狐媚国蚕食分割,竟至灭国;又比作“睡狮”:“原来此山有一只大狮,睡了多年,因此虎狼横行。”即将逝去的王朝在这里留下了残破的旧影。
其二,“未来之国”[4](P9),是晚清新知识分子想象中的理想中国,亦即以西方民族国家为参照所构想的新型国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将其称之为“新中国”。吴趼人的《新石头记》、陆士谔的《新中国》、蔡元培的《新年梦》、陈天华的《狮子吼》(未完成)等小说也都围绕“新中国”而展开对未来中国的想象与形塑。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设想的是未来的“西历两千零六十二年”中国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国家,已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于是各国都来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好一幅国家富强、科技昌明、学术发达的盛世图景。在《新石头记》中,吴趼人让贾宝玉再度入世,寻求救国救民创建民族国家的救世良方。贾宝玉终于看到中国立宪已成,“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上海世博会也盛况空前,“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国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在《狮子吼》中,陈天华设想了一个作为“世外的桃源,文明的雏本”的“民权村”,村里“有议事厅,有医院,有警察局,有邮政局。公园,图书馆,体育会,无不俱备。蒙养学堂,中学堂,女学堂,工艺学堂,共十余所。此外有两三个工厂,一个轮船公司。”[5]这是一个袖珍版的现代民族国家。“民权村”中的“豪杰”不满足“新村”实验,“后日竞把中国光复转来,变为第一等强国。”[5](P36)晚清小说想象中的“新中国”,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国体、政体和国计民生等方面都呈现出现代民族国家特征。
其三,“新生之国”,指民国初年时的中国形象。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新的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想象中的“新中国”已然变成了现实。但“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清王朝的覆灭,并不意味着封建制度的自然瓦解,它是外力压迫、由此提前发生的政治革命、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三种力量重合的结果。在中国的土地上,远未来得及产生足以支撑民主共和国制度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和思想文化。”[6]这使民国初期文学对“新生之国”的想象,远不如晚清小说对“未来之国”的“新中国”的想象那么清晰而热烈,充满了失望、愤懑和哀婉。李涵秋的《广陵潮》、朱瘦菊的《歇浦潮》、平襟亚的《人海潮》、包天笑的《甲子絮谭》、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等作品,都对民国初期军阀混战、社会混乱、灾难频仍、民不聊生等残酷的社会现实有逼真的叙述,对国民麻木愚昧、人性扭曲、道德堕落等也有揭示。民国初期文学对“新生之国”的现实描述与叙事想象,重现了“过去之国”的旧影,展现了“未来之国”的理想被无情击碎的冰冷现实,起到了促发国人觉醒,开启思想文化启蒙的历史作用。因而,也可以说是“五四”新文艺在“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性维度上重塑“中国形象”的历史预演。
二、现代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五四”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态在启蒙、革命与救亡的时代变奏中,不断重组、变换和转型。在历史中抉择而又在抉择中变幻不定的中国,呈现出自身形象的多个侧面与不确定性。在血与火的年代里,想象中国的方式,不仅有小说、报纸等比较传统的“技术上的手段”[7],而且出现了电影、广播、话剧等新的技术手段和传播媒介。以小说、戏剧、电影等叙事性文类为主的中国文艺及传媒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丰富多彩,类型多样。而其最重要者,至少可以概括为如下六个类型:
其一,“病态中国”,这是启蒙话语形塑的中国形象,是与启蒙话语理想中的现代民族国家相悖的国家形象。在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比照下,那个时代的中国,其病态是多方面的,而最突出者就是国民劣根性。国民的精神疾患之一就是在长期的封建王朝统治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臣民”意识,缺乏“公民”意识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梁启超讲要“新国”必先“新民”,鲁迅讲要“立国”必先“立人”,而“新民”和“立人”的重要内容就是要通过启蒙,让国民形成公民意识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老舍曾经说:“‘五四’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8]如其所言,民族国家意识贯穿在老舍的《二马》、《赵子曰》等作品中。如《赵子曰》中的理想国民李景纯走的就是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道路,他教导赵子曰们要为国为民学好真知识,要有真本事,要有民族自尊心,要有国家观念,要爱国:“我们的人民没有国家观念,所以英法联军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德国人搬走我们的天文台的仪器,我们毫不注意!这是何等的耻辱!试问这些事搁在外国,他们的人民能不能大睁白眼的看着?试问假如中国人把英国的古迹烧毁了,英国人民是不是要拼命?不必英国,大概世界上除了中国人没有第二个能忍受这种耻辱的!所以,现在我们为这件事,哪怕是流血,也得干!引起中国人爱国心,提起中国人的自尊心,是今日最要紧的事!”[9]
其二,“青春中国”,这是李大钊呼唤的理想中国,是受“五四”启蒙精神洗礼的中国,是郭沫若诗歌、巴金小说等文艺作品中想象的新中国,是“病态中国”浴火重生的有朝气有活力有希望的民族国家。在郭沫若的诗歌《女神》中,祖国是令人无比眷恋的“年青的女郎”,是令人常常思念的“故乡”,是“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凤凰。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从封建之《家》中突围而出,投身到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激流中,虽然免不了倾轧、斗争和悲剧,但洋溢着浓郁的“五四”青春气息。
其三,“革命中国”,是现代中国文艺塑造的国家形象最突出的一面。革命是近现代中国不得已的历史选择,“近现代中国革命者所谋求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的富强,即现代化。在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之前,或最终决定以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时,都曾对改良或渐进的道路寄以希望,如甲午战争之前的孙中山,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但是,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这条道路是不可能通达中国富强的目标的。旧政权的腐败、面对现代化挑战的无能为力、帝国主义影响的根深蒂固等等,促使他们最终认识到,唯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旧体制,摆脱列强的控制,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立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10]中国近现代文艺的“革命叙事”也是感应历史的叙事选择。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叙事”所塑造的“革命中国”是不一样的,如在中国早期新闻纪录电影《武汉战争》和《上海战争》这两部“多少纪录了一些有关中国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斗争的史实”的影片中[11],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历史旧影;在蒋光慈的小说《短裤党》中,可以看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历史图景;在歌剧《白毛女》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给中国乡村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革命中国”是近现代中国追求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的历史写照。
其四,“都市中国”,是现代中国形象中最为迟滞的一面。但都市现代化是中国这个传统农耕文明悠久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最大、最深刻的“中国经验”,也是最早同时最具有未来意义的“新中国”想象。在晚清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新石头记》(吴趼人)和《新中国》(陆士谔)等作品中,都以幻想中的未来上海“世博会”极显未来新中国的富强,“都市中国”在这些作品中成为“新中国”的理想图景。在中国现代文艺的都市想象中,“都市中国”有多副面相,如“现代都市”、“病态都市”、“传统都市”等。在“新感觉派”小说中,晚清小说想象的“现代都市”已然更加现代,活动在那里的都是跟着感觉走的“时间不感症患者”;在沈从文小说《八骏图》中,都市具有戕害健康生命的“阉寺性”,同样的“都市病”在张爱玲小说中有更冷冽的表现;在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传统都市”日趋崩塌的历史暗影;在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中,可以看到都市不同阶级之间的搏杀与中外资本之间的缠斗;在电影《都市风光》(袁牧之编导)里,则可以直观地看到“旧中国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畸形怪状”[11](P392)。值得玩味的是,代表现代工商文明发展成就的都市,甚至被想象为现代民族国家发展方向的都市,在中国现代文艺作品中几乎总是以负面形象出现。
其五,“乡土中国”,是正在逝去的农耕文明的留驻地,是追求现代化的中国最大的疼痛。在中国现代文艺作品中,“乡土中国”也有多副面相,如“病态乡土”、“革命乡土”、“纯朴乡土”、“翻身乡土”等。在以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等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中,可以看到启蒙话语烛照下的“病态乡土”,国民的精神痼疾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阻力,没有现代国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在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孙犁的《荷花淀》等小说中,可以看到农民在贪婪的经济掠夺与凶残的外敌入侵的绝境中觉醒并奋起反抗,这就有了农村革命。“革命乡土”是“革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等小说中,可以看到“纯朴乡土”,那里的人们仿佛生活在化外之地,而这又可以看成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另一种理想图景。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小说中,可以看到土地革命洗礼过的“翻身乡土”,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共建立政权的解放区这片“翻身乡土”里,形成了自己的雏形。
其六,“战时中国”,不仅仅指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自晚清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几乎都处在战争状态中。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伐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似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这片历史悠久而又多灾多难的国土。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战争造就国家和民族”,“国民身份、国家特性都是在战争坩埚之中凝结而成的”,他引证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的话说:“没有哪个国家不是诞生于战火之中的……没有哪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群体能够不经历武装冲突或战争威胁,就把自己确立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新的和独立的角色。”[12]确如此论,战争给现代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却也唤醒了国民的民族意识,培育了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如《风云儿女》(田汉、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中的东北知识青年在“九一八”后,不恋儿女私情,以民族国家为念,投身到民族解放战争之中。自晚清以来的中国文艺从来就没有停止对战争的叙述,战争影响了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艺,中国文艺的战争叙事也影响了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
三、当代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最迫切需要的前提条件即现代民族国家,最终确立起来了”[13],中国由此告别过去的全部屈辱,进入新的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由此带来中国文艺根本性的变化。在和平建设民族国家的年代里,想象中国的方式,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广播、报纸等艺术手段和传播媒介之外,还出现了电视剧、电视、网络等新型的艺术样式与快捷的传播媒介。有更多新艺术手段和新传播媒介的中国当代文艺,其中国形象塑造,虽然延续了中国近现代文艺的诸多新传统,但也有了时代的新内容新特征。中国当代文艺塑造的中国形象,在不同时期有应答时代召唤的不同形象类型:
其一,“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中国“十七年文艺”塑造的中国形象。这里的“新中国”不是君主立宪、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其形象塑造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叙述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历史,为新生的民族国家确立历史的合法性,如小说《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电视剧《小八路》(姜坦、李晓兰导演)等都是“革命历史叙事”类的作品。第二,反映建设新中国的现实生活,有叙述现代工业建设的,如电视剧《生活的赞歌》(王扶林导演)讲述工业战线技术革新的故事;有叙述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如电视剧《养猪姑娘》(姜坦导演)讲述农村姑娘养猪的故事;有叙述保家卫国的,如电影《上甘岭》叙述上甘岭战役的英勇与惨烈。第三,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新中国”需要“新国民”,“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新国民”的代表,当然也是新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表,如小说《创业史》中带头走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的梁生宝,电视剧《焦裕禄》中的优秀干部焦裕禄,电视剧《麦贤德》中的海军英雄麦贤德等。第四,倡扬新的民族国家精神,培养“新的国民性”。对此,周扬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他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的这个消极的、阴暗的、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十年的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之中。我们的作品就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14]中国“十七年文艺”所要倡扬新的民族国家精神及“新的国民性”,要言之,就是对新中国政体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就是要有过去不曾有的社会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阶级斗争观念和爱国精神。中国文艺作品中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国形象。
其二,“文革中国”,是“文革”及其后两个历史时期中国文艺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在“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中,中国被叙述为“继续革命的中国”,“阶级斗争的中国”,“革命样板戏”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已知的“文革”时期的电视剧《考场上的反修斗争》(杨宗镜等导演)、《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和《神圣的职责》等所表达的也是“反修防修”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文革”意识形态。“文革”后“文革叙事”中的“文革中国”,则是一个动荡、混乱、暴力、愚昧、贫困、落后的大搞阶级斗争、个人崇拜的中国,讲述惨痛“文革记忆”的作品很多,如小说《伤痕》(卢新华)、话剧《于无声处》(宗福先)、电影《芙蓉镇》(谢晋)、电视剧《有一个青年》(蔡晓晴导演)、《蹉跎岁月》(蔡晓晴导演)、《福贵》(朱正导演)、《大公社》(杨真导演)、《血色浪漫》(滕文骥导演)、《孽债》(黄蜀芹导演)等。“文革”后“文革叙事”中的“文革中国”形象,因创作者对“文革”的认识不同而千差万别,但投射的都是历史浩劫导致的国家认同危机与民族心灵伤痛,总体上是一种负面的中国形象。
其三,“改革开放之中国”,是当今中国的国家客观形象,也是中国的国家主观形象和媒介形象,这是国内外公众对“文革”后中国的基本认识和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艺作品,对“改革开放之中国”的形塑是多方面的,最初是呼唤和想象中国改革开放,关注改革与保守之间的冲突,探索改革遇阻的思想、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多方面的原因。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话剧《血总是热的》(宗福先)、电影《野山》(颜学恕导演)、电视剧《新星》(李新导演)等都是塑造中国改革开放形象的最有影响的作品。改革开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持续不断的深化改革,在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前行的同时,也为中国电视剧等文艺想象中国提供了新的现实与新的要求,这就有了不同时期不同的改革开放叙事,因而改革开放的中国形象总是在变的。但不论怎么变化,中国文艺塑造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形象,总体上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国家形象。
其四,“现代中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的国家客观形象,也是中国文艺及各类传播媒介着力形塑的国家主观形象与国家媒介形象。当今中国之“现代”体现在“硬件”与“软件”两大方面。首先,在“硬件”方面,中国的国防、工业、能源、交通、通讯、科技、城市等方面,现代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譬如,在中国近年来的影视作品中,剧中人物使用手机,已由曾经主要是用于炫富的“大哥大”变成了今天必备的通讯工具,手机已俨然成为参与剧情发展、人物塑造的重要“功能”或“角色”;私家车已成为城市居民乃至部分乡村居民必备的代步工具,都市现代病“交通拥堵”已成为剧中最常见的景观。再如,在电视剧《鹰隼大队》(彭昱凯导演)、《沧海》(赵浚凯导演)、《导弹旅长》(谷锦云导演)、《国家命运》(延艺导演)、《神舟》(宁海强导演)中,可以看到中国空军、海军、二炮、“两弹一星”、航天等已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其次,在“软件”方面,中国科技教育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国民的现代民主精神等,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即使是在叙述世俗日常生活的中国家庭伦理剧如《金婚》(郑晓龙导演)、《大女当嫁》(孙皓导演)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很现代的“新国民性”。从“硬件”到“软件”都在快速现代化的“现代中国”是梁启超等晚清作家当年超前想象未来40~60年的“新中国”也不能及的。
其五,“世俗中国”,这是“现代中国”的另一副面相。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世俗中国”也因此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世俗化(Secularization),在西方是指去除宗教神圣性的过程,亦即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祛魅”,宗教由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处不在逐渐退回到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本文则用以指当代中国的“去政治化”过程。当代中国曾经高度政治化,政治无处不在;“文革”后的中国已由“政治中国”向“经济中国”转型,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及国家权力不再全面渗透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国民活动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有了相对明晰的分界线,国民的个人需要、物质欲求等世俗欲望都得到肯定,世俗日常生活具有了现实的此岸意义。中国文艺特别是中国电视剧中的家庭伦理剧,如《渴望》(鲁晓威导演)、《过把瘾》(赵宝刚导演)、《我爱我家》(英达导演)、《裸婚时代》(滕华涛导演)等,都重在叙述国民的日常生活,展示国民的物质追求、情感欲望、婚丧嫁娶和生老病死等世俗生活和情感,从而呈现出积极的正面的世俗化的现代中国形象。
其六,“东方化中国”,是中国文艺特别是中国电影塑造的“东方化的中国”,亦即按照西方人想象中国的方式塑造的中国形象,这是一种“他者化”的中国形象。本文参照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15],将这种“他者化”的中国形象称之为“东方化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不断有国产影片冲出国门走向国际,相继在各类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如《黄土地》(陈凯歌导演)于1985年获瑞士第3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红高粱》(张艺谋导演)于1988年获德国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霸王别姬》(陈凯歌导演)于1993年获第46届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小武》(贾樟柯导演)于1998年获德国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获奖使这些影片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从而也影响了到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问题是,这些国际获奖电影塑造的中国形象多是“丑陋的中国”,而电影中呈现的“丑陋”有些是不真实的,如一些伪造的民俗、刻意凸显的“阴暗面”等,都是按照西方想象中国的方式叙述,是一种认同西方“东方主义”的“自我东方化”。这类迎合西方口味的“家丑外扬”或“自我丑化”的电影叙事,在国内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近些年来,一些传播到海外的中国电视剧,如《步步惊心》(吴锦源等导演)、《甄嬛传》(郑晓龙导演)等,也都存在值得讨论的类似问题。“东方化中国”是一种负面的中国形象,影响到了国家形象的软实力。中国的文艺创作如何摆脱西方视野,中国文艺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文艺创作的自由与责任,影视艺术如何塑造正面的中国形象等问题,已成为时下社会各界特别是文艺界的热点议题。
中国当代文艺作品中的这六类中国形象,是较为重要的几个国家形象类型,远不是当代中国形象类型的全部。“中国梦”激励下的中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埃德加·斯诺在其编辑的小说集《活的中国》序文中所说,中国“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它将使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在中国这个广大的竞技场上,有的是冲突、对比和重新估价。今天,生活的浪涛正在汹涌澎湃。这里的变革所创造的气氛使大地空前肥沃。在伟大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动。”[16]这虽然是20世纪30年代的友情祝语,也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把这样的国家客观形象,表现成可以传播海内外的中国的国家主观形象和媒介形象,是中国文艺和新闻传播的历史使命。
[1]王一川.中国人想象之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中国形象[J].东方丛刊.1997(1、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
[2]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A].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又名《李鸿章》)[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4:46.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
[4]梁启超.少年中国说[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5)[M].北京:中华书局,1989:9.
[5]陈天华.狮子吼.中国近代珍本小说(8).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37.
[6]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648.
[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
[8]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老舍文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346.
[9]老舍.赵子曰.老舍.老舍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73.
[10]吴贤辉.革命、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国现代化[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11]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28.
[12][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6.
[13]吴贤辉.革命、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国现代化[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1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154.
[15][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6][美]埃德加·斯诺.《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序言.文洁诺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2.
[责任编辑:王守雪]
2015-09-19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世纪中国电视剧与民族国家想象”文章,项目编号10BC024。
李兴阳(1961—),男,湖北省麻城市人,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文学;朱华(1972—),男,湖北省荆州市人,湖北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品与视觉传达设计及理论研究。
I206.6
A
1671-5330(2015)06-007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