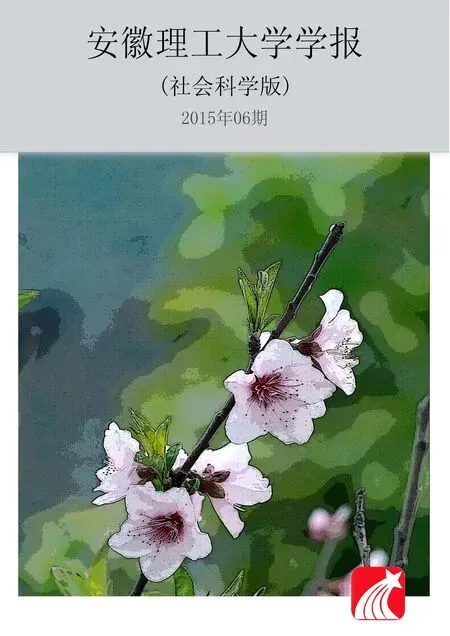爱国书生对法国二战败亡的反省——以马克·布洛赫《奇怪的战败》为主要考察对象
张 辉
(安徽大学 历史系,合肥 230039)
马克·布洛赫(1886—1944)是近代西方著名的史学家,他所提倡的“问题史学”、“总体史观”、“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等观点随着其作品的畅销,尤其是随着其与吕西安·费弗尔一起创办的《社会经济史年鉴》杂志和“年鉴”学派影响的传播而扩散,波及全球。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布洛赫的研究有一定成果,但主要集中于其史学思想的研究,而试图从其在法国刚战败后撰写的《奇怪的战败——写在1940年的证词》这本书去认识、解读布洛赫的则是空白。本文试图以布洛赫的这本名著为主要考察对象,以窥测其爱国情怀、对法国快速战败原因的分析和反省三个方面,力求对布洛赫有更深入的认识。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笔者谨以此文略表敬意,借以缅怀所有为反法西斯战争而牺牲的英魂。
一、一个爱国者的人生
布洛赫出生在法国阿尔萨斯地区一个犹太裔家庭,他的双亲都是热忱的爱国者。所以他从小就受到家庭爱国主义的熏染,他具有非常强烈的爱国情怀,尤其是经历了多达十几年的法国针对犹太公民所爆发的反犹太主义的高潮——对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的误捕、误判的德雷福斯事件(1894 -1906)。受此影响,虽然他看到了由其所引发的可怕社会喧嚣,对法国军队、新闻界、法庭审判等表示怀疑,对“炮制谎言”的摄影记者充满仇恨[1]20-30,但最终他的法兰西爱国主义也为事件的结局所强化。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积极地应征入伍并在战争中英勇无畏、冲锋陷阵,获得四次嘉奖且升至上尉军衔。
战后,他重操旧业,致力于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但是当1939年战争又一次打响时,已经年届53岁、作为6个孩子父亲的布洛赫作为年龄最大的预备役上尉毅然重归军队、再次投入战斗。他以一个“老兵”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践行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的责任。不幸的是,由于各方面原因,号称欧洲大陆最强国的法国在短短6周即战败投降,所以布洛赫声称这是奇怪的战败。“为了不让历史事件成为转瞬即逝的尘埃,被人们遗忘”[2]416,作为历史学家和公民个人的布洛赫,“都必须对二战的进程和它的结局加以总结,对具体的责任进行具体的分析”[3]174。故此,他在短短2个月就完成了《奇怪的战败》的撰写,希望以资后见。虽然后来无耻的贝当政府屈膝投降,但爱国的布洛赫却没有停止战斗,直至1944年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并枪杀。
布洛赫在《奇怪的战败》中首先追述了其家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我曾祖父在1793年加入了军队;我的父亲在1870年投身于斯特拉斯堡守卫战;我的两个叔叔在其故乡阿尔萨斯被德意志第二帝国侵吞后甘愿背井离乡;我从小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没有人比犹太裔的阿尔萨斯迁出民更热衷于维护爱国传统……无论发生什么,法国将仍旧是我心中牵挂不断的祖国”[4]3。并对法国战士在一战中的英勇无畏与二战中的不堪表现进行了比较,心中涌动的是“怒其不争”的张力,爱国心切的作者斥责自己及其同胞使祖国蒙羞。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他浇注于书中强烈的爱国情怀,所以他对“奇怪的战败”原因进行了分析与反思,并期盼着那个曾经战斗着的法兰西民族的荣归,他坚信法国胜利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在书尾他宣称:“我深爱着我的祖国,并竭尽所能为她效力……我生是法国人,死是法国魂。”[4]128
二、一个法国战败者的证词
虽然作为坚定的爱国战士,布洛赫不仅自己践行了对祖国的爱恋,并在《奇怪的战败》中也有叙述可歌可泣的战士和颂扬法兰西民族精神。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懂得理智胜过情感的重要性,于是他把自己在战争中的亲历亲闻以及对法国极速战败的原因进行探讨和分析,以一种“一份证词只有在证人记忆犹新的时候写下来才有价值”[4]1的信念驱使下写了出来,“作为1940年法国溃败的经眼录,试图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理解这次溃败”[5]21。下面笔者将以《奇怪的战败》的论述为主并结合相关论著,从军事、社会-思想、政治-外交三个方面探讨布洛赫视野下法国战败的原因。
(一)军事原因
1.军事组织和军事指挥的失误。布洛赫在《奇怪的战败》第二章开篇即鲜明地指出:“无论是什么深层次性的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其最直接的缘故就是指挥的极度无能”[4]20。这首先体现在法军最高统帅部的运筹无策、指挥不当,对敌方主突方向的判断失误。法最高领导层盲目信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信守防御是最好的进攻,把重兵部署在马奇诺防线一带,只留少量兵力于阿登山脉地区,因为他们认为阿登山脉森林茂密、陡峭崎岖,不便于大部队的展开和坦克机械化部队的通行。而德军却反其道而行之,执行曼斯坦因计划,派少量兵力佯攻马奇诺防线、迷惑法军,进而派主力部队翻越阿登山区、出其不意的出现在法军面前,正如布洛赫所言:“在整场战役中,我们的指挥官总是不甚明了敌人的真正意图……我们始终不清楚他们的行动”[4]33。汉斯一阿道夫·雅各布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战役》一书中描述道,德国的包克将军对这种出乎意料的成功也不无感叹地说:“法国人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否则他们应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情况发生。”[6]21研究二战史的专家利德尔·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也指出,这一役法军的计划几乎和德军预想的一模一样,与德军的计划完全吻合[7]95,他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错误指挥和不知变通自食其果。
其次表现在法军统帅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作风、派系内斗、组织涣散。正如布洛赫所言祸起于萧墙之内,军队官僚的缺点横行在所有的级别,“无论是谁,一旦获得指挥权,就立刻和他的前任对着干。总司令部和部之间的斗争也愈演愈烈,甚至不惜以国家为代价”[4]71。法军被分为3个指挥部,当遇到问题时,他们互相踢皮球,试问这样没有凝聚力的队伍怎么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呢!
2.军事战略错误、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的保守落后。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一书中指出法国军部信守一战经验,顽固地坚持消极防御战略,“他们的思想远不如对方那样的进步,根本不曾跳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圈子以外。”[8]241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也强调法国在1939年9月宣战后,仍按兵不动,坐等敌军来袭,盲目坚持防御战、阵地战,正如曾任法国总理的勃鲁姆得意地说:“我们的体系虽不宜进攻,但在防守方面却是呱呱叫的。”[9]22贝当也强调:只要坚持阵地堡垒与步兵火器相结合,则法国的安全可以保证[10]168。于是出现了奇怪的宣而不战的“西线无战事”,8个月的按兵不动本应使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反思、改革,但他们什么也没做,“我们的指挥部是一个老人的指挥部”,“上下各级,所有军官都仍然被上一场战争的记忆支配着”[4]84-85。因此大部分军官都不知变通,在面对现代化战争变化的新特点和德军的步步紧逼时,仍信守“马其诺防线”的固若金汤,完全没有意识到现代化军备和士兵的重要性。
在法军中自行车、驴车成了最便捷的物资运输工具,他们“就好像倒退了30 乃至40年!德军打的是一场今天的战争,其特征就是速度。而我们却恰恰相反,打的是一场昨天甚至是前天的战争”[4]28。军事技术的保守落后还体现在对坦克、飞机的生产和运用上,他们不仅缺少坦克、飞机,而且多是一战时的老坦克,完全跟不上现实的需要,阿诺德·托因比在《大战前夕》一书中指出这些装备不过是配备了装甲的无枪炮而已[11]1231。布洛赫悲叹道:“敌军的坦克不仅远比我军情报部门所推测的数量多,而且其中有几架出人意料的威猛异常。与我们的装备相比,德军的飞机更是先进得骇人”[4]30。享利·米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指出尽管有像戴高乐将军那样的有识之士,早在30年代初就呼吁加强战备并建立一支机械化、装甲化的激机动部队,要注意新技术、新兵器的发展等,但是这些真知灼见没有受到高层的认可,他们认为坦克、飞机只能作铺助工具,“步兵才是至高无上的”[12]12。布赖恩·克罗泽在《戴高乐传》一书中也提到,当1938年国庆演习上,戴高乐指挥他的坦克部队大显身手时,观看演习的吉罗将军却说:“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想在我的防区看到你的理论付诸实现。”[13]63反观希特勒的大力支持[14]296,则使其的对手更加相形见绌,他认为:“目前,坦克队和空军不仅作为进攻手段,而且也作为防御手段,其技术之高是其它力量望尘莫及的。”[7]46
此外,法军把为数不多的预备队分散在各个防线上,但几乎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当丘吉尔面对德军的猛力进攻,要求增加预备队兵力时,甘末林却回答说没有预备队了。对此,丘吉尔在《战争回忆录》中不禁感叹,一支大军在受到攻击时不留预备队,“这是我一生中所碰到的最令我吃惊的事之一。”[15]42
(二)社会—思想原因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那么在这场战争中,法军甚至社会民众又是怀着什么样的思想去看待和作出实际行动的呢?
首先,厌战、畏战心理与和平主义思潮盛行。法国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一战的胜利之中,但一战中他们也为胜利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所以害怕残酷的战争再次来临,厌战、畏战心理与和平主义思潮盛行。即便当战争不期而至时,他们也呼吁吝惜战士们的鲜血。当达拉弟伙同张伯伦为了眼前利益而炮制了出卖其盟友捷克的“慕尼黑协定”回国时,他本以为会受到国人的痛斥,但恰恰相反的是他却受到了国人的夹道欢迎,和平主义思潮一直肆虐到贝当政府屈膝求和。然而其后果是非常惨重的,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在《慕尼黑—悲剧的序幕》一书中所言:“慕尼黑的那一天对法国来说是灾难性的。它已经牺牲了它整个大陆国的地位,放弃了它在东欧的主要支柱,抛弃了它的最忠实的盟国”[16]190。
其次,统治阶级腐化堕落、社会思想混乱。朱贵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指出,作为英明的统帅和统治者,应是社会凝聚力的核心,然而令人悲痛的是“尽管德国已经大军压境,巴黎还是歌舞升平,达官要人还是优游终日。无线电台广播的是巴黎名餐馆的菜谱、淫猥的歌声。庞纳和赖伐尔之流关心的只是自己股票的涨落。军火生产无人过问,战争动员无声无息”[17]1756。正如亨利·米歇尔曾明确指出的:“我们战败的根源在于放纵了自己”[12]159。杰烈维杨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也证实在宣战后,他们不是在整顿军备、积极备战,而是为了“稳定军民”而组织体育和娱乐活动,并专门讨论了给士兵增加酒类配给问题。此外,达拉弟还签署了一项关于“供作战部队用”的纸牌免税的法令,接着又通过了一项要给军队购买一万个足球的决议”[18]63。重新审视这些行为,我们不禁为此荒唐行径而苦笑。
法军是如此不堪,那法国民众又如何呢?人民群众和官兵的思想情绪、战斗意志是影响战争的重要因素,然而可悲的是他们好像根本不理会“兵民是胜利之本”[19]498的法则。而是像布洛赫所言的那样,官民不仅没有团结在一起,反而隔隙很深,“前线的战士经常对后方的民众感到不满。当前者躺在坚硬的战地上难以入眠之时,后者则睡在舒适的房间里安枕无忧;当前者的头顶上是扫射而过的机枪子弹之时,后方的商店里却是一派生意兴隆的和平景象——熟客们怡然地品尝着外省的咖啡,战争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4]92。莫洛华在《法国崩溃内慕》一书中还记述道:他们为了短暂的安宁,竟恳求军队不要驻防在自己的城镇,甚至反对坦克演习,因为它会摧毁农作物[20]21-22。残酷的战争使人们变得冷漠,连对法兰西民族精神的最后一点余温也丢弃了,德国人的胜利在本质上是精神的胜利。
(三)政治—外交原因
政治上的分裂、无能加上外交的失败是法国迅速败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 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19]468-469然而法国却是建立在腐朽的政治制度之上的,布洛赫也说:“人们将所有的罪恶都归咎于战争之前的法兰西政治制度。对此,我根本不打算说多少好话……拜我们的大臣和议会所赐,我们对战争真是毫无准备。”[4]113而且法国政局极度不稳,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到1940年6月贝当投降的70年中,共换了100 多个内阁,平均寿命不到八个月。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利用职权向最严肃的报纸里植入自己的政见,正如布洛赫所言:“如果相信选举的投票总是根据‘他所看到的报纸所言’,那便是极大的错误”[4]104。由于他们的无能使得他们唯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此外便无所事事,最后只能沦落到屈膝求和的地步。列·库达科夫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感慨道,到贝当、魏刚等投降派接掌政权后,他们更加速谋求和平解决法国“1940年的悲剧”,魏刚认为:法国本部的战争已经失败,法国必须投降[21]616。
我们不应忽略的是,法国外交的仰人鼻息对其战败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开战前,法国追随英国推行绥靖政策,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无耻地出卖自己的盟国。并幻想着祸水东引,希望苏德相互残杀,但结果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22]83-84,致使其后来孤军奋战,自食恶果。即使作为英国的追随者,他们之间的合作也不是那么愉快。他们之间虽有合作,但也存在着相互敌对情绪致使情报联络的缺失,布洛赫抱怨道:“没有什么比我们之间致命缺乏的联络更为残酷了,更确切的说,这种缺乏无所不在。”[4]48他们国家之间以前时战时合的经历在战士们心头无法完全抹去,他们没有完全的推心置腹,相互的交流也只是出于对盟约的遵守和礼貌。在面对法军的顽固无能、步步败退后,英军与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眼看着盟军的热情温度计下降了好几十度”[4]52。在其后的战斗中,英军为了掩护自己撤退,竟不顾是否切断了法军的后路就炸断了桥梁!而且当法军请求英国空军支援时,他们以维护本岛的安全拒绝了,并回复道:“这不是决定点,也不是决定性时刻。”[15]139尽管后来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时,英国在确保全部英军撤退后也搭救了相对一部分法军,但双方之间的隔阂暂时已经无法弥合了。
尽管布洛赫自己也承认他的观察所得和搜集的二手史料受到限制,但他坚持自己作为目击者的可信性。通过以上的论述与分析,我们也认为他作为目击者的证词还是相当可信的,而且他的证词确实给人们以警醒并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借鉴。
三、一个法国人的自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更好地理解法国1940年的悲剧——“奇怪的战败”,布洛赫不得不在其作为一名军人之外补充其作为一个法国人的自省。
1.唤起和导引民族精神,这是一个国家面对侵略战火波及之时能立于不败之地的先决条件。在战争期间,法国上下几乎像一盘散沙,他们没有被激起法兰西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没有形成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战线。社会思想涣散、混乱,魏刚接任法军总司令时也写道:“在军队的上层,普遍的情况是一遍混乱,而在下层,1914年曾使他们能够顶住开头几个星期的灾难的那股坚韧不拔的气概,似乎已经荡然无存。”[23]321法国统治阶级腐化堕落,为了各自的私利而争斗不已,内阁频繁倒台、变迁,所以他们自然就无法动员起民众的法兰西情怀;前线的士兵对后方民众安于现状、无所事事的行为怨声载道,民众对政府、军队的无能而冷嘲热讽。正如布洛赫所言:“整个民族的胆怯或许比个人的畏缩的总和更为致命”[4]96、“漠然的态度确实在战争中广为传播,最终酿成了严重的后果”[4]99,德国人的胜利在实质上说是精神的胜利。法国要想赢得战争,必须恢复思想的一致性,在浴血奋战中重构法兰西民族精神。
2.改革现有政治制度的弊端,使统治阶级制定出一个适合国情的战略,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法国的政治制度名义上是建立在大众参与的基础上,其实它不过是一个老人(贝当)把持的政府[4]125。即使在这之前的政府也没有作什么实质性的工作,“拜我们的大臣和议会所赐,我们对战争真是毫无准备。无疑,最高指挥部在这里也没派上什么用场”[4]113。法国民众尤其是资产阶级在言语上也攻击这种制度,军界亦然,如法国前教育部长泽所说:“对民主制度怀有刻骨仇恨而暗地里赞赏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的军官太多了,有些还是身居要职的军官。”[18]199所以布洛赫认为这个体制是脆弱的,应该参照英国文官体系进行改革,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制定出一个适合国情的战略。
3.改革现有教育现状,采用灵活、自由的教育制度,这是国家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布洛赫强调必须摆脱旧式的人文主义、保守主义,学校教员必须承担起足够的教育责任,应该根据现实的需要灵活的教授知识,鼓励那些突发异想,并认为有异端者是好事儿,不能忽视这条智慧准则而墨守成规[4]110-111。只有这样,法兰西民族才能再一次踏入拥有真正自由精神的学校,并再次屹立于世界。
四、余论
自古以来,战争总是热血男儿最热衷的话题,人们总是幻想着驰骋沙场、建功立业、凯旋而归,但是战争的残酷又是让人多么悲痛。《奇怪的战败》这本书是短短2个月完成的急就章,作为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布洛赫写就了一部真情流露的、易怒的、爱抱怨的作品。在书中他披露了自己的亲历亲闻:军事的失误、政治的腐化、外交的仰人鼻息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了法国的快速溃败。他本想让这些记忆碎片随风而逝,因为记述这项任务“就好比强迫一个人公开揭露自己母亲的弱点,让人备感煎熬,尤其是当她正处于悲惨和绝望中的时候”[4]91。但作为大力提倡“古今相互借鉴”[24]37的历史学家,为了更好的权衡和探究事实的真象,他又不得不写下这份证词。他的目的就是让后人“好好反思老一辈犯下的错误……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认识到错误,并避免错误”[4]124。
尽管对于此书后人提出了非议,如批评其对法国战败的结构原因、财政原因与人口原因轻描淡写[25],对法国军队与政治领袖的批判过于严厉[26]等等。笔者也认为布洛赫的笔下对士兵的懒散和民众的漠视等描述存在失真或并非具有普遍性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应过于苛求古人的尽善尽美,正如布洛赫所强调的: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它需要人们的理解。他也坦诚的说道:“今后更深入的研究将会宣告我的论文已彻底过时,到那时,如果我可以相信,我的错误臆测曾帮助了历史真理意识到它本身的正确,那么我的辛苦就算得到了完全的报答。”[27]2
[1]Carole Fink. Marc Bloch:A Life in History[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20 -23.
[2]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M]. 唐家龙,曾培耿,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16.
[3]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居雷·罗哈斯.拉丁美洲:全球危机和多元文化[M].王银福,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74.
[4]马克·布洛赫. 奇怪的战败[M]. 汪少卿,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5]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 -1989)[M].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6]汉斯一阿道夫·雅各布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战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21.
[7]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册[M].伍协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95.
[8]利德尔·哈特. 战略论[M]. 钮先钟,译. 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77:241.
[9]戴高乐.战争回忆录·卷一·上册[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22.
[10]唐子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史[M].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168.
[11]阿诺德·托因比.大战前夕·1939年[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231.
[12]享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上册[M].究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2.
[13]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M].赵文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63.
[14]小戴维·佐克,罗宾·海厄姆.简明战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96.
[15]Winston S.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athering Storm[M]London:Cassell & Co Press,1971.
[16]约翰·惠勒—贝内特. 慕尼黑—悲剧的序幕[M].林书武,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78:190.
[17]朱贵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75.
[18]杰烈维杨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 卷[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20]莫洛华.法国崩溃内慕[M].赵自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41:21 -22.
[21]列·库达科夫. 现代国际关系史[M]. 郑德麟,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616.
[22]军事科学院军事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二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83 -84.
[23]阿若德·托因比. 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上册[M].许步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321.
[24]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M]. 张和声,程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
[25]Bryce Lyon. Marc Bloch:Did he Repudiate Annales History[J].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1985(11):157 -180.
[26]Douglas Porch.Military Culture and the Fall of France in 1940[J]. International Security,2000(24):181 -191.
[27]马克·布洛赫. 法国农村史·导言[M]. 陈振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