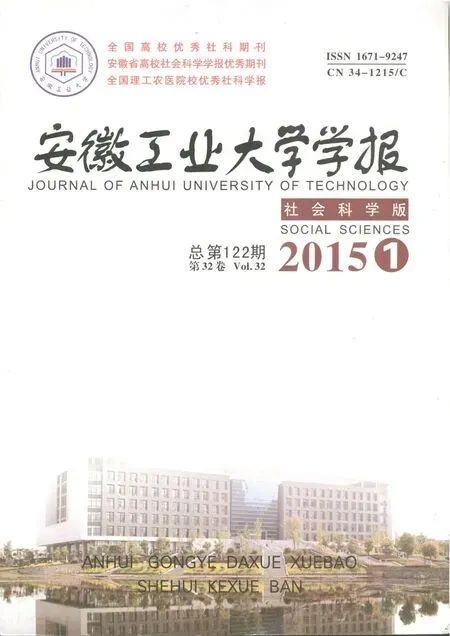解读《一掬尘土》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姚 敏
(安徽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马鞍山243002)
英国作家伊夫林·沃所作《一掬尘土》,被视为20世纪最苦涩同时也是最好的小说之一。文中婚姻的解体,对于宗教的质疑,道德观的沦丧体现了一定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结合悲剧、喜剧和残酷的讽刺,《一掬尘土》描写了战后“疯狂一代”不负责任的态度。最后的婚姻破裂是沃自己离婚的一种痛苦的喜剧式再现,象征着构成社会的一个个有机体的解体。他的作品既有现代主义特征,同时也具有后现代主义特点,值得深入探讨。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特点是“解构”,从对文学作品的解构,到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整体性文化的解构。[1]
一、言语的报复
结构主义学家注重言语以及能指和所指之间任意又稳定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则将之称为“言语报复”(或至少是主体和产生的行为或过程之间关系)。在文本的语境下,形式通过接受者对产生的行为的推理和观察被赋予一定意义。“从游戏意义上来说,说话就是一种斗争。”[2]具有讽刺意味的语句通常包括一个态度或评价的显性表达,但在整个语言环境下说话人的意图是非常不同的,通常是相反的态度或评价。在《一掬尘土》中,反讽是用来描述人物和场景,使叙事话语和叙事内容之间达到戏剧性的讽刺效果。
小说中,布伦达与她的情人比弗住在伦敦的公寓里,为了减少不安和内疚,不使丈夫怀疑她的欺骗,布伦达和一帮说闲话的朋友煽动珍妮勾引托尼。出乎意料的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绅士,诚实的托尼不喜欢布伦达的“善”,以为珍妮是一个小丑。然而,布伦达的朋友认为托尼的排斥反应是难以置信的,他们觉得很不公平,布伦达是一个“好”和“体贴”的妻子。“无论如何,你问心无愧了。为了让那个老男孩快活起来你所做的已经远远超过大多数的妻子了。”[3]这种肤浅的赞扬和作者内心的厌恶产生了一种有意的错位。这种言语反讽,貌似随意,实则深刻,这在塑造人物和描述特定场景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婚姻和家庭中人们已经普遍习惯了戴着面具,扮演欺骗者和被欺骗者的角色,并不引以为耻,作者通过言语报复对这种游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表达了他对传统婚姻家庭瓦解的愤怒和无助。
二、与其他作品的互文性
互文性一词在1966年由后结构主义学者茱莉亚·克莉斯蒂娃创造。任何作家和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凭空产生,或多或少会借鉴已有的作家和作品,因此,互文是必然的。“文学作品可以不再被认为是原创的;如果真的是原创的话,对于读者来说它可能并没有意义。只有当它来自于产生意义的现有的话语文本才具有一定的意义。”[4]这就使文本的意义不再确定,一个文本的意义并非存在于读者正在读的某个文本,而是在阅读中唤醒其曾阅读过的一系列文本后所产生的含义。
小说第六章改写自其之前所写短篇小说《喜欢狄更斯的男人》:一个英国人在遭遇妻子出轨之后,绝望地来到南非的丛林,被一个宗教狂扣留,被迫一次又一次阅读狄更斯的小说。沃的父亲亚瑟·沃很喜欢狄更斯,常常在傍晚看狄更斯的作品,因此,沃也读了很多狄更斯的作品。这种经历对沃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在他的作品中有一些奇怪的人物,如《衰落与瓦解》中的奥古斯都·芬等,可以找到一些和狄更斯小说中奇怪的人物相似的地方,但他不赞成狄更斯盲目相信人类的善意。他认为这种态度不过是逃避现实世界。那篇被命名为《喜欢狄更斯的男人》的短篇小说,本身就是在讽刺狄更斯。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大多数的主角都勇敢、善良、充满爱和同情,有着良好的道德人格,虽然经历许多困难但最终得到幸福,像奥利弗一样。狄更斯认为,好人将得到很好的回报,而坏人终会受到惩罚。然而,小说《一掬尘土》中托尼虽然也像奥利弗一样善良正直,却以悲剧结尾,成为一个野蛮人的囚犯;布伦达嫁给了杰克孟席斯(议员)。好人坏结局而坏人有好结局是讽刺了狄更斯的人道主义——对人性盲目的自信、自我欺骗和逃避。在一个善良被遗弃,邪恶猖獗的时代,狄更斯的思想是没有价值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为托德读狄更斯的小说,受到狄更斯的人道主义的乐观激励,托尼却感到越来越悲观和绝望,认为他再也不能沐浴人道主义的光辉。模仿狄更斯的作品有双重功能,不仅表现出狄更斯的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不切实际的一面,也讽刺了现代社会的衰落和荒凉,体现沃对于工业社会物质至上、人类异化的批判。
三、宗教和伦理的去中心化
像许多当代的文学理论,后现代小说对被冠以自由人文主义标签的理念提出了质疑,如自主性,超越性,必然性,权威性,统一,综合化,系统化,中心,连续性,目的论,闭合,层次,均匀性,唯一性,起源。“后现代主义小说质疑任何确定性的基础(历史,主体性,参考)和任何判断标准,但并非完全否决它们。”[4]在《一掬尘土》中,随处可以看出作者关于宗教与社会伦理的批判性思考和质疑。
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信仰的先验教条已不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信仰的主体和客体之间产生了隔阂。信仰的对象被认为是一些抽象的描述,然后被认为是幻觉,结果只剩下信仰的主体。倡导节俭和积累的宗教伦理被资产阶级所抛弃。精神需要和伦理诉求成了一片空白。
小说中,赫顿村的牧师在布道中没有任何与时俱进的内容,总是以提及遥远的家乡和亲朋好友而结束。而来做礼拜的人们并没有发现这有什么令人惊讶的。教堂里说的从来没有提及他们自己。当牧师开始叙说他们遥远的家乡他们感到很享受,他们知道,是时候拍拍膝盖上的灰尘,检查下自己的雨伞了。显然,宗教不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和神圣的大事。他们去教堂是因为这是一个习惯,履行一种义务。
托尼总是在星期天穿着深色的西服和硬白领去教堂。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礼拜日的习惯,这方面比其父母更为严谨,尽管每次他打扮成一个正直、敬畏上帝的老派的绅士时布伦达都要取笑他,他也要维持这一略显隆重的程序。但在教堂里托尼真的认真听牧师传道了吗?“托尼吸入宜人、略有发霉的空气,跟往常一样坐、站和前倾时,他的心思早就飘走了,全是关于过去的一周,或未来的计划中的事。偶尔一些引人注意的短语在礼拜仪式将他召回他周围的环境,但是大部分的那天早上,他老是想着浴室和厕所的问题,以及如何他们能被改造又不影响房屋外观。”[3]
尼采曾言,“上帝已死”,他并非说上帝在形而下的层面已死;相反地,他表达的是上帝已无法成为人类社会道德标准与终极目的。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人们的所有信仰。现代人不再相信一直存在的宗教,同时也不愿意宣布清醒认识到宗教只是人类的精神鸦片。因此,在无心的信仰和缺乏爱和同情心的社会里,面对未知世界的苦难,人们只能感受到空虚和麻木。约翰(托尼和布伦达儿子)死于一场事故,等待布伦达回来时托尼几乎成了一个空洞的人。他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只是无意识地被他人控制,担心布伦达听到悲伤的消息后的反应。然而,布伦达还沉浸在自己的命运被生活中的四个男人主导的预言中,当她听到了约翰的死讯,得知不是她情人约翰时脱口而出:“约翰……约翰……安得烈……我……哦,感谢上帝……”[3]然后她泪流满面。由此可以看到,宗教不再是一个精神的指导和行为标准,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上帝可以随时随地在任何场合被脱口而出。作为一个母亲,布伦达感谢上帝是她的孩子而不是她的爱人死了,这真是一个宗教讽刺。它也表明,人们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因为他们不再害怕上帝会惩罚他们犯下的罪恶。
同时,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示了荒谬的20世纪早期的社会伦理道德的迷失,伦敦的上流社会充满了空虚和虚伪。与布伦达约会之前,比弗在伦敦是最懒惰的人,他什么也不做,每天等待着被邀请。但他接到的大部分邀请,总是在最后一刻有时甚至更晚。经常是当他已经开始吃饭时却接到了邀请,然而他还是会乘车前去。人们把他当作最后一个备胎,一个小丑,但他自己却不觉得羞愧,因为他本来无所事事。布伦达像是一个被囚禁的公主,在上流社会那个小圈子眼里,她和比弗的恋情只是提供了一个更令人兴奋的和受欢迎的话题。为了减少罪恶感,让她的丈夫对她的事不怀疑,布伦达跟她的朋友商量如何让别的女人勾引她丈夫,他们甚至谈到了所有的细节。虽然布伦达背叛了她的丈夫托尼,但托尼不得不在法庭上被当成被告。他付给一个陪他在海滩上度假的妓女一笔钱,还雇佣两位私家侦探作为他对妻子不忠的证据提供的证人,荒谬的制度导致了这种荒谬可笑的故事。
这种绝对道德观的失去就是虚无主义的开端,而虚无主义是后现代价值观的典型代表。理性的启蒙思想作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北美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指导,同时,启蒙运动促进科学真理和自由后导致了叙事的合法化。在后现代的解构之下,宏大叙事的权威(其特点是人文关怀和自由的精神)被质疑和否定,导致人文精神和价值逐渐减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有关文化和价值的问题正在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因此,他们的精神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贫乏,他们的理想崩溃,失去了诚信、信仰、理想和正义。
[1]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Jean-Francois Lyotard.ThePostmodernCondition:AReport onKnowledge[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3]Evelyn Waugh.AHandfulofDust[M].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Inc,1956.
[4]Hutcheon,Linda.APoeticsofPostmodernism[M].London:Routledge,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