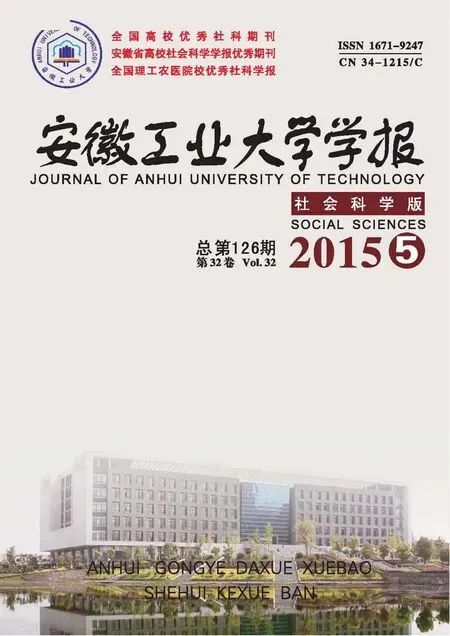公益精神形成规律简论
徐 刚,王 薇
(1.安徽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2.安徽工业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公益精神形成规律简论
徐 刚1,王 薇2
(1.安徽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2.安徽工业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公益精神既是对一定社会群体的关怀,也表达着人类对社会发展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关注与作为。公共性认知是公益精神形成的起点,公益参与实践是公益精神形成的基础,公益精神的形成是多种教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公益精神的形成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
公益精神;形成;特征;规律
社会公益活动作为一种造就他人、实现自我的利他行为,是民间最原始的社会推动力,慈善、志愿等公益行为也因此被誉为“人类最高境界的伦理美德”。现实中社区生活里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合作竞争环境中社会责任的关照、生活世界中人们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关注,都需要一种公益精神作为支撑。在一定意义上,公益精神成为一个国家天良民心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志,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对丰富个体意义、完善个体品格的呼唤。
一、公益精神的内涵解读
公益精神是公益主体基于一定的关怀和利他意识,受主体偏好影响而面向特定社会群体或人类发展共同关注问题的行为的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人格品质。它不仅是人类情感迸发的一时冲动,更是一种以个体主体性获得的前提下的理性精神,是自利与利他的统一。[1]
公益精神具有以下特质:
第一,公益精神是一种公共精神。它表征着一种公共关怀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是一种对于公共利益和价值、公共事务、公共秩序的自觉关心和关注,是对于他人的普遍性尊重和关怀。同时它代表着一种公共意识,即独立自由的个体所具有的一种整体意识或整体观念,这种公共意识一方面是个人主体自由的体现,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对于一个超越于个体自身以外的共同体的体认。
第二,公益精神是一种志愿精神。“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四个方面是志愿者精神的体现,也是公益精神涵盖的科学内涵范畴。志愿精神具有结构上的层次性,其中较低层次的志愿精神表现在社会心理层面,诸如社会风气和个体的情感、态度,大致包括友爱的道德情感和利他的习惯风俗等。较高层次则为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志愿精神,主要表现为明晰的公益认知和自觉的担当意识。明晰的公益认知主要指个体对助人利他的公益必要性有较为清晰、理性的认识,这种认知更多的是在对人我共生理念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方面表现出崇高的追求,如无私利他的奉献精神,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包含有现实性的考虑,如助人为己的互助进步意识。自觉的担当意识是指个体在对公益必要性进行理性审视后,确立起自觉的助人利他的责任意识与自律要求。
第三,公益精神是一种文化精神。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类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也从多个角度对文化进行过概括,但真实完整地反映文化本质的不外乎两大层面:文化的实际行为和存在于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公益精神既有实际行为的一面,又体现为一种价值观。它在行为取向上要求公益主体关注弱势、平等互助、携手公益、回馈社会;在行为理念上表现了公益主体仁爱、利他、奉献和人文关怀的价值观,它引导和支持公益主体的行为方向,渗透着浓厚的文化内涵,当公益精神中所蕴含的信念、信仰赋予个体以特殊意义时,就成为一种作用于现实社会的强大的行为动力。各类公益行为所展现的公益精神一直以各种形式隐没在文化中,唤醒社会良知,引导公益实践,整合人类力量,发挥着推动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文化精神的价值和功能。
第四,公益精神是“有我利他”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在社会公益活动中,公益主体通过参与公益活动,帮助弱势群体,关注公共问题,实现了利他,同时在这种利他过程中也获得了自身精神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达到了自我完善,实现“有我利他”的统一。
二、公益精神的形成性特征
探讨公益精神的形成性特征是为了把握公益精神形成的特殊性,为公益精神的培育提供必要的指导。
(一)公益精神的形成具有人性基础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认为,“人的世界是共同的世界,人在世界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3]这一观点不仅揭示了人的公共性即人与人的相互共享,更揭示出人的公共性的自然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向度。这种双重向度表明人性中天然存在着公共性成分,人天然属于“公共”之人,人的这种公共性构成了人类公益精神的人性基础。
其一,人的公共性的自然向度决定着人类作为公共存在物的相互扶持。从人的公共性的自然向度来看,人自出生起,就被投置于社会关系的各种复杂网络中,不管个人愿意与否,都必然被外界环境影响、与周围的人之间产生各种联系,这决定了人虽为个体却生活在人类自己构建的公共的世界中, 是“公共”的人,并在这种共生共存的环境中互相扶持。人类活动的相互依存性构成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根本特征。人类公共生活中的相互扶持,是人类公益精神萌芽状态的表征,它源自于人的自然的公共性需要,同时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使整个“公共”世界的存在保持稳定。
其二,人的公共性的社会向度决定着人类利他的社会化存在方式。就社会向度来看,生活在公共世界中的人们在自由交往和各种活动中,开辟出社会公共空间,创造出为所有社会成员共享的公共价值,表现为人类在其社会化存在方式中所秉持的价值原则始终明显地存在着若干公共性的成分,使其关心他人命运,甚至于把他人的幸福视为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由于人的自然属性的存在,人类甚至有时被视为自私的动物,其价值原则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利成分,但人类同情、救难、互助、友爱等诸多天然情感和行为证明,人有利己之心,也有利他之求,社会化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个体必然有为他人利益而付诸的实践。而由人的这一社会属性引发的公益精神,始终造就并维系着人类社会化存在方式的延续,并进一步强化着人在社会中的公共性。
可见,公益精神与人性存在着极其深刻的内在关联,公益精神不仅孕育于人类奇妙的“自然”感情和“社会”感情的交叉混合,而且是任何社会历史因素影响或制约下也不会消逝的人性成分,它始终以隐性或者显性的形式天然存在于人性之中。
(二)公益精神的形成过程具有曲折性
公益精神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一方面个体公益精神属于人的意识层面,它的形成极易受人的心理状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个体公益精神的形成状况会因其自身条件、环境因素和实践活动等众多因素的作用,导致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结果的难以预测。如此,使得公益精神的形成表现出明显的曲折性特征。
“情感迷失”是公益精神曲折发展的首要表现。公益精神形成源起于人的同情心与互助意识的类情感,自发产生公益意识与行为。人的社会化使人对个体自我的地位、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认知,这一过程大多会强化人的类情感,促进公益精神的自觉形成。但在某些情况下或某些个体那里,受环境、经历等因素的影响,会出现同情心与互助意识弱化甚至丧失的“情感迷失”现象。如以社会工作者为例,同情心与互助意识的类情感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工作的根本性源头 ,它奠定了社会工作者公益行为的情感基础,但在20世纪中叶的社会工作专业化过程中,跟随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路向,社会工作日益偏重个案服务,尤其是临床心理治疗,却越来越忽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真实困苦的关切也简化为冷冰冰的技术操作层面的事务。社会工作似乎日益接近科学,但却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本该具有公益精神信仰的社会工作者走向了专业理性之下的道德情感迷失。
知行脱节是公益精神曲折发展的另一表现。知行脱节是指个体公益认知和公益行为不能达成一致,公益行为缺乏坚定性和持久性。公益认知水平不高是造成公益精神形成上知行脱节的主要原因。公益认知水平状况可区分为“有知”和“深知”两种状态,对公益行为、公益现象的认识、判断、了解和感知是对公益的“有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解、内化和信念是对公益的“深知”。公益认知水平不高,会限制个体对社会公益以及公益精神的理解。没有正确的理解,就无法使公益行为得到理性的支持,进而会弱化公益行为情感上的认同和意志力的保障,一旦环境条件得不到保障,或者是与个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公益行为通常就会居于弱势,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坚持,更谈不上公益精神的内化。
公益精神形成的曲折性特点,对公益精神的培养提出了要求,一方面要求承认公益精神的形成存在着个体差异性,要因人而异地引导,调整个体的心理状态,促使个体形成社会认同的公益精神;另一方面要求加强公益精神教育,在深化公益认知的基础上,强化公益参与实践,实现知行统一,把公益精神内化为道德信念。
三、公益精神形成的规律
(一)人的公共性认知是公益精神形成的起点
造就他人、实现自我的利他公益活动虽古已有之,但就现实个体而言,其最初的公益行为或是缘起于人的类同情心的自发行为,或是模仿或被动的参与行为,人们在这种行为中获取的还只是对于公益的意识,是对公益的主观觉察与体验,没有上升为公益精神。人们只有具备了对人的公共性的认知,才有可能形成公益精神。
人的公共性是个体在参与共同体生活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属性,是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认识,它是对私人利益的超越,即对人的利己性的超越,表现为对他人、共同利益的关注。人的公共性是形成一切良性共同体的人性基础。人们只有具备了对人的公共性的认知,才有可能在意识层面上形成公共意识,形成对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责任与义务的自觉和对公共领域内利益关系的理性认识,把自己与社会共同体联系起来, 共同寻找并遵守带有普遍性的共识,维护共同的信念和价值;才有可能在态度层面上表现出一种公共关怀,形成对公共事务及公共生活的积极关注、理解和承担的心理倾向性和社会实践行动。
现实中有些人只是在能直接带来个人好处时才会关心公共利益,即使在效果上可能也促成了公共利益,仍然不能认为他们具有公益精神,因为他们只是以“私人”身份参与公共事务,虽然其行动落实在公共生活、公共利益中,但其主观意愿中缺少公益行为的动力,缺少对公共利益的自主自觉追求,从而无法在态度和行为方式上与他人沟通。
(二)公益参与实践是公益精神形成的基础
人类的认识活动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公益精神是人类认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自然无法脱离公益参与实践。公益参与即加入某种公益组织或某种公益活动。现实中个体公益参与程度与其公益精神完整性正相关,即个体参与公益活动程度越高,对其公益精神的塑造越完整。
首先,公益精神作为孕育于公共社会之中的位于最深处的基本道德和价值取向,内涵有一系列最基本价值元素,具体包括同情、诚实、正义、尊重、欣赏、公正、平等、谦虚、忍耐、理解、包容等组分。公益参与通过激发和固化公益精神中不同的价值元素,塑造着公益精神。
其次,不同的公益参与程度激发和塑造不同的公益精神价值元素。初涉志愿服务的浅层次公益参与,由于公益理念和服务技能尚未得到训练,只能实现参与者的同情心、正义感的激发,塑造其诚实、真诚且勤奋的工作态度。中层次的公益参与表现为参加侧重于一些软性服务公益组织的常态服务 ,比如心理支持、暑期支教、孤寡老人照料等,因为有了更多的与人交往的工作,复杂程度明显提升,必然会激发并塑造尊重、谦虚、公正、欣赏与平等等价值元素,以胜任中度参与阶段的工作要求。随着公益参与深度的增加,参与者会接触到一些存在于公益领域的阴暗面,例如大量浪费救灾公益资源,部分受益群体“等、靠、要”,有些志愿者甚至个别公益组织利用灾区“作秀”等,深度的公益参与使志愿者的思维更加成熟,塑造其直面公益领域中灰暗地带的“忍耐、理解、包容和智慧”。
再次,公益参与通过系列的激励机制塑造公益精神。一方面是结构性的激励,即特定社会空间内特定的社会需求对社会公众内在的同情心和正义感的激发,如灾区民众的需要;也有组织性激励,如工作动机和组织认同的激励。另一方面是反身激励,即公益参与者在付出善意和友好的同时,收获对方的赞许、友好和善意,进而产生崇高感、成就感和满足感等愉悦的情感和心理体验。通过公益参与被激发出的价值元素在公益参与之初可能还无法持续太久,但持续的公益参与会不断加强和固化这些元素,最终公益精神被塑造起来,成为参与者志愿公益行为的指导。
(三)公益精神的形成是多种教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公益精神的形成受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等多种教育因素的影响。
家庭是培养品格的第一学校,人们的基本行为准则大多来自于家庭,并伴其一生。正如帕森斯所言:儿童时期的孩子把家庭作为一个参照群体来与之认同,从而将家庭规范、价值标准、行为模式变成自己的东西。青少年在与父母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深受其态度、观念、情感和行为的影响,虽然这一过程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却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得以吸收和内化。
学校是公益精神形成、发展的良好空间,学校教育的目的性、规范性、系统性和有效性,使学校成为公益精神培养的重要场,但个体公益精神的形成仅仅依靠学校教育却无法完成。首先,学校教育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学校教育内容、情感满足,对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方法手段的应用等,与个性化的学生需求都会有差距,其评价结果也不能作为对学生的最终评价。同时受现实存在的教育功利性的影响,学校公益精神教育缺失现象还相当程度上存在。其次,学校教育具有阶段性,而公益精神形成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学校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公益精神培养甚为关键,却也只是阶段性的,个体公益精神的形成需要其不断学习、不断接受教育。
多种教育因素共同培育公益精神。社会生活环境是个体重要的活动场所,在社会生活中,个体受到的影响是不自觉和多方面的,培育公益精神必须高度重视、利用和开发好各种教育资源。
(四)公益精神的形成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国有着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传统,却一直存在着公益精神的缺失,这是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制约造成的。公益精神的成长需要政府、社会共同培育环境土壤。公益精神的形成需政府提供制度环境。公益事业是政府继强权政治和法律统治之外政府社会秩序供给中的第三条道路,它将善治理念通过倡扬公益精神来实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政府对公益事业的合理定位,意味着对事关良好社会秩序获得和公益精神培育深化的重大问题的解决,能为公益精神的形成创设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还要完善法律体系的创设,为公益精神形成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公益精神以公民社会为载体。一般认为,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行为集体,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包括了所有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如专业协会、慈善团体、NGO组织、工会等。公民社会组织中的公民在一个体现自由、公意、法律、秩序相结合的道德共同体——公共生活领域——不仅要求自主创造,也要求友爱、合作、互助、利他、奉献的思想境界和平等、真诚、正义的道德风尚,这种建立在个性自觉基础上的公益精神,是人们获得“类活动”的价值基础。这种公共生活也成了公益精神生成与普及的现实社会母体,它是公益精神的现代载体。
四、结语
公益精神的形成需要坚实的公益文化基础。公益精神毕竟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是在社会历史中生成、积淀和发展的一种过程性存在,它的形成需要积淀、生成着的公益文化作为基石,系统完善的公益文化,能够强化民众的公益精神。
[1]卓高生.公益精神概念辨析[J].理论与现代化,2010(1):87-9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3]海德格尔.存在和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138.
(责任编辑 文双全)
A Concise Comment on the Regularity of Public Service Spirit Formation
XU Gang, WANG Wei
(1.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 Law, AHUT;2.Academy of Art and Design, AHUT, Ma’anshan 234002, Anhui, China)
Public service spirit is not only the care for certain social groups, but also expresses people’s attention and actions to handle problems that we are all confronting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Public cogni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to develop public service spirit, public service involvement and practice are the basic, and its form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many educational factors. Also, it needs a good social environment.
public service spirit; formation; character; regularity
2015-07-12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当代大学生公益精神及其培养机制研究(2011sk724zd)
徐 刚(1965-),男,江苏六合人,安徽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副教授。 王 薇(1963-),女,安徽宿州人,安徽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
C914
A
1671-9247(2015)05-01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