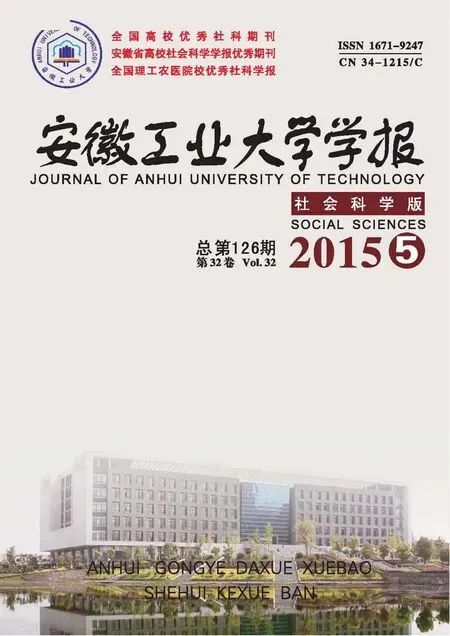婉约词美学特质的跨文化传真
黄淑萍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外语教学部,福建 厦门361021)
一、文化语境
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体裁之一,蕴含生命旨趣,源于生活现实,却又超脱于时代。缪钺先生曾说:“词之所以别于诗者,不仅在外形之句调韵味,而尤在内质之情味意境。”[1]词强调“情真”,突出的抒情性使词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最能触及心灵的文类。以“婉约”为词本色的论述,始于北宋,是词情缠绵、词意蕴藉、词境空灵、词律谐婉的统一。[2]婉约词讲究“婉而细,幽而深”,强烈真挚的情感隐含于阴柔空灵的景象,情景交融、韵味无穷。因此婉约之美质就在于直面生命本真,以独有的意象体系、多彩的柔美品格,鲜明呈现出人的生命本真境界。[3]而这种美学特质,是由其所在的大、小文化语境融合而成。
文化语境是指在特定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这一范畴的第一层意义是指与文学文本相关联的特定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生活习俗、心理形态、伦理价值等组合成的特定“文化氛围”;第二层意义是指文学文本创作者在这一特定的“文化场”中的生存方式、生存取向、认知途径与认知心理,以及由此而达到的认知程度,即文学创作者的“认知形态”。[4]第一层意义可称为大文化语境,第二层意义可称为小文化语境,即文本生成的具体写作语境。[5]婉约词浸润于丰厚的文化土壤,词人由情感触动萌发创作灵感,与相应的景象融化于同一心境里,并逐日形成相对固定的柔美意象体系,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和审美意义。词人的情感心智与巧妙构筑的意象蕴育出深婉悠长的诗意空间,个体的精神世界在大文化语境里律动,道出时代语境的气质,成为那飘忽朝代的最佳文学注脚。随着历史变迁,博雅玄远的婉约境界让读者沉醉于无限延伸的审美体验。
别致的婉约词既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又是古代文学的美质代表。阳春白雪的字里行间流淌着中国古典美学直觉妙悟式的诗性品质,折射出中华典籍含蓄和谐的深刻内涵。片片旖旎的婉约词弥漫着人们内心最柔软的芬芳,将此经典美质跨文化传真,将促进典籍跨出国门、丰富世界文学艺术。
二、跨文化交际与婉约词外译
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途径,对于从民族走向世界的文化战略而言意义重大。同时,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6]多数情况下,译者先与作者进行单向交际以把握原著的交际意义,而后用译入语传达,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了解源语文本内涵。跨文化交际观把翻译领入广阔的文化领域,在婉约词外译的过程中,译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目的语语境之间穿梭来往,需从有效交流的角度去考虑婉约词译本的可读性。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需要,为了建立两种文化间的交际关系,就要重现源语文本的意义。交际意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帮助我们理解每个词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7]诗词是纯文学的最高形式,阴柔旖旎的美学特质是婉约词作的文化核心;写词如此,译词亦然。正如纽马克所言,翻译文学文本,追求的是美学上的真实。[8]传递诗情画意般的审美功效,与译语读者共同品味诗性共鸣和心灵内省,是外译婉约词的第一层交际意义。译者在交际过程中,重新感受诗人曾经澎湃的生命与精神,并向读者诠释这份美学体验。与西学精确直接、逻辑性强的特质不同,婉约词被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赋予了东方美学的典型元素:含蓄委婉表达直接经历的审美自由与深化的内心自省,笔淡情浓于弦外之音。这种差异也是一种互补,婉约词翻译的交际意义由此多了一层美学艺术的超越性追求。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婉约词外译是一项复杂且多维的交际活动,它主要探讨如何发掘和阐释原文的交际意义,在目的语文化语境里传递原词的审美价值,实现译文与原作的功能对等。在这中西文学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中,文化语境的差异是交际的主要障碍。文以载道,婉约词属于文化浓缩型作品,承载着时代的精神财富。语境是婉约词生成的特殊环境,对其翻译涉及作品生存环境的转换,是交际过程的关键环节;翻译过程需重视原语和译语表层及内含的千丝万缕的文化差异,以免因文化误解或缺失而影响到原作美质的重现。原词与译作处于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只有让词作所关联的社会、地理、历史典故等大文化语境因素在译语里适当重现,并加深读者对古代词人的情感心态、精神思想等小文化语境的理解,才能使古词译本在目的语语境中获得新生。
三、婉约词的文化审美与传真
李清照的《词论》确立了以婉约为正统的词体风格论。她的婉约词语浅趣雅、清新奇绝,艺术价值极高,是婉约美质的典型代表,不仅为我国人民世代称颂,也深深吸引着西方世界,国内外诸多名家译匠都曾外译易安词。一代词宗善于旁征博引,朦胧婉曲的词境带有中国文化的总体性特质,因此李词外译时集中体现了文化空缺、差异、误解等跨文化交际矛盾。譬如名篇《醉花阴》只是寥寥数笔,便在汉语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充满了“暗香盈袖”的诗意情怀,而将其译入新文化语境时,如何让遥远从前的芳香如故?
(一)文本生成的文化语境
小文化语境是指文学创作者的认知形态,也是一个文本生成的具体写作语境。从横向上看,它是受着某一事件、某一种心境的触动而引发了创作灵感;从纵向上看,它同作者以前的和以后的创作,同他创作之前的思想和在以后的思想感受之间的对话,就有着一种语境上的关系。[2]隐蔚幽深的意境赋予婉约词多元开放的解释空间,为跨文化交流导入更多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高了文本翻译的难度。小文化语境有助于译者深入体会本真词心,更完满地欣赏并诠释婉约美质。
易安居士善用委婉曲折的笔墨来描绘含蓄的情感:有却把青梅嗅的天真纯净、有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娇柔愁情、还有风住尘香花已尽的悲切凄婉……五十余首留词作为整体映照了一生的坎坷心路;而各首词都是一段时代生活感悟,绝世才华在花姿等文化意象里别样绽放。从纵向的创作文化语境看易安词,更易探求出词心之美。《醉花阴》写于崇宁二年,李清照与赵氏成亲后琴瑟和谐却两地分居,于是在重阳佳节填了一阙词遥寄夫君,因此当属李清照前期相思轻愁词。
全词以“愁”开篇,以“瘦”结尾,落笔绮绝、意味深长:玉肌消瘦的丽影处在娇柔轻细的意象里;李清照对生活的爱、甘苦的思念、高洁的人格融成美好词心,与幽婉的词境浑然天成;瑞脑金兽、东篱把酒等一系列大文化语境因素将诸美合一,与小文化语境构成了该词的文化场,把美质渲染到了极致。而要把这份艺术质地传真异域,就必须注重文化场因素,从隐含的语境层面实现译本的交际功能对等。
(二)从社会生活语境再现美质
婉约词用柔美意象以物寄情,这些载体常由社会文化语境的专有名词构成。例如上阕便以瑞脑金兽、玉枕纱橱勾勒一幅闺阁思愁的唯美画面:淡淡的雾、浓浓的云,阴天让诗人愁闷,香烟袅袅消磨了长昼;夜里秋的凉意透入纱橱渗入玉枕,重阳佳节让她更加思念远方的人儿。然而构成古代文化语境里的专有名词,在现代西方鲜有对应表达。文本翻译时应该如何从社会语境层面再现婉约美质呢?请看以下两个译本:
Veiled in thin mist and thick cloud,how sad the long day!
Incense from golden censer melts away.
The Double Ninth comes again;
Alone I still remain
In silken bed curtain,on pillow smooth like jade.
Feeling the midnight chill invade.(许渊冲)[9]
Thin fog under thick clouds
Sadness endures through the long day
Auspicious dragon incense
Rises from the gold animal
Again it is the ninth of the ninth month
At midnight my jeweled pillow
And gauze-curtained bed
Were saturated with chill.(王红公,钟玲)[10]
瑞脑又称龙脑,是香料之王;金兽指兽形香炉;玉枕纱厨则指代色如碧玉的瓷枕和木格纱帐。这些都是宋代上流社会女子闺房的生活物品。许渊冲用减译法,将“瑞脑销金兽”浅化为“incense from golden censer melts away.”熏香缥缈的意境,使译语读者更易想象出当薄雾浓云、轻烟袅袅与愁绪思恋萦绕心头时,孤寂时光的漫无边际。王红公和钟玲则是解读为“Auspicious dragon incense rises from the gold animal”——名贵龙脑香料和兽形金炉保留了源语的阶层文化特色,为译入语读者铺垫了词人身份的高贵。“玉枕纱橱”在许的译文里是“silken bed curtain,pillow smooth like jade”,纱帘和光滑如玉的枕头,这样的释意法返璞归真,为外语读者清除了理解语境的文化障碍。王红公与钟玲将它们替换成“gauze-curtained bed”和“jeweled pillow”,挂着纱帘的闺床和镶嵌宝玉的枕头,通过具体细节重构鲜明富有的生活情境:越是优越,越是对比烘托出夫君不在身边的缺憾和落寞。
宋代重阳节有亲友聚会、登高插茱萸、把酒赏菊等传统习俗,热闹的民俗语境再次深化情感内涵,反衬出秋夜里玉枕般清冷的心境。移情入景,这些文化意象都变得情深意切,虽不着一字,浓烈相思已宛然在目。许渊冲直接使用重阳节的译名“Double Ninth”,简洁点明文化情境。王红公、钟玲则意译为“the Ninth of the ninth month”,指出日期,并在书末注释节日习俗,补充西方读者欠缺的文化信息,让目的语读者体会到每逢佳节倍思亲,节日氛围让愁肠百结的心雪上加霜的心情。许氏韵体译诗清新晓畅、可读性很强,而王、钟合译的作品语境丰满,凸显婉约忧郁的美学特质。
跨文化交际特性决定了翻译需将特定语境和人物情感结合起来,选择翻译策略从社会语境的生活细微处传达婉曲真挚的美学品质,有助于文化传统功能的传播。
(三)在历史地理语境中传真美质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悠久不断的过程中积淀出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系统。例如下阕把场景转移到黄昏后,“东篱把酒”、“暗香盈袖”的历史典故,以及“西风”、“黄花”等富有地域特色的意象内涵丰富,使婉约美质变得荡气回肠:黄昏后的篱前举杯独斟,隐隐之间花香阵阵飘入衣袖。触景生情,此刻多么渴望与他团圆共饮啊!回到闺房,瑟瑟西风卷起珠帘,帘内的少妇,为伊消得人憔悴,比帘外菊花还要纤弱……然而贯穿其中的文化因素在英语认知语境中并不存在,如何重构文化场、传达情怀之美、再现艺术价值呢?
At dusk I drink before chrysanthemums in bloom,
My sleeves filled with fragrance and gloom.
Say not my soul
Is not consumed.Should the west wind uproll
The curtain of my bower,
You’ll see a face thinner than yellow flower.
(许渊冲)[9]
Now in the yellow twilight
I drink by the Eastern wall,
And a mysterious perfume fills my sleeves,
And carries away my soul.
The West Wind blows the curtains
And I am frailer than the yellow chrysanthemums.
(王红公,钟玲)[10]
“东篱”语出《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田园诗人陶潜在“东面的篱笆”采菊花,归隐生活与菊为伴,脱离俗世纷扰。后人常引用东篱作诗,欲唤起读者对人淡如菊和远离尘嚣的联想,亦即李清照词东篱把酒、自比黄花的俊逸意境。黄花即菊花,凌寒不凋、冷傲独立。花中君子有着高洁品性,也可寓意离别思念。通过“东篱”、“黄花”,诗人匠心独运地在历史语境里创造了情韵高华的婉约美词。美质传真过程中,译好精心构筑的文化语境是关键一环。许渊冲译文首行的“chrysanthemums in bloom”和最后的“yellow flower”两相呼应,巧妙构成上下文语境,让读者能够理解yellow flower所指的是菊花,又保持了押韵特色;归化的方式造成了东篱归隐和菊品脱俗的文化亏损,但基本传递了原文信息。在西方,人们仅用菊来悼念逝者,这一文化有别于原词自喻及相思之初衷。[11]王、钟将“东篱”译 为 “Eastern wall”,“黄 花”意 译 成 “yellow chrysanthemums”;并在书末附注、阐释两个词条的特殊文化渊源和借此达到的旷洒境界,为西方读者构建一个异域风情的文化语境,有效避免了文化误解;但若将“wall”换成“hedge”,可能会更为贴切。
《古诗十九首》有云:“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暗香盈袖与其情境相似:看花时衣袖充满芬芳,多想与身在异乡的心上人共赏;可惜路途遥远,无法送达。李清照将古句化于无痕,行至尾句不直言相思苦,却自比黄花,蕴含无限情,芳馨之中的神骏美质动人心魄。两位大师对“暗香盈袖”的处理方式也很值得借鉴。许渊冲采用增译法,添加“gloom”一词,使读者感受到幽香阵阵,如心事重重、挥之不去。王红公和钟玲则跳出源语文本,充满灵性的一句“and carries away my soul”令人神思飞扬,心灵仿佛也随着花香飘向思念的远方。他们对原作的创译出神入化,又在情理之中;保留婉约美质的同时,使原词的跨文化交际意图与受众的期盼相吻合。
映衬重阳菊花怒放的自然景观,是萧瑟的“西风”。两种译本不约而同选用了“west wind”,关于西风的译法,译介常有争论:如应译为“east wind”——西方地理气候决定了东风才是萧条的,而西风则温暖可人,或是“autumn wind”——表明季节特色。但在全球语境化的趋势下,直译西风更能保留地域语境特色,并增进文化理解。译文若使文化保有各家特色,便更能吸引人们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
从历史地理层面的翻译而言,译者要使自己与婉约词人以及当代译入语读者的认知语境相关联,在读者可接受的范围里重现婉约词的美学价值和文化意蕴。翻译时将客观语境和文化信息充实,有利于译本实现与原文的情感功能等效,保证中西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四)译本在译语语境的新生
清美的婉约词在跨文化翻译的船上远渡重洋,在名家译笔下异彩纷呈、和而不同。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的许渊冲在获得中国译协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后,又于2014获得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正如颂奖词所言:“我们所处的国际化环境需要富有成效的交流,许渊冲教授一直致力于为使用汉语、英语和法语的人们建立起沟通的桥梁。”许先生把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成外语韵文,包括婉约词在内的120余部译著为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卓越贡献。王红公是美国现代诗人、诗歌翻译家。他与钟玲合译出版了含《醉花阴》在内的《李清照全词》,是诸多李清照诗词英译文本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成为学界研究对象。[12]美国华裔汉学家荣之颖称该集是“首个由美国著名诗人翻译的李清照诗词译本”,表明中国文学逐渐受到世人更多的关注,他们的译本在目的语语境得到认可,对世界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婉约美质能在异域重放异彩,与译本中文化语境的解译是分不开的。许渊冲主张通过“三化”即“深化、等化、浅化”的翻译方法使译文呈现出“意美、音美、形美”,让读者“知之、好之、乐之”。他的译例也运用了“三化”策略来创造立体的译本语境,使读者能如原语读者一般欣赏到原诗的美。王红公诗性至上,以创意英译闻名。他用英语读者熟知的本土形式和习惯,对原词的文化语境进行异化和创译,使读者能够认同自己的感悟体验、理解作者的情感意境。王红公与钟玲一起将易安词与中国文化同步推出,满足了目的语读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心理。译者在各自时代背景下,追求译文文本在西方语境下的活力,使婉约美质得以新生,示范了成功的跨文化传播。
翻译交际活动必须在特定的文化场进行,高度凝练的婉约词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除了译例中所展现的历史地理语境,还有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等诸多因素制约着婉约美质的再现。只有以文化语境为基础,在异同得失之间取舍交融、中西合璧,才能重现美妙神奇的婉约美质,使更多人领略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
四、结语
婉约词是歌唱生命本真的灵魂之曲,在独特的文化场里生成柔美多彩的审美品格。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译者应以交流融合的方式在原作和目的语文化语境之间进行选择、变通和再创造,使婉约词融入世界文学,推动中西之间的文化对话,建构全球的文化语境。只有艺术性和可读性并举的译本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学西传,让古典的婉约美质焕发新鲜活力,让读者经历一场芬芳盈袖的文化之旅和美的体验。
[1]缪钺.诗词散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4.
[2]周明秀.词学审美范畴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91.
[3]黄丹纳.生命本真的审美升华[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2):61-67.
[4]严绍璗.“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J].中国比较文学,2000(3):1-14.
[5]房福贤.新时期文学生成的时代文化语境[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71-75.
[6]郭建中.文化与翻译[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7]李巧兰,林大津.翻译中的意义诠释与翻译“信”度[J].外国语言文学,2007(4):266-274.
[8]段峰.回顾、思考与展望——《Routledge翻译研究指南》评述[J].中国翻译,2009(4):30-33.
[9]许渊冲.宋词三百首[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2.130.
[10]Kenneth Rexroth,ling Chung.LiCh’ing-chaoCompletePoems[M].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s,1979:14.
[11]黄淑萍.易安花愁:生态译境里的《漱玉撷英》[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4(12):191-192.
[12]季淑凤,葛文峰.彼岸的易安居士踪迹[J].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报,2013(2):7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