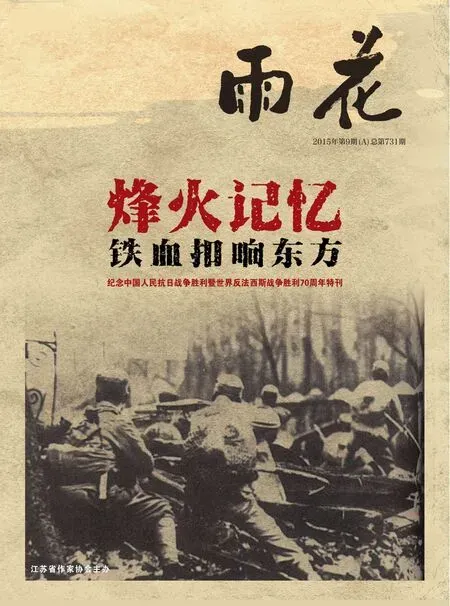战时香港
◎ 唐 海
战时香港
◎ 唐 海
香港告急
记不清是哪一位外国记者,在抵达香港后一个时期的广播中,说香港人民的安定生活,不过是一种鸵鸟式的生活。危险正潜伏在四周,自己却装着看不见,不理会。
装着看不见,不理会,不去想漫天烽火的战争,香港确是安定的。1941年12月7日是一个星期日。特有的安闲。电影院满座,酒吧间挤满了客人,舞场里不停地播放着爵士音乐,四周找不出一丝的战争气息。只是近二三天来香港当局在举行开玩笑般的防空演习而已。没有人想到战争会在明天清晨就光临到这个海岛上,更没有人想到这一个休假日,将是香港和平生活宣告终结的最后一个假日。
1941年12月8日清晨,我看到有的报纸第一条大标题还是罗斯福呼吁日皇停止战争的消息。忽然听到隆隆的飞机声,一阵猛烈的炸弹爆炸声跟着响起来,高射炮亦随着发出声音了,炸弹与高射炮声连成一片,割破了早上宁静的空气。
几个散坐在草地椅子上的人,立即站起来向着落弹方向看过去。那面已经冒着黑烟起火了。不久,一辆疾驶的救火车掠过我们的前面。
才一刻,又听到了飞机声。高射炮重又响起来。我赶紧躲在一间大酒店的楼下,那里早已站满了许多外国人和少数中国人。沿马路住宅里的外国人,男的女的,有的站在大门口,有的倚着窗门往外看。不安和恐慌满堆在他们的脸上。
“是防空演习,还是战争爆发呢?”
大家互相观望着,互相诉说着各人不同的意见。一个肯定地说:“有70%是防空演习。”他为着证实他的观点,举了一下今天早上的报纸:“报上没有说起战争已经迫近了啊。”
近飞机场方向的房子确实已经起火了,远远的,已经可以望见冒起的黑烟。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是战争的来临,希望它仍是防空演习的倒着实有许多人。
那个大酒店的一个华人账房,匆匆从另一个地方跑回来,用英语向大家诉说,“7点钟,7点钟,战争已经到了……”“战争!”这是一颗小炸弹,在每一个人的心底爆发开来。这一句话的威力,远超过在附近爆炸的炸弹!
当我回到弥敦道时,香港澳门中共办事处在开会。平时谈笑风生的负责人廖承志,表情严肃,正在布置将散住九龙的中国文化界著名人士迁往香港。因为九龙连接大陆,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会很快到达九龙,而香港则是个海岛,四周是水,要进攻就得花费时间。因当时时局动乱,为保证安全,会上便指定国新社(国际新闻社)一些年轻记者、编辑担任护送任务。我与朋友一起承担了护送邹韬奋一家到渡江码头的工作。
九龙沦陷
我们由九龙逃到香港是12月10日。中间隔了一天,12日下午,九龙就全部沦陷了。谁都没有预料到仅仅5天工夫,九龙就全部丢了。谁也没有想到准备了好几年的防线,竟是那样脆弱!
九龙的沦陷是可悲的。它失败于部队欠缺勇敢和自信及第五纵队的捣乱。这一个狭长的半岛上的防御,一般估计至少可以守上一个时候,不至于那么短的时期就沦陷。但因为准备不充分,部署慌乱而遭到了失败。
猝然爆发的战争,使香港陷于劣势的地位,战争一开始,就让敌人取得了主动。因此,新界的防线一开始就在炮火和俯冲轰炸下向后撤,而敌人则一步进一步地逼近了九龙。
当战争进入异常紧张的关头,香港当局突然想起了被囚已有几年的我们中国孤军,发给了枪支,立刻叫他们上火线。这可以说是香港战争中最初的援军。这一支有500人的队伍,曾经在前方进行过无数次的冲锋;更由于地理的熟悉,作战的英勇,都使并肩在一起的友军感到异常的敬佩。由于他们的英勇牺牲,使逐步后撤的防线稳定了一个时候。
前方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在九龙市区里,第五纵队已经大肆活动了。这个第五纵队,包括有些C级警察(香港将警察分成ABCD四级。A级英国或法国、美国人,B级印度人,C级广东人,D级山东人),防护人员,以及数目众多的流氓,他们在香港、九龙都具有几年以上的历史。
九龙英军准备全部撤退到香港的时候,战线还在市区以外,但第五纵队已经在九龙最高的半岛酒店上扯起太阳旗来,同时用手枪不断地向下射击。另一面,敌人在荃湾那一线上紧紧地向市区逼近。在掩护退却殿后的印军通过尖沙咀码头时,流氓组成的第五纵队,不停地向装运印军的轮渡扫射,印军也在船后架起机关枪向岸上扫射。
香港守军大炮开始轰击九龙仓库了。炮弹也同时落在尖沙咀码头上。在香港,已经能看到九龙仓库中弹起火,半岛酒店上的太阳旗随风飘扬。
12日晚上敌人便占据了九龙。此后,隔了8分钟航程的两岸,就进入了敌对状态。每天,香港的大炮轰击着九龙,而九龙的大火也一直没有停熄过。70万以上的居民,不知怎样度过这暗无天日的生活!
观战东山台
东山台是香港东区跑马地直上的一座小山。它后面所有的山上,几乎全都是香港守军的炮台。轰击九龙敌人阵地的大炮,大多是从我们山后炮台发出去的。
屋后炮台每隔一刻发射一次炮弹,强烈地震动着整个房子。这面炮台发炮不久,对面阵地的大炮就向这个方向还击。有时炮弹的爆炸使泥土和石块飞进屋里来。因此,我们这个屋子里很少有安静的时候。一听到“轰”的一声,就知道敌方的大炮已经向我们这个方向轰击了,于是赶紧从三楼四楼急急地跑到地下室,等到炮声过后才回到楼上去。晚上也总要下楼三四次,提心吊胆的连睡觉都不安定。
白天,从这里瞭望九龙,沿海边一带看不见人影,海中也没有小艇往来。九龙的商民,现在要躲避英国方面的大炮了。沦陷区九龙同胞,不知如何过活?
到了晚上,这里成了观战场所。敌方的动静,偷渡时的攻守,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12日以后,九龙方面的汽油库大火,一直没有熄过。
每一个晚上都是敌人可能渡海的时候,香港守军严密地监视着海面,防守着沿岸。海面上出现了一个艇仔,守军就立刻扫起机关枪来;同时,大炮也向海面轰击,使敌人的船只迫于炮火而无法渡海。
战争之夜是惊心动魄的。一闪闪火光不断地在山间出现,而一朵朵火花又不断地落在海的对面。九龙的大火遮满了半边天空,探照灯白色的光芒像一条长蛇那样摇摆着。
防空洞
如果香港没有在战前建筑好巩固的防空洞,这一次战争中不知要枉死多少人!
当大炮和炸弹不停地轰击的时候,人们都躲进防空洞了。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里面空气是那样污浊,一阵阵令人作呕的臭味,直向鼻子里钻。但是,就在这样的地方,铺板、布床、椅子、席子,安排得没有一点间隙。人们用手帕把鼻子嘴巴一起蒙住,或者干脆不管一切盖上毡子,整天整夜睡觉。他们有的是8日战争开始那一天就“入洞”的,一个星期,10天,他们都没有回家,吃饭、睡觉,一切生活就都在洞里。
103号洞里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没有估计到战争这样快到来。香港本来是一个内地到南洋或回上海的必经码头,有许多要回内地以及要到上海去的旅客,他们都被困在这里。他们深深地怪着自己的命运,从老远老远的地方特地来,不巧赶上这场激烈的战争。
还有一批从天津来的旅客,他们原来的目的地是上海。可是英国轮船直驶香港,经过上海并未停留,将他们一直载到了人地生疏的香港。他们连一角钱的港币都没有,又没有亲戚朋友,要他们去找谁呢?
防空洞上面的山顶上装有一门大炮。当敌方没有发炮的时候,上面的炮台就一炮一炮轰出去,也不知道炮弹落在哪个方向。轰的一声,防空洞里就似乎轻轻地有些震动。
敌人快逼近的时候,落在山上炮台的炮弹特别多。有时有四五发炮弹同时落在山上,发出一连串的爆炸声,这是敌方的排炮,在轰击这里的炮台。
劫后孤岛
马路上在行路的人,每一个几乎都是慌慌张张的。一个突然跑步以后,其他人也会跟着跑起来,——也不明白是什么缘故。每一个有家的人,尽可能不走出门口,成天躲着;一些有事必须出去的,也尽可能缩短在马路上的时间。
没有地方买菜,粮食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有的地方依旧有水,有的地方则滴水不流,因此,常常要跑到几里外的地方,才能取得水;而一个有水龙头的地方,总是长蛇一样排着许多人。
“排队”似乎已经训练成一个习惯了。战争过程里,买米买柴以及购买一切日用品,什么都要排队,都得依先后挨次序,一个跟着一个,没有人抢先,谁都是耐心地忍受着,至多也不过自己焦急着自己而已。
被弹片击毙的死尸,大多依旧躺在马路上,几天来就这样一直没有人去理会。这个80万人口的海岛,整天被炮击和轰炸,死去了的人有2万以上。
一些大的店铺都给封了门,门口钉上“大日本军陆军管理”,或者是“大日本军海军管理”的牌子。敌人的布告说明几乎包括所有一切物资都在统制之列,没有经过“皇军”的允许,一切物品都不能自由搬动或买卖。
沿着平日最热闹的皇后大道走过去,人们排成了一条直线,来去都靠一面走。没有代步的电车和公共汽车。小汽车驶过,里面几乎都是敌人的军官。马路上,常常有一小队八九个敌兵,背着“三八式”跨着八字步巡逻。
赌博是敌人进占香港后最兴隆的事业之一。从最热闹的皇后大道起,一直到偏僻的角落,到处皆是。起先,只不过路过大道上,摆下了摊子,随后慢慢地扩充了。“皇军”到处,别的职业大多遭了难,而这和“皇军”不能分离的赌博,却如雨后春笋那样的勃兴起来。
日本军队在海军船坞附近,正在整理一捆一捆的猎得物,那些都是用麻袋扎起来的,堆满了一大块空地。在麻袋上面,有一个敌兵在结着小小的票签,上面写的是:“神户……”猎得物聚集了以后,卡车就将它带到西环的码头去,放到了大轮船里,这些轮船就一直驶回日本。
差不多25日以后的一个时期里,每个日本兵都很忙碌。除了举行“入城式”放假那几天,他们都为着搜刮物资而奔走。敌人和我们打了5年仗,很少占领过物资这样丰富的城市,这一次香港战争,他们可算发了一大笔横财。
胡乱喝醉了酒的日本兵,到夜半就四出寻找女人,他们三两个一起,敲打随便哪一家的门户。没有人会自动起来开门的,于是这一群无耻的强盗,就不管一切死命地敲,门板被打得震天的响,敌兵又在门外异样地怪叫着,这情景的确是可怕。
女人们躲在各处,敌兵的电筒就到处乱射,被他们发现的立刻被拖了出去。这几个晚上,许多女人吓得在三四层楼的屋顶上乱跑。
毫无抵抗力量的市民们,想出了一个防御办法。每一条街,每一幢房子的每一层楼,都预先商定:任何一家碰到敌兵来敲门时,一面装作不理会,一面即刻敲起铜锣或者面盆、洋油箱,以及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东西。天翻地覆的闹声,使来找寻女人的敌兵心寒而不敢再来。另外,第一家发出的锣声,也警告了其他的人家,知道万恶的敌兵又来了,女人们应该赶快躲起来。
我曾经碰到一次敌军宪兵的挨家搜查,那是1月10日我决定离开香港的前一天。东区骆克道近国民戏院一带,两面都站起了敌人的岗哨,一辆满载宪兵的汽车停在马路中,不准一个人离开屋子,马路上也不准有一个行人,于是敌宪兵就挨家敲门。一个挂着刺刀的宪兵跑进我们的屋里来,还带着一个翻译。他问我做什么事,哪里人?又搜查我的房间。可是他没有得到什么,在门口用粉笔写了几个日本字走了。可是放在马路中的汽车上,在开走的时候多了几个穿学生装的青年,他们双手被反绑着。
抗日分子是逮捕不完的。早在香港失守时,中共中央致电港澳办负责人廖承志等,要求全力拯救中国文化界的著名人士脱离险境。根据这一指示,安排了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负责护送工作。当时留在香港的有茅盾、邹韬奋等300多人,他们在东江游击队的掩护下,混在难民中间,经过千难万险,最后到达了东江游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