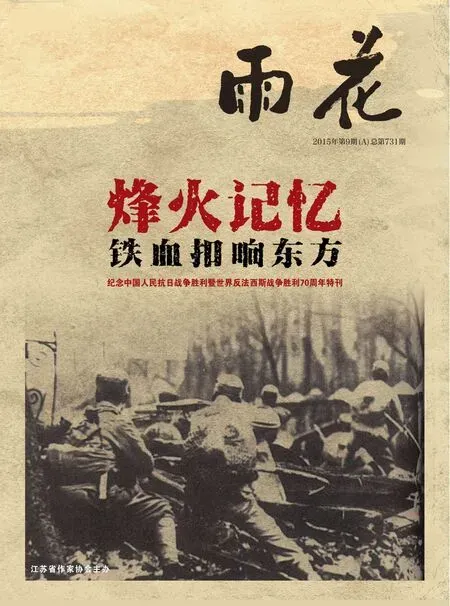惠通桥
◎ 张志明
惠通桥
◎ 张志明
在滇缅之战中,惠通桥是滇西通往内地的唯一咽喉要道。它的坚守和及时炸毁,对当时和后来的抗战大局,带来过深远的影响。
一
1942年5月5日。
天阴沉得很急,黑云压得很低。黑云翻滚中,松山若失,江岸消遁。黑云倏忽就改变了形状,雷声隐隐地由远而近。这正是滇西雨季来临的前夕。
让人惊恐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战事,在初战告捷后,开始连连失利。
中国王牌军第二百师,在予敌重创后,又陷敌重围。
4月28日晚,中缅边境的重镇腊戍,在激战后失守。日军由此一下子截断了入缅作战的远征军的后路,让他们在战败后,想回国都回不成。
二百师在拼死突出重围后,此时正在中缅边境的高山峡谷和原始森林中,苦苦寻找回国的路。在辗转跋涉中,身负重伤的师长戴安澜殉国。出征时一万一千人的精锐之师,此时还剩下不到三千人,途中还不断有人继续倒下。
远征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在丢弃大批辎重后,已率大军在当地人谈虎色变的雨季来临之前,败退入“魔鬼居住的地方”——野人山。
在进山的第一天,某工兵排奉命搭桥,可过了一会儿就皆无踪影。营长闻讯大惊,亲往察看,原来工兵误入一沼泽之中。沼泽中蚂蟥翻涌,每只体长盈尺,粗若棒槌,附于牛马之躯,一次可吸血斤许。一排工兵已尽成骷髅。
可在入山口,还有五万将士和一万难民跟进涌入。在这些即将进入野人山的六万军民中,最后不知能有几人回?
就在远征军大溃败之际,日军乘势从缅甸向中国境内大举进攻。其剑锋所指之处,势如破竹!
5月2日,日军精锐的第56师团坂口支队,越过国境,攻陷畹町。这支三千人的快速纵队,两天之内就向前推进了三百公里。
3日,日军占领了芒市。
日军进攻速度之快,推进之顺利,不仅出乎中国人的意料,也超过了日军高层的预期。当日军的车队开进芒市时,正站在街心的交通警察,还起劲地对车队打手势,示意他们可以继续前行。后来突然发现情形不对,这才撒腿就逃。
神速占领畹町、芒市的坂口少将,此时信心百倍,骄横无比,决心要创造出一个能将日军的坦克开到中国境内“任何要到达之地区”的奇迹。他确信:现在已经没人能阻挡住他前进的脚步。横亘在他面前的壁障只有一个——怒江天堑。
缅甸战事态势的急转直下,同样出乎中国高层的预料。
它的失败,这一失败极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让正在重庆紧急召开的高层军事会议,出现了难得的静场。
当有人幽幽地开始发言时,众人的目光,都随着那声调,渐次移向墙上的一幅巨大的军事地图上,再将直直的眼神,死死地盯在了同一个地方——惠通桥。
芒市距离惠通桥不到一百公里,对坂口的机械化快速纵队而言,那只是两个小时的路程。坂口只要占领了惠通桥,殿后的56师团大部队,就能随之从惠通桥横渡怒江,然后进攻保山,转而进攻昆明、贵阳,最后直逼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到那时,士气低落的中国军队,将腹背受敌,无险可据。到那时,中国的抗战,还会是后来的胜利历史吗?
终于有重庆高层幕僚的神经绷断,他们开始四处呼吁:在此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应立即着手在印度的新德里,成立一个中国的流亡政府。此语一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众,一时间举国哗然。
此时日军高级军官的目光,也齐刷刷地聚焦在了军用地图上的惠通桥。那幅地图在日军第56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的手中,都快被手汗浸湿成了碎片。如果在坂口少将恶狠狠地盯着这幅地图的眼神之间,放上一根枝条,那眼神都能让那枝条先冒烟,再燃烧。
惠通桥,位于云南龙陵县境内一座险峻的大峡谷中,是一座由17根德国巨型钢缆,飞架两岸的钢索大吊桥。全长205米,最大载重量为7吨。
惠通桥是连接怒江两岸的唯一通道,也是滇西通往内地的咽喉要道。
惠通桥两岸,悬崖壁立,重崖叠嶂。桥下,怒江奔腾,吼声如雷。
惠通桥扼天险于一线!
它能挡住日军前进的脚步吗?
二
5月1日上午,就在畹町失陷的两天前,一辆美式吉普急速驶离畹町城,飞奔向惠通桥。车上坐着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将军、陆军参谋团高级参谋萧毅肃中将、陆军独立工兵第二十四营中校营长张祖武。
张祖武精瘦颀长,目光内敛,腰带束得很紧。军装水似的贴在身上,显得气韵十足。
从畹町到惠通桥,有二百公里的路程。面对二百公里即将沦陷的山河,他们本来有很多话要说,可自萧毅肃开口说了句“要是让老头子搬了家,我们三个人的脑袋也要搬家了”后,三个人一路上就什么也没说。吉普车一次次剧烈的颠簸,像是三个人随之打的一个个哆嗦。
吉普车疾驶到惠通桥时,天气已经转晴,怒江大峡谷赫然展现在眼前。
举目四望,松山如黛,怒江如练,惠通桥飞架两岸。桥下,怒江湍急奔流,白波似箭。
桥上向东岸后撤的车辆和人流,在晃悠的钢缆上,更显张皇失措。
三人下车后就匆匆挤着往桥上走,匆忙地连桥头宪兵的敬礼都没回。
走上桥后,三个人就走成了一条直线。渐渐地,这条直线又拉开了距离。马崇六跨步在前,萧毅肃紧抓护栏走在中间,张祖武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后面。走到桥中间,马崇六回头望了一眼萧毅肃,就止下脚步,不再向前走。
远望过去,马崇六正对着张祖武,向四下指指点点,动作和情绪都有点激动。马崇六的指点处,张祖武都看见了,可他的话一句也没听完整。桥下怒江的怒吼、桥上汽车发动机的轰鸣、人声的鼎沸,瞬间就将马崇六吐出的每一个字吞没。
于是,马崇六就对着张祖武耳边大吼。张祖武听清后,就对着马崇六的耳边大叫。在吼叫之间,萧毅肃对着两边频频点头。
马崇六又对着张祖武耳边大吼一声,张祖武没有回应,只是马上立正,敬礼,转身就走。
张祖武回到惠通桥西边的桥头,他的独立工兵营正携带着炸药、爆破器材,分乘着十辆美式大卡车赶到。第一辆开道车,却沿着公路冲过了桥头位置,一直冲到一个叫老虎嘴的崖壁下。副营长在后面的吉普车里伸出头来大叫:——回来——回来——你给我回来!那辆冲出去的大卡车,在一个急刹车后,开始慢慢往回倒。
张祖武走过来,面对肃立桥头的全营士兵年轻的脸庞,凝视了有一分钟,然后大声命令:一连在桥上铺设炸药,二连、三连抢占东岸山头的制高点!
史料载:在张祖武的诸多特质中,有一条是:善使枪。
他长短枪都善使,无论长枪、短枪,只要一到他手中,就成为百发百中的杀敌利器。有这样的营长,就能想象出这是一营什么样的兵。
张祖武布置完任务后,就挤过惠通桥上的人流,往东岸的制高阵地大步走,波浪般起伏的桥面,也没让他放慢脚步。
然而,危险正一步步逼近。
马崇六临行前对他大吼:相机炸桥,刻不容缓!
这样的军令,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
这样的军令,这样的场景,在二战中,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战场,都曾出现过。
那些接受了这种军令的守桥指挥官,无论敌我,到最后都没有好结果——一边是炸桥时间的刻不容缓,一边是急等着过桥逃命的大批伤兵和难民。面对斯情和斯景,那些守桥的指挥官,如何能按下起爆的手!
马崇六似乎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和感情煎熬,他只是命令张祖武——“相机炸桥”。
而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之所以没在桥东岸派重兵掩护,只是准备在炸桥后就撤走,因为只要在日军抢占惠通桥之前,炸了这座天险,重庆的半壁江山就能保住。至于什么时刻炸桥,就看你张祖武如何把握。
而此刻惠通桥西岸的那些伤兵、野战医院、辎重、军政机关、溃兵、坦克、大炮和无数难民的命运,就全掌握在了张祖武手中。
张祖武走到西岸的桥头时,一眼瞥见守桥的宪兵连长,正一手甩在背后,一手戳进人流大声吆喝。这些宪兵,个个会摆谱。排长会摆出连长的架子,连长就直觉得自己是个少校。这个连长是名上尉,就正在用一个少校的口气,对着慌乱的人群指指戳戳。
张祖武站定,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对着那个连长一挥手叫道:到这儿来!
连长转脸一愣,然后就朝张祖武跑来。他在看到张祖武军阶的同时,还看到张祖武那内敛的眼神中的一股寒气,还有那寒气背后透出的一股杀气。刚才他目睹了,就是这个中校,在桥上对着两个中将大喊大叫,当时他连大气都不敢出。
上尉朝张祖武跑来,立定,敬礼。
张祖武问:在这座桥上,现在还有比陆军中校更高军衔的军官吗?
上尉回头朝桥上望了一眼,马崇六、萧毅肃早已登车离去,就回答:没有。
张祖武说:那好。从现在开始,你这连宪兵就归我指挥。现在我命令你:除了站岗值勤的,其余所有的人员,立即分成三人一组,沿线严查那些等待过桥的人员和车辆。日本人惯于偷袭,在缅甸时我们吃了多少亏?他们伪装的伤兵、难民,不仔细盘查,一点都看不出……在盘查过江人员时,要注意他们的口音。检查车辆时,凡车后有蓬布的,要掀开搜查。一旦发现可疑情况,立即鸣枪警告……
张祖武命令完,宪兵连长敬过礼转身就跑。
张祖武的警卫员,从路边搬来一张被丢弃的藤椅递过来,张祖武接过来往地下用力一戳,就在桥头的一座碉堡前坐了下来。
正在过桥的人流、车辆,匆匆从他面前经过,一个接一个,一辆接一辆,好似无尽的长龙。警卫员递上拧开盖子的军用水壶,张祖武摇摇手说:不渴。心里却在想: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
1942年5月1日中午,独立第二十四工兵营一连,在惠通桥体填埋好炸药。
下午,张祖武命一连的士兵,徒手站立在惠通桥两边的钢索护栏前。护栏的间距太大,桥面的铺板总在晃悠,常有惊惶失措的人,凄厉地喊叫着坠入江中。
不尽的人流、车辆,缓缓从铁索桥中间经过,桥面此起彼伏。
桥两边的护栏前,士兵们背倚钢索,紧拉着手,在惠通桥上站出了两道人墙。在那些惊惶的人流中,就会跌倒有人扶。有伤兵、孩子、老人上桥,马上就会有一双双大手伸出,飞快地朝东岸扶送。于是,惊恐的人群,就少了一份恐慌,多了一份镇定。他们在桥上的慢步,渐渐成了快步。那群起的快步,让205米长的惠通吊桥,像波浪一般起伏。那浪一浪高过一浪,从那桥上撤出的人员和车辆,就越来越多……
从5月1日上午到5日下午,无数的伤兵、溃兵、难民,还有野战医院、辎重、军政机关、坦克、大炮,从惠通桥这条唯一的逃生通道,撤退到了后方。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后来都活了下来。
二战中,1940年5月,关乎英国未来命运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在英国倾全国之力下完成的。
二战中,1942年5月,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惠通桥大撤退和大爆破,是靠着机智、勇敢的张祖武,与他的工兵营,还有一连宪兵完成的。
5月4日中午,日机开始轰炸惠通桥东岸的保山。下午,日军侦察机两度掠过惠通桥,反复进行盘旋侦察。
5日下午六时,一辆卡车从保山开到惠通桥,欲与桥上的人流和车辆,逆行争道过桥。宪兵不许,令其返回。车主龙陵商人何树鹏,自恃后台很硬,出言不逊,被宪兵重赏两个嘴巴。何树鹏忿忿然将卡车调头,不料操作过猛,车头与另一车相撞,致使桥面阻塞。
闻讯从西岸赶来的张祖武大怒,命宪兵将其卡车推入怒江。何树鹏不允,以身护车。张祖武火上浇油,命宪兵以“妨碍执行军务罪”,将何树鹏拖到江边枪毙。
“砰——”的一声枪响,不仅结束了何树鹏的生命,也绷断了此刻正扮作一群难民,已携械潜行距惠通桥西岸两百米的日军指挥官的神经,以为行动已暴露,于是急令敢死队冲锋。一时间怒江西岸枪声大作,弹雨将桥上熙攘的人流,打得纷纷坠入江中。
正站在东岸桥头的张祖武闻声立断,对着守在起爆器旁边的连长大喊——起爆!起爆!
刹那间,在刺耳的爆炸声中,一只巨大的火球,在西岸桥头腾空升起。冲天的爆炸气浪,将惠通桥的部分桥面高高抛起,然后缓缓坠入怒江之中,让日军指挥官看得心如刀绞……
1942年5月5日下午六时,日军妄图直取重庆的铁蹄,终于在惠通桥前,踉跄着止住了脚步。
三
由于张祖武及时炸毁惠通桥,阻敌于天险之前。由于他在炸桥前,指挥若定地从这座桥上,撤出了无数军民和装备,被国民政府军委会记大功一次,同时奖励该工兵营法币一万元。
一个月后,一枚由国民政府制作的,惠通桥战役的纪念章面世。
纪念章为铜质,直径2.8厘米。正面为深蓝色珐琅填底,外圈是本色铜边,中间是白色珐琅底的惠通桥图形。图形上方,“惠通桥”三个字和钢索吊桥图案十分醒目。“桥上”有“陆军独立工兵二十四营”字样,下有“五五纪念章”五个字。纪念章背面有:“31年、张祖武赠”的款识。
在整个抗战期间,由国民政府制作,以个人名义颁赠的战役纪念章极为罕见。这是一种极高的殊荣,只有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不朽战功的人,才能享有这份殊荣。享有这种殊荣的人,说他是民族英雄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