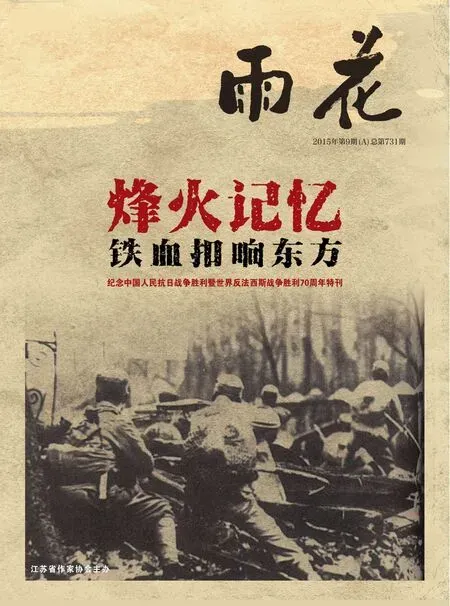神头岭伏击战
◎ 向守志
神头岭伏击战
◎ 向守志
弹指间,岁月匆匆,中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70年了。我也由当年生龙活虎的青年变成了耄耋老人。回首八年的浴血抗战,中国人民以钢铁般的意志,以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精神,以血肉之躯前仆后继,同武器装备、作战素养高于我军数倍的日军进行殊死搏斗,直至最后取得胜利,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在装备简陋的情况下,以游击战术,在敌后不断地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赢得了不少典型的战役,也创造了不少的适合于当时的新战法,发生在山西的神头岭伏击战,就是著名的战役之一。我也参加了这次著名的伏击战。
神头岭位于山西的黎城、潞城之间,是一座长不过几里,宽度在一二百米之间的光秃秃的山梁,不适合于伏击战。八路军129师386旅在陈赓旅长的指挥下,在这不宜于开展伏击战的地方,以出其不意的胆略,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创造了八路军抗战史上打伏击战的一个“神话”。
八路军129师是在1937年8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4、第31军,西北红军第29、第30军和独立第1至第4团以及第15军团的骑兵团等改编的,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下辖第385旅、386旅。第385旅下辖第769、第770团,旅长是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第386旅下辖第771、第772团,旅长是陈赓,副旅长是陈再道。我当时20岁,刚从庆阳步兵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第386旅771团任机枪连副连长。我清楚地记得129师是9月6日,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附近的广场上,在大雨中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到9月底,第129师386旅的771、772团和385旅的769团以及师直属骑兵营、干部营在刘伯承师长、张浩主任的率领下奉命从陕西省三原线出发,经富平、韩城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晋东南侯马地区,包括山西省正太铁路以南、同蒲铁路以东、平汉铁路以西、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
第一次与日军交战不是伏击战而是阻击战、袭扰战。我129师在1937年10月进入了太行山地区,第771团根据上级的命令就在井陉以南的七亘村阻击从井陉出发进犯太原的一个旅团的日军,我所在的1营在一个称之为老爷庙的后山上设防。战斗一打响,一个3000多人的日军联队在强大炮火下向我团阵地发起猛攻,这是我第一次与鬼子作战,也是129师首次与日军作战,互相不知道对方的作战特点,战斗非常激烈,弹片横飞。激战至黄昏,日军在步炮协同下连续多次向我们阵地发起进攻,我和战友们抱起机枪向日军猛扫,3连战士在副营长徐其海的带领下,上刺刀发起反冲锋,把攻上的日军压了下去。在夜幕降临之际,我团完成阻击任务之后撤出阵地。此战,我部毙伤日军70余人,但也付出伤亡30余人的代价。入夜,天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团首长命令我带领第1连到敌人设防的侧鱼镇、老爷庙一线进行夜间袭扰。我们摸到日军阵地前,连续打枪、投弹,声势较大,日军以为我主力部队发动进攻,连忙开炮还击,一夜不得安宁。狡猾的日军在我们完成任务回到驻地休息时也给我们来了一次偷袭。我在睡梦中,突然听到枪响,一骨碌从土炕上站起来,迅速穿好军装,抓起手枪,带领战士们集合,在警戒部队掩护下,我们按预定方案有秩序地转移到集合地点。
首次与日军交战前,我们不知道日军的强点和弱点在哪里,经过这一交战,我们认识到日军与国民党军队确实不同,尤其是经过长期战争准备的头几批“老鬼子”,作战素养较高,步炮协同好,轻重机枪也比国民党军队多,他们的“小钢炮”,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它叫掷弹筒,打得准,近距离有较大的杀伤力。由于日军受到“武士道”精神灌输,作战时,只许进,不准退,嗷嗷叫着往前冲,敢于拼刺刀,还擅长夜战。因此,初次交战时,我们还是沿用打国民党军队的战法,习惯于把敌人放近了再打,试图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压下去消灭掉。事实不是这样,这让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这些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在我们后来作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夜扰战之后,我已经由1营调到2营任机枪连连长。在刘伯承师长的指挥下,第129师游击战术已运用得出神入化。同年11月,在不到一个星期时间内,我们先后在黄崖底、广阳、户封地区连续设伏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刘伯承师长把这三次伏击战称为“重叠的设伏”。在11月末,我771团2营,面对来犯的600多名日军,把1个连分成若干个战斗小组,埋伏在日军前进道路左侧的山坡上以及村庄里,从各个侧面伏击日军,日军伤亡100余人后不得不撤退,而我部无一伤亡。刘伯承师长把这一战法形象地比喻为“麻雀战”。“麻雀战”这一军事用语就此诞生了。
到了1938年2月中旬,侵华日军为配合其津浦线作战,集合3万余人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由于邯(郸)长(治)公路是晋西南日军从平汉线取得补给的主要交通线,3月上旬,第129师奉命集结在邯长公路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寻机歼敌,破坏交通线。日军深感邯长公路的重要性,日军108师团步兵及骑兵1000余人驻守沿途各县的据点里,其中黎城与潞城是两个可以相呼应的最重要的据点。由于距潞城县东北的神头岭一带地形复杂,便于设伏,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徐向前副师长当即决定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战策,拟定了“吸打敌援”的作战方案,即先以一部兵力袭击日军占领的重镇黎城,吸引潞城之敌来援,而后以主力在神头村附近地域组织伏击,歼灭增援日军。
在我们制订“吸打敌援”作战计划之前,即在同年的2月,刘伯承师长就采用攻点打援的战法在井陉与旧关之间的长生口设伏,打击从井陉援救旧关的日军。
水无常形,兵无常势。日军绝对没有想到,我129师再次使用围城打援之计,在神头岭设伏。根据拟定的“吸打敌援”的作战方案,以769团为左翼,派一支小部队袭击黎城,该团主力部队则伏击涉县可能来援之敌;第386的771团、772团以及补充团为右翼,由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指挥,在神头村附近设伏,歼灭潞城增援之敌。
在386旅召开的战前第一次准备会议上,旅长陈赓和政委王新亭介绍了刘伯承、邓小平等师首长的战略意图,请三个团的指挥员就选择伏击场地问题发表意见。团首长的眼睛都盯在国民党军队遗留下来的一张旧军用地图上。地图上显示神头岭有一条深沟,公路恰从沟底穿过,路两旁山势陡险,便于部队隐蔽也易于出击,是个理想的伏击地。大家一致推荐在神头岭设伏。此刻,心思缜密的陈赓旅长发现大家都没有去过神头岭对地形地貌进行实地考察,事前的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于是,立即带领团首长实地勘察。到神头岭后,他们大吃一惊:公路不在山沟里,而是在一道有几公里长的光秃秃的山梁上,两边的地势略高于公路,除了距路边20米至100米范围内有一些国民党军队修筑的旧工事外,这里再也没有任何隐蔽物。显然,这样的地形不适宜伏击,然而除此点以外,附近再也没有合适的伏击地点了。因此,选择伏击地点由信心满满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观察地形很久的陈旅长也注意到大家脸色凝重,诙谐地说:“回去讨论好啦,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想吃肉,还怕找不到个杀猪的地方吗?”
讨论会上,陈旅长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用洪亮而又坚定的声音说:“我看,这一仗还是应该在神头岭打好。”
大家一脸诧异。他具体分析说:“一般地讲,神头岭打伏击的确是不太理想。但是,现在这种不理想却正是我们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的好地方。正因为地形不险要,敌人必然会麻痹大意,放松警惕。而且那些原有的工事离公路最远的不过百十来米,最近的只有20来米,敌人早已司空见惯。如果我们把部队隐蔽到工事里,隐蔽到敌人鼻子底下,切实伪装好,敌人是很难发觉的。山梁狭窄,兵力确实不易展开,但我们是先处战地,可以先敌选择有利地形,先敌展开,这样就更可以迫敌于不利地位,把地形上的不利统统甩给敌人。”
讲到这里,陈旅长问道:“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大家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团徐深吉团长笑道:“我看是谁先下手谁占便宜。”
旅长接着说:“对哇,只要我们做到突然、勇猛,这种地形上的不利条件就只是对敌人不利了,而对我们则变成有利了!”
3月15日,是预定的作战时间。在夜幕慢慢降临之际,部队经过周密准备,深入动员,借着黄昏就隐蔽出发了。战士们情绪高涨。这一时刻,我也特别兴奋,预感到要打大仗了。我率领2营机枪连随队急速跟进。过了申家山,就接近我们的设伏地域了。回头一看,山间小道上,在朦胧的月光中,我们的部队犹如一条游动的长龙,悄悄地向山冈和公路两侧急进。
部队进入设伏位置后,根据战前要求,立刻进行伪装和战斗装备。我逐一检查战士们的伪装,轻声叮嘱:“一定不要随便动旧工事上的土,踩倒的旧工事近处野草,也要顺风向扶好,绝对不能暴露目标。”一名战士很担心地问我:“连长,你说鬼子会不会发现我们?”“当然不会。可是,你们不好好伪装,暴露了目标,那就破坏了整个作战计划。”就在此刻,从东北方向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轰隆声。我一阵兴奋,知道担负“吸敌”任务的769团已经对黎城展开攻击。
听着远处的枪炮声愈来愈密,大家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我督促战士们加快伪装,迅速隐蔽起来。连队伪装完毕,我看了看表,正好是16日4时许。
部队静静地隐藏在工事里,东方的天际也慢慢出现了鱼肚色。黎城方向的枪炮声时不时传来,时紧时松,时密时疏。此时,天已大亮,神头岭一如往常平静,仍不见鬼子的影子,埋伏在工事里的战士已经好几个小时,动也不敢动,心里非常焦急,担心鬼子不上钩。直到陈赓旅长命令部队准备战斗,说日军已从潞城派出了1500多人增援时,战士才放心。
原来,日军正按照我们战前的设想行动。黎城袭击战打响后,涉县的日军以数百人乘汽车来增援。刚过东阳关,就发现第769团设伏部队,双方互击,该部日军比较狡猾,可能意识到我军的目的,只稍做抵抗,即向涉县回撤。
而潞城之敌得知黎城被袭,随即抽调步骑兵1500余人向黎城增援。8时30分,敌先头分队乘汽车2辆和骑兵20余人,沿公路通过我设伏地区向黎城开去,我另一伏击部队将该敌放过之后,把赵店木桥焚毁,截断日军的退路。这一举动,并没有引起日军的警觉,认为这不过是游击队破坏交通的伎俩,不以为然,仍趾高气扬地往前奔去。
就在陈赓旅长通知各团准备战斗时,敌主力纵队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界内:走在前面的是步兵、骑兵,中间是车队,后面又是步兵、骑兵。我远远望过去,日军就像一条巨大的“黄蚯蚓”在蠕动。不久,已接近神头村的日军先头部队突然停下来,难道日军发现了我们?我紧张得屏住了呼吸。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仍不见日军向前走。此时,日军派出了一支骑兵组成的搜索队,沿着一条羊肠小道直奔埋伏阵地,眼看着日军在一步步地接近我们的工事,就要踩到战士们的头了。我们感觉到阵地上的空气就要凝固一般。好在日军在距旧工事10米左右时仍没有察觉就在他们眼皮底下的战士,正如陈赓旅长预料的一样,日军只注意了远处,注意了沟对面的申家山,对于脚下那些见惯了的工事,却根本没有放在眼里。看到申家山没有动静,发出了信号,便继续前进了。后面的大队,随即沿公路跟了上来。
9时30分,当日军主力完全进入我设伏区后,陈赓旅长发出战斗的信号,我各部队按照统一信号,向敌突然开火,发起攻击。第771团拦头,第772团第3营断尾,第772团主力和补充团从公路两侧向敌突击,顿时将敌截为数段。我指挥机枪连开火,日军当即倒下一片,其他连队的战士们投出的雨一般的手榴弹在日军中炸开,山梁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随即,战士们纷纷从工事里、草丛中冲出来,高喊口号,如猛虎一般冲进敌阵,用刺刀、大刀、长矛和日军展开肉搏。激战约半小时后,我预备队第771团第2营一部投入战斗。只见长长的公路上,白光闪闪,红缨飘飘,许多日军在我军突然打击之下,惊魂未定之际便被刺死。剩下的四处溃逃,企图组织顽抗,但在这狭窄的山梁上,无地形地物可以利用,只能在公路上来回奔窜,有的滚进工事里,有的趴在死马旁拼命射击,也有的端着刺刀恶狠狠地向战士们扑过来。
我抓住战机,迅速指挥机枪向这些顽固之敌密集扫射,几十个扑向战士的鬼子立刻就被机枪送上了西天。一名日军中尉想负隅顽抗,向奔跑的日军只喊了一句:“大家一块儿死的地方就在这里,干吧!”话音未落,就被一枚迫击炮弹炸死。
战斗局面完全倒向我方,中断的日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除少数逃跑外,其余的都成了刀下鬼。
在胜利在望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来,一股残存的日军窜到东西两头,东部的日军被我部队截击,但西头的300多名日军却乘隙占领了神头村,企图依据房屋、窑洞固守待援,伺机接应东头的日军一起向潞城逃跑。如果让日军在村里站稳脚跟,就等于让敌人占领“桥头堡”,形势将对我们极为不利,战斗局面就有可能急转直下!
在关键时刻,陈赓旅长斩钉截铁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村子拿回来!
命令一出,战士猛冲上去,同日军英勇拼杀。一名战士负伤四处,用毛巾扎住伤口止血以后再战,一口气刺死六个敌人,最后壮烈牺牲;还有一名战士受伤以后,用毛巾勒住伤口,一口气向敌人丛中投出了12颗手榴弹;一名司号员赤手空拳把敌人摔倒,捡起石头,砸向鬼子,并夺回一支枪;一名炊事员用扁担劈死一个敌人,夺来了一支三八枪;补充团中的新战士,许多没有步枪,就拿梭镖与日军拼杀,勇气使日军胆寒。战斗结束后,陈赓旅长审问俘虏时,一个日本兵说:“我什么武器都不怕,就怕你们的长剑。”
到下午4时,刘伯承师长下令各参战部队撤离。我站在神头岭上,眼前到处是倒地的日军和骡马尸体,还有成捆成箱的辎重和散落一地的文件。
此役,仅有百余名日军突围逃回了潞城。我部以伤亡240余人的代价,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俘虏8人,缴获各种枪支550余支,俘获骡马600余匹,击毁日军汽车百余辆。神头岭成为了日军丧魂落魄的“伤心岭”。
神头岭伏击战给予入侵晋东南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对牵制日军向晋西南、晋西北进攻起到了重要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太行山抗日军民的战斗士气,也震惊了日寇侵略者,他们不得不承认战斗的指挥者有“第一流战术”。一名当时从神头岭伏击战中侥幸脱逃的日本《东奥日报》随军记者,回去后写了一篇题为《脱险记》的通讯,称神头岭之战是八路军129师的“典型游击战术”。
(顾茂富/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