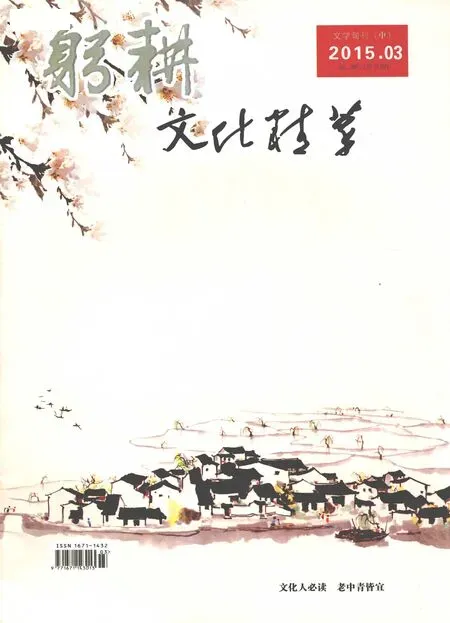风中雀巢
◆ 雨 萍
风中雀巢
◆ 雨 萍
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走得两腿发酸,却不敢停。他怕停下来就永远停下来,这是很可怕的。走吧,走吧。只有走才有希望。他的愿望很低很低,低得羞于说出口。不管别人理想多么远大,他只为自己低廉的理想活着。等到他看到那个熟悉的池塘,就激动起来。野草丛生,环绕在一片蓝天白云之上。他站在池塘边,抬头是天,低头也是天,疑惑起来,思想着自己在天上或是地上?等他看到了瓜棚,清楚自己住过的瓜棚绝对在地上。他敢说绝对,因为他父亲睡在里面看过瓜,他睡在里面看过星星和月亮。他忘了腿脚的酸痛,急不可待地跑向瓜棚,看瓜的父亲也许还在里面。瓜棚本来离池塘很近,可是他跑了好久也没见到瓜地。没有瓜地就没有瓜棚,没有瓜棚就没有父亲。瓜棚没有就没有吧,可是没有父亲,他悲哀起来。悲哀没用,他还得走,他想回家。
他已闻到家的气息,知道家就在眼前,但是,看不到。一棵大树挡住了他的路,怎么都绕不过去。变了,眼前的一切都陌生起来,他居然回不到那生养了他的家。他绕来绕去,鼻青脸肿,脚上起了茧子,衣不蔽体,不知绕了多少年,始终没找到进村的路,面前只有那棵树。一颗陌生的大树。
他停下来,仔细地打量那棵树,才发现树冠庞大,遮天蔽日,上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雀巢。一只只喜鹊忙着飞进飞出。在聒噪的喳喳声中,他听到了娘的声音,嫂子的声音。他的心湿润起来。快步跑向池塘,他要洗得干干净净回家。可是,池塘不见了。满面尘垢,见娘可以,见嫂子绝对不行。他脱下比脸还脏的衣服用力檫脸。用劲儿,再用劲儿。由于用力过猛,脸上的皮脱落下来,血肉模糊掉在地上。我的脸!张勇惊恐万状,吓醒,下意识地摸一把脸,没摸到血肉,也没闻到血腥,愣怔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睡在一间石棉瓦盖的简易工房里,离家好几百里。这是一家木材加工厂。他努力地想,怎么会睡这里。房子外面堆放着一大堆从港口运来的大木头。那些木头生长的地方更遥远,得飘洋过海。迷迷糊糊中,他感觉屋外那些木头似乎来自于他的梦中,无数的人喧哗着挥斧砍伐那棵大树。砍!砍!砍!痛!痛!痛!冷,他感到很冷,坐起来,没拉亮电灯,屋子里却很亮。墙上晃动着一轮透红的太阳。他下床走到太阳下面,朝上伸手摸一下,只摸到一面冰冷的墙,太阳躲到墙那面去了。墙挡住了他的太阳。他不甘,用头撞墙。用头撞起码比站在那里有一线希望。他拼足了力气撞上去。嘭!墙破碎了,他也破碎了。粉身碎骨的痛,彻底地醒了。他的隔壁住着一个女人。一个和嫂子很像很像的女人。
嫂子,一直折磨着他的女人,十六岁那年就走进了他的眼里。那天,张勇和同学一前一后骑着自行车像两匹野马飞奔回村,车铃声和口哨声一起得瑟着,惊吓得村口觅食的小鸡乱飞。他们看到打工回来的哥哥时,口哨夏然而止。自行车却停不下来,两辆自行车追在一起,连人带车都倒在地上。张勇的哥哥扶起他的自行车说:你看你,怎么骑的车。张勇顾不得屁股痛站起来,脸窘的没处放,心里却委屈得要命。谁叫你后边跟着个天仙般的女人?手脚才失去了分寸。他扶着车子偷望着那女人。哇!那眉眼,那胸部,那屁股,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女人。或者以前也见过,却没注意。
他哥猝不及防带回来一个女人,家里什么都没准备。他们只有三间通堂的屋子,连门帘都没挂,东屋放个屁,臭到西屋。他爹和娘住东屋,他们弟兄二人住西屋,当中是他们吃饭和摆了祖宗牌位的堂屋。弟兄共有的那间屋只能给哥了,家里再没他睡觉的地儿。张勇吃着饭就想到了。他没等他们吃完就抹一下嘴巴提着书包出去了,说到同学家去做作业,其实是幌子。村庄不大,村东家来客炒肉了,村西的人在自家里喝着糊涂能闻到那肉香。他哥带回一个女人挤得他没地儿住,他才不想去同学家丢人现眼。他背着书包走出家门,走过他们摔倒的地儿停了一下,反复想着她的模样眼神。那眼神像蜂蜜一样,让他的舌头情不自禁伸出来了,舔着的却是还沾着辣椒鸡蛋味的下嘴唇。娘炒的辣椒鸡蛋是一绝,辣椒辣,鸡蛋嫩。又辣又嫩,那感觉。想象漫无边际。他用书包敲打一下自己的头,该死!继续朝村外走,走进他家闲置在地里的瓜棚。
瓜棚本来就小,平时就没人注意,融进夜色里,显得更小,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但张勇知道它在那里,里面有一张小床和父亲的汗酸味。枕着书包,望着漫天的星星,被群星簇拥着的月亮。喔,那月亮不再是月亮,有鼻子有眼,生动传情,娇媚无比,诱惑着他的手骚动不安。可是他的手不够长,无论是天上真实的月亮或是那个虚幻的影子,他都够不着。他的手只能掐着自己的大腿。一下又一下反复地掐,想用痛来驱逐那不该想的影子。可是他的腿邪气起来,怎么掐都不痛,那眉眼还在眼前晃呀晃的。她的笑她的熟苹果一样的气息淹没了他,让他浑身燥热起来,瘙痒难受。棚外知了的鸣叫,青蛙的聒噪如火上浇油。他脱光了衣服用手抓挠。从头到脚都刺痒,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便站起来,走出瓜屋,在月夜里盲目地奔跑着。没有思维,也没有念想,只是让双腿别停下来。他不知道跑了多远,多久,闻到水的气息,双腿才慢下来。一个装了月影星辰的小池塘,月亮离他不再遥远。啊!他像动物一样尖叫一声就扑进去了。他都记不清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的。只记得出来后精疲力竭,躺在塘边睡着了,直到第二天的太阳照着他的屁股,一只小蚂蚁爬到他胸脯上迷失方向,咬了他一口。他不明白,到底是他嫂子或是那个池塘让他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他知道那种情绪是可耻的。但他没办法。
吃过老板娘买来的热馒头和咸菜条,张勇就走向车间,经过挂上白霜的原木堆。每天,他和老板娘的侄子在原木堆里选一根木头,合力滚进车间,再从轨道滚进机器里,喀嚓喀嚓,完整的圆木被旋剥成漂亮的木纹皮。干这种活需要耐心,细致,还需要蛮力。这蛮力需要他每顿要吃五个馒头喂养。他吃馒头时,老板娘总是皱着眉,而看见他干活,眉头就开了。老板娘的侄子还没来,那活一个人干不了,他就攀到原木堆顶蹲下去,摸出一支香烟点燃。蓝莹莹的烟雾在张勇面前缭绕,散发出丝丝暖意。老板娘走过来了,站在原木堆下,脸上覆上白霜,眼瞅着张勇,嘴里骂着她侄子:死孩子,都几点了还不来。张勇知趣,猛吸几口,扔掉烟头,把手伸向冰棍一样的木头,先独自扒下树皮。拿一样的工资,比老板娘侄子干的活却要多。想到这,他的气就不顺。
快十二点了,旋皮机里的木头还没旋完,张勇看着那木头烦躁起来。让他烦躁的除了肚里的叫声,还有隔壁车间铡皮子的声音。那些声音的操纵者里有赵霞。每当他听到肚里的叫声,就想看到赵霞。两种饥渴参杂在一起,能相互抵消削弱一些,但抵消不了,削弱不了,都像虫子一样在他体内蠕动着。再坚持一会儿,等到下班,他就可以快步跑向隔壁车间,看到她。看到她就够了。他只有权利看,而没有下一步。可以看,可以想,可以想得天花乱坠,就是没有下一步。她进厂比张勇晚一些。第一眼,他就吃惊得差点叫喊出来,嫂子!老板娘叫她赵霞,才清楚她不是嫂子。看到嫂子,欲念像火苗一样呼呼上窜,他得提着灭火机噗噗地灭火。而不是嫂子却像嫂子的女人,他就不必紧张惶恐了。
终于熬到十一点五十五。十二点下班,剩下那五分钟用来清理机器下面的下脚料。张勇看到手机里出现的时间,举起来向老板娘的侄子晃了一下,兴奋得嘘了一声。老板娘的侄子也摸出手机看了一眼,然后关掉电源说:你收拾一下,我有事先走。操,你有事,我就没事了!张勇瞟了一眼老板娘的侄子,脸露不悦。机器下面的坑里,漏满了碎木屑,平常都是他们两人一人一边朝外掏。张勇憋气地掏着下脚料,嘴里骂着狗日的,驴日的,婊子日的,奶奶个腿,娘的个逼。活干完了,骂声才止,脱下工作服,隔壁铡皮子的声音却消失了。怎么就消失了呢?
他仍不死心,固执走进已经空无一人的车间。落寞地走过,听着自己狂躁的心跳,噗噗噗,咚咚咚。抬起头望着挂在墙上的石英钟,十二点半了,狗日的。
走回宿舍,在门旁的洗脸盆里洗一把脸,才拿起盛饭菜的不锈钢碗去厨房。厨房里凌乱不堪,像一个小垃圾场。虽然天气凉了,潲水桶和屋角垃圾堆里还是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每天他们要吃饭就得被动接受那臭味。似乎饭菜产生于臭味里就像鲜花长在牛粪里,不得不一起接受。吃着那些饭菜,偶尔会恶心。恶心起来翻肠倒胃,他就劝自己忍着吧,忍到年底就好了,就可以拿到工资回家备下一部分砖瓦。有了砖瓦才能盖房子。恶心算什么?
一卷黄色的煎饼放在一张脏污的小桌上,墨绿色的菠菜软塌塌盛在一个外面盛狗食一样的不锈钢盆里。他拿出一半煎饼,拔出一半的菠菜在自己的搪瓷缸里。
张勇端着饭菜没进宿舍,爬上院子里的原木堆上。赵霞的宿舍还没开门,她总是等张勇打完饭菜后才去厨房。张勇蹲在原木上吃饭,就可以看到她出来进去的身影。他的眼睛盯着赵霞的门,却用筷子扒拉着菠菜叶。这随便一扒拉,露出一小块碎木屑,被染成了菠菜色。看到木屑,他的气就上来了,不再有食欲,用筷子把木屑夹到碗边,继续扒拉着,希望看到第二块木屑。第二块木屑没露出来,却出现一根红色的头发,还有软塌塌的菜青虫。看到红发丝,他就知道谁做的这菜。老板娘十六岁的女儿晃动着一头红色的头发,像木屑堆里长出的一朵红蘑菇。白蘑菇好吃,红蘑菇有毒,张勇很小就知道。平时她都宅在屋里玩电脑,只偶尔看到她从屋里出来上厕所。张勇的目光会被她带进厕所。假如没有木屑,没有虫子,也许他会激动地亲一下那发丝。但是,她和虫子木屑纠缠在一起,就让他恶心。张勇站起来,走下原木堆。赵霞的门打开了,手里拿着一个空碗站在门口。张勇快走几步,用筷子夹起那根软榻榻的菜青虫。他以为赵霞会和他一样生气,没想到她软声细语说:有什么好看的,扔掉就是。张勇惊愕地看着赵霞没事一样走进厨房。他多么希望她站在他一边,和他一起去老板那里讨说法。没有她的支持,他独自也要去。吃着清水煮菜,每天当牛做马,他的肚子早就怨声载道,只是找不到理由发作。现在,虫子和发丝正好可以帮助他。
老板娘尖瘦着小脸给他开了门,看到碗里的异物,呵呵笑起来,露出两颗亮闪闪的金属牙齿,然后说:俺今天忙,翠翠给做的饭。她推出闺女做挡箭牌,你纵有万发怒箭,面对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能射出来吗?张勇并不买她的帐。
“这菜能吃吗?”
老板娘夺下张勇手里的筷子,把虫子和头发挑出来扔掉说:“没挨过饿,过去阴沟里拔出的东西还抢着吃。”
老板娘一副不屑的表情,张勇很想把菠菜倒在她脸上,忍着怒气说:你吃吧,俺不吃了。老板娘见张勇生气了,变了语气:哟哟哟,这点事值得生气?去去去,倒给狗吃。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五元票递给张勇说:自己去炒一盘菜。厂房外的小饭店,五元可以炒一盘土豆丝或者黄豆芽。
张勇看到老板娘手里的票子,想起小时候青黄不接时村里会涌来一些瘸腿少胳膊的。他们赶在饭时突然出现家门口,嘴里可怜地乞求:好心的给口饭吃吧。他妈就会撕下一角煎饼没好气递过去:去去去,到别家去要。他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要饭的,老板娘变成了他妈。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硬是连在了一起。自己出力挣钱,却是这种待遇,他咽不下这口气。
当初他带着小美来到这里,看到厂子大门外墙上的招工启事:月薪一千,免费食宿,才确定留下来的。
他哥带回的女人到第二年,就怀孕了。他哥只得独自出去打工,把孕妇留在家里。他去上学,父母下地干活,嫂子挺着肚子在家给他们做饭。望着嫂子凸出来的肚子,知道里面是他的侄子或是侄女,他是他(她)的叔,但是,肚子下面的地方,仍然让他胡思乱想。他知道那样的胡思乱想不好,却没办法控制。为了杜绝自己的邪念,他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十七岁开始,就在外面打工,谈恋爱。钱没撇下,人也没撇下。那些女孩都像小蜜蜂一样,飞到他身上,采干净他身上的花粉就飞走了。一个叫小美的女孩没离开他,吸着他的喉结说愿意和他一起睡狗窝。他相信了她的话,带着她得意地回到家乡,就像当年他哥带着他嫂子回去一样。
那时,他家的老屋里有三个热心的观众,他爹,他娘和他。他带着小美回到他家的老屋,热心的观众只剩他娘了。他爹在给他哥盖好新房后第二年就病逝。有人说是累死的,也有人说是愁死的。无论怎么死的,反正那个人没有了。张勇决定把老屋简单装修一下就结婚。小美没说什么,她娘来看到低矮颓败的老屋,皱着眉头带走了她的闺女,说等盖好新房再说。望着空空洞洞的老屋,张勇才知道新房的重要。他迫切需要一座新房。他爹没了,指望他娘日渐干枯的手,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小美走了他不急,他相信只要盖好了新房,还会有另一个小美来到他身边。所幸,没过多久小美就回来了,怕她妈追来,他们刚过年就离开了家乡。为了节省开支,他决定暂时和小美分开,把小美送去工资低工作却轻松一点的大厂,他自己来到这免费食宿的小厂。他劝慰小美说:可以省不少钱呢,就可以早一点盖上新屋。没想到免费的饭菜是这样的。
张勇越过那张五元的票子,眼瞅着老板娘那极不情愿的脸愤愤地说:你嫌做饭麻烦,以后俺自己做,不过得加薪。
老板娘的金属牙缝里蹦出来一句金属一样冷硬的话:自己做可以,加薪没门。
虫子和发丝没让张勇达到预期的目的,却让他和赵霞一起走进了厨房。
张勇叫嚷着自己做饭,其实他从没做过饭。潜意识里认定赵霞会做饭给他吃。第二天早晨,老板就没做他们的饭。张勇走进厨房,像没头苍蝇乱转。赵霞进来,看他那样,知道他不会做饭,找出一个大盆,把案板菜刀菜筐丢进里面让他清洗。张勇看着她麻利地刷锅添水做饭,像小媳妇在自家的厨房里那么熟络,禁不住问:你老公怎舍得放你出来?
“有什么舍不得?他身体好时,我没出来过。”
张勇停下来,吃惊地问:“他怎么了?”
“在工地干活时从架板上掉下来摔断了腰。再也不能干活。”
张勇拿着钢丝球的手停在空中,吃惊地望着赵霞,心里涌出难言的悲哀,后悔自己多嘴多舌。他心虚地低头干活,不想看到赵霞脸上的表情。赵霞却没事似的说:洗快点,该用案板了。
隆冬时节,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把厂里的一切都变得冷硬。张勇买了一打白线手套,每天戴着手套干活,摸着机器,还是刺骨地寒。中午下班后,赵霞骑着老板红色的电车等在车间外。白灰色的线帽,红色的羽绒袄,黑色的打底裤,及小腿的棕色靴子。看那身打扮就知道她要出门。她说去城里买电热毯,让他自己做饭。电热毯,价廉而温暖,他也想要,便说:给我也买一个。
“不行,你不能睡电热毯。”赵霞掉转车头要走。张勇伸手抓住车把问:为什么?赵霞松开一只手打在他手上说:反正提醒你了,不相信自己去买。
张勇松开手,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睡电热毯,想再问,赵霞已经骑远了,心里说不能睡电热毯,那就睡你。
张勇削着土豆皮,还想着电热毯的事。去掉皮的两个土豆光溜溜地白,放进盆里再加进水,就像长在水里的两个乳房。他喜欢乳房,从那年夏天村口见到嫂子半透明的衣衫里若隐若现的乳房,他就陷进去了。他的手颤抖着伸向盆里。
赵霞回来了,只买了一个电热毯,却带回来三节铁皮烟筒和一个。张勇看没给他买电热毯,心里不悦,瞅着铁皮烟筒说:看来想把这当家当日子过了。
赵霞瞟一眼阴阳怪气的张勇说:好歹不知,给你买的。她那瞟的眼神媚而有魔力,让张勇失去自己的思想,甘愿听从她的差遣。
厨房里闲置着一个铁炉子,烟筒却坏了。赵霞先去和老板娘说了一声,然后指使张勇把铁炉子和新买的烟筒搬到张勇屋里安好。其实,张勇不喜欢碳炉子取暖,烧炭时屋里就会尘土飞扬,而且他不会烧炉子。他只想有个电热毯就行了。赵霞红着脸说男的不能睡电热毯。那红像火焰一样向他蔓延。
黑夜依旧比白天冷,但炉子里的碳烧红了,张勇的屋子里就暖和起来。他独自坐在火炉前,想着赵霞脸上的红,她的声音。温暖的夜比寒冷的夜更长。
终于到了腊月二十,老板开着他的白色轿车出了工厂,老板娘宣布停工放假。
可以回家了。还有什么比回家更高兴的呢?这一年的苦,累,委屈都被西北风刮走了,剩下的是领工资的激动和喜悦。赵霞和张勇都忙着收拾宿舍里自己的东西,等着结清工资就走。依然是天寒地冻,但心里高兴,那寒冷也可爱起来。老板娘挨个敲了他们的门说到她那去算账。张勇从正月就出来了,拼命干活。女友丢失,他都没舍得请假休息,就等这一天。他洗了脸,用梳子梳了一下乱糟糟的头发。留着和女人一样的长发,不是为了美观,只是懒得去理发店,而且省下了理发的钱。
他们都是第一次走进老板的住房。外边虽然和厂房一样简陋,里面装修封闭得很好。屋里开着空调,迎接他们的是温暖的热气。老板的闺女坐在电脑前,眼睛和电脑连在一起,就像一件家具摆在那里。张勇瞟一眼她,心里嘀咕着,生在有钱人家真好。
老板娘拿出一个大帐簿,在窗下的写字台上给他们算账。
老板娘算得很精很细,哪天提前走一小时,那个月是小月,不够三十天,他都要扣出来。而他加班的时间,三十一天的月份,只字不提。该扣的就扣吧,加班的时间,就当白干。但是,扣除那些零碎后,还要扣他们自己做饭之前每月二百的生活费。赵霞接受不了,他也接受不了。赵霞拒不接钱,气得嘴唇哆嗦着:俺来时,你们怎么说的?张勇接着说:提供食宿,外墙上的招工启事还在。
“这一片工厂的招工启事都那样写。你们出去打听打听,哪家厂不扣生活费?”
老板娘的嘴确实厉害。他们两张嘴说不过一张嘴。那一张一合的两片薄嘴唇,尖酸刻薄的话语像羊屁眼里拉出的一个个圆溜溜的羊粪蛋。张勇真想抓一把垃圾塞进去堵住。他进厂之前,是老板和他谈的待遇和工资。那老板真不是个东西,躲出去让他老婆对付他们。你不仁,俺就不义。张勇看着电脑前不受干扰的红发女孩,似乎开在悬崖绝壁上的花儿。看着那悬崖之花,他不再心痛被扣掉的钱。
走出暖气洋洋的屋子,外面的寒气呼啸而来,忍不住缩脖抱膀。脖子缩的再短,肩膀抱得再紧,还是冷。索性挺起头,大步走会宿舍,看着他住了近一年的木床,上面只有他孤单的影子。是的,只有孤单。他和小美分开后,他们几天见一次,下班后他去大厂或者她来小厂。可是,有一天下班后,去大厂里没见到小美,宿舍没有,车间没有,食堂没有。他的一个老乡把他拉到一个角落说:她和厂里的一个男工一起“跑”了。跑这个词很带劲,他很喜欢跑。但是,她和别人一起跑的,他的心里就被狂奔的马蹄狠狠地踩了一下。婊子日的,他骂一句后,就去找了婊子。婊子日的,他再一次冲动起来,想去找婊子。现成的小婊子在那里。
赵霞在门外问:收拾好了吗?
他不敢开门,闷声闷气地说你先走吧。
张勇和赵霞隔门说着话,心却系在老板的那间屋里。他听到那门开了,老板娘打着电话出来了。她每天都要出去收账。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老板娘前脚出厂,张勇毫不犹豫冲向那扇神奇的门。他像荒野里一条饥饿很久的狼凶猛扑向一只小猎物。近了,近了。小猎物在绝壁之上。诱人的猎物。他听到自己体内的狂喜爆炸。啊!他只看到美色,看不到深渊。
在他还没靠近时,一双女人的手从后面拉住了他。
“丢开!没你的事。”他粗暴地打掉她的手。她的手火辣辣地痛起来,却从后面抱住了他。她胸部的柔软和起伏像温柔的海,淹没了他。
屋里的空气很冷,他们的身体很热。那热被厚厚的冬衣阻隔囚禁。却阻隔不了体内的万马嘶鸣。是的,万马嘶鸣,要冲破身体的樊篱,纵横驰骋。他感到了皮肉的紧和痛,来一把利器吧。利器。他想起那年回家时嫂子握在手里切肉的菜刀。当时他很想变成嫂子刀下的肉,随她切碎。张勇突然松开了手。他恍惚起来,不知道手里抱着的是他嫂子或是另一个女人。他喜欢嫂子,一直都喜欢,但那是嫂子。也许从一开始就错了,不该滋生对嫂子的邪念。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欲念,却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他像过去逃离嫂子那样逃离开,走出了让他厌恶的工厂大门。他不知要到哪里去,只是走。踩着冻硬的水泥路,在呼呼的冷风里走。工厂,房舍被抛在后面,路旁的法国桐被抛在后面。辛辛苦苦的一年抛在了后面。他不怕吃苦。他希望用自己的辛苦换来房子和女人。女人,房子,无限地变大,像两座山旋转起来,越来越快,他被淹没其中。
找死呀!
一辆迎面而来的大卡车“吱嘎”一声,停在他面前,一个多肉的光头伸出车窗大声地骂。
卡车开走了,前面亮堂起来。大片的麦田和高高的杨树映入眼帘。他走出梦境一样看到了树顶上的喜鹊窝,眼睛湿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