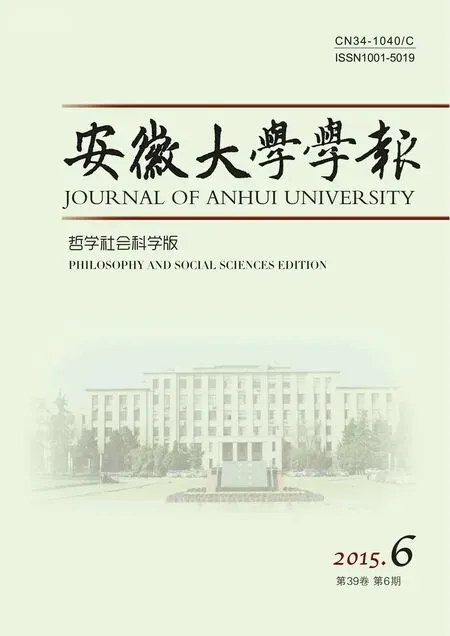史学和文学中的伽利略事件
凌曦
史学和文学中的伽利略事件
凌曦
继伽利略等人所开创的近代科学革命之后,启蒙运动进一步将唯理主义和科学主义变成全面统治人类生活的权威,思想界对此的反思贯穿这一过程,文学也以隐喻和象征的方式深思唯理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问题。本文通过释读德雷克的名著《伽利略》及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探讨唯理主义思想倾向的缺陷及脆弱性,并尝试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
德雷克;伽利略;布莱希特;唯理主义
“伽利略事件”是世界文明史上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之一。1633年,罗马宗教审判法庭以“重大异端嫌疑”的罪名判处伽利略终身监禁,此后三百多年伽利略一直背负着凭理性与科学反对教会和违背教义的罪名。直到1980年,罗马教会才承认,当年对伽利略的判罪是错误的。伽利略与天主教会之间的这桩公案似乎终于以教皇对伽利略的“平反”而告终,然而,由这桩公案引起的理性与信仰之争却并没有就此结束。伽利略之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带来对人类理性主义的顶礼膜拜,这一势头随启蒙运动的发展而愈演愈烈,人类历史进入科学至上的时代,理性主义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一股强有力的统治力量。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这样描述科学宰制生活的趋势:“苏格拉底之后……以前从未预见到的普遍的科学求知欲遍及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仿佛每一个稍具才智的人都有义务将科学推动到汪洋大海之中,并让他从此一去不返。……谁若看清楚了这一切,并且看见现代科学那令人震惊的高高金字塔,就不能不在苏格拉底身上看见所谓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漩涡中心”①Friedrich Nietzsche,Sämtliche Werk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Band 1,hrg.von G.Colli und M.Montinari,München/Berlin/New York: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80,SS.99-100.。
熟悉尼采思想的读者清楚,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借“苏格拉底现象”批评唯理主义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种种现代性问题。所谓“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漩涡中心”,便是指作为一种普世价值的唯理主义的思想倾向。尼采称这种过度抬高人类理性的倾向为“经过深思熟虑的妄念(tiefsinnige Wahnvorstellung)”,即相信“思想在因果律的带领下可以抵达存在的最深处,而且思想不仅能够认识存在,甚至还能够修正存在。这种形而上学的大胆推想被当作是科学的本能,带领科学一次又一次地到达其极限”②Friedrich Nietzsche,Sämtliche Werk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S.99.。观察我们今日的生活现实可以发现,尼采于19世纪诊断出来的文化“妄念症”不仅一直没有痊愈,病势反倒愈益沉重。如今我们正被一股强大的力量裹挟着落入一个科学至上的时代,科学和技术逐步夺取了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包括宗教信仰、情感及伦理道德的绝对统治权。
任何一种观念或理论都顺应一定的历史条件而产生,并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与此同时,与之相抗衡的力量也总是悄然滋生,并必然于或迟或早的某一刻爆发。唯理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同样符合这一规律,对它的反思从它诞生之日就已经开始。罗森(Stanley Rosen)认为,19世纪以来的哲学家们对启蒙运动的认识出现了显著分化,一边是马克思和孔德这些将人类幸福与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家,另一边则是被罗森称为“悲哀的理性”的阵营,组成这一阵营的有谢林、克尔恺郭尔、叔本华及尼采等人①参见罗森《悲哀的理性》,《启蒙的反思》,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7~190页。。19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学也对思想界反思启蒙的潮流做出积极回应。在启蒙文学之后,浪漫派的兴起便是以文学审美的方式进行的一次对理性主义的反思。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种种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学流派,更是在这条道路上做出了各种各样大胆的尝试。
17世纪的科学革命在理性主义夺取人类生活控制权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近代自然科学之父伽利略则是这一道路上的先驱者。本文将借助20世纪英国科学史家德雷克的伽利略研究专著《伽利略》及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的经典名作《伽利略传》,来考察20世纪史学和文学对科学主义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问题的反思。
一、被“误解”的伽利略
从1633年至1980年的300余年里,史学家们关于伽利略与教会关系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大多数都认为伽利略是一个站在科学与理性的立场上颠覆基督教信仰的“哥白尼学说狂热分子”。1980年,历史学家、伽利略研究专家德雷克(Stillman Drake)发表了他的专著《伽利略》,该书向世人公布了一个与传统史学中完全不同的伽利略形象,为科学界和宗教界审视伽利略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德雷克注意到,罗马教会对伽利略一案的审理疑雾重重,根据现有的文件判定伽利略有罪或无罪都难免得出草率的结论,而长期以来大多数史学家们正是这样做的。细致阅读伽利略的著述、通信以及保存下来的案件卷宗之后,德雷克注意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大量历史文献显示,伽利略是一个处事谨慎的人,他为什么会在并无必要的情况下,两次主动前往罗马与教会高层周旋?大多数德雷克之前的史学家们似乎都忽略了这个矛盾的事实,只有爱因斯坦以科学家的敏锐观察力注意到这一点。库兹涅佐夫的《伽利略传》中援引了爱因斯坦对伽利略的评述:
至于伽利略,我以为他与众不同。不能怀疑他热心追求真理——他比任何人都热心。但难以相信,一个成熟了的人会认为把找到的真理同唯小利是图的俗人相结合是件有意义的事。难道说这件事竟那么重要以致要他为它献出晚年的生命?!……他并无特别必要到罗马去同那儿的那些僧侣、政客作斗争。这种情景并不符合我对伽利略的印象——我认为这位老人内心富于独立自主精神。……我仿佛觉得用堂·吉诃德式的做法备鞍上马拿宝剑去捍卫真理是荒谬可笑的。②转引自库兹涅佐夫:《伽利略传》,陈太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97页。
德雷克的《伽利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伽利略确实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狂热者,但他的“狂热”却不是为了维护哥白尼学说和反对天主教。相反,伽利略的“狂热”恰恰是“为了天主教会的未来,为了使宗教信仰不致受到任何可能出现的科学发现的冲击”③[英]德雷克:《伽利略》,唐云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6页。。德雷克发现,如果从这个假设出发再次审视伽利略一案,那么围绕此案的许多疑问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德雷克还从有关伽利略的史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伽利略一案并不仅仅涉及神学和科学之间的冲突,当时在思想界占主流地位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伽利略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研究危及被哲学家们奉为至高无上的教条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家们无法在学术上反驳伽利略,便制造了借教会之手消灭敌人的阴谋。而伽利略恰
恰是出于对上帝的虔诚信仰,而分别于1611及1615年两次主动前往罗马,为避免教会与科学之间的裂痕而奔走。
德雷克认为,伽利略的几封信件对于人们了解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非常重要。第一封信是伽利略写于1615年的《致女大公克里斯蒂娜的信》。在这封信里,伽利略最为详尽地表达了他关于科学、理性及其与基督教关系问题的见解。
伽利略在信中提出“自然之书”那个著名的隐喻,将圣经和自然现象都归于上帝的最高智慧之作。他引用古代教父德尔图良的话来解释自然现象与圣经之间的关系:
我们断定,上帝之可知首先是借着他大工所造的自然,然后还主要是借着他明言所传的教训。①德尔图良:《反马吉安论》(Adversus Marcionem)第2卷。此处转引自G.Galilei,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Drake,New York:Doubleday&Company,Inc.,1957,p.183.
由于逍遥学派的哲学家们挑动教会人士以《圣经》的权威压制自然科学,伽利略感到很有必要在科学与神学之间划分界限。他在信中多次援引奥古斯丁的《〈创世纪〉释要》论证道,解读自然这本大书和圣经的工作分别属于自然科学家和神学家,这两个工作所研究的对象不同,所用方法也不同,因而既没有必要也很难相互融合,尤其是神学家们不可以假上帝之名干涉科学研究的自由。在他的巨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序页上,伽利略警告神学家们,如果神学家将今日的圣经解释作为衡量科学研究的标准,那么他日科学就可能反过来推翻今天的神学:
神学家们,请注意,在你们企图把关于太阳和地球是固定不动的命题说成是有关信仰的问题时,这就存在着你们总会有一天判定某些人为异端分子的危险。那些人声称,地球不动,而太阳在改变位置;我说,终于会有一天在物理上或在逻辑上证明地球是在运动而太阳则是不动的。②[意]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序页。
伽利略看到,对神学和科学不加区分的做法会带来它们之间无止境的斗争。不过他同时又认为,科学与神学虽然应该保持相互的独立性,但却不可能彼此矛盾,因为二者研究的对象都来自同一者,即全能的上帝。作为上帝创造的两本大书,自然现象必然透露圣经的真意,而圣经的真意也必然与自然的真实状况一致,因为两个真理不可能相互抵牾。那么,如何解释神学家声称自然科学的结论与圣经相悖的现象呢?伽利略在信中阐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原则:要么是神学家对圣经的解释发生了偏差,要么是理性的有限性阻碍了科学家发现真理的目光,而上帝的智慧绝对不容置疑。在这个问题上伽利略表现得完全是一个热诚的天主教徒,他再次援引了奥古斯丁的观点:
世上的智者们论及自然的(physical)问题时,他们的观点无论如何不可能与圣经相悖,因此,如果学者们的书中有任何与圣经相悖之处,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那都是谬误。……让我们保持对主的信心,在主之中保藏着无限的智慧宝藏。如此,我们便不会迷失于谬误的哲学的陈词滥调,也不会被伪宗教的迷信所吓倒。③奥古斯丁:《创世纪释要》(De Genesi ad literam)卷Ⅰ,此处转引自G.Galilei,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p.194.伽利略认为,谬误的哲学和伪宗教产生于对自然和圣经的错误理解。历史学家常常批评伽利略以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对圣经的解释提出批评是不恰当的行为。但我们应该看到,伽利略本人一直坚持自己作为思想家的身份。在《致克里斯蒂娜的信》中,伽利略努力处理好神学与科学的关系,这已经远远超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的职责范围。从《致克里斯蒂娜的信》的内容来看,伽利略当时对一种能够最好地安置神学与科学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哲学充满向往。这一新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人类理性和科学的自由认识。
受17世纪经验主义及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逻辑理性与观察、实验分别是伽利略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理论的两个来源。在《致克里斯蒂
娜的信》中,伽利略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科学理论。一种是来自于人的感官的观察及科学实验,另一种则依靠人的思辨能力即逻辑理性而获得。伽利略认为,后者只能是不断向真理逼近而又不断被新的假说所取代的科学推论,因为永远存在人类理性所无法达到之处,这正是人类永远有必要对上帝保持虔敬的原因。
在写于1641年的另一封信中,伽利略进一步谈到科学及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伽利略说,如同他认为哥白尼的假说不完全与真理相符一样,他也同样断定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们的推论不正确,因为他们都没有超出人类推理的范围。我们看到,在伽利略那里,科学还没有染上启蒙运动之后那种绝对主义的妄想狂症状。伽利略承认有一些东西是人类理性永远不可企及的,并且确信人类只能永远行进在向这个不可及之处靠近的道路上。对于他来说,这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伽利略梦想着以一种新哲学代替亚里士多德主义,新哲学必须能将科学限制在信仰的范围之内,并且能与科学与神学都保持和谐关系①[英]德雷克:《伽利略》,第160~161页、159页。。显然,建构新哲学的梦想在伽利略生前落空了,那么,伽利略之后,这种“更好的”哲学建立起来了吗?
二、伽利略之后的唯理主义妄想症
20世纪伟大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他的戏剧《伽利略传》中把伽利略描述为一个唯理主义及绝对的科学自由的狂热信徒。如果德雷克的《伽利略》还原了伽利略的真实面貌的话,那么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则无疑是对历史上的伽利略的再一次误解。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尽量保留了史料的真实性,但剧中的伽利略从精神气质而言是一个发生了“时代错位”的人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被一个启蒙思想家所取代,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文艺复兴之后、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至上及唯理主义价值观的代言人。因此,解读这个戏剧的目的不是试图还原伽利略形象的历史真实,而是对启蒙运动和唯理主义的一次反思。
《伽利略传》一共有三个版本,现在流行的美国版产生于1945/46年间,是布莱希特为该剧在美国上演而修订的版本,当时正值广岛事件爆发,因此美国版增加了第十四场结尾处伽利略的自我批评,布莱希特在那里借伽利略之口剖析自然科学的目的和自然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学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等问题。
全剧开始于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清晨”,伽利略在自己家中偷偷研究并向学生安德雷亚秘密传授日心说。这位自然科学家相信新知识将不断带来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科技的进步不仅能够极大地改善人类生活,而且将取代基督教信仰向人们提供的“虚假的”慰藉。这位启蒙家甚至还大胆地告诉学生:知识将掀开王侯和高级教士的绣金长袍,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腿和我们的腿没有两样;知识甚至能够让我们了解,诸天之上空空如也,并没有什么主宰万物的神灵。这位启蒙家用科学和技术置换了民众心目中的神,将牢不可破的上帝信仰变成了对机器的崇拜。
布莱希特笔下的启蒙思想家伽利略相信科学能够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这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基于对人类理性的坚定信念。当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证实了哥白尼的学说,他的好友萨格雷多警告他要留心宗教法庭的危险时,伽利略争辩道:当初哥白尼的学说仅仅只是一个未经证明的数学推论,而现在他可以用望远镜让人们亲眼看到证据。伽利略反问朋友说: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怎么能够拒绝证据的诱惑力呢?“思考是人类最大的乐趣”,“我相信理智对人拥有温和的威力。他们不可能长久地抗拒这股力量”。显然,剧中的伽利略离开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的威尼斯共和国并坚持前往佛洛伦萨的原因,并非追求真理和传播真理的责任感或英雄气,而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坚固信心:“我相信人,这就是说,相信人的理智!如果没有这个信念,我甚至连早上从床上爬起来的力量也没有。”②[德]布莱希特:《伽利略传》,《布莱希特戏剧选》下册,潘子立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34页、33页。剧中的伽利略多次表达了对理性的坚定信念。
布莱希特的巧妙之处在于,用艺术隐喻的方式深刻而生动地剖析了唯理主义思想倾向的荒诞和虚弱之处。观众看到伽利略的理性主义是与感官享受紧密联系的①关于伽利略贪图美食享受这一点,在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例如在库兹涅佐夫的《伽利略传》中就提到,伽利略在被判终身监禁后还曾写信要求订购美酒,这被某些史学家当成是伽利略的“伊壁鸡鲁式的贪欢取乐”的性格的证据。参见库兹涅佐夫《伽利略传》,第334页。。我们看到剧中的科学家让学生为他擦背,贪爱葡萄美酒,对美味的鹌鹑赞不绝口并惦记着往鹅肉里面“加点麝香和几个苹果”。圣职部宣布伽利略的发现为非法之后,伽利略沉默了整整八年。但是,得知科学家巴尔贝里尼被提名为新教皇的继承者时,伽利略立即旧病复发,迫不及待地要重新开始日心说的研究。“知识将成为一种热情,研究将成为一种乐趣(Wohllust)”②[德]布莱希特:《伽利略传》,《布莱希特戏剧选》下册,第90页。,观众看到,当这位人类理性及知识的推崇者做出如此热情洋溢的预言之时,他的手里恰好端着一杯西西里的陈年葡萄酒——我们不得不赞叹这个寓意丰富的舞台形象:对布莱希特笔下的这个伽利略而言,知识以及科学研究同美酒一样,是一种感官享受的“乐趣”。“乐趣”这个词在原文中使用的是Wollust③B.Brecht:Leben des Galilei,Berlin:Suhrkamp Verlag,1969,S.106.,这个德语词汇的意思是:感官的和性的欲望。在剧中其他地方,伽利略提到科学研究的欲望时,还使用过另外两个词汇,Lust和Vergnügen,两者都含有肉体享乐之意。这些词汇由理性主义者伽利略口中道出,形成强烈反差,然而这些词汇恰恰是理解全剧的关键,是带领读者走近唯理主义者伽利略真实面相的阿里阿德涅的线索。
在《伽利略传》中,还有另一个与感官享受相关的文学隐喻,这首先在第七场中借红衣主教巴尔贝里尼之口道出,巴尔贝里尼称理性的求知欲为“会传染人的疥疮疾患”④[德]布莱希特:《伽利略传》,《布莱希特戏剧选》下册,第67页。。伽利略也患有同样的疾病,而且病得很重。在第十四场里,伽利略向安德雷亚坦白道,他偷偷抄写并保存《对话录》的副本并非有计划行事,而是受一种不可遏制的研究欲⑤在《关于〈伽利略传〉的解释和排练说明》一文中,布莱希特称“这种研究欲几乎同性欲一样有吸引力或控制力”。参见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342页。的驱动而做出的本能反应。伽利略称这种研究欲为“根深蒂固的恶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根除的”⑥[德]布莱希特:《伽利略传》,《布莱希特戏剧选》下册,第124页。,就像疥疮的刺痒令人难以摆脱一样。
如果我们拿布莱希特笔下的伽利略与尼采《悲剧的诞生》中的那个苏格拉底形象对比,将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二人都是逻辑理性发达的理论性的人。不过二者之间又有本质的区别:尼采的苏格拉底是一个本能软弱而逻辑理性过度发达的怪物⑦Friedrich Nietzsche,Sämtliche Werk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SS.90-91.,而布莱希特的伽利略却是将理性与肉体的本能混为一体的,“重要的是工作对他来说是一种感官上的满足。对伽利略来说,以一种优美的姿势摆弄仪器就是一种享受。他的很大一部分感官上的要求是精神方面的东西”⑧[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第357页。。在《伽利略传》中,这一徉谬现象正是理解伽利略这一形象的关键点。
随着剧情的发展,一个疑问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观众的脑际:在鼠疫中不顾生命安全,坚持留在疫区继续从事研究的伽利略,为什么后来会在宗教法庭的刑具前收回自己的学说?贪图感官享受的伽利略形象以及疥疮刺痒的隐喻为我们提供了这个疑问的答案:把伽利略留在疫区,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研究的,是这种类似于感官享受的科学研究欲,一种如疥疮刺痒一般无法克制的本能。感官享受通常并不诉诸理性,而是诉诸快感。但在《伽利略传》中,伽利略的理性是与感官享受连接在一起的,是类似于疥疮刺痒一般的本能反应,因此伽利略的理性接受快感的控制,而不具有更高的目标和价值。关于自己的研究欲,剧中的伽利略这样坦白道:“最要命的是,我知道什么,总想一吐为快,像
正在恋爱的人一样,像醉汉,像叛逆者一样”。在另一处他这样解释自己的科研工作:“我不过写了一本讲天体力学的书,这就是一切。至于从里面能够引申出什么,或不能引申出什么,同我毫不相干”①[德]布莱希特:《伽利略传》,《布莱希特戏剧选》下册,第80页、104页。。至此,我们终于揭开蒙在科学家伽利略的“理性”之上的面纱——科学研究不过是伽利略在本能驱使之下的一场自我满足的游戏,它从一开始就并不承载为民众谋福祉的社会责任。伽利略在宗教法庭上的背叛便是这种绝对的科学自由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三、新哲学的梦想
在《伽利略传》的第十三场里有两句台词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伽利略在宗教法庭悔罪之后,对老师深感失望和愤怒的安德雷亚叹息道:“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则如此回应道:“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②[德]布莱希特:《伽利略传》,《布莱希特戏剧选》下册,第116页、117页。。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唯理主义者伽利略思想发生巨大转折的时刻。伽利略原本坚信理性拥有无人能够抗拒的威力,足以带领人类走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并永不偏离轨道。然而,宗教法庭摧毁了启蒙家对理性的乐观主义认识,使他认识到在纯粹的科学研究以外的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伽利略在这里所悲叹的不是他个人的悲剧命运,而是对人类理性的理想主义观念的失败,是以纯粹的知识和无涉价值观的技术进步为目的的唯理主义的失败。
历史学家们研究伽利略时关注的主要是科学与宗教冲突的问题,布莱希特的戏剧则是从科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这个角度审视唯理主义的不足之处。当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之后,布莱希特要让伽利略再次走上历史罪人的审判台——“原子弹无论是作为技术现象还是作为社会现象,都是伽利略的科学成就以及他背弃社会斗争的产物”③[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第342页。。布莱希特批评拒绝承担现实政治责任的“纯粹的”科学研究,这一思想集中出现在第十四场中伽利略的自我批评一段戏中。近十年的软禁生活使伽利略慢慢认识到:“科学的唯一目的,在于减轻人类生存的艰辛”④[德]布莱希特:《伽利略传》,《布莱希特戏剧选》下册,第129页。,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科学必然与两种斗争都有关系:一方面是用知识之光去照亮自然之奥秘的斗争,另一方面是挣脱强权统治的社会斗争。科学工作需要英雄般的勇气,因为后一种斗争很有可能将科学家拖入到政治斗争的危险漩涡之中。科学家必须承担科学研究的社会责任,他们应该像医生们遵守希波克拉底誓约一样,发誓将他们所有的知识仅仅用于为人类谋幸福的事业。伽利略的自我批评可以说是对全剧的主题,即现代自然科学的目的和科学家的责任等问题的一次总结,我们甚至也可以将它理解为启蒙以来的技术和工具理性的一次自我反思。
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中为现代唯理主义的危机提出一个修正方案,即人类理性的活动不能仅仅诉诸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而必须带有价值的观照,也就是说,必须抱持对人类处境的同情并承担对现实政治的责任。唯有如此,理性主义以及作为其产物的科学和技术才能担负起为人类谋福祉的使命。倘若我们追问,科学和理性应该到哪里去找回同情和责任这些德行,那么,回忆一下300多年前伽利略的时代所发生的那一切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提示。当17世纪的神学家借上帝的权威压制科学时,他们就丧失了对最高智慧的虔敬而将自己等同于上帝。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家们假理性之名凌驾于宗教之上时,遵循的就是同样的逻辑。失去了对最高智慧的信仰的科学像一台失去控制的机车,凭着唯理主义的本能,疯狂地冲向不可知的前方。或许我们来到重思伽利略的那个新哲学梦想的时刻了。
责任编校:余 沉
B5
A
1001-5019(2015)06-0022-06
凌曦,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广东广州 510275)。
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6.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