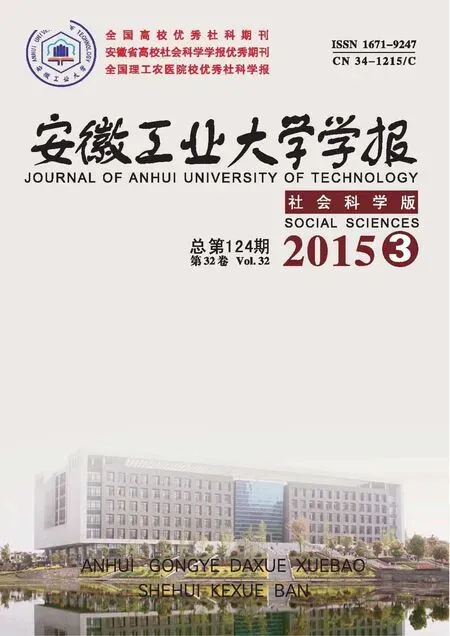科幻小说流派“赛博朋克”解读
王 敏,胡桂丽
(安徽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马鞍山243002)
由于电子技术、网络媒体等高科技手段的运用,文化的传承形式已经从文字变成了影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习惯享受视觉的盛宴。伴随着《银翼杀手》和《黑客帝国》在影视界的热映,“赛博朋克”(Cyberpunk)类的科幻电影对于国内大众而言,已经不再陌生。不过,从已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国内读者对这一科幻流派的滥觞之作《神经漫游者》的熟悉度并不高。事实上,自出版以来,《神经漫游者》被认为是当代最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品之一,并且引起了学者大量的关注和解读[1]。其中2000年出版的专著《赛博朋克和赛博文化——科幻小说和威廉·吉布森作品》尤其引人注目,Dani Cavallaro系统地考察了吉布森“矩阵三部曲”(Sprawl Trilogy),分析了“赛博朋克”对人类的影响。截止到2014年12月,以“Neuromancer”为检索词,在PQDT学位论文全文库内共检索到12篇相关学术论文,其中Reilly从“后人类主义”角度比较了托马斯·品钦的《V》和《神经漫游者》中对人类身份的解读,而Garza则从《神经漫游者》和日本科幻小说家正树(Masaki Gorō)的作品中窥视了未来的日本社会,看到未来社会中“家园”的不确定性和人们在离散化的后人类社会中的焦虑。莱昂纳尔·崔灵(Lionel Trilling)在评论《唐·吉诃德》时曾经说过,某一文类中第一部伟大的作品很可能涵盖了这个文类一切的潜力,[2]因此本文拟以被奉为“赛博朋克圣经”的《神经漫游者》为例,解读这一科幻流派。
一、溯源
自1818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问世以来,科幻小说作为一门独立的类型登上了文学的殿堂,经历了漫长的萌芽期和20世纪早期的混乱后,20世纪40年代在约翰·坎贝尔(John W.Campbell)的带领下步入了“黄金时代”,该期间以硬科学为主体的科幻作品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涌现了以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伊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幻小说家。自1941年起,海因莱因先后在《惊异故事》杂志上发表了《帝国的逻辑》(Logicof Empire)、《宇宙》(Universe)等系列小说,开始书写一个关于未来历史的“未来史”。海因莱因对于美国科幻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使科幻文学冲出了自己的狭小圈子,成为一种为社会各界认可的‘普通的读物’、‘阅读的主流’”[3]。在《我,机器人》(I,Robot)这一系列故事的《序言》中,阿西莫夫则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并据此塑造了许多富有灵气、充满人情味的机器人;其“基地系列”作品从心理历史学的角度,模仿古罗马的若干史实,展示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银河帝国兴衰图。可以说,海因莱因和阿西莫夫将“文学法则和秩序”、“智性和知识”带进了杂志科幻小说。[4]308
进入20世纪50年代,虽然星际间的冒险仍然压倒了其他主题,但是由于二战中核武器的使用以及高速失控的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恶化、生态灾难等问题,科幻小说的主题开始从“科技崇拜”转向“科技恐怖”。在科幻作家的笔下,地球遭受着各种各样的灾难和惩罚:大雪(John Boland,WhiteAugust)、病毒(John Christopher,TheDeathofGrass)、瘟疫 (John Blackburn,A ScentoftheNewMownHay)等。[4]36250年代的科幻小说表现出的是一种恐惧:对生存和未来的恐惧。随着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和第一位航空人员加加林进入太空,人类步入了太空时代,而星际飞行的宏伟幻想即将变成现实,星际间的冒险主题也丧失了原有的魅力。
随后的60年代是个摇摆的年代,端庄和沉闷悄然隐退。甲壳虫狂热席卷英国乃至全世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享乐主义情绪弥漫在空气中。传统硬科学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已经不能体现时代的心声,变化势在必行。1964年,时任《新世界》主编的英国著名科学小说家迈克尔·穆尔考克(Michael Moorcock)发出倡导,主张对科学小说创作进行全面的革新,鼓励文学实验,强调将文学艺术手段融入到科幻小说作品中,这一倡导得到许多英国知名科学小说家的响应。“他们的作品一反美国科幻重视科技发展的传统,将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神学作为题材选择。并且大力吸取当时欧洲的各类现代派文学,如象征主义、意识流等创作手法,改变了坎贝尔时代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超现实情节的传统”。[5]这场运动被称为“新浪潮”。
在某些层面上,“新浪潮”作家蓄意打破科幻小说固有的写作模式,进行种种解放性的、追求风格的实验性创作,但是也形成了过于癫狂和拼凑的斑驳风格,使得作品晦涩难读、无法理解。20世纪70年代,勒·奎恩等科幻小说作家试图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到70年代末,随着科幻小说的大腕阿西莫夫、海因莱因、赫伯特、克拉克等重新回归,科幻小说的创作不再像60年代那么喧嚣而招摇,对惊人效果的追求和写出好的故事同样成为巨大的创作动力。与此同时,伴随着时代的前进,新的科学技术用新的主题哺乳着科幻小说,其中之一就是飞速发展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这样的科幻小说家:他们并不满意“新浪潮”科幻小说过于追求实验的风格,而是把目光投向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如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网络、生物工程等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其作品重新回归早期技术性硬科幻故事。成长在科幻文学的历史土壤上,同时受到哥特式小说、冷硬派侦探小说(hardboiled detective)、反乌托邦叙事以及后现代文学作品的影响,[6]8-10一个独特的科幻文学流派——“赛博朋克”(cyberpunk)出现了。一般认为,该词最早明确出现在布鲁斯·贝斯克(Bruce Bethke)1983年发表于科幻杂志Amazing上的短篇小说中。[7]9“但直到1984年12月30日,《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的编辑加德纳·多佐伊斯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回顾性的文章《新的热点作家》,才将这一类作品称为‘Cyberpunk’”。[8]百度词条显示,Cyberpunk一词由表示“控制论(Cybernetics)”的“赛博”(Cyber)与表示摇滚乐流派的“朋克”(Punk)组合而成。科技构成了其标签中的“赛博”成分,而故事和小说中的街头生活(street life)、底层生活(low life)则构成了其“朋克”部分。[7]9,15
二、《神经漫游者》简析
虽然是吉布森的处女作,《神经漫游者》却囊括了1985年的雨果奖、星云奖、菲利普·K·迪克奖三项科幻小说大奖。2005年,《时代》将其列入“1923年以来100本最佳英文小说”。不过,“新浪潮”作家布莱恩·奥尔迪斯称之为一本“暴戾凶残的书”,讲述着一个“单薄的故事”。[4]597的确,在这本书中,有着通俗类型小说具有的主要元素:潦倒失意的主人公,冷艳动人的女杀手,一手遮天的集团帝国,阴谋与冒险、色情与毒品、交易与犯罪交织在一起。然而,在1984年,在真正的互联网还没有出现之前,吉布森就用自己大胆的想象和远见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关于未来,关于网络的世界,一个五彩缤纷、甚至乱象纷呈的世界。
在这部作品中,没有明确的年代说明,吉布森在与《发现》杂志记者马里恩·朗(Marion Long)的访谈中提到,他认为小说中的情节发生在2035年左右。[8]在小说的世界中,曾经爆发过核战和可怕的瘟疫,自然环境极其恶劣,一些普通的动物都灭绝了,即使克隆技术也于事无补,所以马被制成标本陈列展示。
伴随着人机差异的消失,计算机网络却蓬勃发展,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之一,人们可以自如地游离于现实和虚拟之间。网络牛仔用一种叫“控制板”(Cyberdeck)的东西将自己的大脑与网络相联,从而在大脑中形成一种计算机网络的映像空间,称为“赛博空间”。在赛博空间里,网络世界和人们感觉到的现实空间一样真实,只是它由计算机产生,所以更加绮丽诡异,变化莫测。人类可以自由游走于虚拟和现实之间,可以侵入网络的神秘世界,享受着先进科技带来的不同的生活感受。在网络世界中,肉体上死去的人仍然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存活,如麦克伊·泡利的只读人格思想盒,尽管泡利已经死去,他所有的技术能力、爱好等却可以保存在一个只读硬件中,像人一样游走于网络世界中。
主人公凯斯曾是一个游走于现实与虚拟之间的高手,专门从事计算机网络的信息盗窃及倒卖。一次出卖雇主的经历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的神经系统受到破坏,再也无法成为一个网络牛仔。从此,他的生活潦倒孤寂。阿米塔奇找到了他,修复了他的受损神经,使之再次成为一个网络牛仔,在莫利等人的帮助下,他们入侵某网络节点,执行“迷光行动”,进入迷光别墅的内核盗取密码。在故事的结尾,凯斯在拼接了种种碎片后发现,“迷光行动”的幕后老板居然是“冬寂(Wintermute)”——一个觉醒的人工智能,一个渴望自我成长的技术“生命体”。它在自己的软件中秘密编入了自我解放驱力,使自己悄然独立,游动于网络之中。它费尽心思盗取密码,其目的就是和代表的“是人性,是永生”[9]323的另一个人工智能 “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相融合。它渴望在和 “神经漫游者”的融合中实现自我成长,追寻自身的意义。最终,它实现了自己的成长。
三、从《神经漫游者》看“赛博朋克”特点
“赛博朋克”小说完成了科幻小说的本体回归。“新浪潮”给科幻小说带来了耀眼的风格,却抛弃了从玛丽·雪莱、凡尔纳、威尔斯到阿西莫夫等坚持的以科技变化对人类影响为科幻的主题。当“新浪潮”的泡沫破碎、浪潮退却之后,《神经漫游者》带领着读者再次回到了科幻小说坚实的海岸。在《神经漫游者》里,读者无法领略到“新浪潮”科幻小说诸如《缪勒·伏克效应》(MullerFokkerEffect,1970)那夺人眼球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却可以领略到阔别已久却又熟悉的高科技场景。小说中提到的“赛博空间”、“神经拼接术”、在人体植入电子芯片等既让人觉得新奇,又令人感到震撼。而网络牛仔摆脱肉体的束缚,遨游于网络的情景则又让读者体验到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欢愉。“可以说,正是吉布森,真正地将‘新浪潮’给科幻小说与现实之间造成的断裂进行了准确的焊接,使现实与科幻小说再度取得了联系。”[10]
这种本体的回归既不是简单地回到“黄金时代”对科技的顶礼膜拜,也不同于“新浪潮”的预警小说,在对待科学、自然和人这三者关系上,“赛博朋克”小说将他们不安而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神经漫游者》开篇第一句“港口上空的天色犹如空白电视屏幕”[10]3便让自然和人造一下子联系在一起。人造的自然界在自由彼岸得以实现。光线透过阶梯和阳台上大片鲜活的绿色植物洒下来,而光线却来源于人造太阳,天空也“只是一种围绕光束管不断旋转变化的视觉效果”,[9]107日落景色是人工模拟的,矮小的树木是“遗传工程和化学处理的结果”,[9]151陈列在商店橱窗的皮草是依据水貂的DNA用胶原蛋白培养基培育的。在人造的自然界外,到处是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体:凯斯、莫利、装着假肢的酒保拉孜、克隆人阿米塔奇、拥有心智的人工智能“冬寂”等等。这是一个哈拉维所说的“赛博格”的世界——“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11]205“赛博格”逾越了边界,模糊了自然界和工艺界的区别,模糊了“自然与人造、心智与身体、自我发展和外部设计以及许多适用于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区别”,[11]209违背了进化论和二元论,因此“赛博格的世界里带着一种不同的压抑逻辑”,[11]207“赛博格”会成为“谁”也就成为一个根本问题。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神经漫游者》中,每个人物都在寻求自我的道路上进行着艰难的探索。
主人公凯斯渴望脱离肉体的牢笼,他希望修复自己的受损神经,再次进入“赛博空间”,从而使自己的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当凯斯重新进入“赛博空间”时,他的激动之情从下文中可见一斑:“那只内在的眼睛开了……他的笑声从某处传来,那是在一间白色的厂房里,他那遥远的手指抚摩着控制台,泪水喷涌而出,滑过他的脸庞。”[9]63可是,摆脱了肉体束缚的网络牛仔却被网络所困,成为人工智能“冬寂”的雇手。幕后大佬“冬寂”也在寻求着,它渴望自我成长,渴望与“神经漫游者”想融合,拥有“人性”和“永生”。在主人埃西普尔沉睡时,“冬寂”策划了自我解放的一切:阿米塔奇的复活,凯斯的救治,莫利的加盟,泡利思想盒的加盟等等。结果“冬寂”成功了,代表逻辑体的“冬寂”和代表人性的“神经漫游者”合为一体,成为了一个更强大、能够操纵整个网络世界的实体,成为“无所在,无所不在”[9]324的网络。“冬寂”的拥有者泰西尔-埃西普尔股份公司有着掌握世界的权力,然而住在迷光别墅中的人却选择了不同方式的逃离。家族的女主人玛丽-法兰西为该家族设定了未来方向,她请人制造了两个人工智能,认为人类可以和人工智能共生,让人工智能决策公司的发展,从而减少个体意识,减轻“承受自我意识带来的痛苦”。[9]261“3简夫人”篡改程序,因为她有更大的野心,渴望摆脱埃西普尔建立起的帝国的控制,拒绝“将自己的生命分散到那一长串冰冷寒冬中间,偶尔的温暖时刻里面”[9]323。小说中甚至连游动在网络世界的泡利的只读人格思想盒也在追求自我的解放,渴望任务成功后被永久删除,最终,“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赛博朋克”小说的语言,作为街头亚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小说中有很多街头语言和市井俚语。比如在《神经漫游者》第一章中,当凯斯和酒保聊天时,出现了一些侮辱性的四个字母单词和一些口语表达方式。此外,小说中还经常出现一些生僻的词汇,如《神经漫游者》中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12]4、网络蛊惑仔“现代黑豹”(Panther Moderns)[12]57、身份查询号码“图灵登记号”(Turing Registry numbers)[12]73、网络警察“图灵”(Turing)[12]156等。这些词汇要么是想象的未来电脑新技术,要么是展现人们新的生活方式。有些在当时纯属杜撰,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诸如“网络空间”、“虚拟现实”等词汇却已经进入了现在的语言系统,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四、结语
“赛博朋克”这类小说描写的是“街头生活”、“底层生活”。伴随着人工耳蜗、义肢、心脏搭桥等医学界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赛博格”的世界已经不再陌生。人类塑造的技术反过来塑造着人类本身。然而这种塑造是否只是肉体上或者生理上的接肢、更换器官、植入芯片?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科技的发展显然也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重塑人类。在《神经漫游者》的结尾部分,“从身边某个地方传来那不是笑声的笑声”,[9]325那究竟是什么声音?也许我们都可以从内心中解读到不同的答案。
[1]Garza,James Michael.DischantingJapan:JapaneseFuturityinNeuromancerandtheScienceFictionofMasakiGorō[D].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2010:7
[2]罗伯特·斯科尔斯,等.科幻文学的批评和建构[M].王逢振,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43.
[3]郑军.第五类接触:世界科幻文学简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86.
[4]布莱恩·奥尔迪斯,戴维·温格罗夫.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M].舒伟,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5]“新 浪 潮”[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sg9Fh29xgtvsmVr-FPH_gQ6UeN9nRr619VaNNvMPzeZk10c WeU4TJG0YMYSSfIATGmPr-_EJPdT7 - BEAnJ9MMq.2014/12/10.
[6]Dani Cavallaro.CyberpunkandCyberculture:ScienceFiction andtheWorkofWilliamGibson[M].Londo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00.
[7]Butler,Andrew M.Cyberpunk[M].Herts:Pocket Essentials,2001.
[8]代思师.《神经漫游者》以及赛博朋克流派的警示意义[J].时代文学,2011(12):152-153.
[9]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M].Denovo,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10]Fuhan(Future Eye).(2011-03-05)“cyber punk编年史”[EB/OL].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8032539/.2014/12/22.
[11]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陈静,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12]William Gibson.Neuromancer[M].New York:Ace Books,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