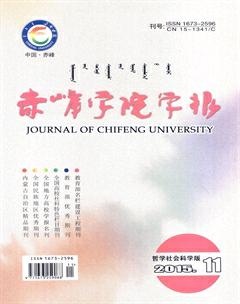试析北宋哲宗“绍述”之前的尊崇“祖宗之法”
刘婷
摘 要:祖宗之法历朝历代都有,而北宋皇帝尤其尊崇祖宗之法,将祖宗之法一以贯之,成为北宋的政治特征之一。终宋一朝,士大夫地位较高,他们不再唯唯诺诺于君王,而敢于直言进谏,这种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宋太祖所立“不杀士大夫”誓约这一祖宗之法,它对于防止皇帝个人独裁,营造较为开明的政治风气,推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而到了北宋哲宗“绍述”后,祖宗之法渐被奸佞之人利用,成为他们党同伐异的工具,因此走向反动。故将主要论述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以及哲宗元祐年间的尊崇“祖宗之法”并以宋太祖“不杀士大夫”誓约为例。
关键词:北宋政治;祖宗之法;“不杀士大夫”誓约;“共治天下”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039-05
一、学术史
有关赵宋祖宗之法问题,学术界目前很难说探讨的比较充分,近年来以邓小南女士的专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1]为代表成果,该书以一种政治文化的理念深刻剖析了祖宗之法对北宋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是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一大亮点。台湾学者黄宽重评价该书:“不仅是理解宋朝政治特性的主要线索、整体把握宋代政治发展的主要课题,更是近年来对宋代政治与文化透析最深、最具创见的学术专著。”邓女士还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以一章节<“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宋>阐明了北宋各种政策包括重文轻武、尊重士大夫、守内虚外、强化中央削弱地方权力等,都体现了北宋创立者“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统治理念。日本宋学研究者平田茂樹《宋代政治结构研究》,其中一篇文章《日本宋代政治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也提到了政治文化问题,认为“祖宗之法”几乎在整个宋代发挥作用,奠定了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政治基调。
邓广铭先生《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2]一文以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了宋朝家法从创立到形成的过程,并认为抵触宋朝家法是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但笔者对此不甚赞同,因为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情况略有不同应区别对待。邓小南论文《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以大量史料证明祖宗之法确实在即位的各个君主决定政策过程中起很大作用。
而有关宋太祖是否立“不杀士大夫言官”誓约[3]及誓碑的研究,最早是民国时期的张荫麟先生。他认为太祖有关誓碑的故事仅见于题名陆游的《避暑漫抄》,故推断“誓碑之说,盖由《北狩见闻录》所载徽宗之寄语而繁衍耳”,而且认为“北宋大臣虽不知有此约,然因历世君主遵守惟谨,遂认为有不杀大臣之不成文的祖宗家法。”最近几年,张希清在《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誓约考论》一文中,举大量事例论证了宋太祖誓约确有其事,该文章亮点是指出宋太祖虽是武将出身,但不是嗜杀之人,为人仁厚,以此来说明宋太祖立“不杀士大夫”誓约并不是偶然的。笔者认为此文是迄今对该问题论述最透彻全面的文章。
关于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研究,余英时专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精辟分析了北宋建立之后,士大夫们要求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他们在回向“三代”思想指引下,以宋学取代汉代经学。该书使笔者对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如政治主体意识、“士”的政治地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二、绪论
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制社会,“行先王之教”“奉先王之制”的理念,自先秦时代即广泛存在并流传。《礼记·大传》有记载:“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4]如汉朝以“孝”治天下,“奉祖宗庙”一直被视为继嗣帝王的头等要事。元平元年(前74年)四月,昭帝去世而无子嗣,霍光等人先立昌邑王刘贺后又奏请太后废之,代之以武帝曾孙刘病已,理由是“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宗庙,子万姓,当废。”[5]唐朝以唐太宗贞观之时的律令、法度为治国蓝本,唐武宗拒绝回鹘可汗“借城”之请的《赐回鹘书意》说“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业,常怀兢畏,岂敢上违天地之限,中墮祖宗之法。每欲发一号、施一令,皆告于宗庙,不敢自专。[6]可见作为儒家礼制的核心—祖宗崇拜的原则与实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小南女士《“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一文以唐至宋的发展变化,看出赵宋皇室的正家之法对国法的影响,所以赵宋祖宗之法才可同义于祖宗家法。凡事举述“祖宗家法”(特指太祖太宗创立制所贯彻的精神及其定立的诸多法度),就是说大到朝廷的理论依据,小到任用官员、确定则例都按祖宗的既定方针办,成为赵宋的政治特征之一,也正是在宋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被士大夫普遍推崇,家国一体得到认定。宋太祖所立“不杀士大夫”[7]誓约这一祖宗家法最早见于南渡官员曹勋的《北狩闻见录》:
徽庙圣训曰:“如见大王,但奏有可清中原之谋,悉举行之,无以予为念,且保守宗庙,洗雪积愤。”又宣谕曰:“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8]
后世许多史著也都有提到,如《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其中最详细的记载莫过于南宋陆游的《避暑漫抄》: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携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或许陆游的记载过于详细,故后人怀疑其真实性,如杜文玉的文章《宋太祖誓碑质疑》谈及此点。时人黄震对宋太祖厚待文臣给予较高评价:“古者士大夫多被诛责,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始终有恩矣。”[9]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其阐论礼制部分有《宋朝家法》一条: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10]
同一时期的王夫之在《宋论》中也有指出: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二、不杀士大夫”[11]
这些都说明不管是本朝之人还是后世人都是从心理上认可此誓约的。故笔者认为藏于太庙的宋太祖誓碑年代久远,也许无从考证,但北宋确有一条不轻杀文臣的不成文之祖宗家法在流传。北宋历代君主也都贯彻了“不杀是士大夫”誓约这一家法,不轻杀文臣,从而营造了较为开明的政治风气,同时士大夫也以此誓约为护身符,不断争取自身权利,从而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推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三、太祖至哲宗元祐年间的祖宗家法
(一)太祖朝的初创
北宋一朝特别优待士大夫,主要是由于北宋创立者对于唐末五代动乱的反思,不再信任武将,而开始重用文臣,出现如“宰相须用读书人”[12]、“事业付之书生”[13]等观念,更有宋太祖所立“不杀士大夫”誓约,基本扭转五代重武轻文的习气。晁归来子序张穆之《触鳞集》曰:“五季文物荡尽,而鲁儒犹往往抱经伏农野,守死善道…太祖皇帝既定天下,鲁之学者始稍稍自奋,白袍举子,大裾长绅,杂出戎马介士之间。”[14]极其生动地描写出士阶层从异化转向认同,即从“在野”走向“在党”的历史过程,这便给宋代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局面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
但必须认识到太祖对于文士的任用,更多地着意于建构统治秩序,着意于文武制衡,对那些曾经与他“比肩”的高级将领只会是“制武”、“驭武”而不是“轻武”,文臣的地位并没有立刻提升至盖过武将,司马光《涑水记闻》载: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钱椒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左庑下……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惶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若知之,当奏闻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因命韩王谢而受之[15]。
虽然有“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惯例,但宋初宰相职权被一分为三,又设枢密使掌管军事,故文臣对国家大事能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太祖对韩王赵普所说的“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这句活也可透露出,以赵普为代表的文官地位不高,国家权力仍掌握在武将手中。
(二)太宗朝的继承与发展
尽管太宗的突然即位争议颇多,但他颁布的即位诏书: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咨尔臣僚,宜体朕心。”[16]
这体现了他对太祖立国精神的继承,例如他很好地继承了“不杀士大夫”誓约这一祖宗家法。太宗时卢多逊图谋皇位,仅流放了事:
“或告秦王廷美欲乘间窃发;癸卯,罢廷美开封尹,授西京留守……会普廉得多逊与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闻,帝怒,戊辰,责授多逊兵部尚书,下御史狱……丁丑,诏削夺多逊官爵,流崖州,廷美勒归私第。”[17]
此外太宗也体会到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是巩固政权的可取法宝,并加以发展,体现在该祖宗家法上即不仅像太祖那般不轻杀士大夫,而且对于士大夫政治地位的提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太宗皇帝……又引缙绅诸儒,讲道兴学,炳然与三代同风矣。”[18]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作用巨大,正如欧阳修所说:“自太宗崇奖儒学,骤擢高科至辅弼者多矣。”[19]这说明太宗重视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不只是“崇讲儒学”。令据《文献通考》记载,宋代进士人数自太宗即位之年(976)起便开始激增,到真宗天禧三年(1019),四十四年间已有9323人,与唐朝二百九十年中共得6442人,平均每年不过二三十名进士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样大数量的进士不断产生,自然有助于责任意识在群体中互相加强,有助于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增强。
(三)真宗朝的过渡
把宋太祖、太宗时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总结概括,将其称之为“祖宗典故”、“祖宗法度”,并且奉之为治国理事之圭臬,始于真宗时期。
真宗时天禧四年(1020)宰相寇准“坐与周怀政交通”,图谋废真宗而拥立太子监国,最后也只是“贬授将侍郎、守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20]
时真宗得风疾,刘太后预政于内,准请间曰:“皇太子人所属望….丁谓、钱惟演佞人也,不可以以辅少主。”…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且欲援亿辅政。已而谋泄,罢为太子太傅[21]。
虽然是以丁谓和寇准政争为背景,但也体现了宋太祖“不杀士大夫”誓约这一祖宗家法的延续。寇准敢于作这样的建议,说明他具有出众的胆识,是敢以天下之重为己任之人。而且真宗朝即便是“居位慎密而动遵条制”,以“镇静”著称的宰相李沆、王旦等人,亦能“识大体”,敢于决断:
大中祥符六年(1013)当真宗考虑允许其“深所倚信”的内臣刘承规之乞请,授予他节度使头衔时,宰相王旦义正言辞地说:“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可听也。”[22]相符、天禧之际,真宗欲以王钦若为宰相,王旦出面阻止,理由是“祖宗朝未尝使南方人当国”[23]。在当时,据守“祖宗典故”成为王旦等人制约帝王行为的有效借口,也是他们行使政治信念的依据。这些都表明真宗朝时士大夫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趋向已初露端倪。
(四)仁宗朝的成型
《圣政》的编纂始于真宗朝,而《宝训》[24]编修始于仁宗:
仁宗庆历三年….先是富弼请选官置局,将三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文字,类聚编成一书,置在两府,俾为模范,帝纳其言,故命靖等编修,弼总领之。明年,九月,书成,分别事类,凡九十六门,二十卷[25]。
此后成为继位君主不容偏废的传统,足见宋朝对祖宗家法的重视。《宝训》编修成的当年,就被士大夫们“付诸实践”:
庆历三年(1043)十一月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事闻,朝廷大怒,枢密副使富弼译诛仲约以正法,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上前。……上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范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26]。
中国古代社会官吏镇压盗贼不利是大罪,但“不杀士大夫”誓约发挥了挡箭牌的作用,范仲淹搬出祖宗家法得以改变了仁宗的决策,饶恕了晁仲约。这些表明士大夫群体自真宗、仁宗朝已发生转变,他们并非唯唯诺诺于皇上,而能以祖宗家法约束皇帝的行为,皇帝的意志也不得不向士大夫群体退让。
仁宗朝时西夏与辽的进攻对北宋构成极严重威胁,再加上国内发生多次农民起义,仁宗深感内外交迫,重用范仲淹、富弼等人,开启庆历新政。不仅如此,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号召下,士大夫中不乏因关心国家富强而跃跃欲试的人:
以李覯为例,他的《富国策》,《强兵策》和《安民策》各十首都写于宝元二年(1039);他上书富弼、范仲淹及其他朝士自荐也大都在庆历之世。受当时士风的感染,年仅十八岁的程颐于皇祐二年(1050)写下《上仁宗皇帝书》: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尽其诚;苟实可用,陛下其大用之……[27]他急于用世的心情跃然纸上。还有谒见范仲淹的张载,二十岁前后喜谈兵,并有志于“功名”。
上述事例表明仁宗朝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意识已成为一种集体意识。
(五)神宗朝的定型
仁宗之后的英宗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英宗嘉祐八年(1063)的诏书:“夙奉圣颜,备闻圣训,在于庶政,悉有成规,惟谨奉行,罔敢废失。”[28]也表明他尊崇祖宗家法的施政方针。到了神宗年间程颐说:
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百年未尝诛杀大臣[29]
时人津津乐道于本朝家法超越汉、唐。下面一则事例可以看出,神宗的决策受到臣下的抵制、皇权受到祖宗家法的制约。
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确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祖宗以来未有杀士人事,不意自陛下始。”[30]
事实上,神宗朝是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正式发挥功能的时期。程颐《论经筵第三劄子》中指出:“臣以为,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31]熙宁四年,文彦博当面向神宗指出:
文彦博曰:“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32]
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也是神宗和王安石共同承认的前提。王安石的秉政更加深了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的观念。他写的《虔州学记》讨论皇帝与士之间关系:若夫道隆而徳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33]这是石破天惊之论,“与之迭为宾主”表明士大夫与天子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事实上,王安石与神宗的关系便是如此,才使得初时熙宁变法得以顺利推行,陆佃《神宗皇帝实录叙》云:
熙宁之初,锐意求治,与王安石议政意合,即倚以为辅,一切屈己听之。……安石性刚,论事上前,有所争辩时,辞色皆厉。上辄改容,为之欣纳[34]。
熙宁三年神宗正式接受了“共定国是”的观念,则象征着皇权方面对这一基本原则的认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架构正式形成。熙宁变法在实施过程中有许多差池,使得后人骂其背离祖宗之法,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正所谓“理论和实践具有不完全一致性。”
(六)哲宗元祐年间的延续
神宗逝世后,即位的哲宗年幼由高太后辅政,宰相吕大防教导小皇帝:
哲宗御迩英阁,召宰执、讲读官读《宝训》……(左相吕)大防因推广祖宗家法以进,曰:“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哲宗甚然之[35]。
哲宗元祐年间,高太后重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党人,施政基本还都谨遵祖宗家法,但哲宗“绍述”后,祖宗家法渐被奸佞之人利用,成为他们党同伐异的工具,祖宗家法走向反动,如徽宗朝的蔡京打着“变法”的旗号,却行祸国殃民之事,故下文不再论述。
王夫之所言:“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36]虽有溢美之词,但北宋历代君主确实都贯彻了“不杀是士大夫”誓约这一家法,优待臣下,而且可以看出士大夫也以此在不断争取自身权利,不断成长壮大,从而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正是“周之士贵,士自贵也”[37]。
四、结语
宋代“祖宗家法”提法的出现,使现实的法度笼罩在宗族秩序乃至道德伦理的体系之下,具有了双重的权威。赵宋的“祖宗家法”,来自于赵宋统治阶层对社会现实与政治现实的反应,但它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寄寓着宋代士大夫自身的政治理想。
宋代以立纪纲为基本方略的祖宗家法,使士大夫得以祖宗成宪的神圣性约束嗣皇帝,避免君主走向极端的独裁专制,也使政治文化风气显得比较自由开放。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给予士大夫一种护身符,士大夫也因而敢于“参政、议政”,创造了北宋中前期无“武将、女主、外戚、宗室强藩、宦官专权”,[38]“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架构。
宋代皇权对于士大夫以政治主体自居发出的种种声音,也表现出了容忍的雅量,这些使得宋代具有较为开明的政治风气,蒙元以后,这种声音便逐渐消沉了,君主专制被强化并走向反动。清乾隆帝驳程颐“天下治乱系宰相”曰:
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以乾隆与宋神宗对比,即可见“士”的政治地位在宋、清两代的升降状态。
参考文献:
〔1〕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关于祖宗之法问题,笔者参考的论文成果:邓广铭.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J].中华文史论丛,1986(3);邓小南.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A].国学研究第七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邓小南.“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J].北京大学学报,2000(4).
〔3〕关于此问题,笔者参考的论文: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J].文史杂志,1941(7);杜文玉.宋太祖誓碑质疑[J].河南大学学报,1986(7);徐规.宋太祖誓碑辨析[J].历史研究,1986(4);张希清.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誓约考论[J].文史哲,2012(2).
〔4〕王梦欧.礼记今注今译[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56.
〔5〕(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875.
〔6〕(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603.
〔7〕笔者采取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一书中的解释:士大夫指朝廷中的文臣官僚主要包括大臣、上书言官等.
〔8〕(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30.
〔9〕(宋)黄震.黄氏日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07.
〔10〕(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21.
〔11〕〔36〕〔37〕(清)王夫之.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20,24,24.
〔12〕〔16〕〔17〕〔18〕〔25〕〔2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0.98,206,264-265,1250,1098,1105.
〔13〕(宋)陈傅良.止斋集[M].台北:世界书局,1988.585.
〔1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402.
〔15〕(宋)司马光.涑水记闻[M].上海:上海书店,1990.233.
〔19〕(宋)欧阳修.归田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0.
〔20〕(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4-145.
〔21〕〔22〕〔23〕〔28〕〔35〕(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1.170,175,179,504,10843.
〔24〕《宝训》、《圣政》是经由润饰而寓意于说教的文字,其中所记录的,是宋朝自太祖以来历代君主的“嘉言美政”,是供继嗣帝王汲取借鉴的本朝经验;就其性质而言,可以说是宋代君主因应治国需求而编纂的一种帝王学教材.
〔27〕〔31〕(宋)程颐,程颢.河南程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260,321.
〔29〕(宋)程颐、程颢.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960.
〔30〕(宋)侯延庆.退斋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67.
〔3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0.
〔33〕(宋)王安石.临川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70.
〔34〕(宋)陆佃.陶山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345.
〔38〕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6.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