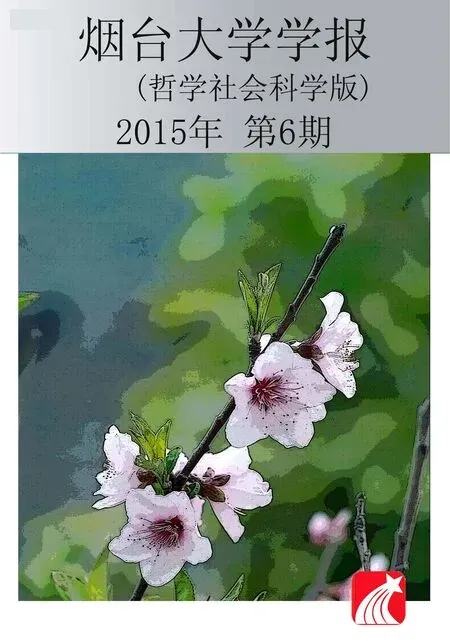论西方纯诗理论与中国现代纯诗写作的和而不同
耿庆伟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论西方纯诗理论与中国现代纯诗写作的和而不同
耿庆伟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由于中外文化传统的差异及接受语境的拘囿,自20世纪20年代引入中国后,纯诗理论必然会发生变异,具体体现为中西诗学追求的差异。但作为一种源于西方而在中国应时而需的美学概念,由于中西诗坛艺术目标的一致性,西方的纯诗理论和中国纯诗写作都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现实指向。纯诗写作受到中国现代诗界的广泛认同,现代诗人通过对这一概念的扬弃,让纯诗理论促进了中国现代新诗的艺术精进和品质提升。
纯诗理论;瓦雷里;区别概念;纯粹美;中国化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6.008
“纯诗”是源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诗学概念,其提出及流变源于对诗弊的思考和求索。纯诗理论虽不完美,但却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并引发了诗界对诗艺的探求热情。纯诗论虽体系复杂,但又相当不明确,总能带给人们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审美回味,自然在中国现代诗界产生广泛而又持续性的影响。如果要探析西方纯诗概念与中国现代纯诗写作的历史性交汇和审美接受,必须要厘清“纯诗”概念,否则就会望词生义。鲁迅曾经告诫我们“中国文艺界上最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涵义。于是各各以意为之。”①鲁迅:《三闲集·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7页。因此切实弄清楚西方诗论家视野下的“纯诗概念”、“如何纯诗”以及“为何提出纯诗”,才能避免在中国语境下出于某种审美期待和功利需要而导致对西方纯诗理论的“误读”,才能弄清西方强势理论话语下的纯诗中国化道路的复杂性以及纯诗理论的现实意义,因而辨析纯诗概念和中国现代纯诗写作的因缘际会也是不无意义的。
一、西方纯诗视角下中国现代纯诗写作的历史观照
如果以绝对的标准膨胀纯诗的至美境界,难免会产生理论反差和审美失落。因为任何美学概念都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而存在,必然有一套相反的、对立的甚至是否定的因素与之相伴而生,换言之,没有非诗就没有纯诗。其实纯诗概念根本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审美范畴,准确的理解它必须抛弃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因为一旦在思维视域中出现一种二项对立的东西,就会出现意识形态的判断,而二项对立正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方式,就强制接受者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不纯只是个参照,而非其剑拔弩张的对立面,芜杂的不纯只是用来确立纯诗理论体系的天然假想敌,因而纯诗并不是诗歌的理想状态而是诗歌追求的艺术目标。既然诗是对大千世界的反映,就应该有玫瑰花和紫罗兰,也应该涵纳苍蝇和蚊虫,不美的事物同样具有美的光彩,也能进入诗学的殿堂并得到缪斯的垂顾。既然诗可以提供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并具有向心性、穿透性的意识形态功效,就必然伴随着对诗歌的功利性征用和价值观念充值。但诗歌无论有多少外在的强加和意义赋予,但诗必须是诗,其允许的理论底限就是具备诗的本质规定,否则就会坠入非诗的悬崖,诗歌的历史自会公正地确认真正诗歌的存在价值。英国诗人、批评家雷达在《论纯诗》中认为纯诗只是普通诗歌的“一种主要的原素”*雷达:《论纯诗》,曹葆华:《现代诗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65页。。
西方的纯诗理论确立也是一个不断被建构而趋于完善的过程,一直被诗人和理论家进行不断地内容填充和意义赋予,最终才整合为具有浪漫主义的激情、唯美主义的审美理想、象征主义诗形的诗歌理念。梁宗岱在《谈诗》中就认为纯诗理论具有“象征主义底后身”,滥觞于“法国底波特莱尔”,奠基于“马拉美”,至“梵乐希而造极”。*梁宗岱:《谈诗》,《诗与真二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7页。一般认为西方的“纯诗”理论缘起于爱伦·坡,在法国由波德莱尔、马拉美等人造成声势,并最终在瓦雷里手中正式提出。尽管时间漫长,甚至跨越国界,可诗论家的努力并未建构起一个外延明确、内涵固定的科学诗学体系,甚至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内在判断标准的缺失既说明了这一概念的混乱,也成就了其体系的开放。爱伦·坡首倡“为诗而诗”论,“一首诗就是一首诗,此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了——这一首诗完全是为诗而写的。”*罗伯特·佩恩·沃伦:《论纯诗与非纯诗》,张少雄译,潞潞主编:《准则与尺度,外国著名诗人文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355页。他把美作为诗的领域,并不排斥具有诗美的道义和真理入诗,但前提是“真正的艺术家要经常设法冲淡它们,使它们适当地服从于诗的气氛和诗的真正要素——美。”*泼德莱尔:《再论埃德加·爱伦·坡》,郭宏安译,《泼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06页。爱伦·坡的诗论的基本精神是强调“诗本身”及并把“美”作为诗的文体要素,并以此将诗与其他文体区分开来,可见并不否认诗歌的意识形态承载功能,关键是不能喧宾夺主地剥夺诗美。作为爱伦·坡忠实信徒和法国传人的波德莱尔继承了他的纯诗理念并在《再论埃德加·爱伦·坡》一文中提出诗的本质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这种本质表现在热情之中,……不能不给纯粹美的领域带来一种刺人的、不谐和的色调;它也太亲切,太猛烈,不能不败坏居住在诗的超自然领域中的纯粹的愿望、动人的忧郁和高贵的绝望。”波德莱尔把对“最高的美”的追求作为诗歌的本质,将生活中自然情感进行艺术化超越,进而超越科学真实和道德功利,合理地区划纯诗和功利性诗学的审美边界。无论坡还是波德莱尔都尽力澄清诗与其他文体的属地和价值边界,引导阅读者关注诗本身。
相对而言,瓦雷里的纯诗理论较为体系化和具有操作性,他认为纯诗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排除了功利感和实用性的诗情:“指的是某一类情绪,一种特别的情感状态”;二是用“没有实体感的言词”传达“诗情”的诗艺,纯诗是“一门艺术,一种奇怪的技巧,其目的就在于重新建立该词的第一种意思所指称的那种情绪”,这一类情感与“所有其它人类情感都不相同,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尽可能清楚地将诗意的情感与普通情感区别开来”。*瓦雷里:《论诗》,段映虹译,《文艺杂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5-326页。真正的纯诗与散文的“东西都不再与之沾边,音乐的延续性,永无定止的意义间的关系永远保持着和谐,彼此间思想的转换与交流似乎比思想本身更为重要”*瓦雷里:《纯诗》,葛雷、梁栋:《瓦雷里诗歌全集》,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303-304页。;完全排除非诗情成分的最美的诗是“纯诗的一个因子”*瓦雷里:《纯诗》,杨匡汉、刘福春编:《西方现代诗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215页。。瓦雷里的纯诗探索偏重于形式层面,向诗歌的内部美开掘,维护诗的审美独立性,阻止非诗因素的进入和干扰。
仔细厘析爱伦·坡、波德莱尔及瓦雷里等纯诗理论家建构起的现代纯诗理论体系,就会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几乎没有进行正面立论,纯诗概念主要作为一个区别性概念被小心翼翼地树立起来,区别不是制造对立,我们也经常看到其他文体的越界现象,诗歌史也一直存在着诗歌散文化、小说化甚至是戏剧化的倾向。并不是说纯诗一旁及其他领域就不纯了,而是通过强调纯诗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来定义纯诗,进而驾驭、超越区别创造出一种海阔天空的纯粹美,其诗学追求就是要摆脱非诗因素的障蔽而孑然独立。不管是波德莱尔还是瓦雷里,其主要的诗学命题强调的是诗与散文的分界、尊重艺术的自主性、重视诗歌语言的重要性以及诗歌传达的暗示性和音乐性等,最终促进诗歌本体的自觉。纯诗理论不是平地起高楼的突兀崛起,纯诗诗学体系是在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诗学反动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而将纯诗与强调“再造感觉世界”的现实主义诗学和偏重情感表现为特征的浪漫主义诗学区别开来。
在西方纯诗视野下纵览中国现代纯诗写作,不难发现在中国现代诗学界,纯诗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一直被谈论着,作为一种诗歌理想被诗人追求着,但在中国现代诗坛却从未存在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诗流派,更谈不上拥有一个径直以纯诗标榜的诗歌团体。能够忝列于纯诗阵营的诗派不过是诗论家对于象征诗派、新月派、现代派和九叶诗派等诗歌流派的笼统称呼,或者说是在与自由诗、普罗诗歌、中国诗歌会诗歌进行比较后得出的一般结论。至于何为“纯诗”定义不明,谁的诗可称得上“纯诗”尚付阙如,能够被冠以经典、样板的纯诗根本就不存在,可能也不会存在。纯是相对的,不纯是绝对的。以新月派为代表的现代诗人皆是中国现代诗坛的纯诗书写者,即便按照西方的纯诗标准来看,后来的读者及文学史皆认定他们就是符合纯诗标准的中国现代最早纯诗写作的先行者和探索者。即便窥破纯诗的理论幻象也不会妨碍纯诗追求者对纯诗理论的探索和纯诗创作的兴趣,中西方诗界只要存在诗歌变革的历史任务,纯诗理论就是审美内需的最佳借鉴,至于理论的模糊似乎是个不必深究的话题。
二、纯诗的诗学追求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变异
中国的新诗发展经历了和西方大体一致的发展历程,即由现实主义至浪漫主义而后象征主义,但挑战更大,在初创期就要面对传统社会秩序瓦解而带来的文学话语大厦崩溃的危机,在废墟上重建现代诗学体系就成了中国现代诗人的历史任务。不可否认胡适的白话新诗对新诗发展做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却将诗写成了“非诗”、“反诗”;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诗学践行为新诗注入了“情感”因素,但在本质上和胡适的“诗体大解放”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诗体解放了,新诗本体的意义和艺术品格却被忽略了。西方的纯诗理论适时引入无疑带给了现代诗人及其论者无限的遐想空间,为现代诗人的诗美探求提供了宝贵的异域资源,促进了中国新诗的艺术精进与品质提升。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纯诗理论事实上也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新诗写作产生了持久而强烈的影响,基本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作为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纯诗”概念自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诗界以后,一方面作为一个重要诗学命题被现代诗坛遵循着,并以现代新诗骄人的创作实绩证明了纯诗理论的活力,每当诗歌创作走向偏执之途时,纯诗理论总是隐秘而又固执地将新诗拉上正途。但另一方面纯诗的中国化也是困难重重,也被中国新诗界批判着,纯诗理论在现代诗史上命运是非常尴尬,从未处于主流诗学体系的地位。现代新诗史上历次新诗论争也都是围绕纯诗化与大众化之间展开的,经过多次论争后纯诗理论却越来越滑向边缘成为一个贬义的指认。
纯诗理论摇摆于两个端口既有中国社会现实的牵扯,更有理论本身的矛盾。细而究之,则会发现“纯诗”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概念本身就是晦暗不明的,在注重实用主义诗学价值取向的现代中国,纯诗注定面临着实用主义诗学的挤压。而诗的本性是越不明白越好,明白是概念的边界,因为诗是最禁忌概念的。对美的认识和感受也是最难捉摸的动态过程,美的观念和标准一旦固定,美也就走上了黄泉末路。诗美有点类似诗经《蒹葭》的境界:“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根本无法对诗歌的生长边界和方向进行圈囿,模糊恰是西方纯诗体系的应有之义,纯诗论者根本无意于制定一个统一的诗美规范供诗人遵循,因为规范一明晰,诗歌的想象空间就会受到诸多限制。其理论基点就是强调诗歌的本体自足和审美超验性,诗人是通灵者,能够透过现实世界的物象发现理想世界的本质,纯诗是通向超验天国的旋梯,纯诗创作更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天国之旅,“纯诗”的艺术目标就是启迪人们探寻内心的“纯粹美”。
康德区分了“纯粹美”、“纯粹的欣赏判断”与关乎利害关系的快感,在哲学层面上将“纯粹美”的价值和意义抬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也引导文学进入对于幽深之境的勘探。爱伦·坡所倡导的美就并非普泛意义上的美,而是特有的“死亡与美最密切结合”的“哀伤”、“忧郁”的唯美,他在《序曲》中宣称:“我不能爱,除非死神自己/把它的气息与美的气息混在一起。”认为死亡与美的美女之死是“世界上最富于诗意的题材”。*马库斯·坎利夫:《美国的文学》,方杰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62页。波德莱尔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艺术领悟,补充、发展了爱伦·坡的美学观,定义自己所理解的美“是某种热烈的、忧郁的东西,其中有些茫然、可供猜测的东西……神秘、悔恨也是美的特点。”美是主体精神活动的表现,人的主观感觉方式非常重要,在波德莱尔看来对美的寻找不能在题材、技巧等外围因素打转,主张从主体的内部感觉上寻找“纯粹的美”,同时强调人感觉方式的差异导致表现的方式的不同,有“多少种追求幸福的习惯方式,就有多少种美”。*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218页。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从恶中挖掘美”,警示人们丢掉对艺术的幻想和偏爱,直面现实,从不完美的现实中发现美,其创作的《恶之花》就是这一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西方纯诗理论最出色的代表瓦雷里充分论述纯诗的思想,他认为纯诗像“完全的‘真空’与绝对的‘零’一样,那些理想是不能达到的,甚至于除了继续不断的努力以外,还不能接近的”。*曹葆华:《现代诗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34页。其实瓦雷里的纯诗世界只是一个不同于实际世界的幻想世界,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一种令人惊奇的特征,这种感受总是力图激起我们的某种幻觉或者对某种世界的幻想……但同时它们与我们的感觉领域存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内在联系。”*瓦雷里:《纯诗》,杨匡汉、刘福春编:《西方现代诗论》,第218页。看来西方纯诗论者的诗意具有某种日常语言无法言传的神秘意味,自然无法落实在现实世界中,从根本上说文学就是一种精神的事业,纯诗论者纯粹性和精神性的诗学抱负虽具有幻想的性质,但却能够在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活中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
“纯粹性”即是一种限定,寻求艺术形式的“纯粹性”不过是为了找到一种独属于自己而在其他艺术类型中无法具备的独特性。无论在自然界和现实社会,纯粹的美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列宁认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人的认识由于没有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而带有某种狭隘性和片面性。”*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2页。纯诗是一种诗学洁癖,拒绝任何他力的强加和外在的负累,概念的不纯粹性,必然表现为创作上的不纯粹性,其诗学内容必定也会因时代、地域、民族的不同而发生语义迁移,但在不断的变化中却又贯穿着一个核心的诗学理想,即在一种自觉诗学意识下努力追求极美的诗歌境界。纯诗与其说是一个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纯艺术理想,表征着人类共同的艺术心愿,也是诗人孜孜以求地在凡俗尘世中构筑永垂不朽的诗歌圣殿的诗学理想,最终诗学用心是“要求着那些怀抱有这些理想的人们长期的与严肃的锻炼,以至于求作诗人的自然的欢欣完全吸收在工作里,只剩余着一种决不自满的骄傲”。*曹葆华:《现代诗论》,第234页。通过对西方纯诗论者的美学理想的厘析不难发现他们对纯诗诗质缺少根本的界定,甚至是语焉不详的,瓦雷里当时就说过“我并没有赋予这个词以什么特别的意义,也没有预见到各种各样的关切诗歌的学者们会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瓦雷里:《纯诗》,杨匡汉、刘福春编:《西方现代诗论》,第216页。
三、西方纯诗理论与中国现代纯诗写作目标的契合
在喧嚣的现实面前,任何强调自己纯粹性的理论不过都是一种学术神话,瓦雷里也认为纯诗的讨论是近乎“神学性质的学术辩论”。正像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指出的那样标榜纯粹性“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它们在企图无视历史和政治时那样能够清楚地表现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性”。*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12页。其实西方纯诗概念的提出也有深刻的现实原因和强烈的功利动机。中西纯诗诗学的微妙之处在于:西方的纯诗理想将诗歌导向了对“天堂之美”中“万花之花”的寻觅,而在中国却被降格为在人间之境中去触摸凡俗人生。在爱·伦坡的时代,美国文学中的道德说教倾向就比较严重,“一切诗的最后目的是真理……每一首诗都应该顽强地给予一条教训;并且就按这条教训,来宣布关于作品的诗的价值的判断”。爱伦·坡提倡“纯诗”是让诗人意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更好地卫护诗歌的尊严、高贵和力量,恢复诗人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对此,他提出了回归文学本体的艺术构想,单纯为诗而诗就是“我们的意图,就会是承认我们自己极端缺乏真正的诗所具有的尊严和力量——然而,简单的事实却是这样,只要我们内省自己的灵魂,我们立刻就会在那里发现,天下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这样的一首诗——这一首诗本身——更加是彻底尊贵、极端高尚的作品”*爱伦·坡:《诗的原理》,杨烈译,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498页。。“为诗而诗”的倡导真正用意是恢复重建与“真正的诗”相匹配的“尊严和力量”。波德莱尔也认为:“艺术越摆脱教训,便越取得大公无私的纯粹之美。……诗不可同化于科学和伦理,一经同化便是死亡或衰退。诗的目的不是‘真理’,而只是它自己。”*波特莱尔:《随笔》,林同济译,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225页。被“教训诗”笼罩的诗坛,诗美被破坏,诗人被社会冷落、抛弃。马拉美感慨到“在这个不允许诗人生存的社会里,我作为诗人的处境,正是一个为自己凿墓穴的孤独者的处境”。*马拉美:《关于文学的发展》,王道乾译,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263页。丑恶的现实孕育灿烂的文学之花,纯诗诗人将一种针对于现实社会的怨恨情绪带进了艺术领域,通过对诗歌形式之美的关注隐含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以艺术的前卫对抗纷乱的现实,纯诗写作显然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现实指向。瓦雷里是纯诗的积极提倡者,也是纯诗写作的热心实验者,诗人张曙光在谈到阅读其诗歌的体会后认为“他的诗与现实的联系比他的老师马拉美或其他象征派诗人更为紧密”*张曙光等:《写作:意识与方法——关于九十年代诗歌的对话》,孙文波等编:《语言:形式的命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80页。。
“纯诗”概念在整个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体系中其实算不上核心概念,瓦雷里在《论纯诗》中谈及他对这一概念的看法,“几年前我在给朋友的诗集写序时信笔提出了这两个字(纯诗),但当时并没有给予它过重的分量”,“纯诗这个词之所以说不太合适,是因为它使人想到与之风牛马不相及的纯道德,在我看来,纯诗的观念是与基本分析观念背道而驰的。”*瓦雷里:《纯诗》,葛雷、梁栋:《瓦雷里诗歌全集》,第303-304页。西方“纯诗”理论虽然概念不确定,内涵亦变动不居,但却有无限的生长空间和诗美空间,纯诗追求者对诗歌创作的态度是认真的,对诗艺的探索是虔诚的。他们心怀对纯粹和绝对美的敬畏之心,不断用诗歌洞开人类灵魂的奥秘,用纯粹美弥补现实的缺憾,在艺术中创造人间天堂,在纯诗园地里结出了累累硕果。西方纯诗理论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引进中国也是符合中国新诗发展内在要求的,旨在倡导纯诗唤起对新诗诗学的自律,力求反拨新诗发展初期过于“散文化”倾向,使“纯诗”理论更好地促进中国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因此纯诗概念的引进具有不可避免的功利性目标和工具化取向。
“五四”时期的新诗白话化和自由化造成了新诗的非诗化,新诗的成熟绝不是白话化,诗化才是追求的结果。周作人认为新诗的“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和回味。”他希望借镜法国的象征主义改变新诗的现状,指出象征主义是“外国的新潮流”,也是“中国的旧手法”,引进西方诗学既有内在原因,中西诗学的会通之处和生长土壤,“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周作人:《扬鞭集·序》,钟叔河编:《知堂序跋》,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97-298页。1926年初,中国纯诗理论的首倡者留日学生穆木天在《谭诗》中历数胡适“作诗如作文”诗学主张的“罪过”,提出:“我们要求的是‘纯粹诗歌’,我们的要求是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我们要求的是‘诗的世界’。”*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1926年1卷1期。努力寻找将新诗从散文中分离出来的“新的思维术”,以此来改变诗歌“类型的混杂”、诗与散文区分不严格的现象。其纯诗论具有明显的“现实的需要”,即借用西方纯诗观念修正中国新诗“诗质”缺乏的弊端。
中西纯诗追求者皆有扭转诗歌创作颓势的宏愿,精神的相通激发了中国纯诗追求者的艺术灵感,触发他们让中国新诗走向世界的冲动,具体路径就是吸取西方纯诗的精神资源促进中国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但中国现代诗人遭遇的是动乱的现实,在真理大于诗美的时代,纯粹的理论犹可闪避喧嚣的世界,乱世诗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躲避政治现实的致命诱惑。王独清认为要整治“中国现代文坛审美薄弱和创作粗糙的弊病,我觉得有提倡poesie pure的必要”。但又申言:“虽然主张唯美派的艺术,但同时又承认这与国民文学毫无矛盾而主张国民文学。”*王独清:《再谭诗——寄给木天、伯奇》,《创造月刊》1926年3月1卷1期。政治使命与艺术使命的冲突,中国文人的生命血液中也一直流淌着重艺术社会功用的文化基因,加之主流意识形态担忧纯艺术对社会发展具有潜在的解构作用。在中国政治诗学总会公开而又固执地制约着新诗的发展,中国的纯诗化道路必然伴随着对元概念的逃逸和拯救,中国新诗不可能完全拷贝西方纯诗的理论目标。纯诗理论体系中,“纯诗”是根本无法达到也不可能达到的理想境界,但在中国明确的现实问题指向偏要将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纯诗诗学理想切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现实任务。
四、结 语
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人们都需要一个性灵放飞的场域,而一种纯粹的诗学理想仍会唤起我们种种感动。美藏在人的心灵深处,而对美的追求是人的自然天性,“纯诗”创作就是抵达“彼岸辉煌”的“最迷人音乐”。梁宗岱认为纯诗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像音乐一样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韵和色彩底密切混合便是它底固有的存在理由”。*梁宗岱:《谈诗》,《诗与真二集》,第7页。
任何纯粹性的艺术追求都是为了寻找专属于自己的特征从而与其他艺术类型区分开来,从而在拥有自己艺术独特性的基础上确立自身的独特价值。纯诗就是一个只具特指性,并不具备普遍性与科学性的美学概念和知识范畴。“纯诗”作为一种诗歌理想一直是诗人难以企及的但又渴望抵达的目标,但其诗学意义是不可轻估的。每当文学生态出现危机时,纯诗及升级版的纯文学就成了人们的审美念想。在中国新诗陷入非诗化困境的时候,“纯诗”理论适时引入促进了“中国新诗第二期革命”*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但由于中外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现代诗人往往以本民族的审美眼光采撷、汲取其有益养分,“纯诗”理论进入中国后必然会发生变异。在20世纪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政治文化等因素不断侵蚀纯诗创作,注定“纯诗”的中国之旅经历坎坷,中国现代的纯诗写作既非单一的心灵性,也不是纯粹的现实性。
[责任编辑:诚 钧]
The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Western Pure Poetry Theory and Chinese Modern Pure Poetry Composition
GENG Qing-wei
(Colleg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contextual factors , “pure poetry” theory is bound to change after entering China since the 1920s, and it is reflected as the differences of poetic seeking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s a kind of aesthetic concept, pure poetry theory in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pure poem writing have a strong spirit of world and reality orientation due to the consistenc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ry artistic goals. Pure poetry writing is widely recognized by modern Chinese poetry field. Through a sublation of the concept, modern poets make the theory promote the level of Chinese modern new poetry art and develop the quality of pure poetry.
pure poetry theory; Paul Valery; Different concepts; pure beauty; sinicization
2015-06-03 [作者简介] 耿庆伟(1973- ),男,汉族,江苏徐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泰州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纯诗’诗学视域下的中国新诗研究”(2015111010203)
I 207.2
A
1002-3194(2015)06-00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