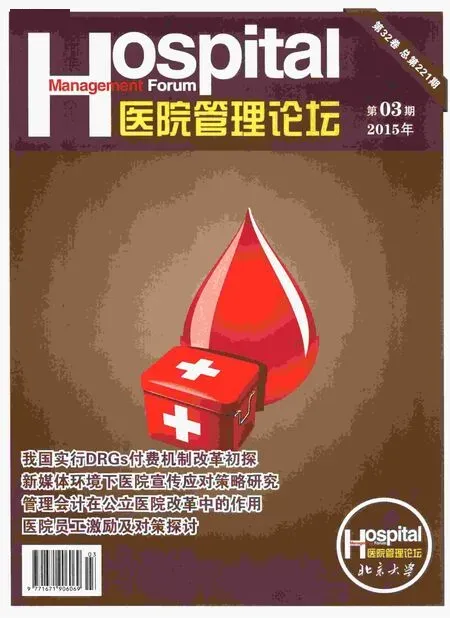医保购买服务:会梦想成真吗
文/周子君 ZHOU Zi-jun
今年召开的人大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下放一批基本公共服务收费定价权。”这意味着长期以来实行的药品政府定价政策行将结束,医疗服务价格制定职权有望下放。
医改以来,围绕治理“以药养医”、“药价虚高”等社会重点关注问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药品政府定价、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基本药物制度、医药分开是政策的关键着力点。按照政策思路,医药分开用以消除医生和医疗机构以药牟利的利益机制;基本药物制度可以保障民众得到安全、价廉的药物;政府定价加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用以控制“虚高”的药品价格,从而遏制“药价虚高”和“过度用药”。但从改革效果看,这些政策“组合拳”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药品零差率销售虽然遏制了医院以药牟利的动机,但过度用药并未有效控制;基本药物制度在保障民众低价获取药品的同时,也因“药品种类不能满足需要”制约了民众去基层就医;而药品政府定价在屡次“降低药价”的举措之后,被证实效果有限,且为不良企业寻租提供了机会。
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管控及其价格形成机制成为“世界性难题”,完全靠市场恐有失社会公允,而靠政府定价则弊端重重。此次克强总理提出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实则是取消政府制定药品价格的行政职责,而非“完全放开药品价格”。未来药品价格的形成政策和形成机制依然有待于政府进一步明确。目前呼声很高的“医保支付价”或有可能成为新的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形成模式,即由医保管理部门通过谈判、批量采购等市场行为达成医疗服务价格共识。
在新的医改制度设计中,医保承担着为参保者购买医疗服务的职责,医保既可以通过付费政策的调整调控医患双方的医疗行为,也可以通过谈判、批量采购等形式形成相对合理的医疗服务和药品支付价格。医改以来,有关医保付费改革虽有提及,但远未达到其应起的医疗行为调控和医药价格形成作用,原因之一就是医疗服务、药品的政府定价取代了医保的购买服务价格形成机制。
如果说医改需要调控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抓手”的话,那医保政策调控所起的作用远大于政府对医疗服务的行政干预。如“总额付费”、“按病种定额付费”等付费方式的实施,既可以有效控制医疗服务费用的快速增长,也可以调动医院、医务人员控制过度诊疗、过度用药的积极性。医保购买服务还可以从根本上化解医疗服务、药品难以合理定价的技术难题。
如果未来医保成为医疗服务的购买方,那么以下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建立和完善购买医疗服务的谈判机制。目前管理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机构多是政府序列的管理中心,药品招标采购也是以政府部门为主,这些机构在处理商业行为时往往习惯于使用行政方式而非依从商业模式,缺乏平等、协商和契约精神,如何在现行体制下建立和完善谈判购买医疗服务的制度和机制依然有待于探索。二是制定规则。建立医保、医疗、药品、医用耗材等医疗服务相关利益方各自的定价行为规范,公开各自的质量标准和定价依据,制定公正的采购程序,并接受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三是各利益方去行政化,建立公平的医疗服务购买环境。政府应逐步退出涉及医疗服务购买的具体事务,成为相关法规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建立公平的医药服务市场环境,在同等条件下,对提供医疗服务、药品、医用耗材的供给者一视同仁。四是要建立完善的医药购买服务投诉和监管制度,对医药服务购买环节中出现的不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置。
政府主导、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此次医改制定的原则之一,如何做好依然有待于社会各界的探索与共识。相信随着社会发展,社会治理会逐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