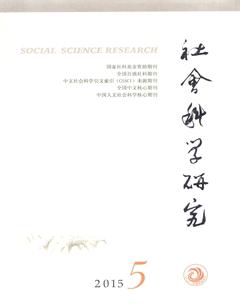传播学中国化:在地经验与全球视野
史冬冬
〔摘要〕 “传播学中国化”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即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梳理该议题的产生及其内涵外延的来龙去脉,一方面形成对“传播学中国化”较为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接续和回应围绕其合法性和可能性引发的讨论与观点。这些论争隐含了“传播学中国化”作为在地经验的研究与西方学术霸权乃至全球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传播学中国化”应自觉置身于全球知识生产的场域中,首先借鉴和入乎西方理论之内,以研究中国特色的在地经验,彰显其理论的特殊性一面,进而超越和出乎西方理论之外,在全球视野中互映中西方传播理论,在对话融通中提升中国传播理论的普遍性一面,最终实现理论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统一的全球在地化。
〔关键词〕 传播学中国化;传播理论;在地经验;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45-05
中国传播学的系统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已有30余年。在此期间,华人学者着眼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当代现实,发掘具有本土特色的传播现象与观念,意图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这在中文新闻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即是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被称为“传播学中国化”“传播学本土化”或“传播研究本土化”等。另一方面,自其伊始,华人学者就围绕“传播学中国化”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展开论争,赞成与反对对立,实践与反思并存,争鸣之声至今不绝,这使其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中几乎最具影响力的议题,也是中国传播学30年来苦苦摸索以求发展突破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传播学的中国化
早在1977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时就已提倡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遗产。首次论及“传播学中国化”这一命题及其内涵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者余也鲁。他在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学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他认为,“文化与传统若不同,作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传的观念、原则、型式也随之而异。因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实际中应该可以找到中国的传播理论。”余氏不仅从议题设置上旗帜鲜明地倡导中国化的传播理论与范式,并且进一步探索它的取径与步骤,就如何在中国历史与传统中探寻传播理论提出了“十二个入口”。〔1〕余也鲁的呼吁成为“传播学中国化”的先导。在大陆,“传播学中国化”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1982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会议形成了对待这一外来学科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要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2〕,该会议为传播学中国化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依据。
1993年,在厦门大学召开“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题涉及中国传统文学、哲学、历史、语言、民俗、人类学、经济等多个领域中的传播现象,会后出版了《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1994),这一标题意味着,中国学界开始正式有组织地展开中国传播学的本土研究。同一时间在厦门,还举办了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心议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正式提出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3〕这一系列传播学会议对“传播学中国化”议题的确立有倡导和推动之功。
此外,研究著述更是代表了这种学术努力的成果。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1988)是国内第一本传播学中国化的专著。此后,中文传播学界陆续出版了一批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著述,专著如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关绍箕《中国传播理论》(1994)、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1997)、张立伟《心有灵犀:儒学传播谋略与现代沟通》(1998)、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2003)及金冠军、戴元光主编《中国传播思想史》(2005)等;论文如陈力丹《论孔子的传播思想》、黄星民《礼乐传播初探》、邵培仁《论中国古代受众的信息接受特色》、何庆良《先秦诸子对传播功能的认识与应用》等。这些研究基本属于余也鲁提倡的研究路径: “回到过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传播观念,从历史经验中总结传播特征,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偏重于传播理论的中国化。此外,“传播学中国化”还有另一种路径:“着眼当下”,借鉴西方传播理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针对当代社会改革发展中的传播问题提出新观点,这种研究更关注传播应用的中国化,其研究成果在中文传播学界更是不胜枚举。
简言之,“传播学中国化”是华人学者倡导的从传播视角研究中国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历史及其思想观念,一方面“将中国历史和传统中所出现的传的现象、事件、思想进行分析,在共同性中寻求特殊性,并提炼出来,作成规律、原则,甚至理论”〔4〕,另一方面借鉴西方理论,对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传播活动展开研究,提供传播策略,解决传播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探索新的传播理论。前者以古代中国为主,后者以现代中国为主,在两者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传播概念、模式乃至理论范式,彰显文化的特殊性,又兼顾理论的普遍性,以期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
二、“中国化”:合法性与可能性之辩
“传播学中国化”在提出后,并未获得国内学界的一致认同,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的合法性与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徐耀魁撰文指出,这一提法的弊端在于过分强调其特殊性,把传播学仅仅视为一种方法,仅局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未免有些片面和狭隘〔5〕,持类似看法的还有陈力丹,他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普遍性的一面,“某学就是某学,一定要某国的什么学,其实很难成学。……不宜简单地将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传播观点,视为是传播学的‘本土化”〔6〕,这两位学者是对“传播学中国化”的合法性、特殊性提出了质疑。然而,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非客观规律,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中国,传播语境、传播主体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传播载体等与西方均有所不同,不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性,西方亦然,因此笔者更同意李金铨的观点:“西方传播学理论不能定于一尊,而且除非经过国际层面的考验,终究还是停留在‘西方的理论层面。”〔7〕换言之,在传播学的西学东渐中,源自西方脉络的传播理论未必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如“现代化理论”以及受其影响的国际传播学经典之作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1958),以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模式强加于中东等第三世界国家之上,如今已受到诸多批判。祝建华也以自己的研究经验证明,西方传播研究中的受众和效果理论,对于个人主义至上、并已被充分研究的西方社会或许并不构成太大问题,但是对于研究中国的受众及效果却有“隔靴搔痒”之效〔8〕,原因即在于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政经体制和媒介环境。因此,与西方传播理论一样,中国的传播经验及其模式观念无疑也具有其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传播学的中国化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学术意义。
对社会科学理论持普遍性的观点,不仅容易忽视本土化研究的文化特殊性,另一方面,这一观念加之西方理论不可否认的强势地位,使一些学者对中国化的研究是否可能也产生疑虑。如李彬曾指出,传播学中国化面临着西方霸权的困境,当人们从传统文化中总结传播学的本土特色时,实际上早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与框架预先设置在思想之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却无一例外地属于舶来品”,这时“以独立独行相标举的本土化,本质上也许恰恰显示出西方话语的支配性。”〔9〕确如李彬所言,传播学从概念术语到研究范式都以美国传播研究为宗,中国传播研究无论方法还是理论都随着美国式传播研究亦步亦趋,不乏以西方理论设定中国的传播议题,或以国内的传播现象附会西方的理论概念,实乃削中国实情之足以适西方理论之履。因此李彬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却不能因噎废食。真正的“中国化”,是从具体国情出发,将中国社会的传播经验摆在首位,直面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传媒变迁中的真问题,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思考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索契合传播实情的学术语言与研究典范。如上述《无形的网络》即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考察独特的语言文字与非语言传播媒介、家族、社团等社会组织及其传播方式、政治体系及其传播控制、儒道法墨等思想流派的传播观念,并从传播视角总结了三种社会化传播结构:“生命〔生活〕—传播结构”“社会—传播结构”“历史—传播结构”,勾勒出一幅较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传播的立体图式〔10〕,在西方传播经验之外展示了新的传播模式,而并无对西方传播概念与理论生搬硬套的痕迹,诸如此类的研究为传播学中国化提供了一些示范性的研究路径。
三、全球在地化:从在地经验到全球理论
在上文中,无论是传播学中国化产生的缘由背景,还是围绕该议题展开的讨论争议,实际上都指向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生产的问题,或曰特殊性与普遍性、在地化与全球化的辩证关系。2000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的年会上,中文传播研究学会组织了一场“中文传播研究之批判性回顾”的专题讨论。会议组织者汪琪教授在其建议书中总结了中文传播研究的问题:“随着中文传播学术圈的扩展,人们对其在国际传播学界中的地位及贡献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有学者在质问西方理论对中文传播研究是否有用,也有学者则批评中文传播研究缺乏理论性。问题是,我们还将偏安于国际学术界的边缘地带多久?”〔11〕边缘化是当代中文传播研究的学术境地,也是传播学中国化所面临的学术语境。因此引出的问题是,地处边缘的传播学中国化如何面对全球化的知识生产?两者的关系为何?
在本文中,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生产主要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由各种基于在地经验的研究构成,并在全球背景下流通。就传播学而言,全球化在本质上仍是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由于学术霸权而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格局。然而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理论仍是一种地方性理论,其解释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需要在理论旅行中接受其他文化经验的验证。二是具有更广涵盖力和解释力的全球性传播理论,这是传播研究中的高阶创新。它必须基于地方性理论之间的比较,在互动对话中抽象出更宏观的理论范畴及体系。对传播学中国化与全球化知识生产的关系探讨,主要在这两层涵义中展开。
首先,在全球化知识生产的趋势下,作为在地经验研究的中国传播学,不再可能如中国传统学术一般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它与西方传播理论不是两套互不相干的理论话语;相反,欧美传播研究作为当前该领域的主流,应作为传播学中国化的参考资源,后者要在充分吸收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展开。这种吸收不是简单地以西方理论观照中国现实,或以西式研究方法解决中国传播问题,而是全面了解西方有关的社会与传播理论,学习其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意识、思路和方法论意识,以之来活络眼光思想,勾勒在地的素材现象,遵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从具体传播经验而非西方理论预设出发直面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才能得出历史契合性的传播概念、思想乃至理论建构,从某个角度,它们又能与西方传播理论形成有效的比较,才有可能“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12〕笔者以为,对西方理论的化用不着痕迹、润物无声,才是上之上者,而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由于传播学的中国化过于强调的是一个‘化字,也就是化他为我,或者仅仅是把他人的东西改造成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这就很容易把思维的重点放在吸收和改造他人方面,而忽略完全基于我国文化土壤和现实基础的原创性追求。”〔13〕一方面,这是将理论手段当成了研究目的,另一方面,原创无疑是传播学中国化的终极目标,但在学术全球化的背景下,原创并不意味着由于“影响的焦虑”而排斥他者、自我独创,而是转益多师,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正如李金铨所言,“先要钻进去学人家的东西,然后要能够跳出来,才能攀登另一个高度”〔14〕,否则“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又如何可能?从现实的角度,中国传播学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译介、研究和自创的历程,原创本就是基于译介学习、研究应用之上和之后的。因此,传播研究的中国化虽然基于地方经验,但无法摆脱先在的西方传播理论的影响而单独发生,只有自觉置身于全球知识生产场域中,不断接受内外的激发和挑战,才能持续发展并具有跨文化对话的全球性意义。
其次更重要的是,传播学中国化与全球化知识生产的进一步关系,在于由特殊性、在地化上升至普遍性、全球化的理论升华。以往的学界讨论和实践主要注重内向的自我研究与理论建构,在方法论上缺乏与西方理论比较对话的全球视野。这首先取径于“文化间际的交互参引”〔15〕,基于第一层关系,中西方传播经验与理论构成不同文化间的交叉互映,由中国化而来的传播概念、方法与理论,一方面用来彰显民族特色,同时也用来“攻错”,即“两个文化之间在相关领域上有所对应,但是对应之间是不一致的,这种差异可以提供相互观看的斜角,也就是透过他者文化与母文化的不一致,产生母文化的问题意识,使得母文化的存在不再是理所当然,而是必须成为思考的对象,并藉着他文化的错位观点,对母文化的物象化过程进行剖析,即可深化母文化的生成机制”。〔16〕“攻错”是母文化与他者文化相互间的过程,一方面深化对自身的陌生化理解,另一方面双方在“错位观点”的烛照下进一步存异而求同。这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由于中西方学术格局的不平衡而似乎触不可及,但像比较文学等其他比较研究一样,在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中加入中西的对比攻错是可行的,正如钱钟书先生对中学的研究始终在与西学的比较与发明中,差异性和共同性并举。与之同理,提倡“传播学中国化”的意旨在于注重中文传播的独特现象与规律,但并不意味着强调特殊性而忽视进一步的普遍性探索,而是力图从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从中文传播的现象出发,探究重大的传播问题及其内在理路,随着抽象思维拾级而上,自然到达理论的层面取精用宏,此时或者形成原创性的理论与西方平等对话,或者在与西方理论的互映中探求联系、互补融通,从在地化走向全球化。在这一意义上,“传播学中国化”只是中文传播研究的起点,方向是国际化;不是特殊性,而是以在地经验充实传播理论库的普遍性,与西方理论展开平等比较与对话。只不过这是在地化与全球化辩证关系的终极目标,在当代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中,尚无研究真正达到这一层面。
四、结语
传播学的中国化,这一提法本身就暗示出知识传播自西向东、由中心向边缘的走向,加之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它所折射出的民族主义和学术自主意识不言而喻,其中焦虑与自信并存;另一边,则是英国学者詹姆斯·科伦(James Curran)等呼吁的传播理论要“非西方化”。〔17〕在这种你情我愿中,传播学中国化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从地方走向全球,从追随西方亦步亦趋到以我为基自主对话的重要路径,其中包含的是地方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辩证意识。在当代中文传播学界,香港一些学者已经在上述第二层关系中展开耕耘和尝试突破;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则倾向于向内看,主要致力于研究总结中国历史上的传播现象与理论,试图建构契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传播理论体系,而对当代中国传播的研究多为归纳与提出观点,尚未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和传播理论,整体上仍处于第一层关系中。因此,未来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具有全球的理论视野,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从具体经验中抽象出理论概念,唯此才有可能实现在地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辩证统一,实现知识生产的全球在地化,而“传播学中国化”这一命题才具有更深层的学术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宣伟伯.传学概论〔M〕.余也鲁,译述.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译者代序.
〔2〕邵培仁.传播学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17.
〔3〕明安香.中国新闻年鉴〔M〕.北京:中国新闻年鉴社,1994:141.
〔4〕余也鲁.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总结〔C〕//余也鲁,郑学檬.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288-291.
〔5〕徐耀魁.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得与失〔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6〕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J〕.国际新闻界,2002(2).
〔7〕〔14〕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一些个人的初步思考〔J〕.传播研究与实践,2014,4(1).
〔8〕祝建华.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J〕.新闻学研究,2001(68).
〔9〕李彬.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J〕.现代传播,1995(6).
〔10〕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后记.
〔11〕Wang,G. Chinese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Z〕// Panel Proposal Submitted to the 2000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Planning Committee.2000.
〔12〕钟元.为“传播研究中国化”开展协作——兼征稿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1).
〔13〕郝雨.浅论传播学的中国化与原创性〔J〕.当代传播,2008(1).
〔15〕叶启政.全球化趋势下学术研究“本土化”的戏目〔M〕//邹川雄,苏峰山.社会科学本土化之反思与前瞻.嘉义:南华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所,2009:12.
〔16〕李维伦,林耀盛,余德慧.文化的生成性与个人的生成性:一个非实体化的文化心理学论述〔J〕.应用心理研究,2007(34).
〔17〕Curran,James,MyundJin Park. Beyond Globalization Theory〔M〕// James Curran, MyungJin Park,eds.,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5:3-18.
(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