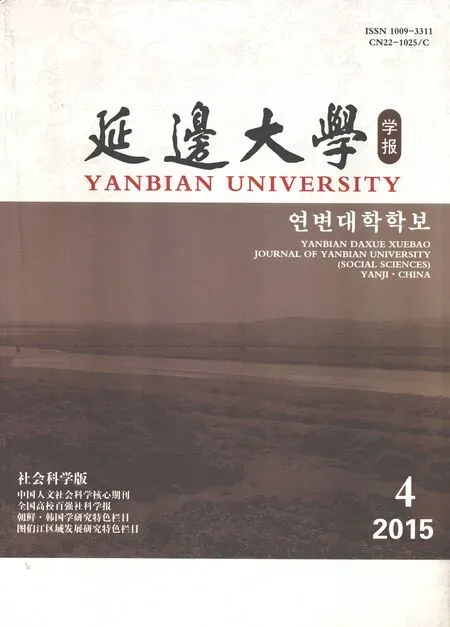韩国高丽朝李奎报对“虎溪三笑”的接受与解读
崔雄权
(延边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在韩国古代文学中,对“虎溪三笑”这一原型意象进行本地化解释的首推高丽文人李奎报。如果说被视为“东国文宗”的崔致远笔下的“虎溪三笑”不过是吉光片羽、李仁老诗文中的“虎溪三笑”也不过是蜻蜓点水的话,那么,李奎报则对“虎溪三笑”不断进行着有意识的、富有意味的诗意言说。同时,因李奎报曾身居户部尚书高位的“榜样的力量”,影响了其后的众多韩国文人对这一典故产生勃勃的创作冲动。故而“虎溪三笑”作为一股创作的内驱力,在韩国古代文坛生发出一系列隽美的诗文作品。而对于李奎报接受和解读“虎溪三笑”典故的研究,不仅可以发现韩国古代文人接受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内在因素,甚而可以发现东亚范围内的中国文化与思想传播的私人机制。而在这里,作为研究对象的李奎报不仅创作了众多与“虎溪三笑”典故相关的文本,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其所蕴涵着的文化审美特征与沉潜为韩国古代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的集体无意识。①范晔《后汉书》卷一一五《列传》卷七五《马韩传》载:“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十月农工毕,亦复如之。”韩国古代文人大量有关“虎溪三笑”典故的书写,可视为“群聚歌舞”的集体无意识的映射。
李奎报生于戊子年(1168年)②有关李奎报的出生年份,多记以公元1169年,而台湾的释圣严在《韩国佛教史略》(载于《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980年第82期,第338页)中则记为公元1167年。实际上,记为公元1169年是不错的,但是按照当下的习惯当记作1168年,比如公元2010年为庚寅年。十月十六日,卒于辛丑年(1241年)九月初二。据传他一生创作了一万多首诗文,大多散佚,现留存的仅2000余篇。1199年,其步入政界,先任微官,后官至宰相,后人称东国李相国。他生活在高丽朝衰败时期,又适逢武臣之乱,晚年又亲历蒙古人的侵略,备尝国家民族内忧外患的痛苦,因此怀有强烈的救国救民、志济天下的理想,但因其禀性光明磊落、刚直不阿而被当权者看作是对朝廷不满的“狂人”。因此,多次遭到权臣的诬告和谗害,屡次被谪贬流放,尝遍官宦生活的坎坷与政治的残酷。却也因此有机会接触现实社会,了解民生苦难,并游历诸多佛教寺院,与佛学结缘。这对其社会政治思想的形成影响深远。
李奎报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在官场上的几经沉浮以及对东渐佛教的沉醉,使得他对“虎溪三笑”典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其文学创作中屡次引用这一典故,并将其放置在韩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予以重新阐释。同时,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通过合情合理的误读,赋予这个典故以新的生命。
一、李奎报接受“虎溪三笑”典故的路径分析
据传,东林寺的创始人慧远法师曾寓居于庐山之下,有言“远公居山,余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不贵贱,不过虎溪”,“倡以虎溪为限”,过此溪流,“辄有虎鸣”,因此,名为“虎溪”。但传说后来“远师尝送此二人,与语道合,不觉过之,因相与大笑”,[1]“虎溪三笑”由此得名,并为后世的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
唐代诗人李白为此留下了相关的诗歌创作,①李白《别东林寺僧》中写道:“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详见《李太白全集》,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353页。由此可知虎溪送别的传说唐已有之。到了宋代之后,石恪创作了绘画作品《三笑图》,苏轼亦留有相关赞文。②苏轼《三笑图赞跋》云:“近于士人家,见石恪画此图,三人皆大笑,至于冠服、衣履、手足,皆有笑态。其后三小童,罔测所谓,亦复大笑。”详见《苏轼书画文献集》,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第89页。由此可知,至中国的宋代,“虎溪三笑”典故已经有了明确的意指,而苏轼的“彼三士者,得意忘言”,即是指三人神情风采的自在与自然,与“魏晋风流”及其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想状况息息相关。虽然有学者指出,“虎溪三笑”典故中的三人,即慧远(334—416)、陶渊明(356—427)、陆修静(406—477),但不是同时代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地相聚一堂。然而,这个典故的隐喻意味在于:以陶渊明喻“儒”,以慧远喻“释”,以陆修静喻“道”。这种看似不可能相聚的相聚,实际暗含着中国古人对儒、释、道三者虽形态各异而殊途同归的考量与认知。而这种超越了思想界限的认识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很早就传入韩国。韩国古代文人接受“虎溪三笑”典故的途径是不同的,其理解也会有差异。而李奎报接受“虎溪三笑”典故的途径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虎溪三笑”典故在韩国古代文人之间的传承。据现存资料来看,崔致远在《嵩山福寺碑铭》中第一次提到了“虎溪三笑”典故,他也由此成为韩国古代最早提及这个典故的文人,③崔致远《大嵩福寺碑名》中写道:“身虽贵公子,心实真古人。始则谢安纵赏于东山,俨做歌堂舞馆。终乃惠远同期于西境,舍为像殿静台。”详见《孤云先生文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1),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180页。但其文章中谢安与惠远的相会则纯属子虚乌有。同时,崔致远也没有开掘出这个典故的深层蕴涵。但是这个典故毕竟由此在韩国正式登陆了,并为以后的韩国文人进一步解读这个典故奠定了基础,其后的李仁老也曾对此有过记载。④李仁老《和归去来辞》中言道:“潜,高风逸迹,为一世所仰戴。以刺史王弘之威名,亲邀半道。庐山远公之道韵尚呼‘莲社’。而仆亲交皆弃,孑然独处,常终日无与语者,三不及也。”见徐居正等编:《东文选》(卷1),汉城:景仁文化社,1968年,第556页。李奎报学识渊博,与李仁老也相去不远,通过崔致远、李仁老等人的诗文,他应该会首先接触到“虎溪三笑”典故,而这个典故在韩国古代文人之间的传承也构成了韩国古代文人接受它的第一链条。
其二,“苏轼热”引发李奎报对于“虎溪三笑”典故的细读。这一点对于“虎溪三笑”典故在韩国文坛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时韩国文坛学苏风气非常盛行,李奎报曾在文章中描述了当时这种风尚之盛,⑤李奎报《答全履之论文书》云:“夫文集之行乎世,亦各一时所尚而已,然今古以来,未若东坡之盛行,尤为人所嗜者也。”详见徐居正等编:《东文选》(卷59),汉城:景仁文化社,1968年,第771页。也坦率地透露了苏诗对自己诗歌创作的影响。前面已提及苏轼是给《三笑图》题诗的第一人。李奎报非常崇敬苏轼,他也一定通过苏轼加深了对于“虎溪三笑”典故的接受和理解,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苏轼则成为连接“虎溪三笑”与韩国古代文人的一座重要桥梁。
其三,新罗、高丽僧人与唐宋僧人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会影响到李奎报对“虎溪三笑”典故的接受。在此需要补充的是,首先,李奎报与当时的韩国僧人有较为频繁而密切的交往。其次,留学中国的高丽僧人的亲见亲闻,为佛学在韩国的深入流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白居易《东林寺诗序》也提到曾亲见有新罗僧隐栖于此。①陈舜俞《庐山记·叙山北第二》:“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东人。”净空法师倡印:《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1),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1030页。李奎报对白居易的诗文也很熟悉,并创作了很多次韵白居易的诗歌,他自然也会通过白居易了解到海东僧人在中国的足迹。同时,高丽朝的金富轼亦在《三国史记》中记载了留唐新罗僧人的一些在华事迹。②金富轼《三国史记》(上)记载:“十二年,春正月,遣使大唐献方物,三月入唐求法高僧慈藏还。”李丙焘校勘,汉城: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48页。[2]另外,与李奎报生活在同时代的僧人释真静,通过留学中国的高丽僧人卓然从南宋浙江延庆寺带回《法华经》,还写下了《法华随品赞》、《天台祖师传》和《净土院赞》等诗文,[3]其中一些诗文引用了“虎溪三笑”典故,如《次韵答柳平章璥》、《奉和答柳平章莲字诗寄呈》等,并效仿慧远在韩国的全罗道康津创建了万德山白莲寺。释真静与李奎报的关系甚好,曾创作过次韵李奎报的诗歌,而李奎报的诗歌中也多次提到了韩国的白莲寺。由此可见,中韩两国古代僧人之间的交流也是李奎报了解“虎溪三笑”典故的重要途径。
二、李奎报与“虎溪三笑”典故
李奎报非常偏爱“虎溪三笑”典故。据李奎报的诗文总集的统计来看,其中直接提及该典故的文本有13篇之多,而以之为寓意背景者,则不胜枚举。③比如,《复和》:“夜深莲漏响丁东,三语烦君别异同。多劫头燃难自救,片时目击总成空。厌闻韩子题双鸟,深喜庄生说二虫。活火香茶真道味,白云眀月是家风。生师演法机锋锐,御冠乘冷骨肉融。邂逅忘形聊得意,不惭当日老庞公。”(《韩国文集丛刊》(卷1),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363-364页)即为前一篇《谢应禅老雨中邀饮》的二重奏,二者的区别仅在于这一篇没有直接提及有关“虎溪三笑”典故的字样而已。以出现的相关意象为例,可概括如下:
(一)“虎吼”意象与李奎报对于“虎溪三笑”典故的化用
李奎报诗文之中涉及到“虎溪三笑”典故的地方非常多,但是他在运用这个典故的时候并没有生搬硬套,而是根据诗文的不同情绪或场景来进行化用,其中“虎吼”意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例如:
赠觉禅老
高掷云间钵,轻浮海上杯。
敲床二虎吼,呪钵一龙来。
水槛青烟湿,风岩翠雾开。
予非陶靖节,莲社日游陪。[4]
在此诗中,诗中颔联的“二虎吼”与“一龙来”喻指“虎溪三笑”典故中三个人物形象谈禅辩理的激烈场景。尾联“予非陶靖节,莲社日陪游”则进一步点明寓意。再如:
赠敏师
青山万里拄筇行,余事能诗继二清。
双眼晓随溪水碧,一身秋与岭云轻。
绕床虎吼狞风散,入钵龙蜿白气生。
本欲避人人自识,他年僧传肯逃名。[4]
在上述诗歌中,“虎吼”与“龙蜿”相对应。“虎床”与“龙钵”对举首见于中国唐代诗人李绅的《鉴玄影堂》[5]一诗。而李奎报则在使用这对具有佛教寓意的词语时,有意用“虎吼”暗指“虎溪三笑”。通常中国古代文人多用“虎啸”,而“虎吼”则是李奎报富有新意的独特书写方式,以“虎吼”对应“龙来”或“龙蜿”意在突出诗歌形象气势的盛大与相关事物的互相感应,其实旨在摹写出形象的风神样貌。于此可见,李奎报对“虎溪三笑”典故的化用不是任意而为,而是充分结合中韩两国的文化实际,却又能别出枢机,显示出李奎报在文学上的深厚底蕴与技巧。
(二)“远公”、“陶陆”与“虎溪三笑”典故的转用
在李奎报的诗文中,出现频率最多、也最鲜明的就是陶潜(陶公)与惠远(远公)的对举。例如,“惠远不禁陶令饮”、[4]“期游远公室,共举陶潜卮”、[4]“他日不辞参入社,远公沽酒引陶公”、[4]“惠远遗风存”、“陶眉不许攒”、[4]“主人接遇一何勤,匡山远老引陶君”、[6]“我今不是攒眉客,投社终随老远公”、[4]“多师有古风,名与远公超”、[4]“陶潜习气犹依旧,尚恐攒眉对远公”、[4]“莫導(道之笔误,笔者注)远公元不饮,尚容陶令劝含杯”、[4]“君不见远公在匡山,亦容陶陆相追随”。[4]毋庸置疑,诸如此类的诗句都是从“虎溪三笑”典故中生发出来的,大多只涉及到典故中的某一个人物。但是,这并不是说李奎报对于“虎溪三笑”典故的理解有偏误,而是对于这个典故中适合诗歌场景与意境的某一方面思想的强调,同时又能兼顾到这个典故的原始意蕴,从而使得诗歌的思想和蕴含更加丰厚与深沉。也就是说,“虎溪三笑”作为原型激发出了诗人胸中郁郁勃勃的诗意情思,进而外化为活灵活现的、带有丰富美感的、意味深远的诗意形象。
(三)“三笑”与“虎溪三笑”典故的直用
相对李奎报对于“虎溪三笑”典故的化用和转用情况而言,其对于“虎溪三笑”典故的直接使用只有一首诗歌,即《又分韵得岳字》:
卜居城东蜗一壳,怯寒无奈缩头角。
偶然乘兴闲出郭,三尺雪深寒蘸脚。
来打禅扉声剥剥,警咳一声虚谷答。
入门眩怳见台阁,似见小空随善觉。
隔林吹火栖鸟落,渴汉求茶泉欲涸。
一夕忘怀这里乐,大胜三笑游庐岳。[4]
从上述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三笑”显然是直接使用了“虎溪三笑”的典故,其寓意亦在其中。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奎报在诗歌创作中对“虎溪三笑”典故的运用极为纯熟自然,对“虎溪三笑”典故中各个要素的挖掘与使用,亦显得游刃有余,可谓造意造语神采兼备。那么,李奎报又是如何将这一典故有效地植入韩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甚至韩国民族文化传统之中的呢?
三、李奎报笔下“虎溪三笑”的审美特征
(一)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想象与理想
李奎报笔下的“虎溪三笑”典故多将儒者身份的陶潜与释者身份的惠远放在一起来考量,而作为道家象征的陆修静只提及一次,还是与陶、陆并称。这并不意味着李奎报与道教思想没有密切的关联,仅凭着一首诗作来加以肯定或否定显然都不客观。
有关高丽时期的社会思想,韩国学者李能和曾指出,“高丽存在道教与佛教混淆的道佛行事,其中典型一例即为类似佛戒实为道教斋醮仪式的‘八关会’”,“这一高丽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姜邯赞、韩惟汉、李茗、郭舆和崔谠”。[7]“其中的崔谠,一度曾在崔氏武臣执政时期担任相国一职并为耆老会的核心人物。李奎报虽未与其有过直接的接触,却不乏诗歌上的交游唱和。”[8]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三十八至四十一中的道场斋醮疏与祭祝文即为反映浓郁的道教神仙思想的典型代表。在《赫上人凌波亭记》一文中,李奎报针对人们批评佛门庙宇楼台的浮夸羡侈反驳道:
予曰:“非也。”且人情之皆欲至于青莲佛界、白玉仙台者,无他焉,盖以其地之清净无尘故耳。夫地之清净,则心亦尔也。未有心清净而为浊恶热恼之所乘者也。由是观之,虽在人间世上,苟得值地之清净,而有以汰其心虑,则是亦佛界也、仙台也。何羡于彼哉?由是而习焉,其蹈佛、仙境界,亦其渐也。[4]
意即“青莲佛界”(佛)与“白玉仙台”(道)之“清净无尘”皆为“汰其心虑”罢了。李奎报在《自贻杂言八首》其六中,也曾明确指出:“化邑由来贵清净,故看吾祖五千文。”[4]另外,在《明日朴还古有诗,走笔和之》中还曾言道:“释老本一鸿,凫乙何须分”,[4]以及《是日宿普光寺,用故王书记仪留题诗韵,赠堂头》云:“若将释老融凫乙,莫斥吾家祖伯阳”,[4]还有“形全与神全,要问漆园吏”[4]等等。
这些诗文表明李奎报对道教的祭祝文书与斋醮仪式相当熟悉,①李奎报《又寄安处士手书》云:“其余四六,皆祷佛祈神之文,不足烦采览,故不敢录呈。”详见《韩国文集丛刊》(卷1),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571页。对其清静无为思想也相当认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李奎报的思想体系中,道家思想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极,如在他的诗歌中也有着“唯愿一入紫微门,奉谒玄元太上君”[4]的夙愿,这绝不是一时的冲动。
出身名门、九岁属文、“时号奇童”[9]的李奎报有着浓郁的“平生忧国深”[4]式的儒家立身扬名的思想。诸如在《开元天宝咏史诗(并序)》中对统治者的讽谏、在《麹先生传》中对士大夫的警示、在《东明王篇(并序)》中对创建国家的先祖的赞叹等等,无不显露出李奎报深沉的儒者情怀。在《同前二首,此二篇朴君皆押旁韵,故依韵》中,诗人就曾直言“早怀济物情,暂隐陶潜酒”。[4]
至于李奎报的佛家情怀,则主要表现在其晚年时期。在《东国李相国集》中,仅诗歌方面涉及佛家思想的就多达250余首,此外还有多篇疏祭文和墓志。[8]这说明李奎报意识中的佛家思想也是极为突出的。
可见,在李奎报的精神世界中,儒、释、道三种意识并存,相融不悖,形象地演绎了崔致远对韩国古代“风流道”文化哲学思想的诠释。这也生动地传达出韩国古代文人对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文化想象,并逐渐沉积于韩国古代文人的潜意识之中,成为他们进行创作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文化想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在他们的意识深层中影响着其后的韩国古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与思想路向,李齐贤、李珥、李滉、郑澈等莫不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李奎报有3次儒、释并论,分别是《诵楞严经初卷偶得诗寄示其僧统》:“儒释虽同还小异,时凭法主略咨疑”、[10]《卧诵楞严有作二首》:“儒书老可罢,迁就首楞王”、[10]《南轩答客》:“况复儒与释,理极同一源。谁驳又谁纯?”[10]这分明就是李奎报笔下的“虎溪三笑”典故何以儒者的陶潜与释家的惠远对举的最好注脚。
(二)以禅解陶的诗意创造
李奎报在《同前攘丹兵天帝释斋疏》中指出:“我国是四洲之仁方,敬佛归僧之有渐”。[10]另据释圣严考证,新罗善德王(唐太宗时期)时代禅宗初传韩国。新罗末高丽初,禅宗勃兴。[11]据《白云山内院寺事迹》云:“太祖敕诸州,建丛林,设禅院,造佛造塔,几至三千五百余所。”[11]如此浓厚的禅宗思想氛围对李奎报的浸染是可想而知的。此外,还有高丽时期的“苏轼热”影响,苏轼可谓以禅解陶的第一人。以上两点可视为李奎报以禅解陶的客观外因。主观内因自然是源于李奎报“我狂渐息堪禅缚”[4]的心性修炼。其在《又用东坡诗韵赠之》中直陈道:“我亦参禅老居士,祖师林下旧横枝。”晚年李奎报嗜颂《楞严经》,②李奎报《有乞退心有作》中就写道:“何以修净业?楞严经在口。”详见《韩国文集丛刊》(卷2),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1143页。如前面所举诗句中的“儒释虽同还小异”、“儒书老可罢,迁就首楞王”,等即为诵读《楞严经》后的感悟。此外,其亦常读《法华经》,曾有三日颂二卷的惊人之举。其在诗中言道:
弟子居士字春卿,稽首妙法《莲华经》。
劫劫生生愿受持,傥见舌底青莲生。[4]
李奎报之所以喜爱并记颂《法华经》,是因为受到天寿寺大禅师智觉的引导。而智觉在听其“背经颂之”后叹曰:“老僧自少业是经,犹未颂一卷一品。而子之捷若是,岂宿劫所习耶?”[4]意为不仅仅是诗人记忆力超人,更多地源自于李奎报具有非同常人的慧根与佛缘。也就是说,李奎报的学禅、理禅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如诗人曾言:“在家未碍先成佛,披毳何须要作僧”。[10]在记颂87500五言的《法华经》后,李奎报坚定而自信地言道:
若人四读未拆理,心犹其心舌其舌。
是舌非舌心非心,然后乃得真寂灭。[4]
此中的“心舌论”便充满了佛理禅机。③释圣严认为,李奎报仍落于小乘的空观。详见释圣严:《韩国佛教史略》,《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980年第82期,第338页。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在有关“虎溪三笑”典故的书写中,诗人笔下的陶渊明雅俗兼具、痴狂并举。例如,通过《赠觉禅老》末句对陶渊明能够让“莲社日游陪”的赞叹,而从侧面表达了白莲社的禅师们对陶渊明这位儒士的肯定。李奎报笔下所谓的禅,既有玄思机变,更不乏随遇而安的生活展现,最富有代表性的如《谢应禅老雨中邀饮》:
数年飘散各西东,今日樽前一笑同。
乍把铜人相话旧,更凭石女苦谈空。
篆畦终日清抽穗,灯蘂侵宵巧缀虫。
浓翠滴窗垂柳雨,暗香扑地落花风。
醉翁情兴狂于白,禅老行装懒似融。
他日不辞参入社,远公沽酒引陶公。[4]
在这首谈古论今、活色生香的唱和诗中,李奎报最后引入“虎溪三笑”这一典故,并以一“参”字道破天机,原来远公沽酒乃为引陶公(潜)前来参禅,而且极富情趣的是大德高僧远公(惠远)竟然亲自沽酒,这恰恰反映出二人都深明禅机佛理,即“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可见,李奎报于陶渊明近乎颓废的“陶令饮”中,感悟出那种更具蓬蓬勃勃的生命意义的诗酒风流。同时,以禅解陶也显示出李奎报构筑诗歌形象的匠心独运与诗意。
(三)“诗酒风流”的背后隐藏着诗性的悲患意识
在韩国汉文写作圈中,“诗酒风流”的称谓为李奎报首创。在《城北杨生林园赏花吟》一诗中,李奎报言道:“君不见,翰林工部醉死各何之?诗酒风流留付吾侪嬉。对花把酒且高歌,无情风雨不肯为君留一枝。”[4]可见李奎报常以“诗酒风流”自赏,所以在《偶吟》中,诗人言道:
无酒诗可停,无诗酒可斥。
诗酒皆所嗜,相值两相得。
信手书一句,信口倾一酌。
奈何遮老子,俱得诗酒癖。
酒亦饮未多,未似诗千百。
相逢乃发兴,是意终莫测。
由此病亦深,方死始可息。
不唯我自伤,人亦以之责。[10]
这里,诗人较详细地诠释了“诗酒风流”的深层内涵。首先,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即“无酒诗可停,无诗酒可斥”;其次,饮酒与赋诗都是摆脱名缰利锁,甚或世俗礼法,而直抵生命本原的精神探求之举,而这些则来自于陶渊明。
一般说来,我们想象中的“虎溪三笑”场景应突出一个“笑”字,而李奎报却大肆渲染其中的“饮”。不仅如此,还将远公(惠远)纳入其中,着力描写其对陶渊明的“不禁”、“沽酒”、“接遇勤”及“容劝杯”等一系列富有意味的描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诗作主要是写给僧侣朋友的唱和之作,故以远公推许对方;另一方面也恰恰体现出诗人抓住了陶渊明“诗酒风流”的精魂所在,也是对陶渊明深层精神世界的诗意传达。
有关陶渊明的嗜酒,同样具有佛教情怀的唐代诗人王维曾指出“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12]其后杜甫则首先将陶渊明的“诗酒风流”理解为“宽心”与“遣兴”。而李奎报在“虎溪三笑”典故中所言说的“诗酒风流”则兼具儒家的养性、佛家的忘性与道家的任性等生命特质,饮酒即为这一风流精神的外在表现。另外,李奎报笔下的“虎溪三笑”所展现的“诗酒风流”还有夫子自况的意味。也就是说,诗人由赞赏陶渊明的“诗酒风流”,进而展现自我以及高丽文人的“诗酒风流”个性。
李奎报曾言道:“平生唯酷好琴、酒、诗三物”。[4]也许李奎报虽喜欢饮酒,但酒量不够好,也曾半夸耀半自嘲自己为“癫狂”。①李奎报的诗歌中有不下4处出现了“癫狂”的字样,其中的代表作为《儿三百饮酒》:“莫学乃翁长醉倒,一生人道太颠狂。”详见《韩国文集丛刊》(卷1),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346页。李奎报之所以常常借酒抒怀,可能是因为酒可以增加诗人生命的密度,而诗则又可以延展诗人生命的长度。故有“病谙诗魄减,醉觉曲神尊”的慨叹,[4]更有“老于诗世界,谋却酒生涯”[4]的自豪。诗作《次韵东皋子用杜牧韵忆德全》的“归去追彭泽,佯狂忆翰林”,[4]即为李奎报亦为高丽文人“诗酒风流”的生动写照。
“诗酒风流”在汉语言文化圈中,有着丰富的生命味道与审美韵味,“诗”与“酒”的结缘是汉文学创作中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致。诗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其本质之一在于“言志缘情”。酒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其对于人的精神作用之一就是可以“解忧”、“忘忧”。二者殊途同归,最终都指向了个体的生命存在。个体通过移情于诗酒,可以宣泄心理郁结、释放生命的自由、使失重的心灵复归于平衡。二者的完满结合,可以让个体的生命与精神达于“风流”的极境。然而,对于有社会承担的诗人而言,“风流”只是生命的驿站,“悲患”才是其生命的旅途,但悲患绝非悲观主义式的,而是怀有诗性的清醒。所以,“诗酒风流”的背后,始终伴随着诗人对社会历史、个体生命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那挥之不去而又绵绵不绝的悲患意识。这种浓郁的悲患意识,即是一种社会道德的自律,也是一切有良知的文人的真实情怀,终其一生,无法忘却,正所谓“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四)隐逸理想及其背后的意象原型
李奎报在其长诗《走笔赠威知识》中曾表达过自己的隐逸思想。[4]例如,“早年抽身名利门,有如鱼鸟不可囚笼池”传达出了陶渊明式的“久在樊笼里”的困惑;而“一朝勇去白云里,采松食叶聊充饥”则表达了“复得返自然”的畅快。同时,这首诗也描写了他期望中的隐逸生活,即“拨泥踏水来扣扃,抚掌迎笑欣扬眉”般的邻里互动与“坐客况有河秀才,铛脚相对语忘疲”似的人生交往。然而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于是李奎报无奈地发出“明发师当去,我岂独受名缰縻”的慨叹。世间的名利牵绊住了李奎报的手脚,也牵绊住了他的心情,使他很难或者说不能随意地发挥与张扬自己的性情。他虽身在高官与厚禄之中,但也一直在培育着自己的真情、至性。诗人的这些描写集中在平淡生活带给诗人的精神上的轻松与自在上,而在这样的描写当中也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隐逸情怀,其中也有佛、道的生命情绪。李奎报的《十九日宿弥勒院有僧素所未识置酒馔慰讯以诗谢之》也表现了他“归去”的想法。[4]其诗中的“君看今人交,有似秋云飘”一句不仅是对于现世的讽刺,同时也是对于现世的不满,他希冀着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沟通与理解,但是却始终无法实现,使诗人产生了“归去”的想法。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李奎报的隐逸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甚至是世间万物相互和谐的思想,或者说诗人将这样的生命思想与情绪隐藏在了隐逸思想的背后,并成为了诗人隐逸理想的动力源泉。超尘脱俗、归隐田园的志向不仅表现了李奎报的隐逸情致,也有对儒、释、道三教合流或消解的思想倾向,这很有可能受苏轼、黄庭坚等宋代文人学者所持有的较强的三教统合观念的影响。换句话来说,在李奎报这里,“虎溪三笑”典故中有三教合流的思想,但是也有“归去来”的强烈愿望。在《走笔赠威知识》一诗中,诗人最后一句以“虎溪三笑”典故作结,“君不见远公在匡山,亦容陶陆相追随”,儒、释、道之间的和谐,在李奎报看来,实际上也就是君臣、臣臣之间的和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李奎报对“虎溪三笑”的这种解读对其后的韩国古代文人影响很深,如高丽末期的元天锡,①元天锡《题三笑图》诗曰:“一笑乾坤窄,忘言过虎溪。”详见《韩国文集丛刊》(6),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149页。朝鲜朝的成三问、②成三问《三小图》诗曰:“神交那复有形骸,偶过溪桥一笑开。千古风流如昨日,宛如相对首长回。”《韩国文集丛刊》(11),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189页。徐居正③徐居正《题双林心上人所藏十画》中的《虎溪三笑》诗曰:“庐阜高僧卧不出,风流二老时往携。问渠三笑笑何事?不觉今朝过虎溪。”见《韩国文集丛刊》(11),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50页。和郑惟吉④郑惟吉《虎溪三笑》诗曰:“山中远公瘦鹤姿,久向风尘头已掉;飘然陶陆双鹄志,忘形久已期同调。”见《韩国文集丛刊》(35),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445页。等众多文人均在诗文中不同程度地讴歌过这种“千古风流”。
四、结语
实际上,李奎报对中国“虎溪三笑”典故的接受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其中有中国的影响痕迹,包括对于苏轼等人所阐释的“虎溪三笑”典故的接受,同时也有本国文人崔致远、李仁老等人的传统。在这种双文化与双传统之中,李奎报有意地塑造了一个自我的“虎溪三笑”典故,并成就了“虎溪三笑”典故在东亚文化范围内的传播。
按照比较文化学的相关理论来说,一国的文人学者在接受另一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时往往会有一个筛选的过程。他们筛选出异国形象的某些特征以适用于自己的主观描述,操纵、控制并最终将他者改塑成如己所愿的那种形象。异国形象的塑造通常以实际客体为参照物,基本遵照客观现实叙述,但在其中会注入作家自身的思想和文化意识,而在这个过程中,异国形象通常会被弱化并不断强化自己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因子。高丽文人李奎报在接受中国“虎溪三笑”典故的过程中,一方面注重接受其中国的原意,另一方面又将其与本国的现实以及自身的思想与情感状态联系在一起以加深其思想内涵,也正是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李奎报在其创作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孕育着自身文化与思想气息的“虎溪三笑”典故,并影响了一代代的韩国古代文人。
[1]陈舜俞:《庐山记·叙山北第二》,净空法师倡印:《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1,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1028页。
[2][韩]金富轼:《三国史记》(上),李丙焘校勘,汉城: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175页。
[3][韩]许兴植:《真静国师与湖山录》,汉城:民族社,1995年,第118页。
[4][韩]李奎报:《韩国文集丛刊》卷1,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300、302-303、307、312、363、378、462、357、358、431、374、366、544、389、378、394、343、323、383、369、365、491、491、491、363、312、503、336、398、302、374、357页。
[5]陈贻焮:《增订注释全唐诗》(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860页。
[6][韩]李奎报:《韩国文集丛刊》卷8,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379页。
[7][韩]李能和:《韩国道教史》,金镇英:《李奎报文学研究》,汉城:集文堂,1984年,第53页。
[8][韩]金镇英:《李奎报文学研究》,汉城:集文堂,1984年,第53、56页。
[9][韩]李需:《东国李相国文集文集序》,《韩国文集丛刊》卷1,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238页。
[10][韩]李奎报:《韩国文集丛刊》卷2,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186、189、195、123、159、232页。
[11]释圣严:《韩国佛教史略》,《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980年第82期,第324、325页。
[12]王维:《偶然作》(其四),陈贻焮:《增订注释全唐诗》(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8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