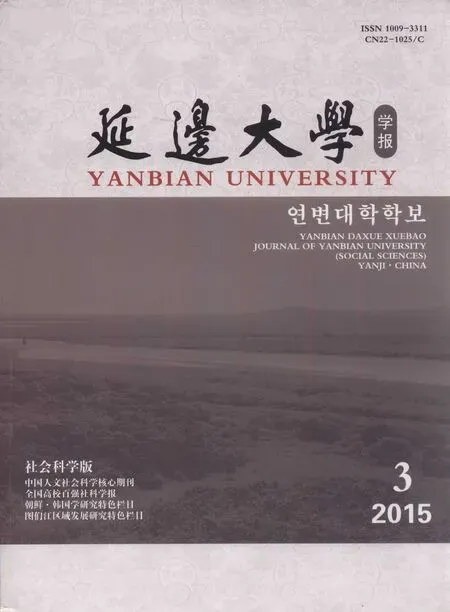东亚秩序与儒学的世界意义
李宗勋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在东亚历史上曾出现过数次较为固定的东亚秩序,即传统时代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近代以来以日本强权政治为主导的东亚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冷战型东亚秩序等。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中国、韩国的崛起和东南亚各国的急速发展,以及东北亚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复杂多变,东亚地区又面临着构建现代东亚新秩序的新时代。当代国际社会,已与传统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和列强时代迥异,已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因此,构建新的东亚秩序意味着以《联合国宪章》为基准,以强劲的巨大经济体或联盟为主导,构建各国互惠互利的国际秩序。而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不治治之”、“仁礼”等思想意识也许会成为构建东亚新秩序的理念和世界价值取向。
一、古代东亚华夷秩序是儒家思想的产物
古代东亚华夷秩序起源于传统华夷观念。何谓华夷呢?在古代,“华”,指中国。《国语·鲁语》:“以德荣为国华”。韦昭注:“华,荣华也”。孔晁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1]即言华夏是讲礼义的大国。“夷”,据李乐毅所著的《汉字演变五百例》解释为“‘夷’原是古代民族名。甲骨文用‘尸’字作‘夷’字;金文‘夷’字是一个人形,身上带着矰(一种带有丝绳的短箭),表现了这个游牧民族的特征”。[2]现在学者释“夷”为“带弓箭的人”。毛泽东在诗词中写道:“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族是带弓箭的民族的代表,“夷”指作为带弓箭的人,泛指游牧民族。后来将蛮、羌、狄、夷等统称为“夷”。“华夷”体现了中央与四方的关系。据《说文》所解:华夏为“中国之人也”。清代段玉裁注:“以别于北方狄,东北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1]王绍蘭在《说文段注订补》中说:“案亦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之人也”。于省吾认为依据《说文》多家注解,都是以中华处于四夷之中心而得名,其实自商代以迄西周,中国与四夷已见雏形,从东周以来就完全形成了南蛮、北狄、东夷、西羌的对称格局。而华夷的“秩序”是由古代的“五服制”深化而来的。“五服制”据《国语·周语上》所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对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3]这些就是说,先王的制度:王都四周千里区域称为甸服,甸服外五百里属于侯服,从侯服到卫服统称宾服,蛮夷边远的地区称为要服,戎狄荒凉的地区称为荒服。属于甸服的供奉日祭,侯服的供奉月祀,宾服的供奉享献,要服的供奉岁贡,属于荒服的则有朝见天子的义务。每天一次的祭、每月一次的祀、每季一次的享、每年一次的贡、终生一次的朝见天子。有不供日祭的,天子就要反省自己的思想;有不供月祀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所发布的号令;有不供每季享献的,天子就要修明他的政令和教化;有不贡献每年的贡品的,天子就要修正名分的尊卑;有不朝见天子的,天子就要内省自己的德行,按此顺序完成了以上自查规定,仍有不尽职的,才能动用刑罚。这一先王规制逐渐演化为先秦华夏“以王畿为中心向外层层扩散的特征,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多重内容”。[4]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自然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华夷秩序。夷,在古代文献中的表达没有贬义,是对以华为中心的夷、狄、蛮、戎周围四方所居民族的表述。由于华夏文明的不断发展,四周所居的夷、狄、蛮、戎的相对落后,出现了中心与周围的差别。
中国古老文明是华夷秩序形成的基础。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文明化身,他所开创的儒学一直得以传承下来,孔子成为儒学的代表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老子倡导的“道”显然已行不通,而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显然有了可用之处。“在一个大道废驰的时代,求道当然不可放弃,但也不能强求,故而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变通办法,并把可以由人力企及的‘仁’拔高到伦理关系中的最高范畴,作为他救世的核心原则”。[5]孔子“仁爱”思想为春秋战国以后的礼制形成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因此中国文化被冠名为礼乐文化(即我们现在所讲的儒家文化)。什么是“礼乐”呢?史学家范文澜的解释:“礼用以辨异,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礼使人尊敬,乐要人亲爱”。[6]由于最初的“乐”只是唱诗奏乐,只是作为情感的粘合剂,其作用较为有限,因此出现了“礼崩乐坏”的乱世,孔子总结历史教训对“乐”又进一步丰富其内容,将“仁爱”思想加入其中,将“礼乐”发展为“仁与礼”合二为一,互为补充,这样其内涵就更加丰富。这种丰富内容从孔子整理“六经”(即《诗》、《乐》、《礼》、《书》、《易》、《春秋》)便可见一斑。其整理“六经”的指导思想反映出孔子的仁的人本哲学,目的是通过文献典籍的整理,来传道施教,即“以把‘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精神体现在文献中”,[7]进而传教世人,稳定社会。孔子一生以维护、继承、发展周礼为己任。这里讲的绝不是孔子以简单的恢复周礼为己任,而是在实践中践行和发展周礼。所谓“克己复礼”的“复”是“践行”之意,是在实践中与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不断践行和发展周礼,这一观点早已有人阐述过了,在此不再赘述。
“周礼”是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是从奴隶制社会跨入封建制社会的一个质的飞跃。“周礼”在周代是作为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而存在和延续的,并在整个华夏民族势力范围全面推广。在当时是否坚持“周礼”是区别“诸夏”与“夷狄”的分水岭。在当时管仲作为改革家辅佐齐桓公建立了霸业,虽然有些方法有失“周礼”,孔子颇为不满,“但孔子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还是十分称许的,并且特别指出它在‘夷狄’与‘诸夏’斗争上的意义,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从维护周礼到自觉地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在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是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来看,把管仲的贡献提到‘如其仁,如其仁’的高度”。[7]其实孔子的华夷之辨和对管仲的“尊王攘夷”之策,与“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思想是对立统一的。其目的是华夷各居其位,谁也不要侵犯谁,深含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在《左传·定公十年》“齐鲁夹公之会”中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华夷”为了正常会盟防止万一出现冲突,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这其中所说的“文”与“武”都是为维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念的一种手段。当这种手段揉合到“华夷”关系处理上就是一种“秩序”,其中强制性硬实力是由武备衍为礼制,柔性的软实力已由“文事”衍为仁爱。孔子“华夷”之辨不是为辨而辨,目的在于如何处理好“华夷”关系,为了稳定天下,因而产生了“华夷”秩序。关于司马迁“华夷共祖”之说也不无根据,秦国僻处西方,与我狄杂处,很少参加诸侯会盟,诸夏对秦也视为戎狄。楚是南方大国,因不用“周礼”也被诸夏视为“蛮夷”,从而可见“华夷”的交叉就有血统交叉的必然性。据《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夷有九种,在古代,九不是实指数字,而是泛指多数,如东夷族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部落,而是由大大小小很多个部落组成的庞大的部族和部落联盟,其中也有夏族部落。根据史料记载:有风姓部落、姜姓部落、嬴姓部落、姚姓部落等。东夷族各部落之主以龙、蛇、凤、鸟、太阳为图腾,以鸟类图腾居多。在东夷族的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部落首领有太昊、蚩尤、少昊、大舜等。根据《尚书·夏书》、《史记·夏本纪》、《竹书纪年》等书记载,夏代不同于夏族的族群有很多,如东方有埚夷、莱夷、淮夷、风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阳夷、方夷;西方有昆仑、析支、渠搜;北方有皮服鸟夷;南方有卉服鸟夷、有苗、和夷、裸国。这些族称都是根据地名、衣着而得名,各居不同地域,而夏朝政权面对这种不同地域族群,实现了周边民族的大融合。[8]商代中原地区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到了周朝,中原华夏族也从戎狄、夷蛮等少数民族中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经过春秋战国500余年的斗争与迁徙,进入中原地区的蛮、夷、狄、戎已大部分融入华夏民族之中,成为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司马迁的“华夷共祖”之说是有历史根据的,九九归一,天下一家是“‘华夷’秩序”形成的最基本理念。
华夷秩序在中国较早体现了帝国理念,早在西周就形成了。《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词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了《孟子》中成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孟子·卷九·万章上·第四章》)。这就是西周王朝分封制的真实表述。[9]周朝以后,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这又是一次质的飞跃,同时产生以土地为纽带、军事等级制、律令制等封建体制为主体的华夷秩序,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可见其进步意义的恒性在纵向跨度上有久久之功。当今海内外学者研究华夷秩序,各自从不同角度研讨,有的叫“册封体制”、“天朝礼治体系”,还有的叫“中国的世界秩序”,当然这都是从历史角度而言的。当今研究华夷秩序避不开其历史局限性,在夏商时期奴隶制体制下,华夷秩序无非是强调一统天下,也就是帝王天下问题。而从西周跨进封建体制之后,出现了以中国帝王为最高领主的层层土地分封,所以帝王一统天下的分封是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对应历史发展的意识形态是进步的,进步性与局限性是社会发展的对立统一。《庄子·天下篇》说:“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10]庄子说的是有限的物体,但它都是由无限小的单位组成的,因此可以无限分割。而笔者借用庄子这句话,讲的是任何事物都应分割地看,也叫剖析。对“日取其半”是人为的方法,事物纳入到历史范围中认识就不一定是等量折半,也可能是三七开,也可能四六开,也可能一分为二,还可能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四等。一个华夷秩序的建构,一部分是承前人的智慧,一部分吸取当时社会的需要,一部分还预示着未来发展的需要。这就一分为三了,总之按庄子之说,分是必然的,分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所以说,前面谈的华夷秩序的进步性与局限性,本身是一种“分”,而这种“分”永远在过程之中,但有一点,即进步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与时俱进的不断扬弃中会永远大于局限性,而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分割却是无止境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固有规律。万万不可因其局限性而抹杀它的进步性,特别是对待延续二千多年的华夷秩序。
二、华夷秩序是东北亚的,也是世界的
“华夷”秩序,源起于中原华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后来发展为以华夏为中心,向外层层扩展为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向周围各国开放,特别是在东北亚,也包括在东南亚形成了最典型的“华夷”秩序,同时,也对西亚、中亚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影响和刺激了欧洲等西方世界的文明发展。
上古华夏族体形成时期,中国中原地域生产力水平尚极为低下,但自然条件恰恰最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生息。正如《何尊》所记载的“宅兹中国”,[11]也如《诗经》所载的“惠此中国,以馁四方”。因此,居此地域生活的华夏民族以此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被视为世界之中心,而周围的“南夷北狄,往来不绝如线”。秦统一中国后为“华夷”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前提条件,汉承秦制,经过400年两汉帝国的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社会快速发展的盛世。两汉时期,社会繁荣发展到了高峰期,对外不断扩大政治影响,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需要。在汉帝国的北方是广袤无垠的北方大草原,自然环境恶劣,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向南入侵中原农耕地带,中原汉族王朝的“外侮”成为永恒的主题。中原汉族王朝基本处于被动的守势。因此,华夏民族面向中国北方的发展是没有出路的。而面向东方,毗邻朝鲜半岛、一衣带水的日本及琉球,再往东是广阔的太平洋。在太平洋的东岸,那时印第安文明发展落后,面对辽阔太平洋相隔,当时简陋的航海技术无法使东亚与太平洋彼岸相联。因此,只有东北亚这个地域条件,才具有构建华夷秩序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厚重的儒学文化优势和文化传承的历史优势,而这为在东北亚构建华夷秩序提供了平台。朝鲜半岛在三韩时期,“公元44年(东汉建武二十年),韩廉斯人苏马偍等诣乐浪郡朝贡,光武帝因封苏马偍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四时朝谒”。日本则在东汉初年,即“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后汉书·光武帝纪》)。安帝永初元年(当日本景行天皇三十七年,即107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后汉书·孝安帝纪》)。倭国或倭奴国还接受了东汉皇帝的赐封印绶。汉帝赐封的“汉倭奴国印”是华夷秩序早期的有力证明。[11]据日本上垣外宪一所著的《日本文化交流小史》中所阐述的,在纪元历史时代之前中国文化就融入到日本列岛的文化中,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稻田耕作为中心的弥生时代文化,其文化主要来源于中国江南地区,是由朝鲜半岛传播至北九州,其后又过了百年左右时间,迅速扩展到了日本东部地区。中国《汉书》所记载的“乐浪海中的倭人,分散为百余国”,这恰是记载着“弥生时代中期的日本还处于小国分立的状态,而各国之王要向中国(当时称做‘汉’)朝贡的史实”。[12]当中国进入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41年,前后不到40年,西汉社会发展极为迅速,国泰民安,繁荣昌盛,据司马迁《史记·平准书》记载:“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杨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13]如此强盛的大汉帝国,辐射邻邦,尤其是张骞通西域,扩大了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力。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今帕米尔是它的一部分)以东,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的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一部分,以及东欧和北非的个别地方,是中国当时就地理知识所及对“西”方地区的泛称。
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汉族和西域各族及相邻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关系日趋密切。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没有铸铁技术,而中国将冶铁技术传入西域。中国又是以盛产蚕丝和丝织品而闻名世界,被称为“丝国”。而张骞通西域,携带金、帛等价值成千上万的馈赠礼物,经由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到达了奄蔡、安息、条支和犁轩等国。从此后,中亚、西亚各国也经常派遣使节到中国汉都长安,开展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汉朝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一条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大量丝帛锦绣不断西运,同时西域的“珍奇异物”也输入至中原。与此同时,汉代又打开了南海水上通道,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地区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逐渐形成了“华夷”秩序的外圈,并同中亚、西亚、地中海世界相连,当时在西方与汉帝国并驾齐驱、处于同一文明梯次的有古罗马文明,二者交相辉映,形成古典“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古罗马帝国在中国古籍记载中被称为大秦,说明汉代中国人已熟知古罗马,也许古罗马帝国的文明和威力也促使中华帝国向更高层次的文明发展,并不断感召东北亚各国与中国中原王朝进行接触,促使东南亚、南亚,特别是东北亚积极参与“华夷”秩序。中华帝国与东南亚、南亚广大海陆地区星罗棋布的邦国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海陆丝绸之路网,推动了古代东亚一体化进程。
可以说建立华夷秩序的最典型还是在东北亚,因为在历史上所处的毗邻的地理位置就有利地定格在“华夷”秩序之中,同时东北亚各地区各国间还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关系,其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促进成为传统时代历史发展的主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东北亚地区整体进步和快速发展。中国早期文明,也直接深刻影响朝鲜半岛,进而加速了朝鲜半岛的文明进程。古朝鲜时期,中原人与半岛人之间已开始大量往来,随着商朝的灭亡,一些东夷族人迁移至中国北方、辽东及朝鲜半岛。“从公元前108年至公元313年的421年间,代表中国中原铁器文化的乐浪文化对朝鲜半岛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国大陆铁器文化的传播,业已存在于半岛诸多部落联盟或早期国家迅速发展成为古代封建王朝,先是在鸭绿江流域及半岛北部地区形成高句丽王国,后又于半岛南半部在三韩的基础上出现百济王国和新罗王国。”[14]当中国发展到盛唐时期,也是朝鲜半岛统一新罗王朝时期,当时新罗人经常来中国学习律令制度和先进文化,促进了新罗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新罗经常派使节出使唐朝,以朝贡贸易的形式向唐输出果下马、牛黄、人参、朝霞䌷、美发、镂鹰铃、海豹皮、金银等,并换取中国的丝绸、书籍等先进文物。民间贸易也异常活跃,新罗商人大量活跃在山东半岛和长江口的许多港城,并形成了新罗人聚居区“新罗坊”。而“新罗坊”在中国有多处。唐代的中国,雄强一世,气宇恢宏,贞观大治、开元全盛,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璀璨辉煌,流光四溢,对周边以及远方的各国及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和吸引力。真可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世界敬仰,万国朝拜,当时新罗人的朝贡次数远远超出其他各国。所以说,我们的近邻朝鲜半岛,就是华夷秩序中的基本成员,也是“华夷”秩序最早成员之一。直到明清时期,二者关系不断促使华夷秩序发展完善。
在东北亚地区的日本,也是较早进入古代华夷秩序的国家。早在汉代,中国与日本列岛各国关系密切,特别是进入盛唐,日本是华夷秩序下最大受益者之一。那时,“日本向中国又大量派留学生、学问僧,可称日本人才发源之路,大量汲取中国先进文化,史称日本书籍来源之路。随着历史的发展,中日之间官方交往虽然有间断,但民间的经贸往来,特别是文化交流从未间断过。日本在亚洲最先走上了近代文明,也是中华文化乳汁哺育因素在其中。李大钊曾指出:‘日本者,吾中华之产儿也。考其立国千年之历史,一切文化制度传袭上国者。是则尔岛自开国以来,吾华无一日不负教训诱导之则’”。[15]李大钊的话虽有一丝大国主义意识隐含其中,但也恰恰证明了日本在历史上已经完全纳入了华夷秩序之中。还有琉球,当时是较为独立的封建王国,与明朝建立了非常紧密的朝贡册封关系,并同样生存在东北亚儒家文化圈内。总结东北亚的华夷秩序的发展历史,按史学家何芳川的话来说,应列入“华夷秩序的内圈”。“华夷”的外圈,通过汉代张骞通西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扩大了“华夷”秩序的影响,这些外扩的地域可以称为“华夷”秩序的外围圈。通过外围圈,凸显了东北亚“华夷”秩序的核心作用。
总之,从国际秩序角度来说,在传统时代的历史上不但有中华文明的华夷秩序,也出现过罗马、波斯帝国文明的世界秩序,还有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与穆斯林文明,亦称穆斯林秩序。这些世界秩序的不同而合,构成了国际秩序。国际秩序包含着“华夷”秩序,“华夷”秩序是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华夷”秩序是东北亚的,也是世界的。
三、“华夷”秩序对今日构建环球新秩序的意义
纵观历史,由古至今,就世界秩序而言,有所谓的罗马帝国式、阿拉伯帝国式、奥匈帝国、中华帝国式、大英帝国式,以及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等,但大多在很短时间内就消亡了,唯独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不断发展完善,延续了二千多年,这必有其深层的内在逻辑。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告诫后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而真正的史学是对历史的“领悟”,获取的是“人文智慧”。[16]史学就是智慧追求之学。“华夷”秩序既是历史的,也是今天的,是今天的过去,又是未来的昨天。有昨天、今天,才有明天。预知未来的国际间秩序,首先要懂得过去的国际间秩序,由古至今去思考未来。
在中国最早形成的天下体系是“五服制”,而后发展为华夏体系以及东亚体系,也就是本文所讲的“华夷”秩序。最早的“五服制”源于《尚书·禹贡》。书中记述大禹治理九州四海,然后封土赐姓,建立方国,强调要敬修德业,不能违背天子所定的原则,[17]亦即以德治天下的儒家仁德理念。在东亚历史上,中华帝国不管如何强盛,对外一直坚持平稳、怀柔、不干预内政、调解纷乱为主的和平政策。历代继承古训,以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广包其荣,遵古人原道训:“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是故疾而不摇,远而不劳,四支不动,聪明不损,而知八纮九野之形埒者,何也?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18]即尊重自然天理,对异族区域和周边邻邦,主张各居所在自然区域,相互友好往来,不得相互侵犯掠夺,“裔不谋华,夷不乱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和为贵”。在传统时代的历史上,中国大体上以“和为贵”为基本原则,不侵略他国,常扮演着调解的角色。从“国”字的结构来看,原作“或”,字形像以“戈”(武器)守卫“口”(城邑),后来在“或”字的周围加方框表示疆域,构成“國”。从这个会意字可见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理念是对外不动武,只是持“戈”在疆域范围内,保卫自己生存的国土。[2]美国学者薛理泰也曾指出,中国的历史贯穿着一条直线,即“积极防御与‘非攻’一脉相承”。[19]在汉代,中国北方是广袤无垠的草原地区,生活在这一地带的游牧民族不断地周期性地南下压迫、入侵中原农耕地带,造成中国历代汉王朝所谓“外侮”的永恒主题。为了求得和平共处,化干戈为玉帛,血泪铺就和亲路,汉代历史闻名的王昭君出塞,还有来自大草原的乐舞天使阿史那公主;到盛唐时期,历经磨难的大唐和藩的第一公主弘化,还有那象征美丽的格桑花的文成公主、雪域高原的和平鸽的金城公主等,中国的一部和亲史,成为国与国、国与地区的和平纽带之一,也是丰富、完善、发展和延续了华夷秩序长达二千多年的其中因素之一。
历史上的“华夷”秩序,体现了中国的王道政治。所谓“王”,儒家经典采取“音训”和“形训”的方式来阐释其意义。从发音看,《白虎通德论》解释说:“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从字形看,孔子指出,“一贯三为王”;董仲舒则强调,“王道通三”,他的解释是,“三书而连其中,谓之王。三书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20]这就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之道,也是和睦邻邦的生态友好型国际秩序。而“华夷”秩序的最大公约数是生态友好型的内涵,特别体现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相邻友好。“回忆历史,中国与朝鲜半岛互为毗邻,唇齿相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犹如‘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那样,共处图们江的上游与下游,此岸与彼岸,在‘同饮一江水’的地缘条件下,每每友好合作,都双双发展,虽然也有过对立和战争,但那只是历史的一瞬,历史上的友好合作使朝鲜半岛的发展曾被赞誉为‘邻居好,无价宝’,中国与朝韩的发展历史恰恰诠释了这句俗语的丰富内涵”,[14]体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华夷”秩序的社会自然生态。所谓生态,简单地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21]历史上的“华夷”所体现的地缘关系,民族与国家同环境的关系,人的民族群体与人的国家群体的生存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相处关系的自然化的秩序,开辟了大中华的封建社会的伟大农业文明。《社会生态通论》的序言中有:“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是‘礼治社会’,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是‘法制社会’,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是‘机治社会’”。[22]什么叫“机治社会”书中又作了进一步解释,其中体现按“自然规律”、“社会运行规律”和“整体协衡”的方式,处理国家内政外交问题。而这其中蕴含的自然生态,恰恰与“华夷”秩序凸显的农业文明有着最大的公约数,对推进地球村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最现实的意义。
2012年10月,英国学派理论领军人物巴里·布赞教授在接受《中国与世界》主编刘德斌教授采访时说:“西方正处于衰落之中,他者无法或没有意愿去领导,这样,权威和合法性就会衰落。但是西方的衰落不会像罗马帝国的衰落一样,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西方也不会像苏联一样消失。西方仍会维持强大的影响。所以欧洲的衰落并不是全面的衰落。日本也不会全面地衰落,美国也不是,而只是越来越多的他者开始加入到大国和地区大国的行列当中。这是因为,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所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拥有众多大国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强大到支配整个体系的世界当中”。[23]这也是全球“去中心化主义”的论点。按巴里·布赞的话说:“没有国家承担起治理全球的责任,其实这一角色本身也已失去了合法性”。[23]巴里·布赞主张:大国要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他举中国为例说:“中国非常清楚它的繁荣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如果国际市场无人治理并开始四分五裂,如20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一样,这种情况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所以我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需要意识到它们应该为此承担部分责任,因为如果它们不承担责任,将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23]正像《易经》所讲的“群龙无首”并不是要无政府状态,而是要做承担责任之“王”,各自去承担自己的责任,“群龙无首”是要群龙共舞,要各自按自己的能力舞出自己的丰姿。“群龙无首”是为了和谐共处,无高低贵贱,互为尊重。效法天道,参与国际社会管理,“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利”,“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所以说,“乾元用九,乃见天则”。按“天则”行事,“天下治也”。[24]“天则”其本质是“王道之治”。在华夷秩序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历史上的日本,即“倭国”、“倭人”,“万里修贡”、“遣使献方物”、“恭修贡职”,从南北朝到大唐一直有增无减。到了明朝,朝鲜朝贡发展到了顶峰。而琉球则后来者居上,计在明代267年(1368-1644)里,琉球对中国修贡182次。到了清朝,琉球朝贡达100余次。在中华帝国对外交往的发展史上“华夷”秩序已成为“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规则和自觉行动,正如《宋史·外国传》所言,“比葵藿之向日”。可见万国朝拜中华帝国是一片丹心,简直好比“葵花向阳”了。穷其深层之道,不但是交往上的“厚往薄来”的利益关系,同时更主要是体现了“天则”。美国塞缪尔·亨迁顿在其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说,历史上中国的“外层地带”的蛮夷,“只需要朝贡(形式),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25]就可以了,并指出“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的共荣圈。其实仅这样讲是不妥的,因为其中还有一个社会生态问题,也就是“天人合一”,构建经济共同体,上升到命运共同体问题。这才是对传统华夷秩序现代化的体现。只有“三才(天、地、人)通一道”共生、共荣,才能构成国际社会机治化,坚持共同、整体、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应是中国积极参与构建的国际新规则或新秩序。
早在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东南亚期间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倡议,仅仅时隔一年,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于2014年10月签署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决定成立亚投行。随后,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新西兰、约旦、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等国相继宣布加入。直到今天,一系列重磅消息纷至沓来。2015年3月12日,作为发达国家的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14日,澳大利亚宣布将在数周内决定是否加入亚投行;17日,法国、德国、意大利表示同意加入亚投行……中国几度回应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开发机构,是对世界金融体系的重大补充。业已加入亚投行的国家中,既有“欧洲列强”,也有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中国将成为各种意见和诉求的主要交汇点,中国将以宽阔的胸怀和实际行动传承东亚秩序的“和而不同”观念,不懈追求“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走“美美与共”的合作道路。
2014年11月10日至11日,北京举办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会议期间,国际上发生了乌克兰东部陷入国家分裂的问题,俄罗斯与美欧相互制裁而彼此再现“小冷战”和美国在亚太大搞“重返亚洲”政策等诸多问题,面对如此复杂的关系,中国在此会议期间,与俄达成了能源协议,加深了中俄能源合作关系。另外,中美在军事上达成海空军避免擦枪走火的信息交换协议,在气候、IT、资本市场、国企对外投资、金融开放、统计标准上达成广泛的合作关系。这一系列合作促使美国对中国态度也有一定的改变。正如澳大利亚精算师协会名誉主席郭生祥所说:“美国比较含蓄地承认,‘重返亚洲’最重要的基石是中美合作,而不是中美对抗。G2的影子再次惹隐若现”。[26]
当今世界,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中美是“老大老二”的关系,在政治上、军事上中美不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经济上也不是零和关系,而是相互合作与自然竞争促进全球发展的关系,“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强化经济关系。经济是滋元育本的基础,也是国际社会生态的基础,只有基础牢,才能在世界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而在2014年北京APEC会议上,中国排除政治干扰,强化经济关系,也是其在促进传统“华夷”秩序现代化的同时创新性地遵循了现代国际秩序规则。中国将在世界进入多极化、权力分散的“群龙无首”境界中,强化经济关系,在走向“不治治之”的自然生态的世界秩序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1]中华书局编辑部:《中华学术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页。
[2]李乐毅:《汉字演变五百例》,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2年。
[3]《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页。
[4]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2页。
[5]何小颜:《早慧的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26页。
[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06页。
[7]匡亚明:《孔子评传》,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330、261页。
[8]云中天编著:《中国历史上的大融合》,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7年,第166-174页。
[9]何力:《纵横国际法》,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3年,第72页。
[10]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96页。
[11]程郁缀、龙协涛主编:《学术的风采·人文科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44、547页。
[12][日]上垣外宪一著:《日本文化交流小史》,王宣琦译,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
[13]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420页。
[14]李宗勋:《图们江区域合作与朝韩历史发展的地缘优势》,《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7、9页。
[15]陈维新:《传统东亚体系与中日关系》,《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3页。
[16]韩升:《唐太宗治国风云录》,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4年,第348页。
[17]《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5页。
[18]《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页。
[19][美]薛理泰著:《盛世危言——远观中国大战略》,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9页。
[20]王绍光:《中国·政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21]王旭烽主编:《中国生态文明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4页。
[22]金建方著:《社会生态通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23]刘德斌主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4、5页。
[24]余敦康著:《周易现代解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25][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46页。
[26]郭生祥:《中国在创新性遵循世界规则》,《环球时报》2014年11月26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