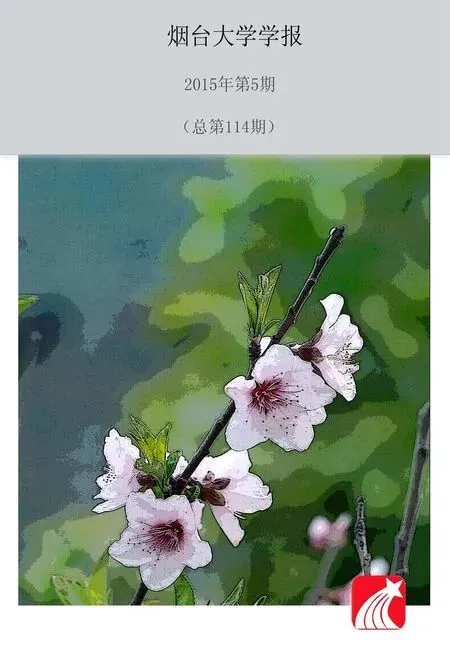犯罪故意“明知”问题探析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15)05-0044-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5.005
[收稿日期]2015-04-20
[作者简介]冷大伟(1988- ),男,山东青岛人,北京大学法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刑法中的犯罪故意作为一个重要、复杂的课题,一直是刑法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也是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点。犯罪故意作为一种基本的罪过形式,主要包含了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部分。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打算实施行为的性质和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方面的认识,我国刑法将其表述为“明知”。正所谓“明知才能故犯”,“明知”是犯罪故意的基础,也决定着故意犯罪的最终成立。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明知”,其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明知”和“应当知道”的界分
“明知”和“应当知道”作为表示行为人主观认识状态的术语,多次出现在刑法和司法解释中。但是,刑法和司法解释对“明知”和“应当知道”的规定却存在矛盾之处,理论界对“应当知道”和“明知”的关系也存在着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机关认定犯罪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对“明知”和“应当知道”进行界分。
(一)刑事立法的梳理
对我国的刑事立法进行梳理可知,1979年刑法关于“明知”的规定共有6处,但并未出现“应当知道”一词;现行刑法关于“明知”的规定共有39处,但只于219条第2款规定了“应知”一词,具体内容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这里的“应知”就是“应当知道”。应该说,刑法对“明知”和“应知”的规定,为正确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必要和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司法解释的梳理
对我国的刑事司法解释进行梳理可知,1997年刑法颁行以前,在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首次对“明知”进行了认定:“认定窝赃、销赃罪的‘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就可以认定”。从该解释以后,“知道”和“应当知道”作为“明知”的两种形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被明确下来,成为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主观方面的依据。此后,1998年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3年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200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7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相继颁行的一系列司法解释,都将“明知”的含义界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可以说,将“明知”的含义界定为“知道”和“应当知道”已经成为司法解释的惯例,其中固然有司法功利性和便利性价值的考量,但也可能产生与刑事立法的规定相冲突的问题,同时也会引来刑法理论界的争议。
(三)刑法理论争议的梳理
在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对“明知”和“应当知道”进行规定的基础上,刑法学界围绕着“明知”与“应当知道”的关系展开交锋,笔者归纳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排除说。该说认为,“明知”就是指行为人“明明知道”,它是不包含“应当知道”的。“应当知道”只是过失心理状态的表现,不应将过失心态的表现解释成为故意犯中的“明知”。 ①二是替代说。该说认为,不能将“应当知道”解释为“明知”的表现形式,“应当知道”就是不知,不知岂能是明知。实际上,在“应当知道”这一用语中,人们想要描述的是一种不同于确切地知道的认识状态。因此,“应当知道”是一种“推定知道”,法律规定中的“应当知道”并不是指在过失中使用的概念,它实际上的意思应该是“推定知道”,用“推定知道”替代“应当知道”才是正确的选择。 ②三是包含说。该说认为,“明知”是应该包含“应当知道”的。对“明知”的理解和认定不能明显违背社会的法规范理性。从规范论的立场出发,认定不存在犯罪故意的标准,不是行为人没有认识到结果的发生,而是行为人对没有认识到结果的发生不具有负责性。不能心理地把故意仅视为“已经知道”,而要规范地把故意视为“应该知道”,即把故意视为“对不知道负责”。 ③
以上三种观点,虽然从不同的立场分析了“明知”与“应当知道”的关系,但是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应当知道”就是行为人事实上并不知道,它是以不知道为逻辑前提的一种认识状态。其中,替代说将“应当知道”替换为“推定知道”的做法避免了故意与过失两种主观心态的混淆,但是在笔者看来,“推定知道”实质上是通过推定的方式来认定的“知道”,因此,不必引入“推定知道”,只规定“明知(知道)”一种认识形式,在认定上采用推定的方式即可。包含说从规范的角度将“明知”理解为“应该知道”、“对不知道负责”,亦无法将故意和过失两种主观心态区分开,因为疏忽大意的过失主观上也是“应该知道”却“没有知道”,也被视为“对不知道负责”。
(四)“明知”的应有含义及认定方法
通过对刑事立法、司法解释和刑法理论的梳理,笔者认为,对于“明知”与“应当知道”的含义界分,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明知”是行为人本身对相关事实的一种认识,而不是司法工作人员对行为人认识状况的一种判断,认定一个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故意,应该以行为人主观是否对相关事实存在认识为基础。“明知”不仅仅意味着确实知道,可能性认识也应纳入“明知”范畴,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坚持的一贯立场。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构成嫖宿幼女罪主观上是否需要具备明知要件的解释》(2001年)中规定:“行为人知道被害人是或者可能是不满14周岁幼女而嫖宿的,适用刑法第360条第2款的规定,以嫖宿幼女罪追究刑事责任。” ①笔者认为,将“明知”作为一个特殊的概念写入刑法中,立法者的初衷在于通过严格限制主观心理要素的认定,进而限制刑法的扩张:当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故意犯罪时,主观上首先需要具备犯罪故意,而具备犯罪故意的前提是行为人要对其行为的性质、危害结果等客观事实有认识,如果不知道这些事实,行为人主观上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犯罪故意,也就不会实施故意犯罪。但是,如果仅仅将“明知”理解为“确切知道”,则过分限制了犯罪的成立,不利于打击和惩治犯罪行为。
第二,“明知”是不包含“应当知道”的。如前文所述,“应当知道”就是行为人事实上并不知道,它是以不知道为逻辑前提的一种认识状态。对我国刑法进行考察也可得知,刑法第219条第2款规定的“应知”与“明知”是一种并列关系,即“明知”是不包含“应当知道”的。反观司法解释,“应当知道”与“知道”是一种并列关系,二者同属于“明知”的范畴。显然,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是矛盾的,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基本原理,司法解释作出这样的规定是不符合立法规定的,其实质是用下位法对刑事立法进行扩大解释,有违背罪刑法定之嫌。再者,“应当知道”一词的确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失心态,从而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混淆。笔者建议,在时机成熟时,可以考虑修改刑事立法中的相关用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相关部委在出台相关刑事司法解释时,应该避免再将“明知”规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简言之,可考虑将立法和司法解释中的术语统一为“明知”。值得欣慰的是,为了避免理论和司法实践的争议,后来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开始搁置“应当知道”这一术语的使用,例如,2007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0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都体现了这一点。
第三,可以用刑事推定的方法来认定“明知”。通常情况下,应该通过证据来直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行为人的“明知”心态往往十分困难,而如果仅仅因为某些犯罪的主观心态难以证明,就放弃对犯罪的打击,又不利于对社会的保护。因此,出于有效、及时打击犯罪,提高司法效率等功利性价值考量,司法实践可采用推定的方法来认定“明知”。“所谓推定,是指司法证明的一种重要方法,是以肯定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为基础,通过对基础事实的证明来实现对推定事实的认定。” ①“推定作为一种思维形式,是一个三段论推理的逻辑结构,根据推定理论与逻辑原理,在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时,完全可以采用推定方法。” ②但必须注意的是,推定还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否则可能超越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成为国家刑罚权扩张的工具。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刑法日益成为风险控制工具的社会里,决策者正越来越多地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中使用推定,它具有使控方的指控与定罪变得容易的功能,其实际上涉及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关系的处理,背后上演的可能是国家权力悄然扩张的一幕。这就有必要认真对待刑事推定。” ③因此,只有当直接证明的方式无法认定“明知”,才能适用刑事推定。在适用刑事推定时也应遵守必要的规则和程序,细化和立足于基础事实,同时允许被告进行反证。总之,刑事推定反映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博弈,其适用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面对认定行为人‘明知’心态的永恒难题,推定只是证明手段的一环,并不能起到‘一推解千愁’的效果。” ④
二、“明知”和“已经预见”的界分
根据我国刑法第15条对过失犯罪的规定,“已经预见”是对过于自信过失的认识因素的表述。从语义上看,我国犯罪故意中“明知”和犯罪过失中的“已经预见”都是对相关事实存在某种认识。但同样是有认识的状态,立法者却将其放在完全不同的两种主观心态中予以规定。可见,两种有认识的状态是不同的。因此,正确区分“明知”和“已经预见”,对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犯罪的主观心态,进而正确地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可以从认识程度和认识内容上对两者进行界分。
(一)从认识程度看,“明知”的认识程度显然要高于“已经预见”的认识程度。“明知”是指认识自己的行为必然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例如,甲用刀刺向乙的心脏,甲明知自己用刀刺向心脏的行为必然会造成乙的死亡结果;或者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例如,甲向站在远处的乙开枪射击,甲认识到自己开枪的行为很有可能会打伤或者打死乙。因此,“明知”对相关事实的认识尤其是结果的发生是一种具有必然性或者较大的现实可能性的认识。反观“已经预见”,虽然也是有认识,但其认识程度显然要低于“明知”。换言之,“已经预见”对相关事实尤其是危害结果的发生并非是一种具体的、具有较大现实可能性的认识,而是一种抽象的、具有较小发生可能性的认识。相反,“已经预见”是对“结果的不发生是具有较大的可能性”的一种认识。如果“已经预见”也需要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有现实可能性或者必然性的认识,就无法合理解释既然行为人从意志上是根本反对危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在有必然性或者具有较大现实可能性认识的情况下,行为人为什么仍要实施该行为。
(二)从认识的内容来看,“明知”和“已经预见”也是不同的。“明知”是行为人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和社会危害性的认识, ⑤对那些确实可能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事实和条件没有认识或者不予关心。反观“已经预见”,行为人预见到的不仅是相关的构成要件事实和危害性, ①行为不仅是由于随后出现的危害结果而表现为不法,而是在其本身就具有了不法性,因为正是行为人的所作所为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创设了一种不允许的风险,并且使法益在这个危险中最终导致了那种危害结果。因此,在有预见的过失犯罪中,行为人也要对相关的构成要件事实和危害性有认识,只不过过失犯罪是以结果的现实发生为成立条件,当结果不发生的时候,就没有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认识到相关事实和危害性的必要。而且对本来可以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事实和条件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这些事实和条件,常见的有行为人自己具有熟练技术、敏捷动作、高超技能、一定的经验和预防措施,以及其他人的帮助或者某种有利的客观条件。因此,“已经预见”表明行为人认识到的是:在实施行为时,有自身的能力、技术、经验和某些客观条件“帮助”,危害结果发生的抽象可能性不会转化为现实可能性。
三、“明知”的内容辨析
“明知”的内容是犯罪故意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仅是认定犯罪故意是否成立的关键,而且对认定犯罪过失,解决行为人认识错误的罪过形式,也十分重要。” ②但在探讨明知的内容时,刑法学界大都围绕刑法总则“明知”的内容进行,往往忽略了刑法分则。因此,也有必要对分则“明知”的内容进行梳理,这也是明晰总则和分则“明知”关系的基础。
(一)刑法总则“明知”的内容分析
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的规定,总则“明知”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结果”,即对行为的性质、对象、结果和过程等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的认识;二是“危害社会”,即危害性的认识。
1.对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的认识。 ③(1)对行为性质的认识。行为是犯罪的核心内容,行为人对其自身行为性质的认识,是司法实践中确定犯罪性质的重要基础。对行为性质的认识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具有能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性质。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的认识主要是对行为客观(自然)属性的认识,即对外部行为的物理性质要有所认识。对行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一般是通过对行为的手段或方式的认识表现出来。例如,在故意杀人罪中,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杀人行为”,在客观上具有能杀死人的性质。(2)对行为对象的认识。行为的对象又称犯罪的对象,是指犯罪行为所欲影响或者改变的事物或者事物的状态。对行为对象的认识包括对对象的实体、属性、状态等方面的认识。例如,在故意杀人罪中,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杀的是有生命的人,而不是动物;在盗窃罪中,行为人要认识自己打算窃取的对象是他人占有的财物;在破坏通讯设备罪中,行为人要明确认识到自己破坏的是正在运行中的通讯设备。 ④(3)对行为结果的认识。根据我国刑法分则对各种故意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同规定,犯罪既遂有四种不同的类型: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和举动犯。 ①对结果犯而言,危害结果属于法定的构成要件要素,要求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该危害结果会发生,否则不构成该罪或者只能构成彼罪。例如,行为人只认识到会产生伤害结果,但对死亡结果的出现缺乏认识,就只可能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而不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然而,对危险犯、举动犯和行为犯而言,是否要求对危害结果有所认识就存在争议。 ②笔者认为,虽然我国刑法对一些故意犯罪的既遂不要求产生法定的实害结果,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些故意犯罪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且不要求行为人对这些结果没有认识。意大利刑法将结果分为“自然的结果”和“法律意义的结果”。法律意义的结果是指对“行为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进行损害或是使之处于危险状态的一种法律上的评价。” ③从“法律意义的结果”的视角可以比较恰当地理解其他既遂形式对“结果”的认识:危险犯、行为犯和举动犯都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举动可能造成某种危险状态。可见,“行为结果”是所有犯罪故意都必须认识的内容。(4)对于行为发展过程的认识。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味着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社会的结果是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因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性质和行为结果,就必然意味着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危害结果有认识,二者是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5)对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相联系的其他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例如,特定的时间、地点、方法和状态等。
2.对行为和结果的危害性的认识。根据刑法14条的规定,“明知”除了要认识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外,还要对行为和结果的危害性有认识。这种认识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和结果的社会属性的认识。问题在于,对社会属性的认识程度有何要求?要求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违法性” ④吗?笔者认为,对行为和结果的危害性的认识可以有两种程度不同的标准: (1)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反刑法规范的。通常来说,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反刑法规范的,就可以推定行为人认识到了行为和结果的危害性,因为法律规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和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反应。当然,不可能要求所有行为人都达到该种程度的认识。行为人认识到对刑法规范的违反,意味着行为人必须明知行为及其结果的刑事违法性,这就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确知道其行为和结果触犯刑法哪一条文,应该怎样定罪判刑,这显然不合理,也不现实。 ⑤虽然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尊重和认识法律规范的努力,但“面对成百上千的法律条文,任何人都无法清楚地记住这些内容。” ⑥不仅如此,要求认识到具体的法律规定也很容易使行为人钻法律的空子,借口不懂法律来实施犯罪并逃避罪责。因此,基于当前国民整体的法认知水平,不可以在认定主观故意时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违法性”的认识。“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反具体法律规范的”是对行为和结果危害性认识的最高要求。(2)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 ①的,即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可能侵犯他人的利益的,是不被社会所认可的、不正当的。如前文所述,我国刑法规范本身就是对其所保护利益的反应,也是社会的主流行为价值观、是非观和道德观的体现,具有正常理智的公民都会认识这一点。因此,当行为人难以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对具体的刑法规范的违反,但如果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侵害了某种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或者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对他人造成某种伤害, ②抑或是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被社会所认可的、不正当的,也可以认定行为人认识到了行为和结果的危害性。易言之,法律维护的是一个社会共同认同的最基本的价值和道德是非观念,两者是共通的。
(二)刑法分则“明知”的内容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分则一共有33个条文、共计38处“明知”。笔者将其按照认识内容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对特定事物的认识。主要包括:明知是“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144 条)、明知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145 条)、明知是“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146条)、明知是“假的或者失去使用效能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147条)、明知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148条)、明知是“伪造的货币”(171条、172条)、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177条)、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177条)、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191条)、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194条)、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194条)、明知是“伪造的发票”(210 条)、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214条)、明知是“侵权复制品”(218条)、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265条)、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291条)、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312条)、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345条)、明知是“不合格的武器装备、军事设施”(370条)。
2.对特定状态的认识。主要包括: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138条) ③、明知“他人有配偶”(258条)、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259条)、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360条)。
3.对特定主体的认识。主要包括:明知是“犯罪的人”(310条)、明知是“逃离部队的军人”(373条)、明知是“逃离部队的军人”(379 条)、明知是“无罪的人”(399条)、明知是“有罪的人”(399条),明知是“企图偷越国(边)境的人员”(415条)、明知是“偷越国(边)境的人员”(415条)。
4.对特定的他人行为的认识。主要包括:明知“前款所列行为”(219条)、明知“他人实施前款行为”(244条)、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285条)、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311 条)、明知“他人制造毒品”(350条)、明知“他人用于出版淫秽书刊”(363条)、明知“友邻部队处境危急请求救援”(429条)。
通过对分则“明知”的内容进行类型化的梳理可以得出,分则“明知”的内容也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个罪中特定的犯罪构成客观事实的认识,例如,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明知“他人有配偶”等。二是对“危害性”的认识。可以发现,分则“明知”的内容中绝大部分都含有否定性的价值评判因素,例如,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中的“犯罪所得”、明知是“不合格的武器装备、军事设施”中的“不合格”等,这说明分则“明知”也要对“危害性”有认识,即使是无否定性价值评判因素的内容,例如“军人的配偶”,但如若将其放在整个构成要件客观事实中,亦要求其有“危害性”认识。可见,分则“明知”内容是对总则“明知”内容的具体化,两者是整体与部分的统一关系。
四、刑法总则“明知”和刑法分则“明知”的关系辨析
同样为“明知”,那么刑法总则中的“明知”和刑法分则中的“明知”有什么关系?对此,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对分则“明知”的必要性提出质疑,认为总则犯罪故意的规定本身就包含了“明知”,为避免给人造成“凡分则规定‘明知’的罪名,其证明责任就在控方,不规定‘明知’的,控方就无需证明‘明知’”的误解,我国现行刑法分则条文中的“明知”以取消为宜。 ①
第二,认为分则关于“明知”的规定属于注意规定,即提醒司法工作人员注意的规定。即使没有分则“明知”的规定,也应该根据总则关于故意的规定,确定必须“明知”的事实。 ②
第三,认为刑法分则中的“明知”不同于刑法总则中的“明知”。持该观点的学者的论证理由又有所不同,例如,有学者提出如下理由:刑法分则中的“明知”,是以对特定对象的明知为唯一内容的,而刑法总则中的“明知”则是以危害后果的明知为核心,不局限于对犯罪对象的明知。刑法分则的“明知”仅仅强调行为人的认识因素,其未必与希望、放任等意志因素联系在一起,而刑法总则的“明知”则不仅是一种认识因素,这种认识因素必然和希望、放任等意志因素相联系。因而两者实际上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③再如,有学者认为,刑法总则中的“明知”是对即将实施的危害行为所要导致的危害结果的一种预想,而刑法分则中的“明知”则是对现存事实的一种认识,所以两者在认识的预见程度上存在重大差别。刑法分则的“明知”并不只是对刑法总则“明知”的重申。因为刑法分则对特定犯罪对象的认识具有自己特定的内容和属性,而这些是不同于刑法总则中“明知”的根本区别所在。 ④值得注意的是,陈兴良教授以德日刑法犯罪论体系中的表现犯为解释进路,将两种“明知”做了区分。他认为,分则中的“明知”不仅仅是总则规定的“明知”的提示性规定,而且具有其特殊的功能。刑法总则规定的“明知”与刑法分则规定的“明知”之间是存在性质上的区别的,随着德日刑法知识尤其是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引入,需要采用德日刑法学中表现犯的概念对刑法分则规定的“明知”予以解读,将分则中的“明知”理解为主观违法要素,总则中的“明知”理解为责任要素。 ⑤
想要正确认识刑法总则“明知”和刑法分则“明知”的关系,需要以正确认识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从总则“明知”和分则“明知”内容的关系切入,同时也要注意正确理解分则“明知”存在的意义。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分则的“明知”和总则的“明知”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统一术语。
(一)我国刑法第101条规定:“本法总则适用于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根据该条规定,可以透析出总则和分则的一种关系:总则对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做出一般性规定,分则对各类、各种犯罪的罪状和刑罚作出具体规定。“总则为分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提供原则性指导,分则促进总则的实践效用。” ①可见两者是一般与特殊、普通与特别、密切联系、缺一不可、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根据总则和分则的关系可以得出,总则的“明知”是有关犯罪故意认识因素的一般性规定,刑法分则的“明知”是对具体犯罪特定的“明知”内容的规定,是刑法总则“明知”的具体化,两者是一种共通统一的关系。
(二)如前文所述,“明知”是指明确知道或者可能知道,是行为人本身对相关事实的一种认识。单从语义上看,总则和分则的“明知”的含义应该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对相关事实的认识,总则“明知”是对全部构成要件客观事实的认识,分则“明知”是对部分客观事实的认识。笔者不能赞同上述第三种观点,因为总则的“明知”要求行为人必须认识到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犯罪的全部客观事实,而刑法分则“明知”对特定事实(特定的物、人、行为和状态)的认识都是总则“明知”对具体犯罪客观事实认识的一部分。换言之,总则“明知”和分则“明知”的内容并不是不相同,而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包含关系。并不能因为刑法分则“明知”的内容是部分客观事实就认为其认识内容有自己的属性,认为这是不同于刑法总则“明知”的根本区别所在,相反,这恰恰是两者彼此共通的依据之所在。此外,刑法总则和分则的“明知”都是一种认识因素,而非有学者认为的“总则‘明知’不但是一种认识因素,而且其必然和希望、放任等意志因素相联系”。对有学者提出的“两种明知存在认识程度的差别”的观点,笔者认为,认识程度的不同关键在于行为人对事实是否认识到、认识到了多少,而不在于认识对象是即将发生的事实还是既存的事实。对于陈兴良教授所提出的“以表现犯作为分则明知的解释进路”的观点,笔者认为虽然十分的独到精辟,但是在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中,毕竟不存在主观违法要素的概念。表现犯作为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下的一个概念被中国刑法理论界接受也尚需时日。况且,将同为认识因素的“明知”分别解释为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和责任要素分列于不同的阶层是否协调,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三)将分则“明知”理解为一种具有提示功能的注意规定是合适的。注意规定的初衷在于警示和提醒司法工作者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的时候要认识到分则中的“明知”与总则第14条中的“明知”是一致的。换言之,假如不存在刑法分则条文中的“明知”提醒,同样也可以以刑法总则中的“明知”为依据认定具体的故意犯罪中行为人主观上需要“明知”的内容。以刑法第144条为例:“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在本罪中,行为的对象——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时)和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销售时)是特定的,它们都属于构成要件的事实,行为人对此必须有所认识,司法人员也必须查明行为人对此是否明知。之所以对后者特别规定“明知”,是因为在销售时销售者很有可能是不知晓食品是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所以为了警示司法工作者,特别写明“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而行为人对自己是否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掺入到食品当中通常是明知的,没有必要特别提醒。所以,尽管刑法第144条并没有要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时“明知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但是根据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故意的规定,仍然需要行为人明知“生产、销售的是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
(四)分则“明知”仅仅具有提示司法人员注意的功能吗?如此,是不是意味着分则“明知”没有单独存在的意义?抑或是立法者的多此一举?其实不然。我们要相信,一个简单的“明知”并不是立法者随意写入刑法的,它必然有其存在的意义。正所谓“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 ①,“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②而信仰法律我们就不要随意批判法律,应该对相关术语做出善意的理解。“没有不合理的法,只有不讲理的人。” ③在笔者看来,不能把分则“明知”仅仅理解成是对司法人员的提示,提示检察机关在举证时要严格证明“明知”以达到排除怀疑的程度,也要看到它也为辩护方提出合理的抗辩提供了有效的提示,即被告可以以主观上没有认识提出抗辩,抑或是控方在适用推定的方法认定“明知”时,被告可以就推定的基础事实提出有效反驳。如此,行为人就不存在犯罪的故意,也就不成立犯罪。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涉及的是对公民最基本的人权的保护,更应该被慎重地适用;“刑法学是最精确的法学” ④,更要求刑法人准确地理解法律。因此,我们更要看到,在分则“明知”的提示功能背后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功能——明确刑事责任的范围,限制刑事责任的最大边界。可以说,在与总则“明知”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对分则“明知”的规定更加彰显了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它突出了对犯罪成立的限制功能,要求司法者在认定犯罪时要恪守罪行法定主义,从而最大程度地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保障公民的人权不受任意地践踏。
Study on the Issue of“Knowledge”in Criminal Intention
LENG Da-wei
(School of Law,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Cognitive factor,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in the criminal intention,refers to “knowledge”in criminal law in our country.In our country’s criminal law theory,there exist different opinions in“knowledge”,and this directly affects the correct cognition of criminal intention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According to analysis and research,“knowledge”is a kind of cognition which contains“know for certain”and“may know”,and it does not contain“should know”.In addition,“knowledge”and “already known”exist differences in the extent and content of knowledge.In terms of content of“knowledge”,it includes understanding of constitutive elements and understanding of harmfulness.The“knowledge”in general provision of criminal law and the“knowledge”in specific provision of criminal law are not opposite,and they are concordant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 criminal intention; knowledge; should know; already known; the content of cognition
[责任编辑:赵守江]
参见张明楷:《如何理解和认定窝赃、销赃罪中的“明知”》,《法学评论》1997年第2期。
参见陈兴良:《“应当知道”的刑法界说》,《法学》2005年第7期。
参见冯军:《刑法的规范化诠释》,《法商研究》2005年第6期。
王新:《我国刑法中明知的含义和认定——基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1期。
皮勇、黄琰:《论刑法中的应当知道——兼论刑法边界的扩张》,《法学评论》2012第1期。
张明楷:《如何理解和认定窝赃、销赃罪中的“明知”》,《法学评论》1997年第2期。
劳东燕:《认真对待刑事推定》,《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
王新:《我国刑法中明知的含义和认定——基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1期。
对此,笔者将在下文“明知”的内容部分予以详细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在过失性犯罪构成中也包含着危害行为。
高铭暄:《刑法专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以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为基础,行为人应该对哪些构成要件事实有认识,学者们的见解存在分歧,主要有三种学说:一是认识三要件说,即行为人应该对除了犯罪主观方面以外的一切犯罪构成事实有认识,我国台湾学者持此观点。见林山田著:《刑法通论》,台北:三民书局,1989年,第120-121页。二是认识二要件说,即行为人应该对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的事实有认识。见甘雨沛等主编:《犯罪与刑罚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2-139页。三是认识一要件说,认为明知的内容只包括对犯罪客观方面的认识。见高铭暄、王作富主编:《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0-243页。笔者认为,对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的认识是指对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事实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客体的认识,因为在四要件体系中,犯罪客体主要表现为行为人的行为及结果的危害性程度,应该属于行为人对行为和结果的社会属性(行为和结果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范畴。同时也不包括对犯罪主体的认识,因为行为人的年龄、责任能力属于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只要行为人具备了这些客观条件,就可以推定他具有认识能力,因此,是否认识到这些条件,不会影响他本人对相关犯罪构成客观事实和危害性的认识。
参见赵秉志:《刑法基础理论探索(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554页。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7-149页。
刑法学界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不能因为法律不以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就否认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必须有认识。参见陈兴良著:《刑法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4页。有学者则持反对观点,认为对行为结果的认识只限于结果犯,对危险犯、举动犯和行为犯等其他犯罪不应当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有认识。见贾宇:《犯罪故意问题》,载赵秉志主编:《犯罪总论问题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16-218页。
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原理》,陈忠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这里的违法性是汉语中的违法性概念,即刑事违法性,指的是违反具体的刑法规范。同样,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也有违法性的概念,它是阶层体系下犯罪成立的一个阶段,有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之分:形式违法性与汉语中的违法性(刑事违法性)含义相同,是对具体刑法规范的违反;实质违法性分为法益侵害说和规范违反说,指行为违法实质上是行为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侵害(危险)或是对社会基本伦理秩序的违反,是一个需做出价值判断的概念,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社会危害性概念相近。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107页。
王世洲:《现代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4页。
这里的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立足于整体的法规范、法秩序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以社会一般的判断是非善恶的观念为标准所作的价值性判断的概念。因此,我们常说违反道德的行为也具有社会危害性,而违反刑法的行为则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例如,A持刀砍向B,要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杀人的故意,并不要求行为人一定要认识到自己违反的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规范条文,如若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对他人生命的侵害,也可以认为这是行为人对行为及其结果的危害性的认识。
刑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该条的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即该条中“明知”并不同于故意犯罪中的“明知”,只是表明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但为了保证论述的完整,将其归入“特定状态”的范畴。笔者认为,立法者之所以将“明知”一词用在该过失犯罪中,可能是基于预防和限制刑事责任范围的考虑:一方面,教育设施的安全关系着师生的生命安全,相关责任人员需要负担很高的注意义务来保障教育设施的安全,因此,立法者将“明知”写入该条,以提醒相关责任人员要时刻警惕教学设施的安全。另一方面,“明知”也限制着刑事责任的范围,只有在相关责任人员发现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才可能将其定罪,换言之,对该罪要求的主观认识的程度要与故意“明知”的认识程度一致。
温文治、陈洪兵:《刑法分则条文中“明知”的证明责任及其立法评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588页。
杨芳:《犯罪故意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以下。
于志刚:《犯罪故意中的认识理论新探》,《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
陈兴良:《刑法分则规定之明知:以表现犯为解释进路》,《法学家》2013第3期。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317页。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28页。
陈忠林:《刑法散得集(Ⅱ)》,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译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