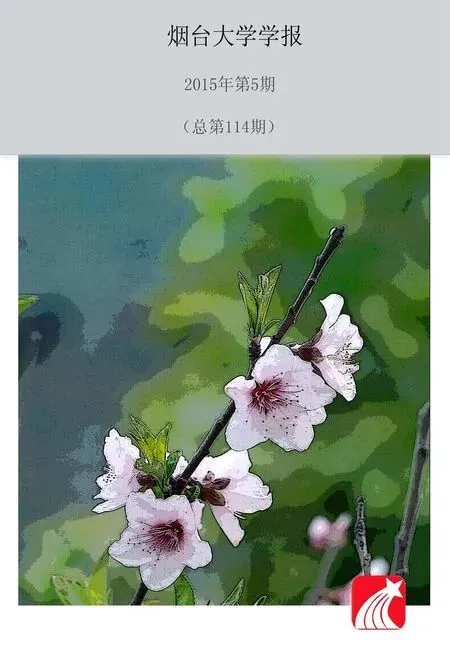朱熹之“理”的价值内蕴与路向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15)05-0001-15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5.001
[收稿日期]2015-02-05
[作者简介]王传林(1978- ),男,安徽阜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伦理思想史。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两宋时期主流价值观的变迁”(12JJD720013);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价值观变迁史”(14ZDB003)之子课题“宋元理学价值观的建构与发展”。
程朱理学以言“理”著称,他们在“崇理”的同时极力鼓吹“灭欲”。循二程之天理,朱熹建构了系统的价值哲学体系并由此将儒家的纲常思想容纳到以“理”为价值本源的间架中;他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解决了人伦规范与政治哲学缺乏“本体”基点的根本性问题,而且也为生活在世风日下的社会中的人们指出了价值目标。细究之,朱熹之“理”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意蕴与内在理路,“理”与“欲”之间又有怎样的张力,“理”又是如何贯通“三纲”与“五常”并由“形而上”落向“形而下”的,“理”的价值又是如何呈现的?循诸问题,本文试从价值哲学的视域去探寻朱熹之“理”的本源意蕴、内在理路、理欲关系,以及“人”在“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进路中的主体性与超越性;同时以期梳理出“理”经由“三纲”与“五常”等向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推衍的价值路向。
一、“理”的价值本源意蕴及内在理路
天理与人欲时刻充满紧张并在个体生命的展开过程中不停地博弈,究竟是天理屈从人欲,还是人欲屈从天理?充满欲望的个人如何在纯粹而至善的天理中敞开?或许,“在德行与世界进程的关系里,两个关系者中的每一个则同时是这两个环节的统一和对立,或者说,都是规律与个体性之间的运动,却是两个相反对的运动。” ①在朱熹看来,“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同时也是挽救世道人心的根本。因此,朱熹主张必须要用德行的规律来扬弃个体性,即个体要革除一切有悖于天理的欲,去服从德行、服从天理。尽管这多少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但却是儒者成圣之路中的必然历程。在此,大抵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去探寻朱子之“理”。
(一)作为价值本源的“理”。所谓本源,“在此指的是一个事物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 ②。推而言之,价值本源亦作如是观。在朱熹看来,“理”是一切存在的价值本源,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大纪》)由此可见,天地万物皆源于“理”,人伦纲常亦皆源于“理”。具言之,“人”只需循“理”即可,无论君臣还是父子应该注重内向性的道德修养并以此为据实现与天理的外向性的融合;如是,便能顺合天理、行有伦常。在朱熹的价值哲学论域中,“人”作为价值主体需要听命于天理的律令,一切行为与规范也应该顺乎天理;“人”的一切有悖于天理的欲在天理面前毫无地位,应尽革之;在“理”的牵引下,“人”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只能局限于“理”的域界内。或许因为如此,朱熹之“理”遭到不少学者的严厉批判,甚至有人指出其容纳了消极因素,成为阻碍中华文化健康发展与“人”之精神全面展开的拦路石。客观地讲,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与流布和时代形势、人文思潮与历史背景都是分不开的,进言之,理学之所以在宋明发端并得到光大也折射出其理论精神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一面。
在程朱理学的视域中,“理”是道德主体之道德信念与价值来源的客观“定在”(确定的存在),其内涵彰显了“人”克欲成圣的实践理性之路,以及与天地、天理合而为一的可能性。在“天理”的图景中,“人”由世俗性存在经由自我超越成就理想人格,从而成为“天理”图景中协调于时间与大道的道德性存在。也就是说,在朱子的眼中,道德个体在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之后,便会融道心于我心,融天理于我心——道心与人心相融通,二者此时在“心”上实现完美统一。诚如朱熹所云:“道便是无躯壳的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的道”(《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这就是说,“圣道合一”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之价值呈现进路中所追寻的根本旨归。进而,朱熹指出:“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朱子语类》卷八);“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同上);又云:“人须当以尧舜为法”(《朱子语类》卷五十五)。较之,朱熹的“学以至圣”与程颐的“学以成圣”可谓是一脉相承的,程颐说:“人皆可以成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概之,“人”作为价值主体通过克欲复理以“自化”,向“天理”趋近,终可“成圣”——“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由此,价值主体之价值便得到最大化的呈现。当然,传统儒学与程朱理学虽然强调学以成人、学以至圣、强调“自化”,但是他们并不否定他者的“教化”与圣贤的“教化”——价值牵引与牵引价值。其实,价值作为“世界对于人的意义”或“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是以“人的内在尺度”或“主体的尺度”为根据的,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性。 ①也就是说,尽管“理”的价值是通过万物来呈现的,但却是取决于“人”之价值判断的。具而言之,在朱熹眼中,“理”是存在的本体与本源,是超越时空的定在,是形而上者;或者说,“本然之理”即“自然之理”,“是最高存在,其中包含着可能的最高价值” ②。他说:“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朱子语类》卷一)因此我们认为,在朱熹的价值哲学中,“理”是价值本源,世间任何存在之价值皆源于“理”,任何存在的价值呈现皆是“理”的另一种形式的展开,任何存在的终极旨归皆是无限地趋近于“理”,即向“理”挺进。
(二)“本然之理”是至善之理。在朱熹看来,本然之理是至善之理,他说:“理无有不善”(《朱子语类》卷八十七);“理便是天理,又那得有恶”(《朱子语类》卷九十七)。可见在朱熹那里,“理”即是最高的“善”、纯粹的“善”,同时“理”也是天地万物的价值本源;尽管万物变化多端、流转无常,但“理”之“善”则寓于其中。相对于万物之为“物”的价值而言,“理”的价值是最高的价值。朱熹指出:“夫天理之流行,无一毫间断,无一息停止,大而天地之变化,小而品汇之消息,微而一心之运用,广而六合之弥纶,浑融通贯,只是这一个物事。”(《朱子语类》卷三十一)同时,朱熹认为“理”是“极本穷原之善”、“善根”、“未发之善”(《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与郭冲晦》);又云:“继之者善,是流行出来。人方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气,则是继之者善”(《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继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资以始”(《朱子语类》卷七十四);“继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同上)。因此,朱熹认为万物之性皆继理之善,“本然之性只是至善”(《朱子语类》卷五十九)。由上观之,在朱子那里,“理”具有“至善”之品性,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万物的本然之性——至善性与价值性。换言之,“天地间某个特殊的人或事物,是否有价值,关键在于它能否继本原之善,顺本原之善” ③。
(三)“当然之理”是价值目标。继“本然之理”后,朱熹又提出“当然之理”。在他看来,“当然之理,无有不善者。”(《朱子语类》卷四)进而,朱熹指出:“义者,人心节制之用;道者,人事当然之理”(《朱子语类》卷五十二);“格物只是就事物上求个当然之理。若臣之忠,臣自是当忠;子之孝,子自是当孝”(《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各有个当然之理,此便是道”(《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当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体,故仁义礼智为体”(《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一)。凡此可见,“当然之理”不仅是“本然之理”的呈现,而且也是“人伦之理”的彰显。这样一来,朱熹便完成了由本然之理向当然之理、人伦之理的逻辑推衍,如此不仅解决了价值来源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而且也完成了本然之理向当然之理与人伦之理的价值转移。同时,朱熹还从教化的角度论涉“当然之理”,他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自书契以来,二典三谟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谓尽矣。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测也,但患人不子细求索之耳。”(《朱子语类》卷十一)又云:“圣人所谓无为,却是付之当然之理”(《朱子语类》卷二十三);“不惑,则知事物当然之理矣。然此事此物当然之理,必有所从来”(同上);“不惑,谓知事物当然之理;知天命,谓知事物之所以然”(《朱子语类》卷六十)。在朱熹看来,“人”作为价值主体应事接物皆应洞悉“当然之理”,“方行之际,则明其当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后,则识其所以然,是习矣而察。初间是照管向前去,后来是回顾后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吃饭,方吃时,知得饭当吃;既吃后,则知饭之饱如此。”(《朱子语类》卷六十)又,朱熹指出:“言视听、思虑、动作皆是天理。其顺发出来,无非当然之理,即所谓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虽是妄,亦无非天理,只是发得不当地头。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为草木固无以异,只是那地头不是。”(《朱子语类》卷九十五)在朱熹看来,为学亦是如此,全在洞明“当然之理”;他说:“大凡为学有两样: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来。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寻个道理凑合将去,得到上面极处,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见得个大体,却自此而观事物,见其莫不有个当然之理,此所谓自大本而推之达道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四)此外,朱熹认为“人”作为道德主体其“体道”过程也是在寻个“当然之理”,他说:“道只是事物当然之理,只是寻个是处。大者易晓。于细微曲折,人须自辨认取。若见得道理分晓,生固好,死亦不妨。不然,生也不济事,死也枉死”(《朱子语类》卷二十六);“盖道却是事物当然之理,见得破,即随生随死,皆有所处。生固所欲,死亦无害”(同上);“所谓道者,只是日用当然之理。事亲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与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朱子语类》卷三十四)。朱熹又云:“父子兄弟君臣之间,各有一个当然之理,是道也”(《朱子语类》卷三十五);“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扎二》)。在朱熹看来,“人”作为人伦之网、社会之网与政治之网中的定在,一切行为与活动的展开皆应去寻“当然之理”。
比较而言,朱熹论域中的“本然之理”与“当然之理”隐含着“实然”与“应然”的辩证关系,可以说,朱熹在此之论已经触及到价值哲学的枢机。只不过,朱熹的理论向度是由“本然之理”、“当然之理”向“人伦之理”的“形而下的推衍”即“以天理明人事”,并不是像西方哲学那样进行逻辑化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分析。
(四)“人伦之理”是价值规范。如果说朱熹论域中的“本然之理”与“当然之理”带有形而上的意味的话,那么他沿着由“本然之理”、“当然之理”向“人伦之理”的“形而下的推衍”则透显出他的伦理关怀与价值旨归。首先,朱熹将“天理”以三纲五常的形式贯通到现实生活中(下文有论,此不赘述)。在他看来,“三纲”中的定位与职分完全是“天分”;他指出:“天分,即天理也。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则安得私!故虽‘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朱子语类》卷九十五);“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的件数”(《朱文公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其次,从个体层面看,“天理”就蕴含在人的现实生活与一切行为中。朱熹指出:人的“一言一语,一动一作,一坐一立,一饮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无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时也食,不正也食,失饪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逆天理。如只吃得许多物事,如不当吃,才去贪吃不住,都是逆天理。看道理只管进,只管细,便好。只管见上面,只管有一重,方好。如一物相似,剥一重,又剥一重;又有一重,又剥一重;剥到四五重,剥得许多皮壳都尽,方见真实底。今人不是不理会道理,只是不肯子细,只守著自底便了,是是非非,一向都没分别。如诐淫邪遁之辞,也不消得辨;便说道是他自陷,自蔽,自如此,且恁地和同过,也不妨。”(《朱子语类》卷三十八)在朱熹看来,人之言行饮食皆藏天理,然而今人自陷自蔽,无视天理,任由人欲,实则可悲!在此,朱熹着意区分天理与人欲其旨在提醒人们应当从日常行为与生活细节做起,层层剥落,剥尽之时,方见天理;如是,人之为人的道德品性便会涌现。
由上观之,在朱熹那里,“人伦之理”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价值本源与逻辑次第的。“本然之理”、“当然之理”与“人伦之理”的“理”是一个“理”即“天理”,三者并不是孤立的、毫不相干的,而是有其严谨的逻辑关联,其“内在精神”是贯通的。
(五)“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是价值呈现。价值呈现是价值主体行为活动的映现,价值主体追求正确的价值目标,正价值便在活动中呈现;反之,价值主体追求不正确的价值目标,负价值便会在活动中呈现。可以说,在朱熹的价值哲学中,“人”放任于“人欲”体现的便是负价值,“复尽天理”体现的便是正价值。换言之,追寻本源性的价值或原初性的价值是朱熹价值哲学的基本旨归,这一点在他提出的“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论见中体现得颇为明显。他指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此是两界分上功夫。这边功夫多,那边不到占过来。若这边功夫少,那边必侵过来”(同上);“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譬如刘项相拒于荥阳成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初学则要牢札定脚与他捱,捱得一毫去,则逐旋捱将去。此心莫退,终须有胜时。胜时甚气象!”(同上)在此,天理与人欲之于“人”貌似一对矛盾,双方时有交战:此进彼退,彼退此进。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做哪?朱熹门人尝问:“凡人所以矜伐者,其病根在甚处?只为有欲上人之心。才有欲上人之心,则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凡可以矜己夸人者,无所不至。故学者当去其欲上人之心,则天理自明矣。”朱熹回答说:“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圣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说,只要人去得私欲。”(《朱子语类》卷三十二)又,朱熹云:“是以圣人教人,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人若每事做得是,则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会得此意,则天何尝大,人何尝小也!”(《朱子语类》卷十七)“天理人欲,相为消长。克得人欲,乃能复礼。颜子之学,只在这上理会。仲弓从庄敬持养处做去,到透彻时,也则一般。”(《朱子语类》卷三十)统而言之,在朱熹那里,理与欲是此消彼长、彼长此消之关系;私欲既去,天理自明;私意净尽,天理照融。
在朱熹那里,“欲”有好、坏之分,求仁、向善之欲是好的,人欲、私欲是不好的;故而,朱熹认为好的应培养之,坏的应尽革之。以水为喻,他说:“欲是情发出来底。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但波澜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类;不好底则一向奔驰出去,若波涛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则灭却天理,如水之壅决,无所不害。”(《朱子语类》卷五)进而,朱熹指出:“仁只是一条正路,圣是行到尽处。……仁通上下,但克去己私,复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后为仁。若必待如此,则有终身不得仁者矣!”(《朱子语类》卷三十三)同时,朱熹认为理欲交战犹如正邪角力,他说:“以理言之,则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易;而邪之胜正,人欲之胜天理,若甚难。以事言之,则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难;而邪之胜正,人欲之胜天理,却甚易。盖才是蹉失一两件事,便被邪来胜将去。若以正胜邪,则须是做得十分工夫,方胜得他,然犹自恐怕胜他未尽在。正如人身正气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又云:“所谓‘五分天理,五分人欲’者,特以其善恶交战而言尔。有先发于天理者,有先发于人欲者,盖不可以一端尽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二)此外,在朱熹看来,“圣人教人,只此两事。博文工夫固多,约礼只是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则是天理”;“天理、人欲,只要认得分明。便吃一盏茶时,亦要知其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朱子语类》卷三十六);“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间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滔滔地流去”(同上)。由此可见,在朱熹那里,“人事、天理间,便是那下学、上达底”(《朱子语类》卷四十四),即天理与人事、人道相融通。具而言之,譬如为学,要在收心,次是功夫;心不放逸,天理可存;心存理得,功到学成。
总的来看,朱熹之“理”是形而上者,具有本体性、本源性与价值性;不仅是万物存在的依据,而且也是形而下者与“物”的价值本源。换言之,形而下者与“物”之价值本体是“理”,其价值呈现是“理”在具体层面的敞开与涌现;同时,一切存在物的价值旨归是趋近于“理”本身,尤其是“人”之价值更是通过“革人欲复天理”来实现的。从本然之理、当然之理向人伦之理的落实与贯通是天理的价值展开与价值呈现,“人”作为道德主体与价值主体通过革人欲复天理向“理”趋近与回归,这是一种基于个体德性绽放与价值超越的复归。从另一个角度看,朱熹强调的革人欲复天理还透显出对“理”的敬畏与终极关怀——对伦理精神、礼义制度与天理定在的敬畏,以及对现实社会与人本身的价值关怀。这种敬畏与终极关怀类似于康德说的:“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考,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①细绎之,在自然与天理面前,“人”的渺小与宇宙的浩瀚,“人”的有限与“理”的无限,此在世界的不堪与彼在世界的美好,现实世界的无奈与价值世界的圆满,……这一切,正是在仰望与反思、革尽人欲与复尽天理的价值向度中达到了某种平衡,如是,心灵才能得以安顿,人之有限才会被超越,人才能够接近无限、抵达自由之境。
二、“欲”作为“理”的悖反被消解
追根溯源,早在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对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就已有详论。程颢云:“天者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程颐云:“凡眼前皆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由此可见,二程不仅将天理或理视为世间万物存在的根本,而且坚称“理”在“物”中。同时,他们将形上之“理”予以普遍化并推展到人伦纲常中。这就是说,在二程的论域中,人伦纲常作为社会与政治规范先天地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它不仅是“天理”的具体呈现,而且也是个体生命活动的展开过程。进一步来讲,“人”作为社会个体与价值主体其存在之本源在天理、其价值之本源也在天理,“人”的价值呈现则是天理的具体呈现。同时,二程指出:“人欲”是蒙蔽本心、本性的氤氲,将会损害天理,以至毁灭天理。故而,他们提出:“无人欲即皆天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其实,“存天理”就是通过格物致知以“致天理”、“明天理”并“葆天理于心中”。在二程眼中,天理本在人心,若不“致知”,仍难得到;“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因此,他们强调“即物穷理”,并坚称“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无穷”(《河南程氏遗书》卷九);“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凡此可见,在二程那里,“存天理”是一种日积月累的工夫,其中存有某种“脱然自有贯通”式的顿悟。“灭人欲”即是通过“克己”、“克欲”与“复礼”来实现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尚书·大禹谟》),唯察“道心”之“微”,方克“人心”之“危”。考镜源流,不难发现:朱熹在理欲关系方面继承了二程的衣钵。
(一)“理”“欲”之价值品性的悖反,及其对“欲”的消解。如前所论,朱熹论域中的“理”具有本源性、至上性、至善性等价值品性,“天理”作为“理”的涌现其价值品性亦同然;相对于“人欲”而言,“天理”的价值品性颇显至高与至上。然则,“欲”作为人之为人的感性存在则是有好、有坏;其中,“人欲”不善、“私欲”多恶,故应革尽。
具而言之,在朱熹看来,“理”不仅是一切存在的本源,而且也是人伦道德的根本。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朱子语类》卷一),并强调“宇宙之间,一理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大纪》)。在朱熹看来,“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故发而为孝弟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朱子语类》卷四);“气不从志处,乃是天理人欲交战处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二)又,朱熹在《孟子集注》结尾处曾云:“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无真儒,则天下贸焉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 ①朱熹自诩承道于二程,沿着二程提出的“灭私欲即天理明”(《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的理路,他更是鼓吹“天理人欲,不容并立” ②。在朱熹看来,“理”是人们应该遵守的先天的大道;同时,“理”不仅是人伦纲常的根基,而且也是人际关系得以和谐与稳定的实在。因此,朱熹语境中的“天理”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天理是本体、定在,同时也是客观规律与伦常准则。诚如他说“合道理的是天理”(《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其二,天理蕴含着“善”,人欲则容纳着“恶”;“理”与人性相融通便是天地之性。朱熹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答郑子上书》)。具言之,天地之性的内容就是“义理之性”,也是“至善”的;亦如朱熹云:“百行皆仁义礼智中出”(《朱子语类》卷五)。朱子沿着二程“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路径进一步推论说:“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伪古文尚书》),“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盛,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十三)。可见,朱熹有意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并认为人欲是人心之恶,是一切不善行为的根源,同时也是导致天理泯灭的祸端。因此,“天理”与“人欲”不可并存,必须“革尽人欲”,如是,才能“复尽天理”。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才能使被欲望遮蔽的本心澄明,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本心与天理皆彰明。可以说,朱熹的理欲观建基于对当时之世人欲横行的省思与批判,其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或多或少地起到了抑制豪强、净化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但是他在天理与人欲上的极端言词也产生了诸多流弊,比如批评寡妇再嫁、宣扬贞节至上等。
(二)朱熹理欲关系论的诘难与另种可能。在“崇理”的语境中,朱熹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此举引出不少非议。有不少儒生认为:理欲关系只是相对的,并非如朱熹及理学家们所言的截然二分;其中,陆九渊对朱熹的批判尤为有力。在陆九渊看来,“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天理人欲之分,论极有病”(《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陆九渊认为,程朱将天理人欲二分则极易造成“天人不同”、“分明裂天人而为二”(《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凡此,势必人为地割裂“天人合一”的逻辑通路。在陆子看来,理欲难分,理欲共在;如是,才不至于阻断天人合一的通路。在程朱理学论域中,“理”在某种程度上是确立价值主体之价值取向与道德选择的依据,而“欲”则是“人”作为价值主体的感性的必不可少的一面,此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悖反与张力;朱熹以为应该革尽人欲,完成自我的超越,即复尽天理。只是这种做法过于刚猛,其试图将“人”的感性而不可分割的部分从“人”中剔除出去;这似乎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原因在于,“人”作为感性与理性的综合存在活泼泼地行走在天地间、人世中,如何能够革尽人欲?这或许正是清儒戴震批判程朱理学的要害之一。朱熹以天理消解人欲在某种层面上造成了对价值主体性的消解,如果说“人”作为感性的存在其喜怒哀乐之情是被否定的,那么则必然造成对“人”作为存在的合理性的消解。可以说,在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架构下,“人”作为价值主体与道德主体其主体性被不同程度地遮蔽了。也就是说,“天理”一出场,“人”便开始隐退,甚至卑微地追寻在“天理”之后,抑或被视为“天理”的对立面而被消解。在“天理”的笼罩下,“人”如若要实现主体价值就必须完成内在超越——革尽人欲;可是,“人欲革尽”时,“人”还是“人”吗?当然不是。在理学的进路中,“人”若革尽人欲更是“圣”了。也就是说,在“天理”的间架下,“人”之生命与价值展开的路向是朝着“成圣”而去的。这种价值取向与进路在某种程度上将“人”从欲望之海抽离出来,将“人”从滚滚红尘中抽离出来,从而完成了“人”作为道德个体与价值主体由关注外在价值向关切内在价值的转向,同时还完成了自我价值层面上的超越与向“天理”的复归。从“有我”(欲望之我)到“无我”(革去人欲之我),再到与“天理”合一,“人”作为存在其生命的绽放与价值的彰显是在无限地趋近于“天理”的过程中逐渐敞开、渐次呈现的;或曰:“人”正是在消解欲望与体认天理的过程中“归于终极而复于本善” ①。
从朱熹的哲学理路中,我们隐约发现:革人欲复天理在相当程度上蕴含着些许的道德乌托邦情结——道德理想主义情结。其实,以理克欲——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完全是一种个人内在性的带有神秘色彩的道德体验,这种活动本身不具有可复制性与可经验性,甚至流于当下一念之间的体验。尽管朱熹强调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要下工夫,要一件一件事地去格、去磨,直到豁然贯通。然而,朱子之后却无人由此法而进,更无真正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
(三)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张力与融通。如前所论,朱熹坚称“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后世学者对此多有附益。我们虽然难以置喙,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在某些细节问题上仍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承认,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程朱,他们对“人欲”多持批判与否定态度,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看到人之为人本来就有“人欲”的一面。具体到个体行为中,或许只是个道德选择与价值取向问题。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云:“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荀子云:“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荀子·正名》)。也就是说,先秦儒家并没有完全否定“人欲”,只是强调个体行为中不仅有“欲”,而且还要有“义”;同时,他们还指出“寡欲”、“节欲”远比“多欲”、“任欲”对个体道德修养有利。其实,朱子也并非完全否认人欲的存在,朱熹强调的所应革去之欲应是如好美食、好好色之欲,即超出人之为人的应当边界的欲望——有悖于天理之欲。朱熹尝云:“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朱子语类》卷七十八);“人心便是饥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饥而思食后,思量当食与不当食;寒而思衣后,思量当着与不当着,这便是道心”(同上)。又,朱子门人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朱熹回答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由此可见,朱熹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或“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并非要完全消灭人之为人的一切欲望,而是旨在消灭“要求美味”、“要求好色”与“要求好物”之“欲”——“过分之欲”。究而言之,在现实生活中,“人”作为道德个体应该如何行动呢?朱熹认为应该恪守礼仪,循理而动;故而他说:“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天理;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朱子语类》卷四十);“盖人心之灵,天理所在,用之则愈明。”(《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又云:“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为所累,何足乐!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于心亦不乐。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动静语默日用之间无非天理,胸中廓然,岂不可乐!”(《朱子语类》卷三十一)这就是说,尽管天理与人欲之间存在难以消弭的张力,但是二者之间仍存在融通之处——本能本然的合理之欲;当然这种欲也需要在礼与理的规约下来表现与满足。由“理”至“礼”,以“礼”制“欲”;“天理”作为客观定在完成了逻辑下落与价值呈现。可以说,“天理”作为人伦秩序的价值本源具体到文化形态层面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直观,更是一种价值涌现与伦理呈现;同时,“天理”架构中的个体欲望的表达与自由则是个体生命与价值展开的持续的感性动力。
其实,在朱熹那里,天理与人欲有分别也有融通,他尝云:“人欲隐于天理之中,其几甚微。”(《朱子语类》卷五十三)朱熹也承认人之为人的本能之欲与生存之欲在一定限度内是合理的,他说:“饥能不欲食乎?寒能不假衣乎?能令无生人之所欲者乎?虽欲灭之,终不可得而灭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也就是说,本能之欲与生存之欲作为“人”的基本欲求有其合理性,但是此欲若跨过合理之边界便是“过欲”,此时当“革之”、“灭之”。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将“好好色”的“人欲”与“我欲仁”的“道德欲”从人之欲中抽出并刻意加以区别与对立,高扬“我欲仁”的“道德欲”并着意贬低“好好色”的“人欲”,凡此在某种程度上对人之为人的整体性与主体性是一种支离与消解。
综上而论,在朱熹看来,“天理”被“人欲”无尽地“延异”与“异化”,为了复尽天理、归于至善,人们应该对欲望进行省察与节制,不断地消解之、革除之;同时应该由衷地向着天理与至善行进,不应因“天理”的精微与高远而放弃对天理之至善的价值追寻,以及成人与成仁的价值实践。抑或说,人欲之泛滥造成对天理的遮蔽,人欲之恶是天理之善的悖反与延异;相反,天理之流行则是对人欲的消解,天理之善的涌现则是对人欲之恶的超越;正是在天理与人欲的角力中人之为人的价值主体性得以彰显,正是在人对至善的追寻中天理的至善性渐次澄明并在人之生命绽开中不断涌现。
三、“理”向现实人伦与社会的落实
在此,我们认为朱熹之“理”是通过三纲五常来向现实领域落实的。诚如朱熹在《读大纪》中所云:“(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又,他在《论语集注·为政》中指出:“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夫自修身以至于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礼。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礼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谓天地之常经也。……与时宜之,而所因者不坏,是古今之通义也。’” ①不难看出,朱熹论域中的三纲五常业已突破前儒的理论边界,已经被推到“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的至上地位。其实,对此并不难理解;愚以为:朱熹之所以这么做,无外乎是要为三纲五常寻找形上依据。换言之,当三纲五常被纳入“天理”的图景中时,此举不仅解决了三纲五常的形上性与合理性,而且也增强了三纲五常的理论性与权威性。
(一)“理”贯“三纲”。在朱熹之“理”的图景中,“三纲”与“五常”具有亘古不易的价值品性。这一点在朱熹与门人的对话中曾有论及,朱熹门人问:“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损益可知,如何?”朱熹回答说:“此所谓‘不易也’,‘变易也’。三纲、五常,异古异今不可易。至于变易之时与其人,虽不可知,而其势必变易,可知也。盖有余必损,不及必益,虽百世之远可知也。犹寒极生暖,暖甚生寒,虽不可知,其势必如此,可知也。”(《朱子语类》卷二十四)又云:“所谓损益者,亦是要扶持个三纲、五常而已。如秦之继周,虽损益有所不当,然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只是安顿得不好尔。圣人所谓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时之运,春后必当是夏,夏后必当是秋;其间虽寒暑不能无缪戾,然四时之运终改不得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继周,酷虐无比。然而所因之礼,如三纲、五常,竟灭不得。”(《朱子语类》卷二十四)继而,朱熹指出:“三纲、五常,虽衰乱大无道之世,亦都在。且如继周者秦,是大无道之世。毕竟是始皇为君,李斯等为臣;始皇为父,胡亥为子。三纲、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损益亦不多”(同上);“看秦将先王之法一切扫除了,然而所谓三纲、五常,这个不曾泯灭得。如尊君卑臣,损周室君弱臣强之弊,这自是有君臣之礼。如立法说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皆有禁之类,这自是有父子兄弟夫妇之礼,天地之常经。自商继夏,周继商,秦继周以后,皆变这个不得。秦之所谓损益,亦见得周末许多烦文缛礼如此,故直要损其太过,益其欠处,只是损益得太甚。……”(同上)由是观之,朱熹以史为鉴,推说天理;旨在将“理”通过三纲五常来完成其向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贯通与落实。在朱子那里,“三纲”与“五常”亘古不灭,其因在于“理”之亘古长存;不难看出,朱子意在用“理”之客观性统摄人伦纲常的内在精神。较之,朱熹从历史之维诠释“理”,其“理”颇具“客观精神”与“绝对理念”的意味;可以说,“理”就是朱熹历史哲学的核心与伦理精神之定在。
站在维护纲常伦理的角度,朱熹认为毁坏三纲五常是贼仁、贼义之行为;譬之伐木,贼仁乃是伐其本根,贼义只是残害其一枝一叶。人而贼仁,则害了本心。进而,朱熹指出:“贼仁便是将三纲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理,一齐坏了。义随事制宜。贼义,只是于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朱子语类》卷五十一)据此,朱熹对当世诸子及佛老进行了批评,他说:“陆子静分明是禅,但却成一个行户,尚有个据处。如叶正则说,则只是要教人都晓不得。尝得一书来,言世间有一般魁伟底道理,自不乱于三纲五常。既说不乱三纲五常,又说别是个魁伟底道理,却是个甚么物事?也是乱道!他不说破,只是笼统恁地说以谩人。……他之说最误人,世间呆人都被他瞒,不自知。”(《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又云:“张孝纯守太原,被围甚急,朝廷遗其子灏摠师往救,却徘徊不进,坐视其父之危急而不恤,以至城陷。时节不好时,首先是无了那三纲。”(《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此外,在朱熹看来,“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由此不难看出,南宋时期的儒道释三家并进之格局以及相互诘难之紧张,置身其间的朱熹紧据儒家哲学力辩之、维护之、批判之,当仁不让地对当世诸子及杂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与回应。值得说明的是,不少学者认为朱熹高扬天理、维护纲常仅仅是为统治者作辩护,其实这是一种政治阶级分析式的剖判与误读。愚以为,与其说朱熹高扬天理、维护纲常是为政治与君主服务,不如说是出于对天理定在、伦理精神与礼义道德的敬畏与对现实和人自身的观照。
(二)“理”统“五常”。在朱子那里,“理”同时也是通过“五常”来具体呈现的,即“理”作为形上存在则形而下地贯穿于人伦规范之中。在朱熹看来,“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气则为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朱子语类》卷一)“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同上);“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义礼智,皆以四者相为用也。”(同上)进而,朱熹不仅以五行与五常相配,而且大有模仿董仲舒之意,提出了不同于董仲舒的五行配五常的新序列,他说:“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朱子语类》卷六)较之,朱熹此论与董仲舒颇为相似,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将五行与五常相配伍,其序是仁木、智火、信土、义金、礼水 ①。遗憾的是,朱熹虽然言及“气则为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但是却没有系统地论证他的五行配五常之序的根据何在,而董仲舒则是依据五行相生的逻辑比附出自己的五行配五常之序的。
“仁”是“天理之统体”(《朱子语类》卷六)——人生价值之原点。朱熹曾从理气相即的角度论及“仁”,他说:“理难见,气易见。但就气上看便见,如看元亨利贞是也。元亨利贞也难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时尽是温厚之气,仁便是这般气象。夏秋冬虽不同,皆是阳春生育之气行乎其中。”(《朱子语类》卷六)又曰:“仁便是恻隐之母”;“若晓得此理,便见得‘克己复礼’,私欲尽去,便纯是温和冲粹之气,乃天地生物之心。”(同上)据《朱子语类》载,赵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统体。’”朱熹曰:“是。”(《朱子语类》卷六)又,朱熹认为:“若能到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处,皆可谓之仁”(《朱子语类》卷九十六)。这就是说,“仁”在道德层面不仅是“天理”的呈现,而且是其枢机;“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这天理,便与礼乐凑合得著,若无这天理,便与礼乐凑合不著”(《朱子语类》卷二十五)。同时,朱熹指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冬则生意之藏也”(《朱子语类》卷六);“仁与义是柔软底,礼智是坚实底。仁义是头,礼智是尾。”(同上)更有意思的是,朱熹以酿酒为喻来诠释“仁”,他说:“‘仁’字如人酿酒:酒方微发时,带些温气,便是仁;到发到极热时,便是礼;到得熟时,便是义;到得成酒后,却只与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间,早间天气清明,便是仁;午间极热时,便是礼;晚下渐叙,便是义;到夜半全然收敛,无些形迹时,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同上)继而,朱熹指出:“圣人亦只教人求仁。盖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头头做著,不用逐事安排。”(同上)较之,朱熹以“仁”包“义礼智”的论见突破了孟子提出的“四端”之序列,虽然孟子将“仁”排列在“四端”之首,但是他并没有明言“仁”可包“义礼智”。在此可以说,以“仁”包“义礼智”确立了人的价值原点,提升了“仁”在“四端”之序中的地位;这甚至可以说是其“理一分殊”在道德层面的具体发用。
“义”是“天理之所宜”(《朱子语类》卷二十七)——价值取向之标准。在朱熹那里,“天理”融通“五常”,义利之间皆显“天理”。故而,当门人问:“凡事只看道理之所宜为,不顾己私。利者,人情之所欲得,凡事只任私意,但取其便于己则为之,不复顾道理如何?”朱熹回答说:“义利也未消说得如此重。义利犹头尾然。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盖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彻,见得义分明。小人只管计较利,虽丝毫底利,也自理会得。”(《朱子语类》卷二十七)不仅如此,朱熹还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指出:“知得事亲不可不孝,事长不可不弟,是为义之本”(《朱子语类》卷二十)。这就是说,“义”作为五常之一,它的价值呈现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价值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应事接物之分寸尺度的把握,二是价值主体在家庭生活中日常行为的依据与凭藉。概之,天理宜处便见义,义之价值源于天理;所以“君子只理会义”,“小人只管计较利”。
“礼”是“天理之节文”(《朱子语类》卷六)——制度价值之体现。在朱熹的视野中,具体的礼乐教化制度也是融通“天理”的;他说:“‘礼者,天理之节文’。节谓等差,文谓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朱子语类》卷三十六);“礼乐者,皆天理之自然。节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乐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这天理本是笼统一直下来,圣人就其中立个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亦如此;其外如此,其里亦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才差其界限,则便是不合天理。所谓礼乐,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则无不可行也。”(《朱子语类》卷八十七)又云:“无礼之节,则无乐之和,惟有节而后有和也。”(同上)可见,在朱熹那里,圣人制礼作乐本与天理“合”,圣人虽殁,但礼乐融摄的天理之精神却亘古长存。礼之节,乐之和,节、和之间,天理尽现。不仅如此,朱熹还从个体层面论及“礼”之来源与功用,他说:“礼者,仁之发;智者,义之藏。且以人之资质言之:温厚者多谦逊,通晓者多刻剥”(《朱子语类》卷六);“知事亲事长之节文,为礼之本”(《朱子语类》卷二十);“知礼成性,而天理行乎其间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六)。朱熹又云:“所以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今复礼,便是天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有君臣,便有事君底节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节文;夫妇长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实皆天理也。”(《朱子语类》卷四十二)因此我们以为:在朱熹那里,“礼”作为人伦纲常与社会规范其价值体现在人我关系中,“礼”作为道德律令其价值体现在个体自我的道德修养与价值超越中。概之,“礼”之精神贯通“天理”,而“天理”之价值则通过“礼”得以彰显。
“智”是“知得事理”(《朱子语类》卷八十六)——价值判断之凭藉。朱熹曾指出:“智是知得到,圣是行得到。”(《朱子语类》卷五十八)又云,“如说仁义礼智,曾认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义?如何是礼?如何是智?须是著身己体认得”(《朱子语类》卷十一);“如论语:‘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谓:‘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同上)在朱熹眼中,为学、成物是“智”之表现,“知事亲事长,为智之本”(《朱子语类》卷二十)。此外,朱熹与门人在讨论“太极图之说”时曾提出:“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气便是阴阳,躯体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其气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义礼智信”(同上);“太极便是性,动静阴阳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义礼智信,化生万物是万事”(同上)。又,朱熹云:“仁,阳也;智,阴也。”(《朱子语类》卷七十四)细绎之,朱熹如是说颇显牵强附会,如若仁为阳、智为阴,那么义、礼为何?四者又应如何统一于“性”与“心”上呢?尽管朱熹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就人身言之,道是吾心”(同上);但是具体到仁义礼智之四端再分阴阳就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了。当然,这似乎并不妨碍朱熹以阴阳比附仁义礼智——“义智属阴,仁礼属阳”(《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至于说,朱熹认为“元亨利贞,仁义礼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将这四个只管涵泳玩味,尽好”(《朱子语类》卷七十五);这便颇具董仲舒式的五行配五常的附会意味了。
“忠信”是“天理之所以存”(《朱子语类》卷十六)——价值呈现之定在。朱熹时而以仁义礼智之“四端”并提,时而以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并论,时而又以“忠信”并说;尽管他在不同场合提法不一,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天理”是融通诸种人伦纲常与价值规范的。据《朱子语类》载,赵唐卿问:“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机决矣!’何也?”朱熹回答说:“他初且言得众、失众,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终之以忠信、骄泰,分明是就心上说出得失之由以决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骄泰乃天理之所以亡。”(《朱子语类》卷十六)突破前人理论之边界,朱熹在“天理”的图景中将“忠信”与“骄泰”对举,在天理存亡之间刻意提升了忠信的地位——将忠信蕴含的伦理精神(修己、为人与交往)推升到天理的高度,从而凸显了忠信在当时之世的伦理地位与重要性。
从五常所体现的相互关系看,朱熹认为:“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智之于贤者”(《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说,更无说处。仁义礼智,似一个包子,里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浑然,非有先后,元亨利贞便是如此,不是说道有元之时,有亨之时。”(《朱子语类》卷六十八)又云:“性便是仁义礼智”(《朱子语类》卷六十四);仁义礼智“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四)。如是,“何以验得性中有仁义礼智信”?朱熹门人如是问道。朱熹怒曰:“理本实有条理。五常之体,不可得而测度,其用则为五教,孝于亲,忠于君”(《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知其自仁中发;事得其宜,知其自义中出;恭敬,知其自礼中出;是是非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实有此四者。眼前无非性,且于分明处做工夫”(同上)。其实,在朱熹看来,“人人有许多道理,盖自天降衷,万里皆具,仁义礼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自家一身都担在这里。须是理会了,体认教一一周足,略欠缺些子不得。”(《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朱熹又云:“人之性惟五常为大,五常之中仁尤为大,而人之所以为是仁者,又但当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昼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废惰;则虽不能常常尽记众理,而义礼智信之用,自然随其事之当然而发见矣”(同上);“每日开眼,便见这四个字在面前,仁义礼智只趯著脚指头便是。这四个字若看得熟,于世间道理,沛然若决江河而下,莫之能御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见得每日所看经书,无一句一字一点一画不是道理之流行;见天下事无大无小,无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发见。”(同上)由是观之,仁义礼智信作为道德主体的德行与规约,于内是道德修养原则,于外是具有普遍规约性的价值准则。
在理学家们看来,如果没有三纲五常,社会必然失序,道德必然坠地。可以说,三纲五常之所以亘古长存皆因天理统贯其中,同时三纲五常犹如无形之网笼罩于“人”,使得“人”的一切行为皆在规则与教化之中。如是,朱子之“理”便由至上的客观的悬设的“定在”落到了“人”、落到了现实。在传统社会中,三纲五常作为道德规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体现在个体的道德修养上,而且还体现在理顺诸种人伦关系上。此种重要性犹如英国哲学家休谟譬喻的那样,“没有规则,人们甚至不能在道路上相互通过。赶大车的人、载客的马车夫和小马车驭手,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相互让道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基于相互的舒适和便利” ①。诚然,朱熹将三纲五常纳入“天理”的图景中是自有其深义的,他不仅要为三纲五常寻找形上本体,而且也要为其在社会与政治中的持续运行作合理论证,同时以期为南宋王朝的绵延与儒家道统的传承注入新思想与新血液。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朱熹理学视域中的人我关系是存在尊卑等级的,并不像西方学者所理解的人我关系完全是存在与存在之关系;譬如萨特说:“我与他人的关系首先并从根本上来讲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而不是认识与认识的关系” ②。如果完全将人我视为抽象的没有情感的存在,以及存在与存在的关系,那么可能就会消解人伦亲情与政治伦常的情感因素,这或许正是中西价值观及其政治哲学的根本分歧之一。换言之,在中国传统儒家的论域中,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乃至政治关系均蕴含着人伦亲情,以及由人伦亲情放大后的政治亲情;例如父母官、民之父母与爱民如子等范畴可以说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父情结与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文化境域中,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其实就是基于现实人伦生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所建构的一套具有规约性、秩序性与权威性的制度规范,其中也曾容涵了某些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合理要素,例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等;可以说这种道德规范并非只是具有单向的约束力,而是具有双向的近乎对等性的约束力。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君主专制与父权横行的社会中,这种伦理制度对“君”与“父”的约束力是很难奏效的,但是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它所隐存的伦理精神与制度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值得肯定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三纲五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推崇与延用至少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大一统”政治架构所营造的尊卑有等的政治环境;二是农耕文明所产生的宗法制度与家族制度之亲亲环境。客观地讲,三纲五常并非只是形而上的伦理设计与哲学玄思,它在漫长的历史流程中也曾体现出其合理性与时代性;也就是说,这种人伦“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 ①。从“人”的角度看,“人的社会生活,甚或社会动物的群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个体依照某些规则行事” ②。当然,我们亦不否认:三纲五常经由历史与政治异化后业已变成一种绝对性秩序与伦理教条,尤其是对处于下位的人来说,它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异化力与逼迫力。在君权、父权与夫权的迫力下,道德规约变成了变相奴役,道德个体被来自政治与制度的力量所裹挟、所异化。虽然我们美其名曰其谓“教化”,但是却不应该忽略这“教化是自然存在的异化” ③,以及“教化的虚假性” ④。其实,“真正说来,绝对的秩序不是通过德行才显露出来的,因为所谓显露,作为一种行动,乃是个体性的意识,而个体性却是要被扬弃的东西。然而唯有通过个体性的扬弃,世界进程的本体或自在仿佛才有它自在自为地进入实际存在的行动余地。” ⑤或许,这才是程朱理学高扬天理、消灭人欲的根由所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朱熹之“理”作为价值本源有着至上性、至善性与定在性等特性,同时也有着从本然、当然至人伦的价值呈现进路。在“理”的间架下,“人”作为价值主体在“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价值向度中实现自身德性的绽放与学以成人、学可至圣的价值目标。当然,朱熹将天理与人欲相对立的意图在于提撕自陷与自蔽之人莫要在欲望的深渊中越陷越深,而应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朝着至善挺进。其实,这种理念就体现在他的“理”贯“三纲”与“理”统“五常”的道德形上学中。在三纲五常的图景中,人之德行与伦常秩序是并行的,人之德性、伦理精神与客观之“理”是贯通的。可以说,朱熹强调天理人欲不可并立的意图在于阐明“人”通过革欲、格物、为学等手段可以实现成人与至圣,以及复尽天理的终极价值目标。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人”作为“存在”是多维的,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是道德的又是欲望的,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的;不仅如此,“人”的欲望也是多元与多层次的,因此其价值需求必然也是多元与多层次的;任何整齐划一的规训与教化或许都将导致对“人”的异化与困累。或许,朱熹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指出:向善之欲、合乎天理之欲应鼓励之;向恶之欲、悖于天理之欲应革除之。或曰:“欲”虽应革,但有边界;要在天理、要在应然。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心存疑问:是不是消灭了人欲就能够使天理流行?是不是个体灭绝了欲望就能够成为圣贤?是不是社会处于绝欲或禁欲之中就能够实现海晏河清?其实,程朱理学论域中的“存天理,灭人欲”与“革尽人欲,复尽天理”隐存着些许的道德乌托邦情结,其现实价值与意义或许并非仅仅在于要在现实社会实然施行之,而是在于引导人们对泛滥的欲望进行节制、对自我的堕落进行反思,以及对日渐沉沦的世道人心有所警醒与关切。
On the Value Connotation and Orientation of ZHU Xi’s“Truth”
WANG Chuan-lin
(School of Philosophy,Be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the predecessors,especially CHENG Hao and CHENG Yi,ZHU Xi not only has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Truth”,but also expanded the extension of“Truth”.He fully affirmed the metaphysical quality of“Truth”,the originality and valuable attribution of“Truth”,at the same time,through“Truth”threads together 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Truth”governs five constant virtues (benevolence,righteousness,propriety,wisdom and fidelity)completed the basic construction of the moral metaphysics in“pushing truth on human affairs”.“Truth”is extrapolated to the human relations,social and political fields,“human desire”is dispelled in the process of attempt,and saw“desires eliminated and returning to nature”as the value presented approach for people to pursue the ultimate value to indicate the direction.Based on this,ZHU Xi not only is for Confucian thoughts to find metaphysical basis,but also for the ethical norm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real life finding the persuasive theoretical foundation.Indeed,“preserving Heaven,destroying human desires”in the domain of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has some complex of moral utopian.Its realistic value and significance not only is to execute social reality,but that lead people to control the flood of desire and self-reflection,and be alert and concerned to gradually sinking morals and human heart.
Key words: ZHU Xi;“Truth”; value origin; value orientation; value realization
[责任编辑:刘春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5页。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1页。
参见孙伟平:《价值哲学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参见蒙培元:《朱熹哲学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0页。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64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77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4页。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5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9-60页。
参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1-365页。
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1页。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第325页。
弗里德利希·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83页。
弗里德利希·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第184页。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8页。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第75页。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