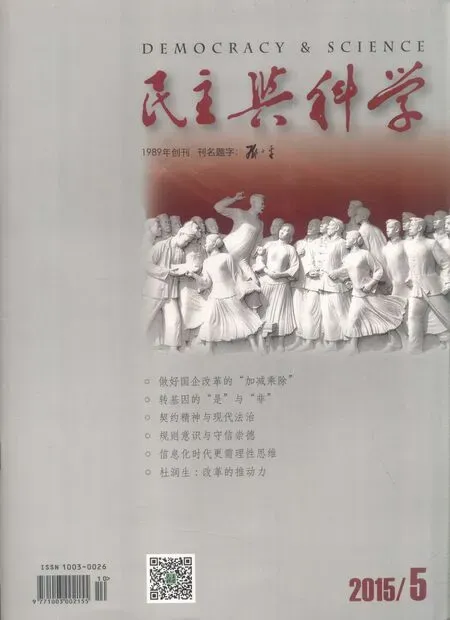契约精神与现代法治
■ 徐爱国
契约精神与现代法治
■ 徐爱国
契约精神是现代的产物。古代法律注重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身份依赖;现代法律倚重个人权利,突出意思自治的契约自由。历史学家称,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演变。所谓从身份到契约,是指法律本位从家族到个人的发展。在古代社会,所有人都依附于家族——妻子依附丈夫、儿子依附父亲、仆人依附主人。依附者没有独立法律人格,不能为自己私利以个人名义做出法律上的决定。现代社会下,个人逐渐脱离家族束缚,也就是摆脱了身份,能够按照自己意愿处理人身和财产。个人之间的合意,可以概括为契约。法律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便是古代法向现代法的过渡。
契约精神物化为具体法律,可以称为以法治为目的的行为规范。财产法的现代精神是个人自决地取得、占有和处分个别财产。而在古代社会,个人并不能取得和享有私人财产,财产实际上为家族或村落共同所有。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乃是现代法治的体现。一个人将自己的财产按照意愿转让他人,双方合意通过等价交换达成互惠互利,是财产契约的基本属性。古代社会财产交换注重财产转让的外在“仪式”,现代则注重双方当事人内在的合意和协议,有了自由意志和个人自决,契约法才从古代发展到现代。继承法的现代意义是,个人可以按照自己意愿立遗嘱处理自己财产,继承人只继承权利而不承担无限义务。而古代继承则是“概括继承”,继承人同时承担被继承人的权利和义务。这意味着,死亡者的肉体人格虽然死亡,但是他的法律人格依然存在,毫无减损地传给继承人或共同继承人。现代婚姻以两性生育和抚养子女为基本特点,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是神法与人法的结合。婚姻是一份契约,男女双方合意共同生活、生育抚养后代。因为双方平等契约,所以夫妻有平等对待的权利和义务,有相互扶助的义务和责任,夫妻存续期间所得归夫妻共有,离婚时男女均分共有财产。与此不同,古代婚姻目的有二,一是家族延续,二是通过联姻扩展政治权利。婚姻权归家父,而非男女双方,于是才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说。
契约理念与个人自治和自由竞争的现代观念一致。19世纪历史学家与18世纪理性主义者对法律现代化的认识相同。不同的是,19世纪法律史学家把研究课题从现代追溯到古代,探讨古代法律如何历史地过渡到现代,展现了西方社会亦即他所谓的“进步社会”的法律发展史。简练的“从身份到契约”的口号,成为19世纪后法律界广泛认可的法律名言。英国人梅因考察了以罗马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法律和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法律。在他那里,西方社会是少数和进步的社会,东方社会则是多数和停滞的社会。在法律发展模式上,法律自发的发展东西方没有差别,都经过了从宗教意味的个别判决到贵族垄断的习惯法最后到法典的过程。此后,东西方法律发展发生分野,少数和进步的西方社会经过“法律拟制”“衡平”和“立法”完成从古代向现代法律的转型。
当西方社会在近代兴起时,东方社会开始由兴盛转向衰落,其中原因,就是东方人喜欢静止和抗拒变化的本性。历史学家的判断总会有相似之处,梅因“少数与进步”社会的法律进化论,与后来德国人韦伯“唯有新教伦理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及“法治只是西方社会特有的偶然现象”命题,同出一辙。在1922年发表的《法律史解释》中,美国人庞德承认梅因“从身份到契约”的著名论断“为英美法律思想所普遍接受,并一直统治到19世纪末。它现今仍在美国宪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将个人契约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可以说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石就是社会契约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传入中国最早的政治法律著作之一。从他的社会契约论,中国人开始知道“人民主权”“公意”“自由”和“平等”,甚至“法治”这样的名词术语。18世纪的卢梭不是社会契约论的发起人,而是社会契约论集大成者。政治权力源于人民授权;通过主权者与人民之间的契约,人类社会从野蛮的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的现代社会;政治和政府的任务应该是保护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宣告。这些现代法律精神在17至18世纪的学者那里屡见不鲜,其中有人们熟知的格劳秀斯、普芬道夫、霍布斯、洛克、狄德罗和孟德斯鸠等。社会契约论与其说是哪一个人的思想成果,还不如说是整个17至18世纪世界性的思想启蒙运动。
近代社会契约论是讲,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没有公共权力,也就没有法律,他们按照自己本性过着野蛮生活。当人民感到自然状态无序和混乱所导致的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的时候,想到一种相互结合方式,利用集体力量来保护个人权利,于是就通过社会契约方式联合起来。人民把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权利转让出来,把个人权利组合成一种公共权力,这个权力让一个凌驾在个人之上的主权者掌握,这个主权者可以是一个君主,一个代表机关,也可以是一个抽象人格。因为公共权力来自人民授权,因此君权民授或者主权在民;因为主权者与人民有契约,因此主权者行使政治权力时候要保护人民利益;因为大家都遵守自己诺言,因此就有了共同意志之下的法治。从这个意义讲,社会契约论实际上是一种公共权力起源理论,即国家与法律的民主起源说。
社会契约论在实践上发生了革命性影响。法国人特有的浪漫、激情和博爱打动了欧洲人,最后通过殖民活动,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理论传遍世界。法国《人权宣言》称,人生而平等自由,主权源于国民,法律是公共意志表现,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语言基本上来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美国《独立宣言》称,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是人们不可转让的权利。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来源于洛克的《政府论》。即使是孙中山的“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和“共和国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命脉在国会”,乃至他的“五权分立”,也无不有着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理论的影子。社会契约论摆脱了人类历史包袱和羁绊,让人民容易直接将自己的理想转化为政治与法律现实。
当代学者在设计社会公平理想制度时候,也会回到社会契约论。罗尔斯社会公平论的核心是,自由优先、平等纠错,他的论证方式还是契约论。他的“无知之幕”和“原初状态”的理论前提,不过是社会契约论中“自然状态”和“权利转让”的一个现代翻版。德沃金声称自己不是一个传统自由主义者,当他提出“认真看待权利”口号的时候,他所呼吁的“自由和尊严的不可侵犯性”和“社会弱者的保护”,他所倡导的法律原则优先于既定法律规则的法律帝国,都从17至18世纪社会契约论的遗产中得益颇多。
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法治社会,必定要经过从家父权到共和国的过渡。一方面,动态上考察,中国实行法治,必定要以现代个人自治取代家长制观念;另一方面,静态上考虑,必定要树立民主观念,国家公共权力来自人民。这个过程经过百年,但是任务依然艰巨。
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结构为家庭,小家庭有家长,大家族有族长。家长对外代表家庭承担家庭成员的法律责任,对内享受家父权。瞿同祖说,每一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秩序自可维持。亲亲相隐、留养存嗣、子孙违反教令、一夫一妻多妾、亲属相犯与相奸,都是浓厚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
对于中国古代法律特质,法律史学家有各种各样的描述,不过,公认特质便是法律上的家族主义和等级特权制度。社会基本单元是家庭,男性长者为家长。家长既握有家庭成员的惩戒权,同时也是对外法律责任承担者。若干同宗之家,推选同族族长,族内纠纷的处断者便是族长。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关,家族内的纠纷先由族长仲裁;不能够调解处理,才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亲属间的杀伤、盗窃和奸非按照亲属远近服制惩戒,一般原则是尊犯卑减免处罚,卑犯尊加重处罚,完全不同于常人间的犯罪与惩罚。亲属间的容隐既是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也是法律义务。
西方现代法律起源于启蒙学者对封建法律的批判,从理论角度看,18世纪的社会契约论战胜了古代社会的君主主权论,法律人道主义战胜了法律暴虐主义。19世纪后,西方各国在政治和法律制度层面确立了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到中国清修律的19世纪末期,西方各国已经完成法律的人道主义改造,而当他们殖民到东方世界的时候,遭遇东方专制主义。清末修律的象征意义,就是要在中国对野蛮的法律进行人道主义改造。百年过去了,家族制基本上在法律层面消失,但是人民当家作主尚未实现。官僚主义、等级特权和家长遗风,在社会中依然存在且根深蒂固。这是中国当下法治面临的艰巨任务。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目标,实现这个理想,中国法治才有希望。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马鞍山市博物馆馆藏契约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