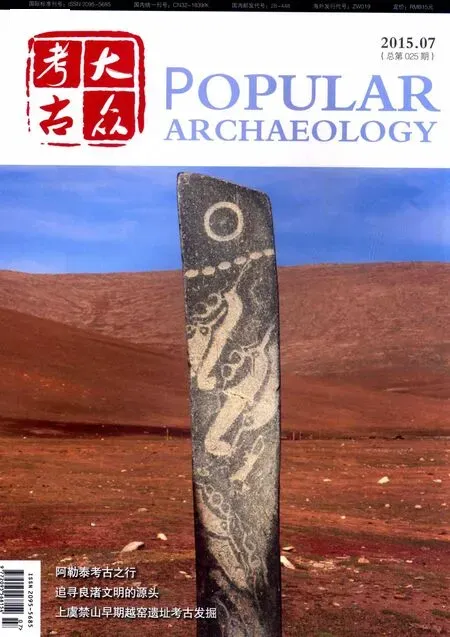南北朝墓葬中的“皿花”图像与佛教
文 图/崔贻彤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人对莲花的喜爱源远流长,早在《诗经》中便有吟唱。而南北朝墓葬中的“皿花”图像已经超出了早期质朴的审美观,完成了从“形”到“质”的升华,从而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
“皿花”图像是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出现的一种装饰题材,顾名思义,就是以细长颈瓶或博山炉作为盛器,里面插有盛开的莲花。中国人对莲花的喜爱源远流长,早在先秦的《诗经》中便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彼泽之陂,有蒲与荷”的吟唱,不过那时多是以莲(荷)花隐喻美丽的女子,继而作为情爱意象的化身。南北朝墓葬中的“皿花”图像已经超出了这种早期质朴的审美观,完成了从“形”到“质”的升华,从而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
“皿花”的雏形
“皿花”图像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至东汉时期,在河北望都东汉源阳侯孙程墓的墓道壁画上,绘有一陶质卷沿盆,置于方几之上,内插等长、等距、同形的6 枝红花,画面右上方还有“戒火”的题字,陈直先生曾对此做过考证,指出“《本草》有记载‘景天,一名戒火,一名火母,主明目轻身’,据此,则瓦盆所画为景天,因又名戒火,取绘其象征性也”。
魏晋时期,“皿花”图像目前仅在青海海东市平安魏晋画像砖墓中发现一例:画面正中是一庑殿顶的房屋,屋内两人相对坐于一巨案之上,二人头部之间有一瓶,瓶中插有花草;左边人物的左臂同右边人物的右臂,连臂放置于二者之间的一件钵上;案下有一小人双手捧一侈口细颈圆腹罐,做跪伏侍奉状。有学者认为这一画像与佛教有关。
南北朝墓葬中的“皿花”
南北朝时期,“皿花”图像逐渐盛行起来,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南朝时普遍用于墓葬装饰之中,并且主要出现在构建墓室空间的画像砖上。比如福建闽侯南屿南朝画像砖墓,墓壁第十三层立砖上绘有宝瓶图,瓶中所插之花,与同墓出土莲花纹砖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此墓左壁第五层立砖上绘有一供花僧人图,右壁与之相对应的位置则绘有一诵经僧人图,说明此时皿花成为佛教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河南邓州南朝彩色画象砖墓也有相似的题材出土。其中两组“人象画像砖”下部的构图形式皆为画面中央为人裤腿下部,左右两侧各有一瓶花图案,即耸立的莲花枝上各立有一净瓶。同样出于此墓的一幅“飞仙画像砖”上,瓶花的形象则被烘托得更为高大,画面中央为一细长颈折腹瓶,瓶中插有莲花,两侧各有一飞仙面朝瓶花作跪拜状。
南京油坊桥南朝画像砖墓也出有一花供图,在墓壁柱的转角处,模印于小长方形砖的端面,一侧为插在净瓶的莲花,另一侧为置于果盘上的供品,二种纹样分别倒置、互为对称。
湖北襄阳贾家冲画像砖墓中则出土了大量的有关佛教内容以及儒家题材的画像砖和花纹砖,其中在北壁第八层丁砖层的飞仙图上,中央绘两净瓶立于覆莲之上,净瓶上方和两侧饰有莲瓣和卷草纹。净瓶两侧的飞仙相对呈蹲踞状,手中捧物,头梳双髻。此外,还有净瓶莲草纹砖,嵌砌于墓室和甬道自下至上第四层丁砖层上,和正面供养人相间排列。
此外,南朝墓葬中还有一类“皿花”图案是以熏炉作为容器出现的。还是在襄阳贾家冲南朝画像砖墓中,有一幅飞仙图,两仙相对呈蹲踞状,手中捧物,画面中博山炉立于覆莲之上,炉顶立莲瓣,两边饰莲草纹,四周有忍冬纹边框。
北朝墓葬中的“皿花”图像似乎就不如南朝盛行,目前仅见的一例出现于河南泌阳西向北朝墓。在其画像石棺床上有一幅以熏炉为中心的图画,棺床前腿是三个单独画面,左幅和右幅均刻有两卫士,表情庄重肃穆,中幅则刻一半身裸体侏儒,头顶薰炉,并由双手扶持,炉顶有莲花和莲蓬,两侧有忍冬、莲花衬托。
南北朝时期的“皿花”图像已经形成了一套基本固定的构图规范,从画面的结构来看,往往与飞仙、供养人、僧侣等人物形象相组合,作为佛教文化的因素已经非常明显,表现的可能是一种供祭仪式,但这还需要考古材料的进一步印证。
“皿花”图像的渊源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皿花”图案的出现并非偶然,首先,它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有关。东汉末年印度佛教汉文译本问世,东汉康孟祥译的《修行本起经》中写到:“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道行经·昙无竭品》也说到:“其像端正姝好,如佛无有异,人见莫不称叹,莫不持花、香、缯来供养者……”可见早在东汉,佛教教义及佛前供花的理念就已经传入中国,为“皿花”图像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精神土壤。不过当时的社会认可度有限,而且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理念也并未真正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也可见到关于“皿花”的相关记载,如《晋书·艺术传·佛图澄》中就记载,石勒召见佛图澄时,“勒召澄,试以道术。澄即取钵盛水,烧香咒之,须臾钵中生青莲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两晋时期佛教因为是“夷狄之神”,曾经遭遇过一定的阻力。《晋书·列传第四十七》载:“彭城王绂上言,乐贤堂有先帝手画佛象,经历寇难,而此堂犹存,宜敕作颂。帝下其议。谟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艺,聊因临时而画此象,至于雅好佛道,所未承闻也。盗贼奔突,王都隳败,而此堂塊然独存,斯诚神灵保祚之征,然未是大晋盛德之形容,歌颂之所先也。人臣睹物兴义,私作赋颂可也。今欲发王命,敕史官,上称先帝好佛之志,下为夷狄作一象之颂,于义有疑焉。’于是遂寝。”
到了南北朝时期,以花供佛的做法真正在宫廷和僧寺等场所中流行起来。《南史·齐武帝诸子》:“晋安王子懋,字云昌,武帝第七子也,诸子中最为清恬,有意思,廉让好学。年七岁时,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罂中稍有根须,当世称其孝感。”可见当时僧寺之中瓶花供佛的做法已较普遍。而在北朝,北魏龙门石窟浮雕中宾阳中洞的《皇后礼佛图》也可为佐证,画面中一名贵妇手执花束,以一枝莲花为主,两边各衬比主花低的莲蕾等,前有捧瓶状之物的佣人,北朝宫廷法会上“花供”的情形可见一斑。
《簪花仕女图》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传为唐代周昉作。作品取材当时贵族妇女游乐生活,精细地刻画了几个身披轻纱、高髻凌风的贵妇在庭院中闲步、赏花、采花、戏犬等生活情节。人物步履从容,但眉宇间却流露出若有所思的心态。圆浑流畅的线条,艳丽丰富的色彩,出色地表现了“绮罗纤缕见肌肤”的效果。
民间爱花佩花的情愫使然
中国人对花的喜爱古已有之,其爱花佩花的风气最早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在四川汉代画像砖中,就发现有一幅三人宴饮图,画面中右边一人即手持莲花作敬献状。而最早的古人簪花形象也出现于汉代,如洛阳八里台出土西汉彩绘人物砖,有簪花三女;成都羊子山西汉墓出土女陶俑,其发髻正中便插着一朵硕大的菊花,周边还簇拥着数朵小花;东汉时期,簪花女俑更多,四川彭山汉代崖墓、重庆化龙桥等地均有发现。簪花之风愈到后代愈盛,著名的唐代《簪花仕女图》描绘的便是贵族妇女将大朵的牡丹以及莲花簪在头上的情景。文献方面,北宋高承《事物纪原》中有《彩花》一条云:“《实录》曰:‘晋惠帝令宫人插五色通草花。汉王符《潜夫论》已讥花彩之费。晋《新野君传》,家以剪花为业,染绢为芙蓉,捻蜡为菱藕,剪梅若生之事。”也可相佐证。
文人雅士的精神追求
此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受战事频繁,、政局动荡之影响,文人雅士们为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寄情于山水,吟诗作画。采折鲜花供置盘中待客会友也是一种形式,如北周诗人庾信曾作有《杏花诗》:“春色方盈野,枝枝浣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后代与此相关的诗文记载不甚枚举,“皿花”之风在此后也被寄予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萌芽于东汉的“皿花”图像,历经两晋、南北朝之后,从最初原始的盆栽艺术形象,逐渐被赋予了崇佛礼佛和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文化内涵,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它是当时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直接影响下的产物。“皿花”图像较为固定的构图形式可能表现的就是当时的一种佛教供祭仪式场景,遗憾的是,虽然当时流行在墓葬中设置祭台的做法,祭台上及其周围也发现过一些随葬器物,但迄今为止并未发现直接的实物证据,所以也只能是一种推测,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发现来推进这一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