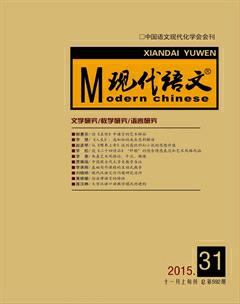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家庭世界
摘 要: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女性的笔触刻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世界,这种叙事在她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她的代表作《到灯塔去》。小说着力描写了拉姆齐一家人十年的生活变迁。这期间小说中的家庭世界发生着重要变化,父女关系从敌对走向和解,母女关系却从亲密走向背叛。由于夫妻关系在家庭关系中占统治地位,它影响着父女关系和母女关系。从女性主义视角来审视这一变化,对理解作家的女性主义视角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家庭世界 弗吉尼亚·伍尔夫 女性主义
英国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位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先驱。在她的随笔以及小说创作中不断实践着她的女性主义主张。她的成长过程深受英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熏陶,熟悉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对其中的女性寄予深切的同情。在她的小说《到灯塔去》《达罗威夫人》等一系列作品中,她都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展示了其中的家庭世界。本文以《到灯塔去》为例,从分析亲子关系入手来审视其中的家庭世界。一般学者认为《到灯塔去》是伍尔夫以自己的父母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作品以“到灯塔去”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描写了拉姆齐一家和几位客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生活片断。在小说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拉姆齐一家的方方面面,包括在夫妻关系影响下的亲子关系,作者通过这种描述着力彰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和男性压迫下的生存困境。以此视角去审视该部小说中的家庭世界,去关注人物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对进一步理解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双重失语有重要意义。
一
无论是父女关系还是母女关系都会受到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影响。波伏娃曾撰文指出,夫妻关系、家务劳动和母性形成了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整体。若妻子能和丈夫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就可以愉快地承受家务负担;若能对有孩子感到幸福,她就可以容忍她的丈夫。但这种和谐不是轻易就能够达到的,因为分派给女人的各种职能彼此不协调。[1]由于男权制的根深蒂固,造成两性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极不平等,男性自然而然地拥有远远优于女性的许多特权。因此,这些因素决定了在夫妻关系中,男人处于支配地位,而女人处于被支配地位,没有自主权。
这种夫强妻弱的夫妻关系进而影响到父女关系和母女关系。夫妻关系在家庭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女儿不管是否愿意,从小都要接受父亲的供养,因为母亲在经济上没有地位。因此,无论母亲如何保护女儿,女儿都要受到父亲的伤害和影响。“只要丈夫仍是家庭的经济首脑,孩子十分依赖的就是他而不是她,尽管她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比他要多得多。”[2]由于父亲拥有绝对优势,女性对于父亲的感情是矛盾的:一方面父亲的强权对女儿构成威胁,父亲对女儿的漠不关心造成女儿对父亲的仇视;另一方面,由于从小父爱缺失,女性长大后,又渴望父亲,进而向父亲妥协,或者寻找替代性的父亲。这些都会影响女性对于异性的态度,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终生的。波伏娃曾说,“母子关系是她整个生活的一部分,它取决于她同丈夫的关系”。[3]可见夫妻关系影响着母女关系。由于母女都处于父权的统治下,共同处于受压迫的境地,她们不得不联合起来反抗男性权威。但是,由于父权制的根深蒂固以及夫妻关系在家庭中的重要影响,无论如何母女关系都处在男性中心主义的阴影下。男性的性别优势和男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让女性陷入困境当中。
二
《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先生认为事业是他们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途径,因此他们逃避家庭事务,暴躁易怒,终日所关心的只有自己。他还是个严厉的父亲,喜欢讽刺子女,有些专断,从不关心自己的孩子,根本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女儿们在没有父爱的环境下成长,因此儿女们都不喜欢他,对父亲感情疏远甚至怀着敌意。拉姆齐先生不但不关心女儿的感情需要,反而不断地向女儿们索要安慰、赞美与同情。从这一点上来讲,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父亲。
小说开篇写了女儿眼里的父亲形象,“他站在那里,瘦得像一把刀,咧着嘴巴露出讥笑”,“像一把刀”[4]就是拉姆齐先生性格的象征:坚硬无比。他常常从理性出发,不顾孩子的感情需求,对子女的态度简单粗暴。在第一章,全家一起商议去灯塔的事情,父亲拉姆齐先生一口断定,“明天别想去灯塔,一点希望也没有”。[5]他一下子打破了孩子们的希望与梦想,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在最小的女儿卡姆心底埋下了憎恨父亲的种子。拉姆齐先生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女儿多么优秀、可爱。自己的女儿普鲁美丽动人,将来会比“最漂亮的卡米拉姨妈”还要漂亮,父亲却说,他一点也看不出来,还责怪夸赞女儿的母亲说,“你在教你的女儿们夸大其词”[6]。
十年之后,拉姆齐夫人已经去世。拉姆齐先生为了表达对夫人的悼念,决定带上一些夫人在世时经常带的东西去灯塔。詹姆斯和卡姆却认为父亲的决定仍然是作为一个暴君那种“绝对服从我”的行为,因此他们决心抵抗到底。出发之前,拉姆齐先生还为启航的准备工作大发雷霆,父女之间本来存在的芥蒂进一步加深。卡姆坚定地认为是父亲榨干了母亲的生命力,内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不满,面对父亲的专横粗暴她发誓要反抗暴君。但在前往灯塔的航行中,她看见父亲指挥若定,勇敢坚毅,和船夫亲切地谈话,而且父亲居然夸奖了詹姆斯划船的能力(这是詹姆斯内心所一直渴望的),对自己也和善体贴。她突然认识到父亲的优秀品质,被父亲的儒雅风度感动,胸中的对立情绪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高高兴兴地登上了岸。女儿与父亲最终达成了和解,也就是说父亲恢复了话语权,实现了对女儿的统治。
三
女性主义者指出,母女关系对女性的成长影响最为重大。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在分析母女关系时指出,母女关系是多么复杂:女儿对于母亲来说,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外一个人;母亲对女儿既过分疼爱,又怀有敌意。母亲把自己的命运强加在女儿身上:这既是在骄傲地宣称她具有女性气质,又是在以此为自己雪耻。[7]女性主义理论家普遍认为母女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为母之道(motherhood)是女性主义理论化的中心课题。母女关系其实是复杂的、多层面的,而并不仅仅是发自本能的爱和依恋,虽然这爱和依恋可以说是一切情感中最深挚最本源也最为动人的,但一定不是全部,人性的复杂决定了爱的复杂多味。男人对于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丈夫对于妻子的夫权压迫以及父亲对女儿的漠不关心,使得母女之间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她们所仇视的父权制。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把拉姆齐夫人塑造成为完美的女性,她管理着整个家庭的一切事务,是家庭的精神支柱。小说中的拉姆齐夫人是以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天使”的面孔出现的,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女性的美丽、善良、温柔和智慧,这样的母亲自然赢得了女儿们的喜欢和爱戴。
一方面,拉姆齐夫人同情、理解女儿,把女儿视为自己的骄傲。拉姆齐夫人不希望小女儿卡姆长大成人,希望她“永远像现在这样,是淘气的小鬼、快乐的天使”,这样母亲将永远不会失去这个女儿;拉姆齐夫人认为自己的普鲁“与人相处时真像一个小天使,现在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夜晚,她的美已经令人惊叹”。[8]她了解另一个女儿罗斯双手灵巧,最爱缝制衣服、布置餐桌。拉姆齐夫人关心疼爱自己的女儿,孩子们想要去灯塔,虽然天气状况并不乐观,但是拉姆齐夫人作为母亲,还是好言劝慰,给孩子希望和信心。
另一方面,女儿尊敬母亲。担负起教养孩子的职责、以孩子为骄傲的母亲拉姆齐夫人在女儿的成长中,充当了主要的角色,是她们成长的引路人,对她们的生活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即使是拉姆齐夫人已经去世,她的光环还是笼罩在女儿的头上。小女儿卡姆一直怀念母亲的美好,幻想着若是母亲还在世会怎么样,该会享有多么美好的生活。
然而,在母女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母女之间还有很大的隔膜。女儿有着母亲不知道的秘密,另一方面母亲总是担心孩子们会嘲笑自己的丈夫、他们的父亲。由于夫妻关系在家庭关系中占统治地位,它影响着母女关系。拉姆齐夫人崇拜自己的丈夫,让他居于“生活的中心”,但是由于丈夫刚愎自用,对待孩子冷漠、毫不关心,因而孩子们敌视丈夫。孩子们背地里认为父亲不停地榨取母亲的生命力,使他们早早地失去了母亲。这就间接造成了母女之间存在隔膜。母女双方因为家庭中同一个男人的专横粗暴而向彼此寻求理解和安慰,又因为这个男人的存在而彼此产生隔膜和误解。
综上所述,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向我们完整地展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世界:父权制是家庭的中心,父权是家庭的主宰力量。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影响着亲子关系,而这一切家庭关系都受制于父权制。在父权制的统治下,家庭世界以父亲为核心,不论这个男人作为丈夫和父亲是否称职,家庭活动和决策都应听命于他。只有解构父权制,赋予女性同等的社会、经济地位,女性才能在家庭世界中获得平等的话语权。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洛阳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世界中的家庭关系”[项目编号:2015B239]的成果之一。)
注释:
[1][2][3][7]陶铁柱译,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9页,第479页,第476页,第257页。
[4][5][6][8]马爱农译,弗吉尼亚·吴尔夫:《到灯塔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第27页,第59页,第51页。
(倪坤鹏 河南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47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