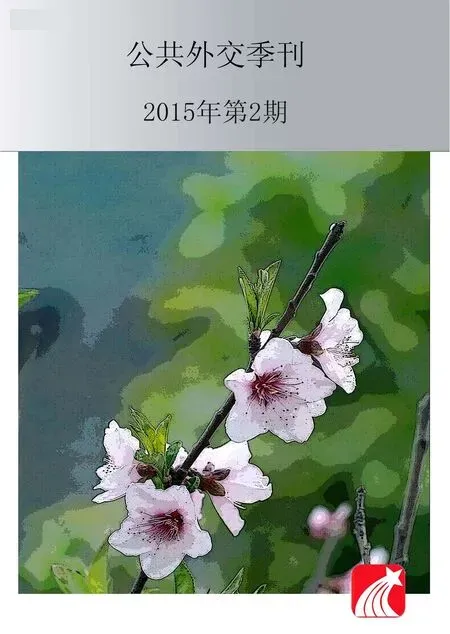好的对话:智者的交流与反思
——读赵启正与帕罗《江边对话》
陈 洪 丁 峰
好的对话:智者的交流与反思
——读赵启正与帕罗《江边对话》
陈 洪丁 峰
《江边对话》(赵启正、帕罗著,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堪称成功对话的典范。对话双方不仅成功完成了一次和谐的人际交往,还向世界示范了一种立场迥异、甚至许多观念完全对立的两个国家或两种文明之间的和谐交流和精彩对话。两位智者的反思并未限于自身,还有对人类命运的更深广的反思。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将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联结、沟通起来的就是——用话语呈现出来的对话关系。可以说,人类生活本身就是对话性的,而人类的文明,也正是在持续不断地理解性对话与交流中推进发展的。纵观人类的历史,会让我们想起诸多的精彩、睿智的对话:从孔子、曾点到弘忍、惠能,从柏拉图、苏格拉底到德里达、伽达默尔……当然还有庄子与惠施的那段著名的“子非鱼”的“濠梁之辩”!不过,留在历史记忆里的对话,好像以辩居多,就像人类发展的主要线索也总是由战争和冲突构成。
“真理越辩越明”,真理是否真的越辩越明?房龙曾说:世间万物,唯有真理离我们最远。也许唯一可以辩明的真理就是,作为对话方式的一种,有效的辩论能使辩者对话题的理解更为深入更加明晰,这就是“真理越辩越明”的真实内涵。现实中的很多辩论,尽管较战争和武力进步了许多,但是实在离真正的“文明”尚有一段距离。单纯以说服为目的的辩论,带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在强烈的征服欲望支配下,容易陷入“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由此产生的盲目和偏见往往导致暴力和纷争。显然,这样的辩论并非“好的对话”。
什么样的对话才是好的对话
如果以各自为中心的意图征服对方的辩论并不能带来和平与理解,那么什么样的对话才是好的对话?《江边对话》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本书两位睿智的作者的对话,堪称成功对话的典范!对话双方不仅成功完成了一次和谐的人际交往,还向世界示范了一种立场迥异、甚至许多观念完全对立的两个国家或两种文明之间的和谐交流和精彩对话。正如本文扉页中标明的一样:这是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有神论者的对话;这是一个科学家和布道家的对话;这是一个东方人和一个西方人的对话。他们之间的差异是深刻的,而他们之间的成功对话,其示范意义同样广泛而深刻。
实则,对话的可能就存在于差异之中,没有差异,对话就没有必要。文明的对话预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差异使对话显示出渴望、必要和价值。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民族和宗教传统都会遭遇不同的文化或信仰体系的挑战,它们也经常从这种相遇中获得巨大活力。基督教神学因希腊哲学而繁荣,伊斯兰教思想因波斯文学获得启示,中国思想史则因佛教传入更加丰富。
然而差异也使对话成为一个艰苦的过程,甚至常常是冒险。正如本书的译者林戊荪先生指出的那样:真正有效的交流并非易事,既要有尊重对方和容纳百川的心态,又要有优异的理解力和表达力。就《江边对话》的两位主人公而言,思想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尖锐和根本的。但是,这种尖锐的对立和根本的差异并没有使两位主人公的交流走向冲突和隔膜的危险,反而使对话的内容精彩纷呈。
对话不同于辩论。对话求和,辩论求胜!杜维明认为对话不是一种说服的技巧,而是一种需要精心栽培的艺术。对话不仅是要去传自己的道,也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批判异己的言论。而是要通过对话,倾听不同的声音,了解别人,增加自我反思的能力,学到未知的东西。现实的世界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隔阂是普遍而深刻的。如果那种迫使他人皈依的意识压倒了倾听和学习的渴望,对话便会陷入困境。《江边对话》的双方显然已经超越了征服和说服的目的,两位保留各自立场,互相尊重信仰,进行平等对话。房龙警告人类:信念一旦被赋予正义的外衣,就容易走向偏见与盲目。以自我为中心而形成的种种偏见,会遮蔽人的智慧。而这两位智者通过相互不断提出问题,不断寻求答案,碰撞出闪耀的智慧火花,发人深思,启迪心灵,令人愉悦。在本书的引言里,两位智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与对方的谈话促使自己对原来的知识体系进行反思,思考原来较为生疏甚至从未设想过的问题。
对人类命运的反思
“江边对话”两位智者的反思不仅局限于自身,还有对人类命运的更深广的反思。
全球化的到来,使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同时也使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碰撞愈益频繁,无论是摩擦龃龉还是友好交流都比以往更加便捷。早在1993年,亨廷顿就预计到了这种碰撞加剧的趋势,他说,“后冷战”时代的到来,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之争将让位于“文明的冲突”。凸显文明冲突加剧的趋势是亨廷顿远见之处,但把文明间的冲突描绘成人类的宿命,应该说暴露了他的思维的僵硬与狭隘。其实,历史进程中文明的融合或生成从来就是在冲突中展开的。问题是解决文明之间的问题是否必须选择一种“冲突”的方式。亨氏的冲突论,其本质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结果,是“冷战”思维的延续。
事实上,世界各国负责任的领导人都越来越关注整个地球所面临的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寻求通过协调和以合作的精神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一种共识正在逐渐形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旦发生大的“文明冲突”,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文化,都不可能置身于伤害之外。因此,寻求、建立文明、文化之间的对话机制,其紧迫性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强烈。
过去两年,中国政府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并将“和谐”理念延伸到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中,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好评。200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中国在亚非峰会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如今,和谐社会的建立已经从探讨阶段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其实践也从中国内政延伸到外交。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指一种“配合得适当而匀称”的关系,包括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谐。《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和谐中国”和“和谐世界”事实上都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发扬。 此外,“和谐”思想也为世界认同。《联合国宪章》提出,为“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要“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这里的“宽容”“和睦相处”,都是“和谐”理念在国际事务中的体现。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同时服务于内政。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中国必须“把自身发展与人类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关系反映的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和谐文化滋养的东方人,“智慧的哲学家、思想家”,以及提出和谐世界理念的中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赵启正先生显然表现出了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观察力,“江边对话”体现的就是一种在平等基础上的“和谐”对话。
“我们的坦诚使不同的信仰不能成为我们的障碍,不同的语言不能成为我们的障碍,不同的教育背景不能成为我们的障碍,我们都愿意为地球的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特定的宗教、文化、种族和民族的背景下,固执自我和无视他人是造成傲慢、偏见和仇恨的主要根源。孔子曾把“忠恕”说成是自己全部学说“一以贯之”的精髓。后世解释“忠”是对自己信念的认真信奉,而“恕”则是对他人信念、立场的宽容与理解。这种解释表达出一种富有智慧的人生境界。这“忠”与“恕”两个方面的圆融,将使我们学会最大限度地欣赏他者的独特性,从而也使得我们自己的信念上升到一个更高更自觉的层次。
“和谐”对话的一个前提就是超越,也就是“跳出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彼此站得高了,就会忽略枝节上的分歧,互相谅解以致理解;彼此站得高了,眼界开阔,就会看到共同的天空和共同的大地。例如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如果各自闭锁在一教一派的范围,彼此间只能是相互否定;而如果都站到终极关怀的高度,彼此间就有了相互理解的可能。同理,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如果彼此都站到俯瞰人类文明史的高度,都以理性精神为慧眼,也就有了相互了解、理解和尊重的可能。
那么如何才能站到“最高层”呢?答案是:广博的知识和仁者的胸怀。前者可以使对话者摆脱因无知而产生的傲慢与偏见,后者可以使对话在温暖的阳光下、徐徐的和风中展开。“江边对话”的两位主人公恰好具备了这样的素质。他们都对人类的现代自然科学有相当的了解,而赵启正先生更是具有专家的身份;他们都对人文社会科学有相当的了解,并把这种了解同自身的职业圆融起来。于是,他们的对话得以在渊博的知识体系下展开,得以在既严肃认真又轻松幽默的氛围中展开。而对于读者来说,无论是对话者阐述的知识与道理,还是他们卓越的口才与机敏的反应,以及二人因旗鼓相当的对话而碰撞出的智慧火花、心领神会的愉悦,都可以给我们以生动的启迪,引导我们走上好的对话之路,让和谐之辉光洒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这或许是本书奉献给人们(人类)的最大价值吧。
智者乐水。生命的河流在智者的微笑中川流不息。巴赫金断言:“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方式的建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
好吧,为了生存与发展,让我们开始更多好的对话吧!
(本书已翻译成多语种出版,韩文版由韩国熊津出版社出版发行,西班牙文版由西班牙Circulo de Lectores出版社出版发行,英文版由美国Zondevan出版社出版发行。中文版、英文版均多次重印。——编者注)
陈 洪:南开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丁 峰:南开大学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