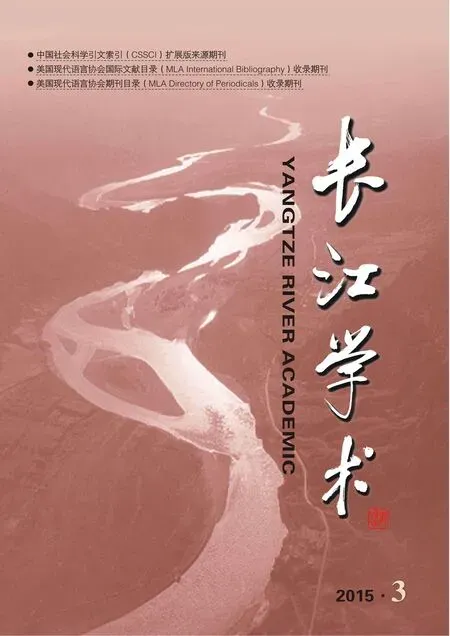中世纪中国戏剧的多种形态:如何改编文本以满足演员、观众、审查官和读者的不同要求
〔荷兰〕伊维德 何博 译 程芸 校译
中世纪中国戏剧的多种形态:如何改编文本以满足演员、观众、审查官和读者的不同要求
〔荷兰〕伊维德 何博 译 程芸 校译
勾勒元杂剧从元代商业剧场逐步登上明初宫廷舞台,最终走向晚明文人士夫案头的演变进程,可以发现一个历史事实:元杂剧之所以有诸多版本的差异,这源于它们面对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群体,如观众、演员、宫廷审查官以及文人读者的不同需求。这些版本的文本差异,反映了不同的刊印目的和实际演出的变化。
元杂剧 意识形态 版本 改编
今天的西方戏剧史通论都会提及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出色的文学性——尽管该剧确如伏尔泰其他创作一样文思敏捷、才情出众。我们之所以提及这部戏,是因为它对作为戏剧要素之一的演出服装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孤儿》在它的时代是欧洲戏剧舞台上广受欢迎的一部戏,男女演员身着“真实的服装”,用法语和其他语言在欧洲各地演出。一直到十八世纪很晚的时候,悲剧演员的演出服装样式都非常有限,而在《中国孤儿》中,他们穷极一己对于中国的认识,努力装扮成中国人的样子。和任何演出实践中的改革一样,这一大胆创举也一直饱受非议和诟病。一位荷兰评论家在观看了荷兰版的伏尔泰《中国孤儿》后说,那些披挂着层层东方织物的演员们在台上汗如雨下,看起来更像是“亚美尼亚商人”,和中国人压根扯不上关系。
众所周知,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只是第一部被翻译为西方文字的中国戏剧——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在十八世纪的众多欧洲改本之一。关于纪君祥,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曾活跃于十三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很可能是作为一名剧作家服务于当时大城市里蓬勃兴起的商业性剧场,其中首推大都(即今日的北京),这是蒙元王朝的都城。纪君祥和他的北方同行所创作的,是一种被称为“元杂剧”的戏曲样式。由于杂剧相对而言篇幅短小(现代出版时多分为四折),能够描写任何可以想见的题材,且通常都有一个喜庆的结尾,我在过去曾用英文“comedy(喜剧)”一词来翻译“杂剧”这一名称。不过亟待澄清的是,中国传统戏曲根本没有所谓“悲剧”与“喜剧”的分野,而这一区分对于西方戏剧传统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西方戏剧的创作或许还要重要。直至二十世纪,悲剧、喜剧这些术语才在中国广为人知,并由此引发了热烈争论:中国传统戏曲是否有“悲剧”?如果中国没有产生出一部完全符合西方戏剧准则的悲剧,我们是否可以将之命名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悲剧”?这在很多文学评论家看来也许是可行的。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初,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就被列为中国最早的悲剧作品之一,这并非如有人所猜测的那样是因为该剧十八世纪的法国译者马若瑟曾称其为“中国悲剧”。
在古代中国,戏剧的类型并不是依照剧中人物的社会地位或者剧情的性质来划分的,而是以曲子所用的音乐类型和整体的背景音乐风格为分类标准的。后者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中国传统戏曲,无论何种形式,都属于“叙事歌剧(ballad-opera)”:剧中都包含按照有限数量的音乐调式而创作的“咏叹调”(唱段),共享同一特定曲谱(及相关音乐制式传统)的剧作即构成一类戏剧样式。杂剧或喜剧用“北曲”创作唱段,一出戏中所有的演唱都只能由一位男演员或女演员来担纲。在一出戏中,男女主演从始至终只能饰演一个角色,其中只有一方能演唱,因此在核心的戏剧冲突或爱情关系中,只有一方享有充分表达个人想法与感情的自由,这使得杂剧呈现出一种极不对称的结构特征。在偶尔的情形下,男女主演也会饰演多个角色。这不太可能是缘于剧本笨拙的情节架构(如评论家长久以来所批评的那样),而极有可能是如金文京教授所言,剧作家在创作时即以某位男演员或女演员为对象,希望通过他或她在舞台上展示表演的丰富多样性。例如在《赵氏孤儿》中,男主演(正末)不仅要在第四折中扮演年满十八岁的孤儿,而且还要在前三折中分饰三个不同角色(孤儿的生父驸马、将军以及老宰辅),他们都为了保存婴儿之性命而慷慨赴死,或被杀或自尽,使孤儿得以幸存并长大成人,最终向杀尽赵氏一门三百族人的恶棍报仇雪恨。
马若瑟译本的读者不会因为原剧让同一位演员在前后相续的剧情中扮演不同角色而大惑不解,因为译者在翻译时,有意删除了所有唱曲。所以他的欧洲读者看到的,是一部完全用散文(而非诗体)写就的戏剧。事实上,马若瑟译本的意向读者原本就并非欧洲大众,作为出入北京宫廷的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也是一名出色的语言学家,他翻译《赵氏孤儿》的初衷是为了给当时巴黎一位研究汉语的学者傅尔蒙(Tienne Fourmont)提供一个现代汉语口语的全面样本。为找到这样一个样本,马若瑟最终选定了臧懋循在1616至1617年所编的《元曲选》,这部收录了100种元人杂剧的书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戏剧选集。他选出的《赵氏孤儿》不仅是卷帙浩繁的《元曲选》中唯一的五折杂剧,而且恰巧也是宾白最多的一部戏(因此即使删去曲词,剧本也足以精彩)。直到1734年,在马若瑟不知情的情况下,杜赫德(Du Halde)将这个原本是供语言学研究的译本收入他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中出版,《赵氏孤儿》才被视作第一部真实的中国戏剧的典范而大受欢迎,并在“中国风”盛行一时的法国引来大批如今早已默默无闻的剧作家和歌剧作曲家的追捧。然而,完全删掉曲词而仅保留对白的马若瑟译本与现存最早的《赵氏孤儿》中文原本相比,简直天壤之别。《赵氏孤儿》最早刊印于约十四世纪的上半叶,整出戏仅有曲词而全无宾白或舞台指令(甚至简略到未说明曲词是分由四个不同角色演唱的)。马若瑟所依据的原本,来自三百年后的《元曲选》,它显然既有曲词又有宾白和舞台指令,但若两相比较,我们就能明显看出:晚出的版本并不只是早期版本的简单扩充。在后世的版本中,不仅新增了完整的第五折,而且音乐上尽管沿用了相同的曲牌联套——曲子的数量和顺序没有改变,但几乎每支曲子的唱词都重写了。因此,前后两个版本的《赵氏孤儿》在情节、人物塑造和主题寓意上,都有着显著区别——此处我们不讨论文字学家所关注的细节差异,因为这些与学习表演的学生没什么关系。从《赵氏孤儿》的早期刊本到后世《元曲选》中的经典版本,二者之间发生了极其引人瞩目的变化。
今天我们要追溯元杂剧文本演变历程中的某些阶段是可能的。这样的研究会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一个事实:杂剧文本的某些变动源自于它们所面对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限制,这在它们从元代的城市商业剧场逐步登上明初的宫廷舞台,最后又走向晚明文人雅士的书斋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其中有些变动反映了数百年来演出实践的不断变化。但现存不同版本在文本上的诸多差异,则确乎与其被刊印的目的以及版本与演出的不同关系密切相连。
以备观众之需
当我们关注戏剧文本与舞台表演之间的多种关系时,首先要明确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演员登台演出并不需要一个文本。即使舞台表演在某个方面会依据某一文本,在实际演出中这个文本也是“不可见的”(今天福建地区的木偶戏艺人在演出时依然会表演到哪一页就把剧本翻到哪一页,但他们实际上并不会真地去看剧本,因为剧情台词早已烂熟于心,演得兴起还会即兴发挥)。在中国以及其他许多文化中,很多戏剧表演样式都根本没有形成文字的剧本,或者剧本是在表演者一次又一次反复的表演实践中形成的。
那么谁才是需要剧本的人呢?很有意思,我们必须再回到《赵氏孤儿》的最早版本——那个只有曲词的剧本。若作为演出的文字脚本,这个版本显然是不堪用的。若没有晚出的版本,我们简直无法重建早期版本中的叙事线索。元杂剧的元刊本若没有后世刊本为参照,是很难甚至是无法重建其情节细节的。该领域的研究者大多认同这样的解释:在元代,这样的剧本很可能并不是为演员之需而刊印的,它们针对的应该是那些常去剧院看戏、但有可能听不懂演员唱词的观众。而元杂剧现存的绝大部分元刊本都来自于南方的杭州而并非北方的大都,这更进一步加强了上述假设的可能性。杭州(马可波罗笔下的Quinsai“行在”)这座大城市曾是南宋王朝(1127—1278)的首都,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依然是南方行省的地方行政中心。元代的杭州自然生活着相当数量的北方人,但他们的朋友或随从中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是把杂剧表演所使用的北方方言作为第二语言的。在元大都肯定也生活着来自中国各地的大量移民。去戏院看戏的不少人也许听懂对白没什么障碍,但要理解曲词则有不小的困难。换句话说,观剧者也许比演剧者更需要一个戏剧文本,而且他们需要的并不是完整的演出脚本,而仅仅只需要一种“助听本”(hearingaid),这种助听本只提供剧中难懂唱段的曲词,就像今天在现代剧院上演歌剧时会用投影打出歌词一样。而且,数量巨多的剧场观众很可能会给刊印者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以备主演之需
那么,一个颇具经营头脑的出版商最有可能从谁那里找到某个戏的完整曲目呢?最方便的途径当然是戏里男女主演的角色分剧本(roletext)。现存的30部元刊杂剧中,有5部完全只有唱词,另外25部都或多或少可视为较为完备的男女主演的角色分剧本。上述刊本中既有男主角或女主角的唱词、基本念白,以及相对而言比较具体的舞台指令,也有针对其他角色的极少量的舞台指令和开场白。关于现存元刊本很有可能依据了当时演出的角色分剧本的推测,或许可以从舞台指令那里得到印证。剧本中的舞台指令常常是针对某一特定演员而发出的:“待某某如是行毕或言讫再如何、如何……”。而这类刊本中宾白和舞台指令的数量是逐折下降的,这似可说明这些刊本也是为了满足听戏者所需而出版的。
习惯上我们都将元刊杂剧看作是一种“缺本”(defective text),因为通常意义上的“全本”(fully written-outtext)要求剧作家提供完备的舞台指令、人物对白和唱词。但事实上元代剧作家是否真的创作过这样的“全本”,是应当存疑的——至少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所谓的“全本”元杂剧的刊本或抄本。实际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的:剧作家既要满足不断推出新戏的市场需求,又要服务于演技虽然精湛但大多目不识丁的专业演员,故只能一方面为剧场的相关各方提供一个基本的情节大纲,另一方面为主演提供一个更为详细的角色分剧本。毕竟口语化的宾白较容易现场发挥,而须严格遵循曲律的曲词则很难在场上即兴创作出来。
作为专为主演创作的脚本,角色分剧本可以写得非常详尽,不仅要有全场演唱部分的完整唱词,而且舞台指令应详述备尽。例如在关汉卿所著《拜月亭》的元刊本中,不断出现对女主演的提示,要求她表演出角色的种种矛盾情绪(做某某科)。但是即便在最完整的角色分剧本中,剧作家似乎也认为没必要反复下指令,或者非得写出大家应该心知肚明的信息。在《拜月亭》中,经常出现提示女主角交代或解释前面的剧情的文字“云了”,由此可知剧作家相信男女演员能够在台上即兴创作出恰当的宾白,因此没有必要精确地规定他们的台词。这里,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中国的传统戏班就像是“股份公司”(stockcompanies):男女演员从小就按照某一特定的角色类型来进行训练,因此上台之后很清楚如何扮演其角色;在一部新戏中他们只需知道究竟哪些“新东西”需要演出来就可以了。在中国戏剧史的这一发展阶段,剧作家的要务并非一定是创作新戏,而只需在有限的、既定的规则下进行个人的适度创造。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或详或略的角色分剧本的刊印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剧作家原本的面貌,也无从知晓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他人的改动。我们所能确定的是,大部分现存的元刊杂剧极有可能是在距原作诞生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且并非在原作诞生地出版的。这种情形就如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最早版本只有无韵体诗部分,出版它们只是为了满足查理二世在巴黎的流亡朝廷的演出需要。
以娱友人
现存最早的能够提供较为完整文本的杂剧剧本,直到十五世纪上半叶才出现。它们并非早期元人杂剧的版本,而是明王朝(1368—1644)早期剧作家创作的版本。之所以出现这样较为完整的剧本,很显然是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南曲戏文剧本的影响,戏文中所有角色都有演唱,因此剧作家有理由在一个剧本中囊括所有曲词。然而即便是朱有燉,这位明代的周藩王,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杂剧作家,刊刻他自己的杂剧时每每在剧首自豪地标出“全宾”二字,其实也并不能完全地“名副其实”:有时候他剧本中的宾白至多也只能算是粗陋,给演员的提示常常只是重述前面的情节,或者“云云”,而且也没有任何文字提示那些众所周知的舞台程式。因为任何一对称职的丑角都知道如何叽里呱啦地插科打诨,所以没必要写出所有对话内容和舞台指令,一句简单的“作戏谑科”足矣,除非剧作家本人想要说出他自己的更为机智的话。就朱有燉而言,我们知道他的某些剧本是专为某一次演出而创作的,可以想见他会把剧本刊刻出来作为纪念品赠给演出现场的宾客。
供宫廷官员审查
明初,杂剧被皇室接受,成为宫廷演剧。而明王朝早期的不少皇帝都性格乖戾,宫中无论谁都不愿承担冒犯龙颜的罪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诞生了最初的一批被完整写出的剧本。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些全本的杂剧是专供宫廷审查官审察之需的,他们必须在皇帝观戏之前认真审查每一部戏的剧本。有一些明显的禁忌需要引起重视(例如,舞台上不得出现表演皇帝的角色),但显而易见的是,严密审查下的改动或重写远远地超出了这些禁忌的限制:社会批判性的成分被大大地削弱,而国家统治的权威则被极大地加强。以《赵氏孤儿》为例,孤儿复仇的本质从杀死弑父仇人的个人复仇行为,转变为奉朝廷之命铲除奸恶之人。不过我们现在更感兴趣的是:戏剧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完整的戏剧文本,这个时期的剧本不仅曲词宾白兼备,而且包含所有的对过往情节的重述以及老套的插科打诨。显然,审查官员最关心的是剧本的唱词和对白,因为舞台指令往往粗疏潦草,远没有像元刊本杂剧的分角色剧本或明初朱有燉杂剧那样地详细完备,朱有燉喜欢给出详尽的舞台指令,以获得他所需要的特殊表演效果。假如审查官员认为要监控台上演员的肢体语言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只会更为坚定和执著地审查后者的台词与唱词。
有相当数量的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早期的宫廷杂剧手抄本被保留了下来,其中既包括明代宫廷演出中留存下来的元杂剧,也有十五和十六世纪明人创作的杂剧。我们不清楚这些手抄本原稿的创作时间,但可以较为肯定的是,绝大部分创作于十五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中叶。到了十六世纪晚期,杂剧基本已经退出舞台,因为在竞争中杂剧完败于形式活泼多样的南戏,失去了宫廷内外的观众。事实上,倘若没有少数杂剧迷(aficionados)的努力,以及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出版业的兴盛,杂剧很可能早已退出舞台,在文学史上完全地销声匿迹。十六世纪末以前,杂剧的刊本其实都相当罕见。然而,十六世纪晚期江南地区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出版业也因此而获得了空前发展,为了满足突然出现且供不应求的对于休闲阅读(light reading)和消遣文学(entertainment literature)的需求,出版商开始刊印戏剧与小说读物,数量与日俱增,版本日益精美。这些出版商(鲜有例外)首先会考虑刊刻他们从宫廷手抄本中发现的戏曲文本,尽管有时候也会为了增加刊本的吸引力而配上木刻的插图。这些插图描绘的是戏曲故事中的某一场景,而非戏曲演出的高潮片断;因此尽管有时候它们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但对于演剧史研究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供成熟读者欣赏
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所刊行的元曲选本很快就湮没于臧懋循所编《元曲选》的光芒之中,后者共收录了元人杂剧100种,上下两部各50种,相继于1616和1617年问世。《元曲选》中的杂剧剧本基本上也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宫廷手抄本为基础的。它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取代此前的元曲选本(后者因之完全湮没无闻,直到二十世纪才被重新发现)?原因显而易见:《元曲选》中有超过200幅的木刻插图,皆出自名家之手,技艺精湛、印刷精美,文字部分亦印刷精良、品质一流。时至今日,《元曲选》仍是中国及世界各国学者研究元杂剧的文学与演剧价值的基础文献。但是,其中收录的杂剧剧本历经改动,早已大异于元人的演出,即便是与明代宫廷的演出相比也大相径庭。因此《元曲选》之所以风行于世,除了它刻印精良、代表了十七世纪印刷出版业的最高水平之外,一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答案存在于臧懋循匠心独运的编辑策略,正是他成功地将杂剧的台上演出之本(更准确地说,供审查的宫廷演出本)转变成了文人雅士们鉴赏的案头读本。
依照中国文学的传统观念,这些戏曲文本要成为可供阅读的案头文学,首先需要确定其作者,因为中国的文学传统认为文学创作首先是作家的主体情感和独特个性的表达。依据以前的戏曲目录,臧懋循苦心孤诣,无视后人对元人原本的诸多改动,尽可能为更多的剧作找到有名有姓的作者。紧接着,臧懋循对这些文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校订,使原本为优伶搬演的演出脚本转变为可供文人赏析的文学文本。他的编辑整理始于文字校勘,如错字别字、用典之误或对仗不工等。但臧懋循绝不止步于此,相反,他对选本的宾白曲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进”,并使情节关目更为紧凑。虽然臧懋循宣称要重现元人杂剧的原貌,他本人仍深受其所处那个时代的戏剧变革的影响。南曲戏文、传奇的创作讲究大团圆的结局,因此臧懋循着手将他的“元杂剧”改造成更完美的戏剧样式。这就意味着他不仅要紧凑关目,而且时常得改动剧情。一方面,他会大刀阔斧地砍去一本杂剧前三折中冗长臃肿的曲词和宾白;另一方面,他又时常大手笔地扩充第四折的篇幅,并自己创作曲词、宾白。因此,原作的基调和主旨必然发生或隐或显的改变。譬如说,那些为宫廷演出而改编的剧本彻底地删除了原作公开批判社会不公的内容,而臧懋循在改编中却往往会加入针砭时弊、直抒胸臆的社会批判性话语。通过多方面的改动,臧懋循的元杂剧版本成为可读性极强的案头之作,其风格与主旨实际反映出他本人所代表的十七世纪早期江南精英阶层的审美趣味与思考。
在现代研究者眼中
臧懋循成功地将明代宫廷版本的元杂剧转变为中国文学的一种次文类(minor genre)。作为一种文类,它的地位在二十世纪之初得以进一步提高,其时的现代中国学者开始建构中国文学史这么一门学科。他们受到西方史诗与戏剧观念的影响,坚信小说与戏剧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中都给予了小说和戏剧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当他们这样做时,被视为新经典的仅仅涵盖几个世纪以来被精英阶层赏读的那些戏曲样式,如经过臧懋循编辑整理的元杂剧。提高元杂剧地位的努力,更进一步迷醉于这样一个事实:从十八世纪起《元曲选》中的部分作品,以《赵氏孤儿》为开端,就被翻译成西方语言,并对欧洲戏剧产生了相当可观的影响。而《赵氏孤儿》作为一部悲剧被介绍到西方世界的这样一个事实,则进一步加强了该剧在建构中国传统文学史的现代主流叙事(modern master narrative)中的经典地位。但是,在这一主流叙事中,根本没有那些中国传统戏曲抄本的地位,其时它们正活跃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戏台上。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都深深鄙视那些能够上演且流行的戏曲样式,比如京剧,他们希望能尽快地用西式戏剧——即中国人所称的“话剧”——取而代之,使它从音乐剧的中国传统中决裂而出。
The Many Shapes of Medieval Chinese Plays:How Texts Are Translated to Meet the Needs of Actors,Spectators,Centers,and Readers
〔HOL〕Wilt L.Idema Trans.He Bo Proofread.Cheng Yun
By retracing some of the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Yuan drama,a conclusion can be made that some textual changes are due to the variable ideological constraints to which zaju was submitted as it moved from the urban commercial theater of the Yuan dynasty,to the court stage of the early Ming,and eventually to the studio of the late Ming literati.Th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arious preserved texts reflect the specific purposes for which the texts were produced and the different relations of those scripts to performances.
Yuan Drama;Ideological Constraints;Performance;Transform
责任编辑:张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