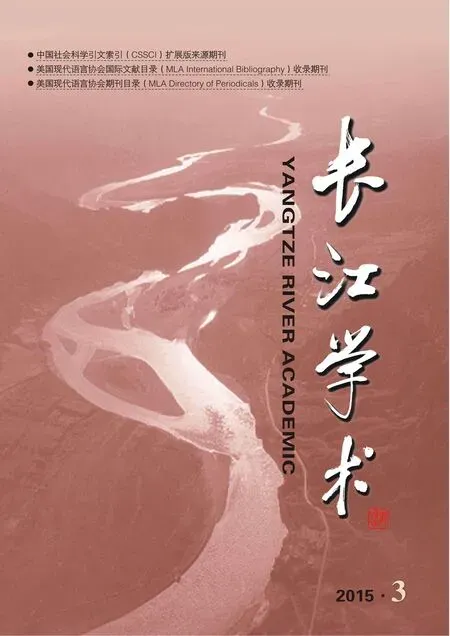论宋代文化之基本形态及其在中国史上之位置
〔台〕戴景贤
(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台湾高雄80424)
论宋代文化之基本形态及其在中国史上之位置
〔台〕戴景贤
(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台湾高雄80424)
宋代之于中国历史,处于中古史之晚期。宋代文化之特殊性表现在:学术思想形成一种具有“形而上学”意义之“认识论”,将有关“知识”理论与“道德”理论既分别亦合一;政治制度方面,在于企图打造一“彻底官僚化之文官体制”;文化方面,展现一种截然不同于汉唐之风格,宋代士大夫欲将政治之“理念”、“知识”与“效益思惟”三者合为一种动态之“识见”;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利用“崇儒”、“税商”、“劝农”、“奖工”等措施,活络社会之流动,产生发展之动能;宋代“民”之意识逐渐成为奠立“社会共同体”之基础;宋代科学技术与医学“相对发达”,并将技术运用于民生与商业;宋代之艺术与文学,不仅创作展现独有之风格,且发展出一种系统化之批评理论。宋所处之时代,乃至其位于中国历史之阶段,皆与欧洲文艺复兴相近,特其年代稍早。而理学崛起,及其所带动之影响,亦若具有一种浓厚之“人文主义”精神。宋代文化之于中国,就其内在之性格而言,实是一种文明之跃升,且以“潜在”之意义而言,亦具有一种“世界性影响”之可能。
宋史 中国史 中国史之历史分期 宋代文化 宋代思想 宋代学术
一、宋史研究之关键性议题及可有之诠释选择
清代王船山(夫之,字而农,号薑斋,1619—1692)之论“宋代之治”云: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治,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宁而后,法以斁,民以不康。繇此言之,宋其裕矣。夫非其子孙之克绍、多士之赞襄也。即其子孙之令,抑家法为之檠括;即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为之熏陶也。呜呼!自汉光武以外,爰求令德,非宋太祖其
谁为迥出者乎?
船山此论,称颂宋之为治,除子孙之克绍、多士之赞襄之外,特标出“家法为之檠括”、“政教为之熏陶”二项,而以太祖之德溯其始。此一以政治体制、措施,与政治对于社会文化之正面影响,以论宋代文治对于中国历史所产生之扭转之效之说法,可谓具有深刻之观看历史之眼光;发前人所未发。唯以今日之历史研究所需言,则尚有数项关键性之议题,亟需解答:
第一项议题,是如何以“世界史”之眼光,看待“宋代中国”之兴起;并判断宋代处于中国全史中之位置。第二项议题,是如何以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与文化史,论述宋代对于中国之改造;并由此观看其后之变化。第三项议题,则是如何依宋代之学术文化条件与社会之状态,探讨中国史与欧洲史此后发展走向不同之原因;并期待由此差异,得以理解中国最终未于明、清二代产生类似西方“工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之缘由。此三项议题,既牵涉“世界史”之研究,亦牵涉“中国史”之重新诠释。
关于第一项议题,属于“世界史”之部分,所需之讨论,除同期各文明之比较外,另有一关键之要点,即是“阶段论”之分期。此因欧洲史之三阶段论,于近代史学展现极强之诠释功能;以是不同形态之“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皆试图为此历史之进程,提出合理之“功能论”(functionalism)、“形态学”(morphology)或“社会演化论”(socialevolutionism)之说解。因而如所谓“世界史”(world history)具有真实之“解释历史”之意义,“中国史”即应为适用之对象。否则,即必须承认“世界史”可有不同之路径;或各民族、各区域,皆可能发展出不同之历史进程。
以“宋代史”之“世界史”议题而言,首先应解决之问题,为对于中国史之研究者所察考而得之宋代之进步性,与其对于明、清之影响,应如何界定其性质?相较于其它因素,何者方是决定中国历史“阶段论分期”之关键?其次,则是如何尝试建构一种可能之“论述”,并不断检视其诠释之效果。
至于有关“宋代处于中国全史中之位置”之讨论,其核心问题,虽在有宋一代对于中国之改变与影响;倘欲予以正确之评估,则应有数项关联之研究基础:宋代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对外之关系,宋代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商业贸易;宋代学术、思想与智识阶层,宋代农工生产、制造与科学技术,宋代医学、美术、杂技与其它艺术,宋代民间宗教与社会组织。
关于第二项议题之所以特为重要之原因,则在宋代学术、思想,以及士人透过“政治参与”所形成之政治文化,对于中国产生若干方面极为重大之影响;使中国“如何发展成为一具有理想性之‘儒教之中国’(ConfucianChina)”,于理论上成为可行。
至于第三项议题之所以产生,主要来自中国学界于清末以来,针对中国现状之落后所产生之焦虑;故其呈现之方式,带有提问者当身之“时代色彩”。且就其所期待之答案而言,亦必于前两项议题,获得较为坚实之研究基础,始为可能。
关于以上三项属于现代史学所提出之关切议题,本文作者有一综括性之看法,即是于中国史之“分期阶段论”,主张以秦、汉以前,为中国史之“古典时期”(classicalantiquity),其前段为夏、商、周;后段为秦以至东汉之覆灭。“中古时期”(themiddle ages)则始于三国、魏、晋,以迄宋、元;而以三国、魏、晋为前段,隋、唐、五代为中段,宋、元为后段。“近代”(the modern era),则以明帝国之建立,以至鸦片战争(First Opium War/First Anglo-Chinese War)之起,为“早期近代”(early modern period);其后则逐步进入“后期近代”(late modern period)(即中国史之“现代”)。
此一论法,之所以未将宋代之若干进步特质,说之为乃中国已进入“中国史之近世”之明证,从而确认此一“近世”,同时即属世界史意义之“近代”,如部分学者所评估;主要乃基于下列数项原由:
第一项原由,在于所谓“世界史”意义之阶段论,如具有模拟性,其最重要之意义,在于人类进入以“国家”(state)形式发展文明之后,社会组织、经济形态与价值理念,逐渐成为彼此密切相关之整体,因而此数项因素连结所产生之“推动变化”之动能,为小规模社会所无从比拟。然“企图扩张效益”与“企图维持稳定”,于此状况下,亦持续成为“文化体”(cultural entity)内部不易平衡之两项因素。文明历史之出现可划分之段落,甚至形成具有“特质”之文明阶段,即常由“发展之偏向成长”所带动之不稳定,或“不稳定之逐渐调整结构”从而趋于稳定所造成。
本文作者之认同“世界史”存在具有意义之“发展阶段”,非基于一种本质性之“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ism)或“社会演化理论”(theories of socialevolution);而是基于世界文明截至目前为止,事实存在之某种“可模拟性”。此项“可模拟性”,非由“决定论”所衍生,亦非由单一之“功能论”所推导。而是基于一种“现象”(phenomena)之归纳。此种现象之归纳,展示人类社会发展之差异性中,存在不同层次、不同面向,与不同意义之“相似性”。此种“差异性”与“相似性”之交织,于有限范围内,透过文明之传播、学习与抗争,甚至相互间之局部毁灭,使其最终形成之历史脉络存在某种“可模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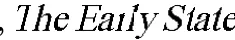
然古典时期之伟大帝国,最终皆面临无法维持之局面,西罗马帝国之崩解,且造成欧洲广大范围内秩序之崩坏,使西洋史进入中古。汉帝国同时亦遭遇草原民族之侵扰与掠夺。汉覆灭之后,三国与西晋虽能大致维持局面,此下北方中国,却亦进入长期“华、夷交争”之纷乱局面。故对于中国与欧洲而言,皆进入一种新形态之重整。
中古形态之文明重整,并非“世界秩序”(world order)之恢复,而是由混乱与纷争中,逐步于古典社会存留基础之上,实现一种统合社会,凝聚社会向心力之新形式。此一新形式,于思想面,无论展现为“富于哲学之宗教”,或“带有‘类宗教信仰’之哲学”;其根源,皆来自具有超越“世间”意义之崇高理念。而其发展之过程与成效,则复杂而多样。“复杂”之原因,源出“超越‘世间’意义之崇高理念”,与“属于‘世间’意义之现实思惟”间之相互适应,与不同群体间之利益冲突;“多样”之原因,则是一切发展,皆无“可以预想”之方式,而止能于现实中逐步调整。
对于欧洲而言,此一“中古史”之由萌昧而苏醒,其主轴,即是以“基督宗教”(Christianity)为信念之核心,逐渐融合希腊、罗马,以及其它多元民族之文化,以重新组构政治与社会。其间虽存在种种纷杂与争斗所造成之暗昧,以大趋而言,其中仍有重要之发展;此发展,即是日趋稳固而昌盛之“国家”与“教会”(church)之体制、城市社会之组织,与中古末期之“文艺复兴”(Renaissance)。以是奠立其进入“近代”之基础。
相对于此,中国之中古史,虽于前期,广大之北方疆域为异族所侵扰、统治,以“中国体制”作为“统治形式”,仍以一种精致之方式,延续于南方;且于事实上,中国所长期存在之以“人文理性”为核心之政教理念,仍是周边民族仿效之对象。此点与西罗马崩溃后,其治下地区之景况全然不同。然仿效中国体制,与全盘接受中国之“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与“历史理念”(historical ideas),为不同之两事。纯然儒学式之政教观,于“族群差异”极大之社会,其融合之力仍属有限。以是南北朝时期道、释二教之流传于中国地域及周边,即发挥极大之功效。尤其“大乘佛法”(Mahayana Buddhism)之盛行于中土,与汉译经典之成为最要之传法依据,更使具有“超越性”(transcendentality)之宗教信仰,成为降低“差异意识”之有利因素。三教之并存,且逐渐于“现世性义理思惟”趋向一致,使隋、唐之融合各族而为新形态之大帝国,大致仍以汉族之语文、中国之体制,与中国之历史意识,作为主轴。而此一中古之成就,则为欧西所不及。
然中国之“中古”成就,亦造成中国之“中古”危机。此一危机,即是一种兴盛之后,因“过度扩张”,所引生之“粗暴”与“轻忽”之心态。而此二者之结合,即是船山论唐、五代时,所谓“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嚣陵噬搏之气”。
因此,就宋之智识份子而言,其重新提倡儒家“圣学”之内在意图,并非依循隋、唐,而为一种“伸张”;亦非摆落隋、唐,而为一种“创新”。而系惩唐末之弊,而为一种“精神之内敛”。此种“精神之内敛”,虽以“辟佛、老”为其展现之方式,实则并非单纯由“出世”转向“入世”;而系以儒学之立场,于主观之意识中,期待以“在世”之精神,灌注于“在世”之事业与生活。而非以“出世”之精神投入于“入世”之事业与生活;或以“入世”之精神,证成“出世”之境界;或于“出世”之境界中,指出其亦不碍“入世”。而在其思想理念中,由于仍是具有超越“世间”意义之崇高理念;从而亦使其哲学,带有“类宗教信仰”之特质。其所透过“义理学”与“哲学”之努力,所造就之学术新样貌,与建构之新传统,则使唐光启以来嚣陵噬搏之气,乃至政局之纷乱所造成之危机,于宋之体制与政教发展中,逐渐获得稳定。此种需求与改造,于性质,仍是属于“中古”之形态;而非类近于西方所言之“近代”。
作者主张前述“分期论”之第二项原由,在于视“中古”之进入“近代”,关键是西洋史家与社会学者所强调之“经济结构”之变迁;此项变迁之必要条件,来自工业技术之发达,与经济因素中“资本”(capital)之逐渐产生之支配力;且其积极性之动能,必须累积至足以造成整体社会结构之变迁,乃至价值观念之改变,方始具有“阶段论分期”之意义。而在其发展中,应有之区分,为“工业革命”前之“早期近代”,与工业革命所带来之“成熟”义之“近代”。
所以应有此项区分之缘故,在于“工业革命”所需原创性之知识突破,来自学术传承之特殊发展,并非经济条件成熟即必然发生。故欧洲历史进入早期近代自有其途径;此途径虽系可有,并非必然。中国可以依其自身之条件,进入具有世界史意义之“早期近代”;甚至可以前于欧洲。然中国自身如无欧洲之影响,并无法产生“工业革命”,及其后续发展所需连续性之知识突破。单项技术方法之取得,即使产生连带效应,亦可能因范围有限,无法持续造成“革命性”之影响。且就社会发展而言,“形态”意义之“进步”,与历史整体之进程并非一事。中国历史上出现“进步”之形态,就局部观,常发生极早;却于历史之进程,极为缓慢。此与中国之持续维持为一“大国”之形态相关;并非事实之不进步,或于文化特质具有令其“必然趋于迟滞”之理由。
本文作者主张前述“分期论”之第三项原由,在于视“学术史”、“思想史”与“一般史”三者虽必然具有发展之关联,或相应;然彼此并非同步,亦无“决定论”之关联。因而论者无法以“学术史”、“思想史”之形态发展,单独作为评估“一般史”分期之依据。宋学对于明、清时代之影响,乃至对于欧洲之启示,虽系事实发生;此种属于“文化感觉”之亲近性,并不即能推导出中国于宋代已于“一般史”之分期,进入“世界史”意义之“近代”。
然如宋代之于中国历史,仍处于中古史之晚期,而另一方面,具有对于元、明以下社会之重大影响力,则其文化之特殊性,是否亦可如若干学者所诠释,乃属于一种中国形式之“文艺复兴”?此则有待进一步之分析与讨论。
二、宋代文化之特殊性及其对中国历史之影响

collective conscious),科学技术与医学,宗教,艺术与文学。

宋代学术思想最重要之发展,在于形成一种具有“形而上学”(metaphysics)意义之“认识论”(epistemology),将有关“知识”之理论与“道德”之理论,既分别亦合一。亦即是:于“知识”之理论,说明“物性”之由来,与其所以可成为“知识”对象之原因;于“道德”之理论,说明“善”之根源与其成立之条件。而于综合之理论,说明“知识”与“道德”之关联,乃至“直觉之知”与“理解之知”之何以可成为一体。
之所以将此视为乃宋代学术思想建构其基础之最重要发展,而非仅是一种“恢复传统儒学观点”之努力,在于:此一属于“认识论”之发展,于设立之基础,一方面能以“存有学”(ontology)与“宇宙构成论”(cosmoloy)相互结合之方式,对抗二氏之学以“道体”为“虚无”之理论;另方面,亦能将于“认识论”自身,将“对象”(object)、“主体”(subject)与“心识”之关系,以新的哲学高度,加以厘清。此两点相对于之前之儒学,有极大之进展。
此一发展,有利之处在于:一是能弥补汉、唐以来,儒学专注事物之“应然”而未知深究其所以为“应然”之缺失;从而增强儒学之哲学性格,推动“学理性知识”(theoretical knowledge)之概念。二是透过“认识论”之提升,使“义理之学”成为具有“形上学支撑”(metaphysicalsupport)之“可实践”之“进修之术”。
不利之一面,则是完整之儒学理论,亦使中国非属宗教理念所延伸之“现世”观点,为此种合“义理学”与“哲学”为一之方式所支配。“科学”(science)概念无法独立成为一种知识概念,并将“寻求确定性”(questfor certainty)发展成为一种知识态度;因而亦无法因“科学知识”(scientificknowledge)之增长产生“知识理论”(theoryofknowledge)之驱迫力。所谓“宇宙构成论”之设义,持续停留为“形而上学理论”(metaphysical theory)中之一环。此一局面,从大体而言,直至清末始由西学之输入而改变。于此之前,唯明末清初之方以智(1611—1671)与王夫之,因接触西方“质测之学”而有进一步属于“方法学”(methodology)上之反思。其他以“汉学”反“宋学”者,虽承清初若干“反形而上学”学者之影响,而有不同于宋儒之“穷理”理念,皆未能深及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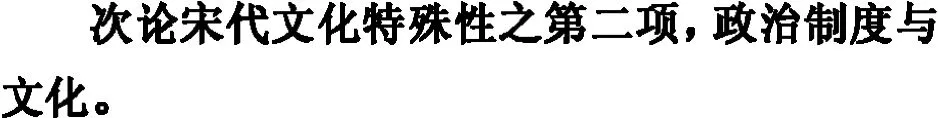

此一改制思惟之方向,显示由唐而宋,中国逐渐由帝国之“统合”思惟,走向严密之国家“管控”思惟。此一发展之方向,不仅可于明、清制度,见出影响;即在现今体制,亦仍有部分之延续。
就文化面而言,宋代士人由于学术风气之导引,与国家对于文人士夫之重视,展现一种截然不同于汉、唐之风格。宏观而论,宋人所理想之儒者风范,乃是“性情”在于礼教之中,“干练”在于体制之中,“风雅”在于涵养之中,“理想”在于笃行之中。而于具体之政治实践,宋代之士大夫,则是欲将政治之“理念”、“知识”与“效益思惟”三者,合之于一种动态之“识见”。以备条件于此者为人才。
所谓“政治之理念”,一层为“治术”,一层为“治道”。“治术”之设想,出自于经,演之于史;而于更制,则有“激进”与“徐改”二者思惟之不同。其关注之焦点,一在惩唐与五代之弊;一在针对宋初以来立国之规模,与现实存在之种种问题而为谋画。至于“治道”之部分,则期待将此时之中国建设为一“道德国家”。
所谓“政治之知识”(knowledge of politics),由于牵涉政治之实务,故除“考之于史”外,亦赖大批智识份子实际参与政治,从中获取经验。宋代政制中对于基层事务,如漕、盐、茶榷、河工、医局等之分项,乃至田税、力役等,皆有一种以当时之世界标准而言,颇为精细之处置,即是一“政治知识”(political knowledge)进步之展现。宋代史学之发达,产生多样之著作形式,皆是其效。
至于“效益思惟”,则为政治实务讨论中所必然涉及。与“伦理学”(ethics)中之“义”、“利”之辨,或于“治道论”中辨帝王之心术,议题之性质不同;以是难于举其一例,即概其余。学者或将二者混淆,皆属个人识见上之偏失。
而所谓宋代之士大夫欲将政治之“理念”、“知识”与“效益思惟”三者,合之于一种动态之“识见”,更是宋代儒学对于“政治人才”之一种新定义。此点常可于“理学家”对于当代人物之评骘中见出。此点影响后代亦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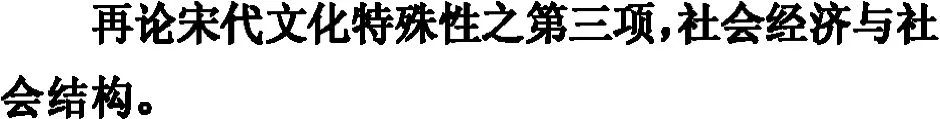
宋代社会结构相对于唐,发生巨大转变之原因,来自中晚唐以降,战祸频仍对于社会旧有结构之破坏。就整体中国史“社会发展”之进程而言,此种经历盛极一时之治世,最终导致门第崩解,政治集团势力解构之最终出现于唐末五代,终结东汉晚期以来各式以“政治血缘”结合“经济占有”而形成之中古形态之阶级特殊化。故宋之开基虽不稳实,宋却可利用“崇儒”、“税商”、“劝农”、“奖工”等措施,活络社会之流动,产生发展之动能。
此种新形态之社会局面,如未受“过高税赋”之挤压,与北宋覆灭之影响,其所积累之经济成长,即可能将整个中国带入“早期近代”。然辽、北宋灭于金,金与南宋最终亡于蒙古,此一“可积累”之效应,并未于事实发生。整个蒙元时代,对外而言,承接属于欧亚新关系之影响;对内而言,则是逐步开启南北长期对峙后之新融合。于此状况下,“崇儒”、“税商”、“劝农”、“奖工”虽仍是治术思惟中之所有;其结果,则已非依“宋人之策略”,所可充分理解。中国开始出现“君臣”、“士庶”、“贵贱”持续不断之冲突,政治与社会之斗争走向激烈化。凡此,皆有其发生之原因。因此,从另一面言之,实亦可能显示中国确已进入一新的历史段落。本文作者之所以提出不同常论之历史分期,即是着眼于此。

宋代之具有一种普遍之集体意识,来自“阶级感”之淡化,从而使“民”(“百姓”)之意识,逐渐成为奠立“社会共同体”之基础。宋儒以《大学》一篇作为“平民教育”之理念模板,即是由此出发。而“民”之意识之上升,其理想性,则表现为宋儒所谓“成德”之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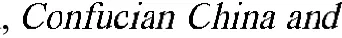

宋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之“相对发达”,具有五项有利之因素:
其一,两晋南北朝以来以“精”、“神”、“气”、“质”为核心概念之“物论”,逐渐使原本存在于“气”论中之“阴阳”说与“五行”说,逐渐剥离其残存之“神秘性”,走向一种涵括“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之“有机之自然论”;此点有助于机械学、物理学、化学与医学之发展。虽则此种科学与技术之学,尚缺乏构成“近代科学”之基本质素。
其二,宋代“理”、“气”二分之说,于存有学主张一元,于宇宙构成论则将之分论,此点有助于将“局部现象”之理解,脱离于哲学之宏观论述。
其三,宋代社会,由于产业之发展,“技术人”之技术利益,与“技术人”之知识身份逐渐获得重视;政府且有若干之辅导与奖掖,此点使科学与技术之学获得推动上之提升。
其四,宋代出现以当时之标准而言之伟大之科学家,且将其发现笔之于著作。
其五,宋代之海外贸易,开拓宋人之商业视野;并使其经营策略具有早期之近代特质。亦使其思惟中,理解“利用之学”之商业价值。此点并不与儒学所主张“人伦关系当重义理”之原则相冲突。
综合而言,宋之技术运用于民生与商业,对于明、清影响亦大。特科学与技术之发展,常有瓶颈需要突破,亦有若干属于“科学哲学”(philosophyof science)之条件有待建立;故此种发展,并未于事实上,将中国推向符合“现代科学”(modern science)之层次发展。

宋代之宗教发展,分佛、道与其它民间宗教三类。而其特殊性,大约可分说为五:
相对于唐之于政治面,三教并重,而于其内心,更尊视佛、道;宋之群臣,则期待所谓“尧舜其君”。而宋之帝室,亦常以“天命难谌”自警惕。此点使宋之政治文化,于政务烦剧之中,常带一种儒学之“道德气”。此点对于清代前期锐意图治之君亦存在影响。康熙之尊理学,除政治考虑外,此亦是一不应轻估之内心想望。整体而言,此种儒学精神之提振,成为政治文化之一环,使中国后代即使帝王祭天祀孔,崇道信佛,亦不可能将整体政教之形态,带往建立“国家宗教”之方向发展。此其一。
禅宗于唐极盛之后,弊端亦渐随“传或不得其人、或不得其法”而浮现。入宋以后,“默照禅”与“看话禅”之争,更是凸显禅宗教法入细后,不易深明其理之困难。然于宋一代,其上焉者,终能立心为宗,抉择精进;“禅”、“教”之相融,“净”、“禅”之相救,即属其例。此外缁、素之以高行化世,而见史传者,亦不绝于书。此与理学之兴盛,乃属不同脉络;并无“消、长相嬗”之必然。此其二。
理学之兴,虽沿韩昌黎(愈,字退之,768—824)“辟佛”之说;然二者实于哲学之理论,可相对话。此种儒、释之对话,成为促进中国哲学与宗教持续发展之重要因素。此其三。
道教于宋代,亦与儒、佛有发展上相互影响之关联。特其重要性,以思想史而言,不及儒、释之交涉。此其四。
宋代对于寺庙与宗教传播之管理,具有政策;此一政策,考虑之因素属于政治与教化,而非宗教义之“相互排斥”。此点亦影响后代。此其五。

宋代之艺术与文学,不仅于创作展现独有之风格,且于其中发展出一种系统化之批评理论;其中包含“美之理论”(theoryofbeauty),亦包含“艺术之理论”(theory of art)。此种系统化之理论发展,不仅显示宋人于“艺术与文学之创作”方面之成熟;亦显示宋人于“艺术与文学之理论”方面之成熟。对于前者而言,宋人之基础,来自唐五代之辉煌成就;由此而走向自身方向。对于后者而言,宋人之高度深化,则来自三教观念相互渗透下,由特殊议题导引所产生之一种哲学领域之拓展,与哲学系统化之延伸。此点与唐以前美学理论、艺术理论之未充分“系统化”、“学理化”有所不同。而此项深化之结果,亦使宋以后艺术与文学之创作,常伴随种种属于“批评”(criticism)之意识与理念而发展。
此外宋代之艺术与文学,另有一项精神层面之转向,即是“精神之内敛”。此一“精神之内敛”,特别表现于“诗”与“画”,促使文学家与艺术家,企图于“心”与“物”间寻求一种“精神性之关联”;从而将“心”与“物”间之疆界打破。此点深化文学家与艺术家对于传统美学概念中“象”义之认识。元以下艺术与文学之发展,虽非皆是以此为方向,然此一因素之加入,亦有其不可轻忽之影响。
三、宋代文化崛起之性质

此一问题,由于仅是属于“历史诠释”之范围,为一种“提示”,而非可因其结论,据之以推导出一种解释“特定时期历史本质”之论述;因此并无真正之严肃性。然于相似之中,指出不同,亦有助于理解其各自之特性;故此设想,亦值得加以讨论。
首先应厘清者,为“俗世文化”(secularculture)与“宗教”间之关系。其次则为“人文主义”于中、西文化中性质之差异。
盖伟大之世界性宗教,皆带有某种“出世性”,此为今日研究宗教者,大致所可同意。而其原因,则是因对于“现世”之悲观态度,以及期待“拯救”或“自我救赎”之心理,能激发人崇高之情操。然任何一发达之文明,绝非仅有严肃之宗教,而无属于“世俗”层面之生活;或此“世俗文化”,仅具有“依附于宗教”之意义。
而从另一方面言,带有“出世”性之宗教,亦未必不能同时产生与其教义并不冲突之“人文精神”,或接受某种类型之“人文精神”。特此种“出世宗教”与“人文主义思惟”间之关系,各个地区则有不同;而中国与欧洲之差异极大。

对于中国而言,原始萨满教之思想存留,具有三种面相:
第一种发展,即是维持“形式”上之祭天、祀祖,以之作为“人出于天,受命于天”之理念之象征。此一发展,虽透过历代各式“典礼”之制订与实践,持续成为“政治正当性”之支撑;然其理念,已非属纯粹之宗教性,而系同时带有一种“以人合天”之人文性。第二种发展,乃是以地域性、民俗性之宗教方式,将之传衍于民间,成为广义之“道教”形态之一部分。而第三种面向,则是以祠堂之祭仪,作为“宗法”观念延续之表征;其意义在于依“血缘意识”而扩展之伦理。
此三种面向,唯第二类,具有真正之宗教性;其一、三类,事实上属于儒家“治化”观、“教化”观之一部分,仅有“类宗教”之性质,而非真正属于严格义之“宗教”。
至于高层次之宗教发展,则有兼具“哲学”义与“修行”义之特殊义之道教宗派,与外来之佛教、景教、回教、犹太教、祆教、摩尼教等。其中,道、释之影响尤大。
然就汉及其后之状况而言,无论何者,其发展之背景,皆是已充分“儒教化”之伦理社会。各式宗教之最终能否于中国社会存续、并良好发展,其关键在于是否与此一社会之特性兼容。南北朝之“辟佛”,有所谓“三破”之论,即是凸显此点。
而佛教对此,不仅有所回应,实际亦有所适应。此后回教之流传于西北,耶稣会之来华,皆有类同之景况。甚至其后藏传佛教之于明、清,亦发展出一种特殊之说法,使其传承中所存在之“政教”体制,与中国本土发展之政治理念,可以相互接受而不发生剧烈之冲突。
故特殊宗教之于特定时刻在中国盛行,理论上并不构成思想上之冲突。中国之利用宗教以强化其统治之正当性,皆系建立于原本之儒教基础,而非取代原本之儒教基础。此点与欧洲“神学观”之可能于某一时期凌驾于“哲学观”之上,或宗教文化之可能长期成为社会建构之主导力量,形势不同。
亦因此,将宋代之儒学复兴,说之为乃自唐代宗教弥漫之气氛苏醒,或于另一种论点,将宋、明理学之兴盛,说为乃形构一种不利于“理性发展”之“暗昧”,皆非确当之说。
而正因“俗世文化”与“宗教”之于中国,其关系乃系“分别”之中有“融合”,而非于性质上“对立”;故若欲以“人文主义”之概念说明中国儒家思想于中国之发展,亦应与西方历史陈述之方式有所区隔。此即所欲阐释之第二点。
“人文主义”之概念,是否与宗教观念冲突?常视主张者自身之哲学立场,以及彼对于此一概念之诠释而定。因此,对于仅将“humanities”作为一种现代教育之内容,或于另一论域,主张人可依凭人性之发挥,决定自身之命运,从而视宗教为无益,或径直主张一种“无神论”(atheism)者而言,由于此一发展,乃西方近代十八、九世纪以后事,缺乏与“宋代”之对比性,故凡试图将宋代之儒学运动,比附于一种具有“文艺复兴”意义之人文主义,其“人文主义”之意指,多指“Renaissancehumanism”而言。
对于此种论述之是否可行,在于须先决定“认真”之程度。盖如仅属一种“宽松之模拟”,以此为方便,亦无不可。然如认真而论,即应提出赞成或反对之理由,且此理由应具有一种有助于“深入双方历史研究”之导引性。本文之立论,所以于此,并不持“赞成”之意见,主要在于两点:
首先即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子学”兴起后,直至宋代,即使社会于不同时期流行不同形态之宗教,有时亦不免存在某种近乎“迷信”之思想,甚至透过政治力,以特定方式对于不同于己之信仰者进行迫害,皆未曾真正造成长时期对于“理性思惟”之压制。此点与中国“士阶层”之建构方式,与其社会功能相关。因而于三教各自流传之氛围中,儒家以“圣学”或“理学”之方式产生一种儒学方式之“天人合一精神”之召唤,仅属“有限范围”内之一种精神提升;对于文化基础而言,仍是承袭于前者多,不足与“文艺复兴”之于欧洲相模拟。
其次“文艺复兴”之伟大,在于其思惟中所内涵之一种融合“信仰”、“知识”与“创造”之精神原理;此精神原理,具有“普世性”之价值。因而具有一种可伸展之影响性。对比于此,宋代之人文性之创造,透过其文学、艺术、科技、哲学、宗教、治化,乃至士人之人文精神,亦有类同之处。宋代理学思想之流传于金、元,影响于明、清,乃至域外之朝鲜、日本与安南等地,甚至启蒙时代之欧洲,与现代接受西方文明冲击后之中国哲学;皆是其证。然而由于宋代理学思想之结合“义理”与“哲学”之方式,其真正之影响,须作用于已受儒教深厚影响之社会;如不具此种特殊之条件,则其传播所造成之作用,皆止能成为一种范围极为有限之“启示”因素;理学思想之于欧洲与东亚、东南亚,皆是如此。此点与今日世界之仍受“文艺复兴”以后延续于欧洲之若干文化因素之影响不同。至于宋代人文性创造之其它方面,其“民族文化”之属性更强。其无法模拟之处在此。
虽则如此,宋代文化之于中国,就其内在之性格而言,实是一种文明之跃升;且以“潜在”之意义而言,亦具有一种“世界性影响”之可能。特此种“潜在”意义之“世界性影响”之可能,依本文作者之见,实须透过中国之现代化,将之与其它文明之有利因素结合,始得以彰显。

Discussions on the Basic Character of Song’s Culture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History
〔TW〕Dai Jingx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Kaohsiung 80242,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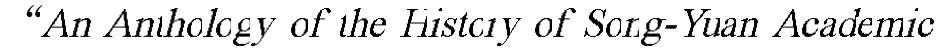
Song Studies;History of Song Dynasties;Chinese History;Song Culture;Academic Thoughtof SongDynasty;Philosophy of Neo-Confucianism
戴景贤,字嘉佑,祖籍安徽合肥,一九五一年出生于台北市。自高中时代起,即师事国学大师、著名史学家钱穆,前后逾二十载。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班,获文学博士学位。自同年起,任教于高雄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迄今,并曾担任该系教授兼主任。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台湾高雄中山大学特聘教授。研究领域涵括学术史、思想史、美学、文学批评与中西思想比较。曾获中山大学研究杰出奖、杰出教学奖,并经遴选为该校传授教师(mentor)。此外亦获颁“教育部师铎奖”、“国家科学委员会杰出研究奖”,及多次“特殊优秀人才”奖励。众多著作,编辑为《程学阁著作集》,将陆续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刊行《明清学术思想史论集》上下编、《王船山学术思想总纲与其道器论之发展》上下编、《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论集》,共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