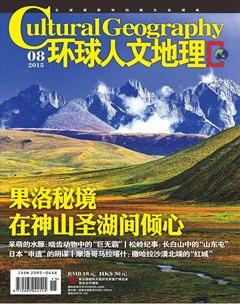天生三桥
哑铁
盆景:忧郁曲
你们一定来自大野
带着某种隐秘,众多手掌摊开的
柔弱,有微微的颤抖
空出来的小惊喜,刚好蜷缩在墙角
这跳动的绿,怯怯地逡巡、游走
迷恋窗外避雷针上的鸟影
也像我,偶尔发发脾气
我总是误认为那三只灰喜鹊
叫声异样,居心叵测
听听,总有鸟音从窗户拐进来
或许只是幻像
只是这些叶片,不甘寂寞的私语
我端详这些盆景
凝望——像两株盆景
这种对峙,唯一区别
在于:他们,多像春天的诗行
对瓶:登梅图
两树梅,共同拥有一句台词
在花瓶上练习口型。喜鹊从暮色中赶来
翅膀上溅起黎明,这形式主义者
足爪深深抓紧梅枝,用羽翼
敛紧风霜。梅花一开口说话
红色的隐喻,从一树枝头爬向另一树枝头
一对瓶,挨得很近
在太阳升起前,用怀中的梅香相互取暖
现实中,梅花开了又谢了
那句台词,有着褪色后的淡影
留在枝头的对白,需要喜鹊耗尽前世今生
可以再靠近一点,看明白
梅花的形状,类似于起伏的岁月
有多少蜿蜒的目光,像花瓣一样
挂满枝头,恣意开放
梅花的芬芳隐隐袭来
喜鹊从一枝梅飞抵另一枝梅
需要绕过对瓶,划一道优美的弧线
生日诗
多么锋利啊
这薄薄的刀刃
人生,就这样
被一截截快速削掉
栀子花
多年前,我从祖母坟边
领回一株栀子花
在阳台上精心侍养
虔诚地施肥、浇水、除草
以减轻对祖母的歉疚
多年了
我耐心地等待花开
等待,祖母从另一世界
寄过来一张笑脸
今晨,栀子花终于开了
颤巍巍,多吝啬啊
一生节俭的祖母
我总看不清她模糊的身影
竹杖
20年前,一只竹杖
领着祖母走过很多地方
20年后,另一只竹杖
领着父亲
将祖母走过的山路
重走一遍
古佛洞
如果通向彻悟的路需要预习
拜谒古佛洞,是否可以拥有慧根
看清百年后所要经历的幻像
弥勒佛的笑口微微张开
这洞口,仿佛是整座山凝聚的沉默
将雨水和饱胀的欲念
一并交出去,让紧紧抱住你的浓雾
松开手臂,就像我们自己放下
甬道曲折幽暗
要有宁静心才能洞心明见
一点点佛性也会点燃内心的火把
在佛光的照耀下
我们先得学会为自己照明
佛法在宏大的洞体中微微漾动
灯光晦暗,有如佛在讲述
苦修的过程,佛法浩荡
一批批膜拜者聚拢又散开
轮回的因果永无休止
佛的头顶,空出巨大空间
莲花台下
众生的空间多出了一席之地
天生三桥
是谁撞开了这裂隙
可以静静地安放一条小河
用这几小片盆地
安放月光冷冽的忧伤
三座天然石桥
呵,应该更亲切些
称它们为铆钉,或者脚手架
它们是那撞击之初
唯一没有倒塌的信念
三只手臂,挽在一起
从巉岩绝壁上伸出来
试图将开裂的大地
渐渐收拢、抚平
如果用一大堆词语可以形容
那么,我将穿行
诵读草木之诗
用喧响的流泉,把自己灌醉
或者,干脆长成
绝壁上的第四只手臂
旧风衣
暗下来的天空
空无一物
但每往前一步
都有辽阔的寂静在张开羽翼
我害怕转身
害怕身后那高大的暗影
他穿着旧风衣
用我的恐惧
将夜打磨得更加漆黑
前面
白天走失的过程被低述
我要赶在黎明到来前
收走那件旧风衣
事件
河流穿过自己的身体
像一朵云穿过另一朵
小心翼翼,惟恐弄伤自己
月光用一袭薄纱覆盖万物
苍山影影绰绰
河流安静时
声音依然裸露在外
替换
生活很干净
我用一匹瘦马驮走秋天
试图将金黄的部分
替换出来
就像用一场雪
诅咒整个冬天
我试图将腐烂的部分
替换出来
那些掉进底层的声音
越陷越深
我试图用柔软的春风
将撕裂的伤痕
替换出来
故事
正午,猫在昏睡
一只狗猛然扑向墙角
夺慌而逃的老鼠发出吱吱尖叫
逃散的
还有它迎娶新娘的美梦
树荫下,一个挑担的人坐下来
与身边斜躺着的柴捆
各自想着心事
手里的烟卷忽明忽灭
像那一寸寸矮下去的光阴
田野浩荡无垠
蝉鸣声将群山推向旷远
某个屋檐下传出的咳嗽声
飘浮在空中
被长满荆棘的苍茫
轻轻压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