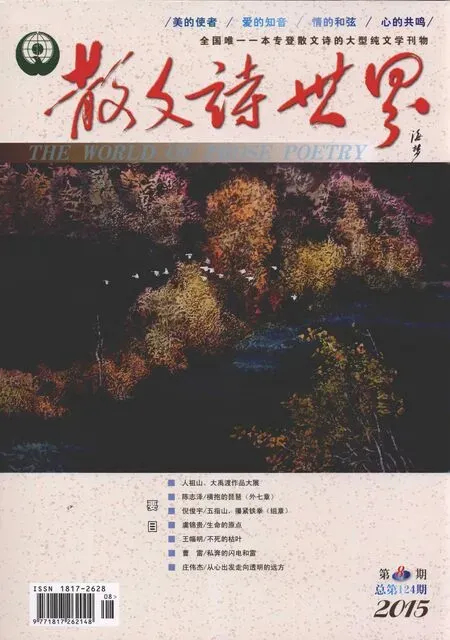记忆三堆(四章)
四川 王清蓉
记忆三堆(四章)
四川 王清蓉
白龙湖往事
白水泱泱。
二十多年前,一声吆喝,挥舞着长臂的机器,破了大山的沉寂。宝珠寺电站的大坝,截住湍急的流水,从此,白龙江水为三堆而宁静。
水,漫起来,漫起来了。轻轻地呼吸,慢慢,绵绵。
年迈的大爷坐在湖边,凝望水底的白云、森林、农田和青草,飞过晒坝的麻雀,还有炊烟,都沦陷在时光里。
他们的家园,在水底静静安眠。
那些过往,弥漫着硝烟的历史,马蹄踏过的岁月,平常人家的悲喜,还有包容了时光的高山峡谷,都在水底静静安眠。
他没有悲伤,只是一锅叶子烟呛湿了双眼。
子规声里,细雨如丝。白龙湖里,轻舟翩然。
自然的博大与人类的智慧在这里交融。湖底,暗流涌动,时光流转,灯火辉煌。
青山在绿波里绵延,鱼儿穿过林梢。一些欲望,把湖水染得敏感忧郁,凝重。飞鸟的羽翼,低不进故园的水土。
尘烟深处,我们只是过客。
打捞起那些狂热的欲望,让远去的流水丢了负累。一泓清水,可以照见我们灵魂最初的原乡。
三堆老街
喧哗的车声不再。熙熙攘攘的人群,随821厂和水电五局远嫁。世事如烟,繁华落幕之后,三堆老街静默如初。
月光清洗过的夜里,每一块石板都很安静,它们在清凉的夜色里梳理记忆。走过的人,滑过的车辙,在身体里慢慢安眠。
魁星楼是个古老的符号,为三堆老街留下完整的注脚。
清晨,魁星楼外的两棵老皂荚树在晨光里梳洗,枝叶擦得鲜亮。年轮,孕于岁月之外。
院里的音乐,舞动的水袖,还有挂在墙上的唢呐,都是忠实的朝拜者。
老粮站的大秤躺在屋角,粗重的秤砣铁了心地要休眠。昨天,母亲还背着粮食站在水泥地上,等待过秤。我倚着冰冷的门框,街前,行色匆匆一地过往。
理发店的躺椅,染上斑驳的时光。理发师傅一身白衣,坐在转角的门口,眯着眼仰望,浅蓝天幕下,屋檐镶嵌的“国营”两个字渐至模糊,淡出岁月。
老街沉默在黄昏的夕阳里。
亮瓦是忠实的坚守者。那束穿透屋顶的阳光,流动着经年的微尘。石头缸伫立在天井中央,一尾红金鱼穿过碧绿的水兰,把陈旧的时空摇摆得宛若新生。
菜籽油的香味醉了老街。油坊低矮的屋檐下,再没有背着背篼来来往往的人群。
游荡在炙热的夏日,怀念冬天的早晨,穿过纷飞的雪花,我们把冻僵的手笼在校服宽大的衣袖里,穿过那些逼仄的小巷,站在老街守望又酥又脆的核桃饼。
二十年的时光不远。
街角的屋檐下,我还是那个红着脸的姑娘,刚从遥远的山村走来。
风中的唢呐
腮帮子一鼓,手指跳动,唢呐就响起来了。唢呐一响,风中流淌的色彩就丰富起来。
唢呐穿着古铜的衣衫,在山间小路蜿蜒,任旷古的风沾染裙裾。一路颠簸,任它严寒酷暑,任它秋月春花,任性地流淌一曲又一曲的离别。
哽在喉里的心事,不吐不快。
唢呐欢快,把幺妹子从李家梁送到三堆坝。唢呐吹得花轿摇摇晃晃,晃悠里的幺妹子哭了又笑。幺婶站在风口,眼神瘦了村头的麻柳树。
唢呐激越,隔壁的张嫂从媳妇熬成了婆婆。唢呐的喜悦,推开眼角的鱼尾纹,开了花。
唢呐悲怆,把三爷吹进黄土地。唢呐吐出的每一粒音符,都是对三爷这一辈子的注释,简单又繁复。从此,他长住在柏树湾的坟林里,任灰色的纸蝴蝶翩翩飘落。
吹过希望,咽下苦难。唢呐收藏悲喜。背井离乡的脚步匆匆,伫立在风中的唢呐哑然失声。
梦里,唢呐声声回故乡。春花遍野,老屋的檐下雨滴清寂,日子蓬松而轻盈。大雪无垠,就着红灿灿的火盆,鞭炮声声龙腾狮舞。
或许明天,唢呐声将抚过山的脊梁,吹得白龙江岸一派丰收的模样。
花香井田
井田是一个弥漫着花香的地名。
犁铧走过的春天,井田是一湾金灿灿的油菜花,铺天盖地,炫亮那方山水。
菜籽刚刚穿过初夏的饱满,井田坝就沉静下来。
一支支碧叶撑开水面,擎起朵朵清香。田畴上,几枚鸟鸣划过,被泥土收藏。
花开的声音如此寂静。一只蜻蜓飞过,翅膀端不起骄阳。
姑娘的花裙,安静的阳伞,轻轻飘过。花叶的清香深及灵魂。
苍穹冷,青云垂,几番疾风骤雨。荷塘走过的女子,长发飘飞成最美的风景。
江心的三堆巨石岿然,湖水环绕,涟漪清漾。荷塘之外,小镇如浮在云雾间的一幅水墨画。
荷塘里,落在花间的珠玉,是夏日素净的心事。留一抹纯度最高的阳光,几分矜持,几多含蓄。只需轻轻触摸,便抖落许多遐思。
我想站立成一片荷,守着月白风清的夜。潋滟的梦想交给六月,繁华之后的留白,赠予寒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