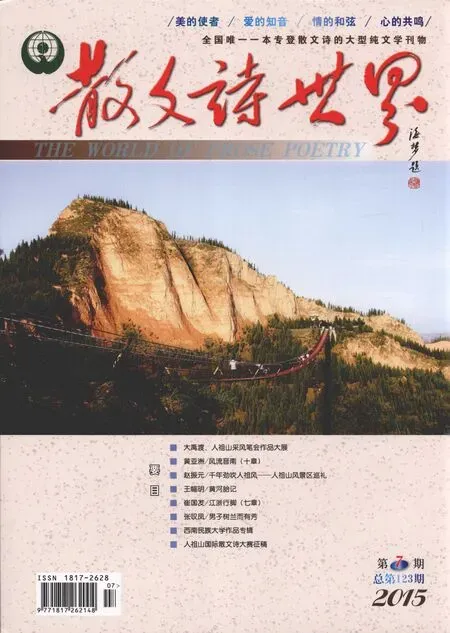彼岸有风(四章)
广东汕头潮南区古溪初中 李佑启
彼岸有风(四章)
广东汕头潮南区古溪初中李佑启
棋手
棋子是有思想的,当他知道自己成为别人的棋子时。
只是,棋在江湖,身不由己。
棋子知道,无论是闲棋还是臭子,抑或,残局,都是一个悲剧。
棋子还知道,不管输赢,棋子的梦,最终走不出棋手的故事。
不是所有的战场都刀光剑影,不是所有的厮杀都血流成河,有的时候,有的东西,不显山,不露水。就像不是所有的城堡都会露出成堆的白骨,所有的宫殿都会构筑在阳光之下一样。
高超的棋手,他的棋盘与棋子,都在心里,谈笑之间,已决胜于千里之外。
棋逢对手时,棋子就是生命,生命,也是棋。
观棋不语者,不一定真君子。真正的君子,喜欢博弈,但常常并不博弈。
谁是棋子?谁是棋手?谁是最后的棋子?谁是最后的棋手?
棋手不说,棋盘也不说。
当棋子和棋子对弈时,彼此都是棋手。当棋手和棋手对弈时,彼此都是棋子。
有时候,你是我的棋子,我是他的棋子,而他呢,又是你的棋子。
然而,在棋盘的眼里,所有的棋手,都是棋子。
冬麦是个好女孩
冬麦命苦,深秋启程,春天谢幕。
但冬麦是个好女孩。
将她嫁去山坡,她就在山里扎根安家,无怨无悔,一如我善良的母亲。
冬麦怀孕时,我常干瘪着肚皮,嶙峋的瘦骨如同起伏的麦浪。
冬麦回家时,父亲将她捧在胸前,双手合十,念叨着:“好了,好了,我们不用挨饿了。”
于是,我们以朝圣的姿势,虔诚地迎接冬麦回家。
那些青黄不接的日子,从此有了喜悦的光泽。
冬麦遗传了父亲的风湿病,所以,连再冷再冷的冬天都不怕,但怕湿。
母亲说,父亲永远是一株受伤的麦子。
父亲掀起一铲麦子,迎着风,高高扬起,什么也不说。
他能说什么呢?
麦壳随风而去。那纷纷落下的,便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啊!
一片挂在檐角的云
云不喜欢呆在山里。因为心里装着水。
曾经,水是云的化身,或者说,灵魂。
一阵雷雨,云的姐妹都翻过山梁,从山旮旯里,风一样飘走了。
而云,一不小心,被屋檐挂住了。
云,沉默了。
云的老公是个老实人,曾老老实实地在南方打工,一年才回家一次,有时两年。因为车费。
最近听说,云在外面有了一个叫风的发廊小姐。说是小姐,其实是大姐了。还听说,那大姐的年龄比云还大,相貌比云差多了,而且……
想到水,云心里那个屈啊,泪水滴滴下。
然而,云只能背着儿子和父母,偷偷的哭。
云也向往山外的世界,但是,却被屋檐挂住了。
云用泪水延续着先前的故事:
水曾说:“放心吧云儿,不管我流浪何方,有你盯着哩。”云幸福得痴痴地笑,说:“是啊,我盯着哩。”
“没有云就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云。”洞房花烛夜。
曾经,电话里,云问:“水啊,你的心在哪里?”水说:“朝着家的方向哩。”
那时,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然而,那只是曾经。曾经是一块含在梦里的糖。
本来,天上有云,地上有水,云水相连,天上人间。虽然思念有点痛,但痛得幸福,痛得甜蜜。
都是风惹的祸。风让云吃了哑巴亏,让水起了漩涡。
云心里那个愁啊,那个苦啊,那个怨啊,那个恨啊,汇成了一条河,天天在淌。
有时候,河咆哮着,汹涌着,很想掀了那角屋檐!
暗流涌出花开的声音
灯光是夜的语言。人不懂,但夜,它懂。
灯光从窗口探出头来,一如初恋的女孩站在窗口张望着情人的身影。
灯光与灯光交流着,交流着白天那两只公鸡大动干戈,交流着村口老槐树上的喜鹊好多天了还未搭出一个像样的窝……
灯光一粒一粒的,星子一粒一粒的,走着走着,他们就走到一块去了。
而我们呢?一粒一粒的,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灵魂是眼睛的路标。嘴巴不懂,但心,它懂。
萤火虫能掂量出黑暗的斤两,却说不准露珠与叶尖的距离。
苍穹把无边的夜色抱在怀里,无边的夜色把黑暗抱在怀里,而黑暗深处的眼睛,却把萤火虫一只一只地豢养在瞳孔里。
我在黑暗里寻找荧光,那荧光就是我的太阳。
露珠站在叶尖的边缘,竭尽生命所有的力量,希望迎来一缕明媚的阳光。
露珠不后悔。
但有的人,后悔了。
不需要安慰。因为时间。
比如:涌动的暗流;比如:朽木的味道;比如:树影的舞蹈……
甚至,连装腔作势的样子,都采用了省略的方式。
然而,阴影里漏出的一滴鸟鸣,它也许可以引来明天清晨一声嘹亮的鸽哨。
比如:黑暗之外的一丝看不见的云彩,它早已将一方干净的蓝天,搁在了你的窗台之上,只待你明天一觉醒来,拉开昨晚封闭的窗帘……
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只要舍得放下。
只要你能为自己找到一个理由,只要你能为内心的踏实腾出那么一点点空间,只要你还拥有三尺阳光,那么,明天晴朗的天空,就能填补你瞳孔以外所有的空白!
今天还下着小雨,但是,月亮已经爬上了你的窗台。
猫儿的脚步很轻,轻得能听到月光爬上窗台的声音。风儿的脚步很轻,轻得能听到墙上游鱼戏水的声音。巷子里的犬吠,也很轻,轻得能听到吴刚醉酒、嫦娥挥袖的声音……
轻一点,再轻一点,我们就能听到春天花开的声音了。
如此静好,明天,一定是个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