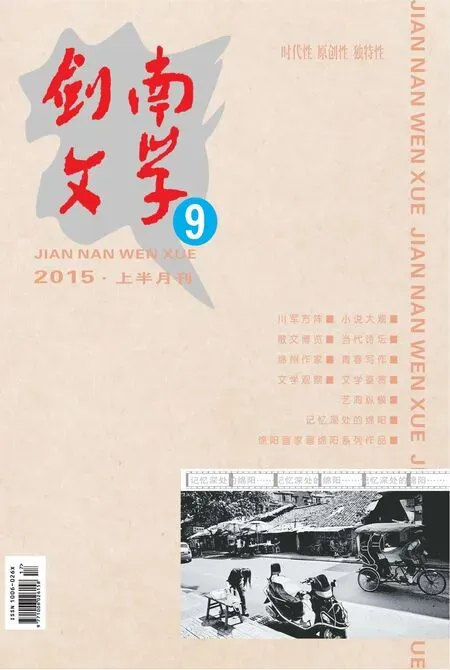贾樟柯的小城镇叙事
■孙晶蕊
贾樟柯的作品始终围绕着中国北方小城镇展开。20 世纪70 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一直是贾樟柯关注的焦点。他们所经历的经济高速转型期的创伤,以及小城镇难以抵制全球化浪潮冲击的窘境,成为了贾樟柯电影的叙事主题。
贾樟柯的作品带有明显的空间性特点。位于中国西北内陆地区的小城镇汾阳,是《小武》和《站台》最主要背景。贾樟柯的电影背景,本着走出当地的欲望,从汾阳转移到大同,导演把小城镇作为电影的主要背景书写,不只是个人对故乡的追忆,更是创作者对当代中国都市化进程中小城逐渐被抛弃的真实记录以及切身体会。
一、安稳的小城
电影中处处显示出旧有的价值观念,淳朴的民风,勤劳踏实的人们。首先,以明知小武是个小偷的派出所郝警官为例。他一点没有警官架子,主动与小武寒暄,不仅没有歧视他,反而像父亲一样关心他的近况,敦敦教诲他。其次,小武虽然是个小偷,但是他也是一个重情重义、信守承诺的人。他允诺要在小勇结婚的时候送他六斤钱,可是如今,他们曾经的情义对于小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他依然坚持信守自己的承诺,去送上自己的礼钱。最后,朴实的三明因为没有钱,娶不起媳妇。可是为了妹妹能上个大学,有个出路,他选择去签下生死契,去煤矿打工,默默地付出。
二、变迁的小城
贾樟柯没有选取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南方城市作为叙事背景,而是把焦点对准了一个远离沿海的内陆小城镇。自此以后,汾阳便成为了贾樟柯电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汾阳小镇抵抗时代变迁的历史被永远地记载下来。
小城被动地承受着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改变。拆字被写在各种熟悉的陌生的地方,预示着即将发生的变化。影片最为突出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它的空间叙事。是正在拆迁中的城市,是那些随处可见的钢筋水泥,是在废墟中无奈坚守的墙垣。小镇变成一个可以不断毁灭和无限复制的空间。贾樟柯的电影通过人对地方的依附,从空间的横向、时间的纵向两个纬度将人置身在历史和记忆中,用影像不动声色地传递停滞中的故乡和瓦解中的故乡之间的张力,以及这张力中的诗意。观众则在这不动声色的背后陷入不可遏制的彷徨与无措。
三、无所适从的小城镇人
贾樟柯表达的是一种生存的无力感。《小武》中,小偷身份注定了小武的结局。他在电影中一出现就是干这个的,这个身份,让他经历了亲情的冷漠,友情的背叛,爱情的遗弃,最终他因行窃被警察拷在街头,供人围观。他的生活最终走向何处,没有人知道答案。《站台》中的崔明亮们,在对外开放体制变革中,历经着改制、承包、走穴等带来的动荡不安的生活,而最终回归在带小孩的日常生活中。《任逍遥》中的小济和斌斌,他们的青春年华被堵死在考大学的道路,而赵巧巧则放纵着青春,在沉沦中无力自拔。
通过城镇电影文本可见,在城墙、街道、生活空间等城内空间里,小城镇生活显露出一种缓慢而沉静的气质,通过大量的空间叙事表现出创作者们对传统生活和人情关系的怀念和不舍,但是现代生产及其价值观的冲击粗暴而彻底,无情地颠覆了注重人情的传统小城镇空间秩序。小城镇电影不仅仅是为了让观者缅怀过去,留恋于历史的镜像,而是让中国电影能将目光转向以往不被重视的当代小城镇,使它不为人所见、不为人讲述的一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些新生代导演直面现实的勇气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