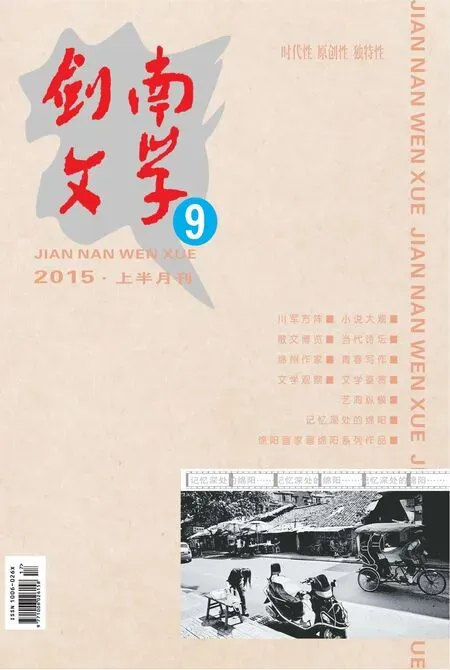行走在麦尖上的记忆
■廖伦涛
五月,正是农村瓜果飘香、小麦成熟的季节。
约上几个 “老知青”,坐在探乡的车上,车窗外成排的桑林一晃而过,层层的麦田映入眼帘。在丽日蓝天下,一望无垠的麦浪翩翩起舞,甚是壮观,滚滚的麦浪把大地和天空涂成了一片晕黄,黄的殷实、篷勃、浩荡,黄的翻江倒海、惊心动魄。 “哇!好美的麦浪!”我们一齐惊叫起来。迅疾下车,拿出相机, “嚓嚓”拍照,然后坐在路边,敞开胸怀,微风吹拂,任闪闪的目光和思绪,随着那起伏的麦浪,不断向沟坎、地角、直至天边伸展。
回想 “上山下乡”时,才到农村,什么也不会,也曾把麦子当韭菜、把巴蕉当香蕉。可几年下来,通过农忙,目睹灾荒,才真正知道粮食的珍贵。千百年来,传统的农耕时代,无非就是将一些植物和动物生长直至走上餐桌的过程完整地置于人们的面前,让你参与其中罢了。一粒稻谷,一颗麦子,一苗油菜, 从发芽到分蘖开花, 再到最后结籽,那都是天和地还有人共同作用的结晶啊!为了这,需要“天公作美”,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而且雨还不能太大,恐冲毁庄稼;风也不能太小,太小又推不动云雨。还得及时。当然,太阳是万事万物的第一营养。地,也要肥瘦适宜,水土保持良好,通风透气,抓住季节,适合什么种什么。二者俱备后,经过人们辛勤的选种、犁田、耙地、播种、施肥、除虫、田管、收割、打场等环节,在漫长的几个月后,除去鸟啄鼠伤抛撤,和缴足国家的、 (公粮)留足集体的, (村社提留)最后才能成为农人一年辛勤劳作后分到各家手中的粮食。
黄灿灿的麦子收回家, 还要经过风干、晾晒、保管和推碾,一般年景下,表面的那一层,阳光一样的肌肤要先交给猪和鸡,里面白白胖胖、 银光闪闪的那部分才属于人。那可是天下最好的东西——那个纯正的白啊,透着古道热肠,见着世道人心,白的晃眼,白的晶莹,白得透彻!如果遇上灾年减产,这鸡和猪吃的就只有先免了,那仅有的、白胖的就只能留给孕妇、月母子、小孩和老人。 至于年轻人嘛, 瓜瓜菜菜, 汤汤水水,加上点麦肤和粗糠啥的都行。
记得一个秋末, 和妇女们一起种小麦,累了歇气,自然少不了女人们“咬舌根”。后来才知道,与我彼邻的马婶,年轻时也是川北 “z”县城一个挺上眼的 “大美女”,她是和队里的刘君大叔结婚后才来的这里,一晃多年过去了,她就像地里那株最耀眼夺目的麦苗,在这扎根了,生长了,开花了,结果了, 把自己一生都都交给了这寂寞的大山里。
自古“z”城出美女。她们给人的第一映象就是:个儿高挑,腰身细软,皮肤胜雪,声音如莺,而且个个都能干。那时,县城的南街有个姓马的老头,老婆死得早,他一人又当娘又当爹,常年雇了个小工,开家茶馆和小食店,这在解放前虽说不上富贵,可保管一家人吃穿还是没问题。 马家膝下有三女,就好比是三朵刚打春的桃花,一个更比一个美。老父爱女如珍宝,夏天怕化了,冬天要捂热, 特别是排名老幺的马三妹, 还上了“女子初中”,这在当时嘛,可也称得上是个“大学姐”。那天,避开父亲那道颇不高兴而来的目光,只有十四五岁的三妹硬要在学校表演走 “时装秀”。夜晚,台上的灯光通明,三妹高跟鞋作道具, 旗袍上身, 腰肢轻摆,莲步挪移,曲线曼妙,把少女那热情、大方、温柔、典雅、可爱、清丽的性情与气质演绎得琳漓尽致,着实把台下的的人美翻了、看傻了, 在县城还掀起了场不小的 “民国风”呢!
到解放时, 马三妹巳到了 “谈婚论嫁”年龄,上门说亲的不断,可任凭媒婆怎样巧嘴如簧,她就是不乐意。记不得什么时间了,也说不清是哪个又“撮合”,她和县城一个中学教师叫刘君的认识了。刘君虽不是 “高大帅”,倒也一表堂堂、干净精神。在月白风清之夜,泥暖水美,蛙声呱呱,莹光闪烁,一对青年男女就这样在弥江河边相会,一个吹着竹笛,一个唱着情歌,情真意切,友谊俱增。
可 “天有不测风云”, “土改”划成份,马家被定为“资本家”,除了留点自住房,其余财产被 “充公”,门庭日益冷落。那些年,资本家的女儿哪敢碰?沾上都要倒血霉!两个大女匆忙嫁到大西北,屋里就只剩下父女孤单两个人。而刘君在五七年 “整风反右”中成了“右派”,开除工作,回乡务农。马三妹也因上街为父亲买桑果泡酒,用报纸作包装而污染了 “红太阳”被 “街混混”沿街追打骚扰。那时,三妹已有二十五六岁,于是不顾父亲反对,一气冲到乡下,两人在麦地里述委屈、道衷肠、互安慰,最后竟钻进了刘家的红花被。
马三妹真的很特别:在嫁给刘君的第二天, 她就脱掉锦锻旗袍, 穿上了篮布简衫。初来乍到,连走山路都要学,看到猪牛粪捂鼻子, 可不出几年, 她就成功 “转型” 了,地里、家里的活全都会。还学会了绣花、打毛线、做衣裳;人们常说,女人生育是闯 “鬼门关”,可一到临盆分娩,她从不喊疼,牙齿“咯咯”咬得紧;三更炕头,她献身至爱;五更鸡头, 又劝喻男人;男人 “长洋”, 他是他,她还是她;当家的落魄, 她又和他共担承;三妹一直爱清洁, 前几年, 还带着几个女子,去响水崖洗过月光浴!虽然农活累死人,常把人搞得灰头土脑、筋疲力尽,可山里的人从来不失眠,一觉醒来,稍加梳洗,马三妹仍像麦地上那道绚丽的彩虹,清新可爱,光彩照人;要是冬天去赶场,贴身花袄一穿,三步两步走开,也如莲荷浮动,杨柳随风,仍不失为街头场尾的一道靓丽风景。
“牵了姑娘手,就要一起走”。大山深处,一个是清风满袖落难的“右派”,一个是城里来的“大小姐”,尽管生活再苦,他们都十分恩爱,荆衣布衩,粗茶淡饭,把盏黄昏,吟诗唱合。农活之余,书是刘君的世界,她就是他的颜如玉。
“山高皇帝远”。尽管那些年, “阶级斗争天天讲”, 可大山里的人对马三妹夫妇也没怎样。有次竟把公社书记鼻子气歪了,连说:“你们哪里阶级斗争就没有 ‘新动向’?对 ‘右派’ ‘资本家子女’ 要看紧哦!” …..“书记指示”传下来,可不知咋的,大家能敷衍的就敷衍,能对付的就对付,该吃吃,该喝喝,该干活干活,就当蚊子挠脑壳!
火一样性格,海一样宽容。大山里的人就这样:有劲你就尽力使,有泪你就尽情流,有话你就尽快说!
说到马三妹,虽然有时脾气怪,可队里上下几百号,还没有人不喜欢她。年轻女子围着她,心里有话给她说,就是耍个男明友,要找她参谋;买什么丝线,挑什么花边,穿什么衣服, 该怎样打扮, 要向她讨教; “小两口”打架找上门,她也先给来个 “一顿吼”,然后劝道:“男人是屋头大梁,女人是家里基石,大梁只有扎根基石,才能顶天立地;基石支撑着大梁,才能坚固有力。”…..经她口干舌燥一席话,男人像皮球泄了气,女人也丢掉了农药瓶,你推我攘、挨挨掐掐回家去;同龄男人围着她,按照其它娘们的话讲:“当然娃儿是自巳的亲,老婆是人家的好,家花没有野花香”罗!老人小孩喜欢她,就是刘叔的板胡一明亮, 她就为你来段 “样板戏”……
这大山女人还疯狂。要是哪个男人敢把她们“惹毛”了,只要三妹一喊“上”,几个女人立即扭一砣,你压手,我扯脚,保管把他裤子脱了笼在脑壳上……
当然,岁月不饶人,昔日的马三妹,在我下乡时,也有人开始叫起“马婶”来。
马婶对我特好。风寒署热生病,她帮我煎汤熬药;铺盖床罩洗不了,她又帮忙洗;有时来不及做饭,她又端来茶饭叫你凑合一顿;我砍不了柴坡,还是她和几个女子砍了给我背回来……面对马婶的知寒知冷、 热心帮肋,我真的心存感激,无以回报。可她总是不以为然,轻轻地说:“谁愿我们都命苦,还是从同一个县城而来的”。……“我和你刘叔,一个是 ‘马粪’,一个是 ‘驴蛋’, ‘歪瓜’配‘裂枣’,一辈子也只有这样了,可你们不同,人还年轻,迟早总要回去的”……
到了70 年代初,农村政策稍放松,虽仍是 “学大寨”、 “挣工分”,但允许社员保留少量自留地。这样,有了自留地,社员们自然很振奋。一场雨后,忙着赶着种上瓜果蔬菜和小麦。不久,那地里的小麦呼啦啦地直往上蹿,绿油油、 胖乎乎,着实可爱!这和集体地里那些稀拉拉、蔫搭搭的瘦苗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临近小满,地里的小麦全黄了,永远是黄土地、黄皮肤的颜色,也做好了被收割的准备,麦芒坚挺地刺向空中,麦粒硕大饱满,如同含苞待放的花朵。麦粒与阳光紧密融合,看得人心里眼里一片敞亮。微风吹来,麦浪起伏,如同琴弦奏出 “哗哗”声响,给人以万马奔腾的气势和夜阑听海般的美感。
麦子成熟了,生活就会有起色,马婶笑得好快活。她走地里,驻足观望。在她心里,这块麦田,寄予了她太多的情感、太多的期待。这时,空气微微波动了一下,她仿佛听到了麦粒的笑声,闻到了麦粒的清香,听到了美粒的呼唤。她走到麦地中间随势抓上一把,搓了搓,吹掉麦芒,迫不及待地放到嘴里大嚼,感受它新鲜而成熟的气息。回到家后, 几声小曲哼, 一素布围裙, 立于灶前,做几个农家小菜。清椒炒肉丝,凉拌小豇豆,一盘花生米,一碟泡咸菜,是全家人的最爱。饭做好后,立于檐下,门前张望,只等着干活的男人归来。
那些年,每逢清明、端午、春节,我最爱看马婶蒸馒头。看马婶揉面,是绝美享受。阳光照射屋里,斑驳的光线照在她雪白的脸庞和颈脖上, 自由摆动的双臂更加灵巧动人,一寸一寸地揉,一团一团地揉,一遍一遍地揉,直揉到面团极其均匀而结实,提起来晃动,却十分柔软,完全可以在手指间从容流动。这和面虽累,却可以用美丽和精致来形容。
和面之后是 “醒面” (老面里所用的酵母菌也是她自已养的),熟睡的面团经过四小时发酵,慢慢 “醒”来,变得膨胀活泛。切好馒头后,呈 “一字”排开。要蒸时,毛边大锅烧开水,涂抹油、上馒头、搭纱布、合蒸笼等环节,在马婶手上竟是那样的连贯俐落,一气呵成。半个钟头后,小火,等会再揭笼盖,雪白的馒头顿时朝人发出甜甜的微笑,清香扑鼻,热气腾腾,怒放出一个个最大、最泡、最美的花朵。看在眼里,喜在心上,那时候我以为马婶蒸出的馒头简直就是一件天下最精美的工艺品,是一颗颗放大了的白珍珠。
看着马婶端来的白馒头,我感到无比的舒服。那雪白新鲜的馒头既实在又朴素,透着阵阵暖和劲儿,在那些 “怎么都不对”的日子,像一个大大的拥抱,感到生活还有希望和收获。吃到嘴里,是怎样的软、怎样的柔、怎样的有嚼头、怎样的舍不得吃、怎样的吃不够,怎样的回味、只想用一首好诗来赞美,可任凭怎样挖空心思,可就是写不出,怪只怪牙齿匆忙、舌头灵活、肚肠漉漉。是啊,像马婶这样用新麦、用心血蒸出的馒头用钱买不来,城里人也吃不到,用来敬庙宇、祭祖先、拜灶神,他们也喊安逸。分送给邻里或倒路的乞丐,也充满了温暖和善良。献出一份爱心,收获一份感动。
粉碎“四人帮”,我终于结束了漫长而痛苦的 “知青”生活。我要走了,可马婶和她的乡亲们却要永远留在那。回城拼搏,时光如棱,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但我依然少不了对她们的思念。回想昔日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我, 如今巳成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不禁平添了几分心伤,而远在深山的马婶还好吗?
到了生产队,竟然有人还认出了我。兴奋之余,问起马婶来。他们告诉说,你走后不久, “三中全会” 召开, “地富反坏右”一律摘帽,取消了阶级成份,刘叔也落实了政策, 安排在本地教书。 马婶不愿再回城,巳习惯了农村 “养猪种菜”的生活,还当了几届村队妇女主任, 深受大家尊重。 以后,他们还有了自己的重孙。还是在去年,她们二老都做过了八十岁的大生,是在同一年相继去世的。送殡那天,十里八社的人们赶来,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葬礼。
走进半山处,我看见了麦地里增添了两座新坟。它极像两个大大的馒头,在那里静静地隆起。 它们挨得仍是那样近, 那样亲,像牵手,像拥抱…..相互守望,永不被打扰。坟边,有几树槐花飘落,几只小鸟掠过,碧绿的桑柏和麦苗在微风的作用下,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的泪不禁夺眶而出。
望远处,一片苍茫,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风还在吹,雨还在下,麦子照样生长,可时光呵,永远回不去;人啊,却再也不是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