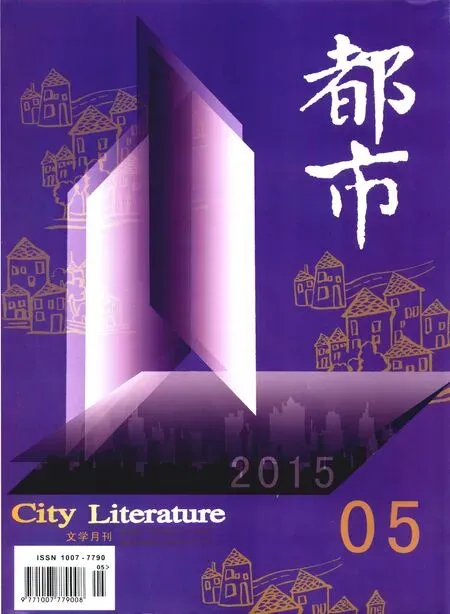凤鸣随笔(三则)
聂尔
凤鸣随笔(三则)
聂尔
我的任务
我从未有信心完成任何一件任务。大的任务,那些事关国计民生或者至少与他人的相关的事情,本来也落不到我的头上。就是小的任务,比如往墙上钉一颗钉子,接待一位不速之客这样的小事情,我也从来不能做得令人满意。
不记得是几岁的时候,父亲命令我划着一根火柴,以点燃一堆年火或别的什么(我记不清了),我的几次尝试都被风扑灭了。父亲瞪了我一眼,从我的手中夺过火柴,亲自点燃了那一堆已在我的记忆中消失的火。此后很长时间,虽然我记牢了顶风划火这样的作业规程,但每逢事到临头,仍然难免失败。
完成特定任务的手段,做某些事情的方法,我心里也是清楚的,但我却无法自如地去运用那些方法以达到目的。甚至,我心中的方法愈是明确而自觉有效,我愈是不能去直接地运用它。对于某人,如果我夸奖他,他会高兴,这我很清楚,我清楚地知道他正在等着我对他的夸奖和恭维,我仿佛看到了他那颗热切的满含着期待的心,但最终我如果没有说出令他不满的话,顶多也就是保持了沉默,这样他就仍然不满。而我对自己说的话是,反正无论如何他也是不会满意的。实际上我完全可以让他满意。
我不仅不能完成别人期待于我的任务,我甚至不能完成我自己想要完成的任务。如果我制订一项工作计划,那就肯定是完不成的。如果没有这个计划,说不定我还能做一些事情。我在心情不错的时候,在兴致勃勃的时候,在窗外春光明媚,屋子里有着甜蜜的安静,一切都有利于我去做满心想做的事情时,反而会浪费掉整个下午,甚至到了令人痛惜的黄昏时分,我都没有丝毫的悔意。我好像不许自己产生出懊悔或类似的情感,因为那样我就必须承认自己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而我打心眼儿里不曾承认过任何事情绝对地与我相关。所以我最常做的事情是放弃,而非承担。每逢我放弃了一项任务和一点可以争取的利益时,我就向自己说,这就是我所放弃的,那是因为我并不真的需要。
是的,我并不真的需要。那我需要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只需要这个世界。但我所需要的世界非常虚无。如果世界是实有的,那我就不需要了。世界上有很多事物,有花,草,树木,山石与河流,以及城市,但如果谁说这就是世界,那我是不会相信的。我不相信具体事物的绝对性,正如我不相信任何特定任务之于我人生的必然性。
我是这样一个人:
我坐在屋子里,但我随时可以走开,尽管我知道没有地方可去;
我在看一本书,我看它是因为我知道随时可以把它合上,然后离开它;
我在下一盘棋,那是因为我知道棋局转瞬就会结束,棋子终将散乱如街道上的过客;
我回忆过往人事,许多人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我知道我可以不写下他们;
我在写一些文字,但我知道我并不指望突然发现文字丛中有一条隐秘的道路;
我的心情忽然忧郁起来了,但我知道没有任何原因。我并且知道,只有忧郁这种情感是没有任何针对性的,因而它呈现为一种广阔的蓝,如同一个终会到达黑夜的晴天一样。
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就像暂时地坐在一个晴天之中。
于是,我知道我没有任务。
我清楚地知道,没有人可以指派我去完成一件任务或扮演一个角色,包括我自己。我的情感,意志,思想和愿望,只是偶尔浮现出来,一当发现它们,我就会像皇帝放逐诤臣一样,将它们流放到看不见的地方,以便我能够耳目清净,不受任何干扰。
爱的话题
那天下午,我和一位朋友坐在那个小广场上。我们两个并排坐在花坛边。以任何外人的目光来看,我和我的朋友肯定是在进行一场谈话。事实上,我们的确在谈话,我们谈到圣经,谈到上帝之爱,谈到耶稣是如何对待税吏(世人眼中恶的化身),而我们是如何看待当今的权势者集团,以及此二者之间的差别。
在我的朋友滔滔不绝地向我宣讲神的旨意时,我则多次向他指出,我们对面的高楼恰好挡住了夕阳(如果有夕阳的话;实际上我们谈话的当时天阴欲雨,根本没有任何夕阳),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在我看来,广场的功能之一是便于人们瞭望远处和天空,如果广场四周被高楼围拢,人在其中只能坐井观天,那与其说是广场还不如说是一个天井。我的信仰基督的朋友对这些具体的问题显然不太关心,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去猜测和景仰神的旨意。
当我的朋友讲到耶稣是如何对待行奸淫的妇人这个我早就耳熟能详的故事时,我屁股后面的手机响起了巴赫音乐的铃声。在路边喧嚣的广场上,巴赫音乐显得如同上帝的旨意一样,微弱,美妙,似有似无,但我还是正好听见了。原来是我的一位正在清华大学进修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要求我为他公司刚刚创办的一份内部报纸写一篇文章。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在遥远的清华大学,在繁忙的学习之余,仍然操持着他公司的事务。他真是我这个懒惰的,没有责任感的人学习的榜样!
我问我信仰基督的朋友,我该写一个什么样的题目?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说,爱,写爱,爱是圣经的灵魂。他的回答让我感觉到惊讶,他回答时的语气,他脸上决绝的,木然的,向着高空仰望的神气也令我惊讶。他是从不写文章的,但他知道应该写什么,我是经常写一写的,我却时常不知道该写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呀!我以写作为生,我曾以此自豪,后来我像大部分此道中人一样落入了“文章只为稻粱谋”的俗套;当我写下一个题目时,我的生活便暂时地以这个题目为中心,为意义,我在写或不写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我是否在爱着这个世界,这些人们,我更没有爱过我所不知道的上帝,或者别的神圣。
在我看来,爱是一个过于古老的话题,简直就是陈词滥调。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的朋友教导我应当写一写爱时,我立刻为之所动,我好像已经能够触摸我的心里突然涌上的爱。可就在这时,我看见广场另一头有一队妇女,她们正随着粗俗的音乐跳集体舞,她们远远地一遍又一遍地跳个不停。在跳舞的妇女们周围坐着,站着和走着一些观看的人。我从远处望着那些跳舞的人们和观看的人们,我意识到了爱的困难。且不说更为遥远的距离,就是从广场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我的爱都无力抵达。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些渺小的人形,他(她)们如何能够成为爱的对象呢?
这样,我最终做到的只是无谓地重提爱的话题。在这个小小的然而却足以造成爱的距离的广场上,在这个天阴欲雨的没有夕阳的下午,我和我的朋友谈到了爱。正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在清华园里游走的朋友打来了电话。因为这些,或者并不因为这些,爱的话题以及它所出现的那个下午,成为未被忘却的,并由我来作出记录。
黄昏
黄昏的天空是最小的,像个倒扣的锅底。
走进一块草坪,伸腿就坐下了。抬起头来,一颗最亮的星就在头顶,伸手可摘。真的要伸手时,发现那颗星并不在正头顶,是在左上方的低处。可能因为没有坐在草坪的正中央,如果坐在正中央,星星就在正头顶。想要挪动一下位置,却起不了身,不是因为懒得动,没有任何原因,只是既已坐在此处,此处就是自己的,别处就不是自己的了。
天空的中央是晴朗的,那种黄昏的晴朗,逐渐变暗的灰蓝色,其中缀有疏星几颗,最亮的就是左上方的那颗;天空中央晴朗,四周却黑云垂挂,仿佛包围着我的四周都在酝酿着阴谋,或者危机。但是,一点也不可怕,它只是一种包围而已,对我的包围,对人的包围,对暗蓝色中央的包围。人无往而不在包围之中,事物也同样。它不是为了更人性,更温暖,或者更恐怖,它只是包围而已。
我再次抬起头来,发现黄昏的天空的确是最小的,像个倒扣的锅底。
黄昏愈来愈是黄昏,所有的景物都在模糊和消失。草地已经看不见了,我只是知道自己坐在草地上,因为屁股底下有柔软的湿润。
我像一个醉汉,跌倒在这里,我以我醉了的朦胧双眼,前所未有地仔细查看这前所未有的黄昏。我发现黄昏有细节。它消泯掉别的事物的细节,让它们只剩下轮廓,当所有事物淡出为轮廓,它们就成为了黄昏的细节。大小之辨,于斯为最。多少之争,在黄昏缄口。黄昏的细节只在明暗之间。黄昏是最为简洁的艺术。宇宙的艺术都是简洁的。只有人的艺术才追求繁复多义。
当黄昏成为锅底,一切都变得低矮。不远处的街灯成了低处的微光,奇怪的是那光还显得不可思议地遥远;近在咫尺的高楼成为疲倦男孩手中的积木,静悄悄地委顿于地;不远处那个学骑摩托车的女孩的惊叫声,比任何一种声音都更像是一种温柔的安慰。
当黄昏成为锅底,我在中央。我们都是黄昏里的游鱼,而此时的我,连游都不游,是一条静止不动的鱼。看不见的草地成为我的池塘,我在其中静止。
责任编辑 高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