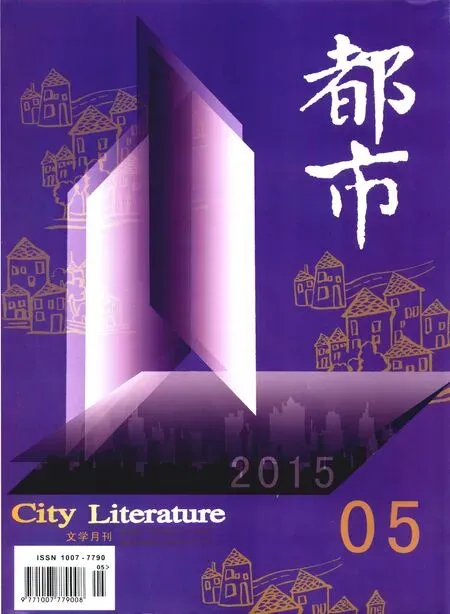流离
王明明
流离
王明明
出走1
走下大巴之前,蔡青就后悔来到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了。从九江过来这一路,他的心情就跟意外死亡前的心电波一样,在穿过鄱阳湖大桥和两个狭长隧道的某一刹,湿冷的湖风拂过他探出车窗的脸颊,左边是山、右边是湖,前面是不规则的崖壁,齐整的柏油路从脚下偷偷溜走,依山傍水的蔡青不经意就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位韩剧里的文艺小青年了,在阳光的照耀下,他骨子里的浪漫开始从每一个毛孔里往外渗,以至于他需要迷上眼睛、深深的吸气,这么源源不断地补充着体内的浪漫,让自己存活更久。后来,这样澎湃的景致被一段土豆地取代,前后左右漫无边际的绿,车子就像漂浮在一块原始森林的头顶,让蔡青无法跟他要去的那个鄱阳湖和长江的交汇口的地方画上等号,水在哪?船在哪?白花花的太阳又在哪?不过,好在有养眼的绿,有整齐划一,让蔡青自己也觉得通体透明,格外干净。
可从大巴进入湖口县城开始,蔡青的脸就越来越长,窗外乌七八糟、垃圾遍地,就连作为一块水边洼地该有的湿润都丝毫寻不到踪迹,车子每前进一米,车尾就会卷起二米远的灰,更别说井然的秩序和富庶的民风了。大巴刚拐进县城的心脏,在距离汽车站一百米的胡同口就不得不停了下来,前方已被横七竖八的杂货摊、菜摊果摊挤满,大巴车根本进不去。蔡青被司机哄下车时,蔡青眉头紧锁,石钟山在哪?你不是说路过石钟山吗?
谁跟你说路过了?司机师傅说,你去那边打个摩的,十五块钱就到。
蔡青顺着司机手指的方向,发现那里竟是个小广场,司机指的正是广场的另一端。蔡青恼羞成怒,几乎骂司机的娘,但气势随即又被司机脸上的横肉给逼仄回去。
噢。
这跟自己居住的那个小县城有什么区别呢?到现在,蔡青才发觉自己纯属是疯了,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是那么好玩的,从一开始就百般不顺,千般无奈。蔡青昨夜下决定出走,今一早从他居住的那个小县城塔上奔南昌的短途火车,他想只要在南昌下了车,不出站台,随便上哪一趟北上的火车,肯定都会到九江吧,毕竟九江也算大站。为此,他在南昌下车后就直接踏上了一趟开往西安的火车,就在他冲上火车,勉强挤到列车补票席准备补票时,列车员却告诉他该车不停九江,下一站就进湖北地界了。蔡青赶紧回头往下挤,好在火车在南昌停车时间还算长,他几乎从车门一下来,列车就开动了,惹得列车员用明显带有陕北口音的普通话给他一顿训斥。
蔡青就在陌生人的一顿训斥中,开始了他的旅行;现在,他又在另一个陌生人的斥责中,走下大巴车,来到了广场对面的摩托车司机跟前,师傅,我要去石钟山。他说。
他坐上了一辆摩的,在那个胡子拉碴的男人身后,想象着他会穿城而过,到郊区,然后走在空旷的旅途中,最终到了那个空无一人的鄱阳湖和长江的交汇口,他要一个人去看看湖水和江水的交融处,他想象着那样一个地方,应该拥有凄凉的江风、绝望的空旷和醉心之美。
直到这个间隙,他才突然思考起自己此次一个人出行的动机,是为了纪念与韩江雪的这一段短暂的爱情,就在两天前,韩江雪对他说,我们都冷静下来好好考虑考虑我们的关系还有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好吗?他点了点头,默认了她委婉提出的分手。可问题是倘若真是那样,他又为什么选择来他的初恋——那个叫苏米的女孩的故乡呢?苏米是九江人,他不记得当年他在大学里和苏米把他的初恋演绎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苏米说过她家是在九江的哪个县了,毕竟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只记得苏米说,她的家就在庐山脚下的一个县城。可真当他到了九江后,才发现挨着庐山的县岂止一个……
NONONO……完全不是这样。蔡青有点乱,他想起他来九江仅仅是一个念头闪过,好像是昨夜做了一个什么梦,然后一早醒来后他就听见自己坐在床头说,去九江吧。
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或许他脑子里一直在思考这个小长假该怎么过,而他能肯定的是他想起那个叫苏米的女孩时,已经是他在九江下了火车之后了。先后关系确实是这样。
蔡青觉得他这一趟出来纯粹是随着心的,随便走走。当然,如果韩江雪此刻正在满世界找他,那他肯定会像打了一场胜仗一样高兴。
摩托车开了很久,身旁的店铺一点点向后退,可蔡青却发现完全没有出城的意思。退到身后的是脏乱和嘈杂,前方迎接他的是新的脏乱以及嘈杂。他隐约感觉在嘈杂中,他腰间的手机震动了几下,他刚要低头掏手机,眼睛的余光中,那辆牌照为‘豫’字打头的车超过了他乘坐的摩托。他一挥手,几乎要喊出来,当他随即意识到车里的人并未看到他时,他只是用羡慕的语调小声嘀咕了一句:这对老夫老妻呦!
手机里有三个未接来电,是雷蒙的。还有两条短信,一条写的是“下午去打球不?”另一条内容如下:还在生哥的气?小心眼!
寻找1
你把崭新的‘翼虎’停在门口,下车时不忘把方向盘前方的半盒中华揣进衬衫口袋。
你走进派出所时,黄昏的雨还在下着。初夏的四五点钟,天已经黑得不成样子。你收了伞,立在案件科的门口,点着烟,来回踱步,皮鞋跟与地面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要不要进去呢?你在门廊雨棚下来回晃着,晃到了一个略显繁忙的门口,门里传来一股连日阴雨导致的霉味,门牌上写着“户籍室”。这时,一声闷雷在头顶响起,你回过神来,还是朝着案件科的门口走去了。
我要报案。你说,你并没让自己的身体完全走进那房间,而是直直地立在了门口。
没人理会你。那个年轻一点的男孩正蹲在地上整理一卷一卷的材料,明显上了年岁的男人端着茶杯等待最后下班的时间。
没听见也好。你想,这或许是上天给出的选择,来之前,你在车里扔了好多次硬币,到底来不来呢?最终你来了。现在命中注定,你不该来。你猛地转身,跟人撞了个满怀。被你撞到的小个子男人手里的一摞东西散了一地,干什么的你?杵在这儿,门神啊?
我——
我什么?小个子男人弯腰捡地上的卷宗一样的东西,发出了与他身高明显不协调的音量,那声音充满底气。
你逃不了了,只好低三下四地迎上前,一支烟顺理成章递了过去,嘴里发出了微弱的声音:我报案。
小个子男人没接你的烟。你以为小个子男人没听见,或者会故意装作没听见一样让你再说一遍。可小个子男人捡完地上的纸,缓缓直起身与你四目相对了,说,下周再来吧?你看大过节的,我们要下班了,这都忙着搬家呢,我们要搬到新址办公了,在梦湖桥那边,周一直接到梦湖桥那去。
可我有急事,报案还能等的?你突然变得很急躁。小个子男人绕开你进了屋,把手里厚厚的卷宗往桌角一放,急事?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看你也不像有什么急事的人!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不是邻里矛盾就是消费纠纷的——
你打断他,我朋友失踪了。
你以为他会跟你一样紧张,可男人还是不慌不忙地说,什么时候的事?
你在等他会拿出本子仔细记录,他却仍在忙着他手里的活,我问你话呢你没听到?
噢,昨天。
他瞪了你一眼,等你说下去。
我今天中午去找他,他不在,我想——应该是昨晚吧。
没超过四十八小时报不了失踪。
可我觉得他遭遇了不测。你说。
你有什么证据?
我——我——感觉。
小个子男人挑起眉毛白了你一眼,刚刚慢下来的手里的动作再次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我真的感觉他遭遇了不测。
你别闹了,小个子男人将你向右轻推了一下,奔着墙角的铁皮柜去了,显然,你挡住了他的路线,这里是公安局,是讲证据的。再者说,他失踪了他的亲人呢?怎么是你来报案?
他是外地的。我是说他一个人住在这里,没亲人。
我没猜错的话,你只是今天没见到你的这位朋友吧。看你这年纪,——他再次上下打量了一下你,你的朋友应该也有三十来岁了吧?他难道不能去找朋友玩?
他没朋友。
那你是什么?
我是他唯一的朋友。
噢,那他或许去旅游了呢。明天就五一小长假了。
你愣在那,回答不出小个子男人的问题。
我给你个建议,你或许可以打电话问问他的——小个子男人第三次打量了你的脸,你这朋友应该没成家吧?
你点了点头。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的父母问问。小个子男人狐疑地看着你,他看到了你脸上真切的焦急,关系这么铁?他露出一丝狡黠的笑。
你愣在那。
我建议你可以趁着小长假出去玩玩,等你回来,说不定你朋友也回来了。
出走2
蔡青到达石钟山景区门口的时候,那对老夫妻正站在门口嘀咕着什么。
老先生见蔡青上了台阶,并无太大热情,像见到同事般顺理成章地说,来了?反倒是蔡青异常惊讶,他惊讶于世界之小,上午在那个叫星子的县城刚刚见过这对夫妻,这会儿又在这里碰见了。
你们也到这里来了?蔡青问。
你这小伙子啊,上午不是和你说了我们下午到湖口,到湖口,肯定要来石钟山嘛!老先生正了正斑白两鬓上的玳瑁色的眼镜,颇有些教育般的口吻说道。
蔡青这时才隐约记起上午跟此二人分别时他确实随口问了他们下一步的行程,当时老先生也确实说了一个地名,只是当时蔡青并未在意。那时蔡青并不知道自己下午会来这里,他是中午从星子返回九江后,买了张九江的旅游地图,随即发现了“石钟山”这一他中学课本里就知道的地名,接着他就跑去问汽车站工作人员石钟山在哪,然后他就来了湖口。况且,旅途上相识的陌生人,彼此的聊天也就是随口一说,又有几个会认真听又当真呢?他们现在相识,用不了多久,又将再次投入自己的那个和他人毫无交集的生活,再次变成陌生人。
被老先生一说,蔡青红了脸不好意思起来。他开始越来越对眼前的这对老夫妻充满了兴趣。
还有半个小时就关门了,我刚问过,咱最好明早再来。老先生说。
有道理。你们住哪?蔡青问。
老先生随手指向低矮的远方,目光顺着景区大门旁的胡同拐进去,在湖边,停着老先生蓝色的房车。
蔡青一拍脑门,再次羞愧起来。
上午在星子县郊的鄱阳湖草洲,他们聊天时,蔡青问过老先生这个问题,当时老先生也是这么个动作,指向了停在河堤下草洲边的这辆蓝色的房车。那是一辆由普通的农用四轮车改装成的房车,“房车”是蔡青赋予它的美好称呼,其实不过就是老两口把锅碗瓢盆和煤气罐都带了出来,还有棉被棉衣及桌椅,他们毫无规则地拥挤在搭了挡雨棚的车大厢里,跑在路上,倘若是有风的天,雨棚绝对会一路哆哆嗦嗦着。
上午在鄱湖草洲时,风就挺大。风吹拂在灰蒙蒙的天地间,有浓重的雾气。在雾气中,蔡青隐约辨认着远处老两口的房车,忍俊不禁。这拉风的车子着实和老先生的身份不太搭。
老先生虽然把自己打扮得还真挺像个时髦的旅游,运动鞋、紧裤脚的宽松休闲裤、速干衣、鸭舌帽,但他白净略显松弛的脸以及他复古、文气的眼镜,将他文质彬彬的气质暴露无遗,显然,倘若现在有身西装换上去,要比他现在这身强了百倍,他就像个拿着报纸喝着茶水的领导。相反,老妇人的装扮和气质就显得粗鄙了一些,她个头直到老先生的腋下,微胖,衣着也没那么讲究,但脸部的表情透露给蔡青的信息是,她更像一个干粗活出身的农家妇女,皮肤黝黑透着硬气。就连那根拐杖握在她手里都丝毫没了拐杖该有的意义,更像她用来探路或者对付坏人的。蔡青实在想不通她拿个拐杖做什么,又没爬山,况且,即便爬山,她也明显用不着似的。老妇人应该有着极其平易近人的口才才对,可她却不大爱说话,老先生和蔡青聊天的时候,她只是一个人默默地望着远方。
那时,他们沿着高高架起的湖堤走下来,面对着一望无际的草洲。草洲依偎在县城的怀里,因为有了草洲这苍茫的美景,附近的设施,不论是湖堤公路、还是湖堤下来的廊道和沿洲公园、健身实施等都建设得格外雅致,有特色。鄱阳湖在这一块沉潜,干涸,裸露出数万顷的湖底高草,俯瞰下去,既有蒙古草原的阔达又有江南的温润,那些密集高草像人工培育的一般整齐划一。人们利用了草洲,在偶尔被湖草抛弃的更低矮处的雨水洼里养起鱼虾,自然就少不了农人忙碌的身影,还有小舟,有盘旋在草洲上空的水鸟,它们就像点缀在宣纸上的墨点,点出了诗一般的鄱湖草洲。
透过轻雾,正北的远方是庐山的南麓,西北则是滚滚长江,游轮嗡嗡叫唤着。
蔡青终于抵挡不住美景的诱惑,像个沉不住气的孩子,让有思考和凄凉相伴的一个人的出行热闹了起来,也俗气起来,他开始站定,背靠着湖堤,让老先生给他拍照。
拍毕,他试图回报老先生,我给您两位也拍一张吧?
嘘!老先生制止了他。
蔡青不知道他在嘘什么,不敢作声。
老先生说,我们下去走走,去那个塔看看,你去不去?
这时,在一爿雾气漂浮过后,蔡青才隐约看清在草洲的正中间,在自己脚下到庐山的中间,目测也有几公里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塔,或者一座庙,蔡青也说不清那是什么。
泥土太湿滑了,挺危险的,我不去了。
老先生笑了笑,带着老妇人下去了。
蔡青看着他们,消失在了茫茫草洲中。
就像现在,蔡青再次看着老先生和老妇人的背影,朝着石钟山旁边的‘房车’里走去。他不知道那辆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整晚,蔡青百无聊赖。他先在石钟山旁边的一个小旅馆开了间房间,那是一个不太干净有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招待所感觉的旅馆,老旧的房子,进门正对着宽绰的楼梯,然后楼梯从两侧折上去到二楼,老板就坐在进门的右手边,像单位的看门大爷一样。
蔡青开了一个单人间,放下身上的挎包后,锁好门,出来找吃饭的去处了。不知道为什么,蔡青突然开始抵触再次碰上那对老夫妻,可在这么小的一个地儿,要不碰上他们实在有点难。蔡青就朝着夫妻二人房车所在地的反方向走。他吃了碗面之后,就开始在那些青春时尚的饰品店里盘旋,像贼在找东西一样。
这时,他开始关注起洗发廊。当然,他早该关注一两间亮着粉色灯光的洗发廊。有那么一刹那,他想两眼一闭直接闯进去,解决掉自己的第一次,可是他总是狠不下心把眼睛闭死,他透过眯着的眼睛看着门里两侧那些白花花的大腿时,心里就一颤,然后又退了回来。雷蒙说的没错,他是个没种的东西,他恨不得抽自己个大嘴巴。
午夜之前,叫蔡青的男人躺在异乡旅馆的床上,不肯睡去。他千方百计地让自己高雅起来,他想自己正睡在石钟山脚下,梦里会不会有古人来找他?他又会不会听到“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或“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南声函胡,北音清越”这样的美乐。可高雅却始终无法光顾他的头颅。他拿起手机看到雷蒙的未接来电已经达到了五个,又增加了几条短信,最后的一条是: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再不回复,我可报警了。
假惺惺!蔡青把手机关掉,这个人真的太假了。他越来越发觉自己和雷蒙怎么就相识、相知成为好朋友了,还是他在他所生活的南方某市里唯一的一个朋友。可当雷蒙得知他和韩江雪相处了两个月就分了手,要命的是,他直到分手都没和韩江雪发生过实质性的行为时,雷蒙竟然发自内心地鄙视他,雷蒙夸张地说,不是吧,你是不是男人啊?这么没种!那你不亏大了,那你两个月都干了什么呢?我以为你们早住在了一起,大哥,现在是什么时代,要讲究效率啊,你这什么能力呢?不可能,你骗我吧,你绝对是在跟我开玩笑。
雷蒙一本正经地说。
蔡青那时已酩酊大醉,可他听到雷蒙嘴里的话时,还是羞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一晚,蔡青仔细回想着跟韩江雪在一起的两个月,偷偷流了些眼泪。分手之前的那一幕再次盘旋在他脑海里。
我不相信爱情。韩江雪说。
那时,韩江雪坐在蔡青的对面,隔着餐桌,甩出这句话。
蔡青发觉哪里不对劲,可还没容他发问。韩江雪两片鲜红的嘴唇立即变成了马达,这是他们认识两个月来她首次滔滔不绝。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韩江雪说,我不懂爱情。你能告诉我爱情是什么?
蔡青刚要接话。韩江雪又说,两个人在一起,什么爱不爱的,归根结底还不就是凑在一起过日子。过日子就是钱的问题,这就是现实。
韩江雪一摆手,拦住了她自认为蔡青要开口说的那句话。继续她的。
我的意思不是没钱日子就过不下去,就得离婚。
天,她竟然冒出来“离婚”这个词,他们难道不刚开始恋爱嘛!
而是,归根结底、追本溯源,婚后的吵吵闹闹都能追溯到钱的问题上。男人不给女人花钱,日子怎么过?男人是干什么的?不就是给女人花钱的。还有,以后两个人在一起得要小孩吧?现在养个孩子有多贵,奶粉钱、尿片钱,好的一套下来,一个月也得两三千。没钱怎么要孩子?穷人根本没资格要孩子。……你说,一个女人嫁人图的是什么?还不就是过好日子,如果嫁了人反倒比没嫁过得惨,那她干嘛嫁人?你想想看,夫妻两个成天为吃什么、为菜价问题,为花钱吵来吵去,迟早感情破裂,感情破裂不就分道扬镳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韩江雪耸了耸肩,停下了,咬了咬吸管,面前那杯鲜红的西瓜汁就少了三分之一。
蔡青心里一紧,像是自己的血被吸了三分之一似的。他愣在那里,有些懵。心想,即将进入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啊!然后,他脑子里不停在晃动着几个数字,他每月一千五的工资,据韩江雪说养孩子每月两千的奶粉和尿片钱,身为月光族的韩江雪每月一千多的衣服钱。……一块石头就压在了蔡青的身上,他盯着韩江雪:一只硕大的蛤蟆镜挡住了她二分之一的脸部,蛤蟆镜有着厚实的塑料框,茶色的,很复古。复古的蛤蟆镜配在女人那张纤瘦、白皙的脸蛋上,矛盾层出不穷。女人是时尚的,蔡青清楚她的美是被胭脂、香水、假发诸如此类包装出的现代美,他觉得现代美的女人不该佩戴这样一幅复古的蛤蟆镜。蔡青在蛤蟆镜里看到了一个小人,进而看到那小人在和女人争吵、然后摔桌子、大叫,最后,小人摔门而去。门就关上了,关在门里的,是茶几上的一纸离婚协议书。他觉得那小人是他自己。
这一晚,蔡青躺在床上,想起和韩江雪在一起的两个月,真是苦了她,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她又干嘛答应和他相处呢?就因为她三十岁了,就因为她家里逼婚吗?
相亲真是不靠谱,尤其对他这么个外地人。
旅馆房间的隔音效果差得惊人,男人用力的声音、女人叫床的声音、床碰墙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会从蔡青的身后传来,一会又从前面传来。蔡情知道,几十元甚至十几元一晚的房价,让这里成了民工常年固定的家,进门的墙上全都是包月住多么多么划算的广告,走廊里晾晒的都是一家家大人小孩的内衣内裤,狼狈不堪。
有一刹那,蔡青想,隔壁住的是不是那对老夫妻呢?随即他又发现自己犯傻,人家是住在房车里呢。大半夜,蔡青难以入睡,时不时开门探出头在走廊里望,偶尔有穿着破内裤端着洗脸盆奔波于房间和洗澡堂之间的男人;有两次,他还看到成群结队穿着脏兮兮挽裤腿带着安全帽的民工从楼梯口吆五喝六地结队走上来。空气里透着浓重的男性荷尔蒙气味,这气味被偶尔飘来的一股股霉气取代。
蔡青和衣躺在床上,不敢盖被。这哪里像个旅游的地方,怪不得发展不起来。可再怎么不起眼,好歹也算是处景致,却完全跟任何一个潮湿的南方乡镇并无二致。
蔡青的身体再度发酵,可他已经困得不行了。他想,明天回到九江,他一定把自己的第一次奉献出去,不能再让任何一个人瞧不起,包括雷蒙。
睡梦中,他听见砰地一声,楼梯里都是人的脚步声。他听到墙外的街道上传来人们的议论声,哪里爆炸了?
是地震吧?
蔡青却一点不想动,他觉得人们太大惊小怪了。地震?震就震吧,让自己死在这,没人知道。
寻找2
在午夜的S酒吧里,女人们身体如蛇,在舞台中央舞动着。韩江雪变成了齐耳短发,一根根头发丝被一片银白冻在了她脑袋上。她身着一身紧身皮衣,随着疯狂的音乐,正跟对面的路人甲配合着身体的律动,路人甲扑过来,她就将身子后仰,相反,路人甲仰下去,她身体又会紧跟着迎合上。
蔡青第一次把韩江雪正式向你介绍的时候,你就发觉她一定是这种女人。后来有一次,你一个人在S酒吧里邂逅韩江雪,当时,她正在和一个大肚腩斗酒,斗得面红耳赤。你竟然有些高兴,因为你看到了她的真实,这就对了嘛,就是该脱掉那张虚假的面妆,这样才显出你的可爱。你当时是这么说的,你难掩的小高兴更在于这验证了你对一个人的判断是何其准确。但是现在,在蔡青消失的第二天,你却厌恶死眼前这个女人的浪荡摸样。你真希望她快点从你眼前消失。
可是你忘了,该消失的是你,你完全可以离开S酒吧。可事实是,你自己主动找来的。你断定韩江雪会在这里灯红酒绿。
太不靠谱了,你必须自己行动起来。第二天一早,你就这么对自己说。
不能再坐以待毙了,一旦那个叫蔡青的小子遭遇了不测,你这辈子都将没办法原谅自己。
不,不是你不能原谅自己的问题。确切地说,你不能少了这个朋友。
在疯狂的音乐声里,你的每一分钟都被无限度地拉长。不知怎么,你满脑子都是蔡青。他像一个恶魔缠着你,使你摆脱不掉。妈的!这个假期过的——啊——你扯开嗓子,狠狠地骂了一句,但是声音立马被湮没在音乐里,没人听到。你独坐吧台,抽了很多烟,想了无数种可能性,还是逃不掉最大的一种可能,蔡青出事了。
你快步上前。够了!一把将韩江雪扯了过来。
她并未惊讶,似乎早等着你的这个动作。得承认,你从进到S酒吧到现在的时间里,一直把自己掩饰得很好,非常好。你不想让任何人,包括韩江雪看到你心里的慌,那种轻而易举让你的成熟男人躯壳露出马脚的慌。担不住事的人,连你自己都瞧不起。
可她像早等在那里一样,让你兵败如山倒。韩江雪说,说吧,什么事。
你勉强支撑着心里的帐篷,让它彻底撑开,显出平静,你和蔡青是不是出了问题?
这和你有关吗?女人说,喝水一样地把桌子上你的半杯扎啤灌了进去。
其实你和蔡青根本就不合适。你说。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你以为你是谁?
女人的躯壳渐渐开裂,明显的征兆是她急了。这是一个谁沉不住气谁就失败的世界。
雷蒙,我告诉你,你别太自以为是了。女人说。
我自以为是?
韩江雪又叫了一扎啤酒。刚要开瓶,你拦住了她。显然,你判定她喝得够多了。
女人很浪,热得不行,解开了上衣扣子,露出了白色的裹胸。
你在找蔡青吗?
你默认。
为什么找他?
女人把你问住了。你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甚至,你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她这么问,倒问得你一肚子狐疑。你想说,他是我朋友,最好的朋友,难道我不该找他。可你看了看女人的眼睛,收住了能让她抓住把柄疯狂反驳你的话。
他跟你说过什么吗?你问。
唔——他说你买了辆新车,嫌他关车门太用力,嫌他鞋底脏。
还有呢?
唔——还说你们和领导一起吃饭,你们聊到一些让他摸不着头脑的同事关系时,他小声问你,你却没搭理他。
还有呢?
你还想听?
想。
他说跟你不是同路人,说你城府很深,说你瞧不上他。
我瞧不上他?
是的。他是这么说的。
我瞧不上他为什么满世界找他?
这得问你。——其实他也想不通。韩江雪说,他说你身边的朋友都是对你有用的人,但是他一点作用也没有。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在一起玩,是你主动地吧?
妈的!啤酒瓶底被你在桌子上敲得丁当响。你没有兴趣再问下去了。韩江雪站起身,再次投入到疯狂的舞曲中。
你在这种疯狂中安静了下来。愤怒持续了一刻钟之后,你也恍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满世界找蔡青。你的生活里,蔡青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外地人蔡青,人际关系几乎为零的蔡青,确乎对你起不到任何实用价值。他的存在似乎就只能让你一味地施舍他?你在这种施舍中找到你虚妄的存在价值吗?不,不是。你立刻否定了自己,你觉得想对现在的你来说,蔡青是简单的,那种简单和固执,那种对自己不管不顾的坚持让你看到了你应该有的样子。你对那样的自己,羡慕不已。
你搀着韩江雪走出S酒吧时,天上薄云翕动、月光暧昧,夜色浓烈得像韩江雪深紫色的唇。你扶她钻进车里,她顺势搂了一把你的衬衫最上面的那颗纽扣,露出你此起彼伏的胸。你呼吸忍不住加重。你知道,今晚,她是得罪你的小兽,也是得罪蔡青的小兽。你要竭尽全力捕获她,摧残她,这想法让你顿时心潮澎湃起来。
出走3
你知道吗小伙子,昨晚地震了?老先生说。
真的地震了?蔡青狐疑。
是的。震感还挺强烈呢,好在镇子上的人和房屋都没事。后半夜可热闹了,他们都跑到码头这块空地来了。
噢。蔡青像有幸逃过了一劫,倘若地震再强烈点,以他昨晚的状态,肯定要死在那个乌七八糟的小旅馆里了。
这会,他和那对老夫妻三人并肩站在码头上,等那只去往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口的游览船。上午十点钟的太阳很白,白得耀眼,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就把石钟山游览了一遍,蔡青有些失望,也就跟任何城市的某个小公园一个档次,唯一不同的不过是它三面环水,走在景区里,更多的感觉像在一个岛上。
可它还是太小了,没几步路,就转了个遍。为了避免和老夫妻俩再度相逢,蔡青故意放慢了游览速度,可他从景区出来来到码头上时,那对老夫妻还是准时等候在那里了。
我们都等了二十分钟了,也没艘船。老夫人说。
这毕竟算不上大景区,位置又这么偏。老先生说。
主要是现在五一假期短了,也没多少人出来玩。蔡青说。蔡青原本不想在这儿耗下去,石钟山着实让他失望,早没了……欣赏的人也没了那种情怀,多数的房屋都是后期休憩的痕迹,景区治理也不整洁,旁边轰隆隆地响着采砂船。
可千里迢迢来了,总得有头有尾。他们现在坐在游船里,就是游览的尾巴,从外围欣赏石钟山。船舱里稀稀拉拉的人,他们干脆把活动椅从舱里搬了出来,摆在船尾,以便更真切地观看这座傍水的小山。
随着轰鸣,船底的巨浪不断向外翻滚着,山上的寺庙、塔、和标志性的松树都看得一清二楚。在蔡青眼中,他们更像是在转圈,围着石钟山转,开始看到的是山的这一面,没一会就变成了另一个侧面,山也随之转了起来。蔡青早分不清了东南西北。
阳光耀眼,蔡青左顾右盼,看看白花花的鄱阳湖大桥,再看看黄澄澄的湖水,自己被一片陌生的虚幻包围着,可这,却是他最真实的生活。
私人船家介绍,他们已经到了鄱阳湖和长江的交汇口,现在他们正坐在这个交汇口上,他们可以有十分钟在这里停滞欣赏的时间。
你怎么一个人出来旅游了?老先生问蔡青。
五一放假,一个人无聊,出来走走。蔡青不假思索地说。
没回家?
提起家,蔡青就有些伤感。自己一个人从遥远的东北来江南读书,然后一个人留在南方工作生活,五一三天假时间哪里够回家的呢?如果早几年,他还在校园里,他或许会约同学一起郊游。可现在,他工作的那家国企,单位同事中除了雷蒙外,都是成了家的人,其中有一半还都濒临退休。他与他们,实在没多少共同语言。
蔡青脸上掩饰不住伤感,老先生却似乎不以为然。
也是。老张,我年轻那时也跟这小伙子一样,那时一个人在开封闯荡。老夫人说。
蔡青有些摸不着头脑,揣摩起老夫人的话以及她的神情后,小声问道,
您二位不是两口子?
老先生笑了笑,你觉得呢?小伙子。
我——
老先生笑得更用力了,婉转地回答蔡青的疑惑,我老伴可不喜欢出来折腾,我们可是沿着青海、四川一路过来的。
第二天再见到两位时,蔡青提高了警惕,聊天时开始专注于对方的任何一句话,甚至表情,无疑,老先生是个认真的人。蔡青不想给他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当然他也担心自己不会说话,说错话,他干脆让疑惑藏在心里,捡他并不真正想知道地问,接下来去哪呢?
去浙江。然后顺着江苏、山东绕到东北去,就是你老家。
蔡青下意识望了望远处码头的位置,那里有他们的房车,可由于距离太远,他现在什么也看不到。
脚下已分不清是湖水还是江水,颜色并未明显变化,只是水流相对之前来比,湍急了许多,但完全看不真切水流的方向。船夫讲解说他左手边是鄱阳湖,右手边是长江,水就是从鄱湖流向长江的。可蔡青看了半天,看不到长江的长条状,也看不明白水流的方向,他只知道他身在其中,他的周围全是水。
回到码头后,老人开始整理行囊,他们即将搭上去浙江的行程,而蔡青要返回九江,他今晚要在九江过夜,次日返程,结束短暂的五一小长假。
他们在码头就此别过,蔡青心头燃起了依依不舍。
出来第二天,蔡青应对各种事情都变得从容不迫起来,买票、打车、找店吃饭、住宿,不再像前一天一样略显紧张和无助,更要命的是伴随着一丝忐忑和孤单,让他很没底,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一样。现在,蔡青就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很久一样。
他在市中心一家不错的连锁旅店住了下来,吃过晚饭后,趁着月色,忍着头皮走进了街旁一家窗帘遮去大半,粉色灯光暧昧丛生的店。
很静!静得全世界只有他叫的那个28号女人每一次手指与蔡青脑门碰撞的声音,女人摸蔡青的脸、脖子、头发。此刻,蔡青断定他的思维与身体出现了长久的分离。他绞尽脑汁地想该如何开口进行下面的事,可是我的身体却如同失去了直觉似的。蔡青知道,除了脸,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没有丝毫反应,包括呼吸。他的意识从最开始的羞赧立刻演变为不要脸了:我是顾客。顾客是上帝!人都已经躺倒这张床上了,再装下去只会把状况弄得愈发尴尬。他思考着,大概十分钟过去了。
女孩问,怎么不说话?
蔡青说,说什么?
女孩哂笑,不会是第一次来吧?
你觉得呢?
女孩说,我不知道。
说“你觉得呢?”这句时,蔡青已经露出了暧昧又淫荡的神色,他开始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嫖客。他瞬间抓住了女人的手:
你们这里还有什么别的服务吗?
先生,你想要什么服务呢?……顿了顿她说,我们这有泡脚、按摩、足疗、洗头……她一本正经地数落着所有她能想起来的服务。
装什么正经!他假装愤怒起来。
屋子里很暗,这会儿越来越暗。28号把被子一扯,反身坐到了蔡青的肩膀旁,她跷着二郎腿,轻车熟路地一摆左手,把掌心迎向我,大方且直白地说了句:
拿钱!我去拿套。
趁28号出去的空当,蔡青铆足了劲去了趟厕所,再回到期待已久的床上时,他却突然空虚起来,预谋已久的兴奋渐渐退去,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他阳痿了。他侧躺在那,背对着脱光了下身的女人,无论怎么用力,思维反倒从这间屋子里飞了出去。他想到了韩江雪,接着又想到了苏米。他觉得他应该想想苏米,这或许能让他兴奋起来。可是人就无济于事。他又想到了那对老人,开始的时候,他很羡慕那对老人,他渴望跟一个女人生米煮成熟饭,成家过日子,一起去旅行,但当他开始怀疑那对老人的关系时,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私奔?驴友?这么想着,他的思想就彻底回不来了。
就这样,蔡青把他的第一次放纵演变成了一次和28号陌生女人的倾诉。他说,你能陪我聊聊天呢?他暗示她,他已付了钱。28号当然愿意,她本已经疲惫不堪,一脸无奈的神色。这会儿,她似乎也轻松起来,把枕头扯回床头,并排和蔡青坐着。
这无疑是个丢人现眼的夜晚,完事后,蔡青一个人沿着长江大堤散步,那种手淫后才有的巨大空虚感清润着他的身体。他不清楚为什么,他这个三十岁的老处男在经历了刚刚那场失败后,竟厌恶起自己,他发誓不再动那些歪脑筋,转而一个人静静地与长江为伴。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雷蒙一定不会知道今晚的事,他已经把自己的第一次交付出去了不是嘛?他完全可以这样想,只有这样,他才信心倍增。
寻找3
你和蔡青再次坐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你几乎叫起来,你他妈去哪了?
蔡青说,我去旅行了。短途行。他有些自嘲地说。
这时,警车在你们身旁停下了。
这一幕,让蔡青摸不着头脑。他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神情紧张。
你知道吗?我都报警了。你说这话的同时,那个小个子男人从警车里走下来。你开始向他介绍,跑了几次派出所之后,你显然和这个年轻的警察渐渐熟络。
找到你朋友了?小个子问你。
找到了。妈的,还真被你说着了,这小子一个人背包去旅行了。
你找我?他问。
是啊。
你为什么找我呢?他问。
你有些尴尬。
小个子警察与你四目相对。
喝酒,喝酒,坐下来一起喝一杯李警官。你招呼着小个子。
我是问你为什么找我呢?有事吗?蔡青问。
唔——没事就不能找你了?你说,找你喝酒啊。
对,找你喝酒。小个子警察附和道。
喝酒,喝酒。
责任编辑 手 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