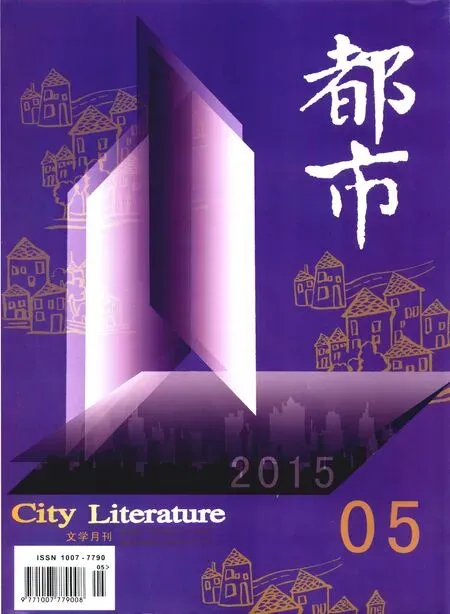揖之所赐
彭图
揖之所赐
彭图
一
柳下镇是座破落的江南小城,城墙年久失修,苔藓侵蚀,藤萝爬绕,城头长满荒草野花,出北门便是富春江,城里人出外多走北门,四门中便只剩了北门还完整如一座城门。
柳下的破落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前明时这里还是一座富庶小城,城中有近万人口,富春江上舳舻相接,驿马道上,车毂相错。南来北往,商旅频繁……。最后却因一户姓朱的人家而惨遭屠城之祸。
朱姓人家本是白际山中一户茶农,种茶积累了家私,便由农兼商,往来于徽浙之间,看到柳下交通方便,风光宜人,便在柳下城中置了一处宅子,作歇脚之用,后来财多人广,倒成了柳下城中大姓。白际朱家与前明皇室虽同属朱姓,却从无来往,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同姓本家。却因一句“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的童谣而累及柳下。当年的杭州将军带兵围剿柳下朱家时,朱家族人因为白际山中种茶祖业不能舍弃,往来两地,并不全在城中,得已保留了一支血脉。然而,柳下受株连之族却并非全为朱姓,屠城清军半为抢夺财产而来,所以城中富户只要能牵连上者,一无幸免。等到皇上明白过来,下旨阻止时,柳下城已经三门残破,万户萧疏了。虽然朝廷都已清楚此朱非彼朱,但那童谣毕竟是皇家心中一块心病。雍正爷登基后,这童谣便又重被提起了。
雍正三年七月的月末,一匹八百里加急驿传快马从驿道上急驰而过,栗色驿马和伏在马背上背着黄袱的驿卒身上甩下一路急雨般的汗滴。
驿马过后,当最后的梅雨洗出一天瓦蓝时,柳下镇的人们惊异地发现,柳下镇从无兵丁把守的北门口,像地底冒出来一样,忽然多出了一个把着红缨大枪的守门老兵。
梅雨过后,炎炎盛夏疯长的绿色中,守门老兵大枪和帽顶上两朵红缨十分的亮眼。这个前胸后背印着烧饼大小“兵”字的守门人,在佝偻着腰,比他更老的看门人一开城门,便准时地出现在城门口,笔直着身子笔直着红缨大枪,头上的帽檐虽然压到眉毛以下,过往行人却常常感觉有两束冷如霜刀的目光射到身上,不由就打个激灵。
城门旁杂草荒漫着,野屎狼藉着的守门房不知什么时候也被清理修葺出来,从此,守门房半墙那方小小窗洞里灯光便常常红到夜深。
这老兵是为着什么来的?这座久被遗忘的江南小城又被朝廷记起了吗?
在镇人茫然的目光中,老兵笔直了身子笔直了红缨大枪,一丝不苟履行他守门人的职责。
“军爷,您老……?”
“您老,军爷……?”
“……”
老兵初来时,有好事的询问者上前搭讪,您老的军爷或这军爷的您老仿佛是个聋子,怎样声音的问话都如春风马耳,自管抬了头看天上云舒云卷,眉毛也没动一下。渐渐地,人们从他面前走过,便都紧闭了双唇,目不斜视了。
自这老兵来后,那些私盐贩子,绺窃毛贼都主动绕道而行,不再从北门出入。镇里的治安忽然安宁了许多。
于是那童谣风一样吹进柳下人的耳中,说是雍正爷又要屠城柳下,为此专调威镇西北,杀人不眨眼的年羹尧为杭州将军,圣喻中说:有你统朕之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年羹尧到杭州后,每天都穿着官服亲自在杭州城门口坐镇,令兵丁查察奸宄。三江口各城都派了心腹兵丁把守城门。有的更说,这老兵就是年羹尧本人,因为上次的屠城,柳下镇便是重点,年羹尧不放心,就亲自来了。不久又传说年羹尧因未查出首恶,被降十八级调用,这才放到柳下来守城门……
这些传言搅得柳下人胆战心惊,风声鹤唳,许多富户都在悄悄收拾细软,随时准备逃离了。
而这些传言却似乎与守门老兵并无关系,他照例从不与人交谈一语,照例笔直了身子笔直了红缨大枪忠实执行着他的守门职责。
不管老兵是不是年羹尧,不管老兵如何地忠于职守,也不管江南小城柳下镇的治安状况如何好了起来,惶惶终日的柳下人却谁也不愿去招惹这个老兵,如果他是年羹尧呢?如果他是年羹尧,谁去招惹他?贩夫走卒、普通百姓是抱着敬畏之情敬而远之,毕竟曾是康雍两朝皇爷的宠臣,朝廷的一等公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达官贵人、乡绅之家是怀着恐惧之心惧而避之,一次次邸报上说得清楚,抚远大将军降为杭州将军,杭州将军又降十八级调用……。眼见得是圣眷不再,大祸就要临头,避之唯恐不及,谁还敢去理他?更何况还有那童谣与屠城之说呢?
渐渐地,那老兵自做他的守门人,自履行他守门人职责,过往行人则都低了头进出城门,自顾自走自己的路。独有一个年轻书生表现得与众不同,这书生无论进出城门,都要遥遥对老兵深深一揖。有时,书生打着伞,见到老兵也要收了伞,揖过才再打开伞走路。
二
书生名叫柳子朱。柳子朱这年三十三岁,三十三岁的柳子朱仍然单身。家穷,父母下世早,虽然考了秀才,有了一领青衿的功名,婚娶的事却一误再误,一年前,兄长去世后,就更无从提起了。他倒也看得开,为避与年轻寡嫂瓜田李下之嫌,他搬出祖宅,住进城外华藏寺读书。华藏寺建在城外半里处的小土山上,下临富春江,于茂林修竹永远的绿色中半露殿宇屋脊,苔痕上阶,钟罄悠扬,精舍俨然,沐浴着寺庙烟火的芳馨读书作文,是柳子朱久已向往的美事了。
每天的中午,柳子朱要回家去和嫂子侄女吃一顿午饭,然后带上晚饭与第二天的早饭,在庙里修习功课。柳子朱能有如此造化,全凭了经商的兄长柳子丹。柳子丹遵照老父嘱托,要将弟弟培养成家族的读书种子,改变门风,进入士绅。从小请了先生教弟弟,弟弟中秀才后,更是不让弟弟参与家务,只要他一心读书,乡试、会试、殿试,一路地上去,金榜题名,金殿对策……。为此专门给他攒了一份经费,去世前一再嘱咐妻子,无论家境再怎么困难,这份钱财都不能挪作他用。兄长走后,嫂子靠纺织与给人缝纫度日,供他一日三餐,自己与女儿省吃俭用,对他却从来有求必应。这使柳子朱常常心不自安。堂堂七尺男儿,岂能久困于笔砚之间,受寡嫂奉养乎?
然而,既走了科举之路,又中了秀才,便只有一条道走下去。兄长病重时,他也曾动过心思,开个馆,教上几个学生,赚些束修以补家用,不料话刚出口,兄长便生气,咳嗽得喘不过气来。嫂子态度亦很坚决,他只好打消了念头,静下心来苦读。心想,好歹下次杭州乡试时,中个举,运气好时,选补个官缺;即使运气不济,给人当幕僚也有了资本。
有了这样的念头后,柳子朱开始留心官场,选择着将来自己入幕的幕主,读书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四书五经,功课之余,诸子百家,刑名钱粮,兵法阵图之类经邦济世的东西逐渐地进入他的阅读范围。
在对幕主的选择上,柳子朱首选的就是年羹尧,年大将军坐镇西北,兼主西南,朝廷给他选官特权,称为“年选”,如果能入了年羹尧之幕,前途自然无量,何必苦苦熬那两榜出身。
主意一定,心胸豁然开朗,读书困了时,便登上华藏寺钟楼远眺,赏富春江水潋滟波光,看富春江上舟来舟往,望越山青吴水碧。脑中便出现即将到来的八月乡试的离别画面:蒙蒙细雨中,江南村镇水天模糊,细雨击打在透着青竹绿意的穹形船舱上,发出沙沙沙丝绸摩擦的声音,披着褐色蓑衣的舟子弓腰解着缆绳,他紧抓舱棚摇摇晃晃站在船头,一只袖子擦了把脸上雨水,向低垂的杨柳岸上,披着紫色油纸衣翠袖掩面的她频频挥手……
这个她自然不会是柳子朱温柔贤惠的嫂子,对于嫂子,柳子朱从未有过丝毫的不敬亵渎念头,那么,她是谁呢?柳子朱自己说不上来,但那画面上却确实总有个她,挥之不去,而且夜间还常常闯入他的梦中。自古才子配佳人,三十三岁的柳子朱是该有个她了。中举后的柳子朱是肯定会有个她的。那时喜报送到家中,锣鼓喧天了柳下镇,打扮得有眉有眼的媒婆们纷纷上门提亲……
正当他做着八月乡试中举的美梦之时,忽然就听到了年羹尧被贬杭州将军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柳子朱心中先是一喜,这不是正瞌睡给了个枕头吗?自己想着入年羹尧的幕府,年羹尧便到杭州了,他来杭州自然少不了用些本地的读书人,求见年将军入幕岂不少了许多盘缠跋涉?不幸得是,几天后便听到了年羹尧降十八级调用的消息。所以当柳子朱第一眼看到北门口那守门的老兵,便认定这就是年羹尧,留心官场已久的柳子朱,自然知道降十八级降到何等地步。亲眼见到不怒自威,英气满身的年羹尧,心中不免一热,不由自主便是深深一揖。事后想起。虽觉荒唐,却又马上给了自己肯定。英雄虽然落魄,但仍然是英雄,看那老兵气度,看那忠于职守,即使不是年大将军也值得我柳子朱一揖。再后来听到雍正爷对年大将军那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呵责,看到世人见那老兵仿佛对了瘟疫的态度,柳子朱便更加坚定了敬拜的决心,那揖也便作得更加虔诚恭敬。
想来寒心呀,年大将军如此功劳,竟遭如此待遇,莫非真是侍奉君王不到头,伴君如伴虎,飞鸟尽,良弓折,兔死狗烹吗?
当又要柳下屠城的传言吹进柳子朱耳朵后,本来就是被迫热衷功名的柳子朱,功名未就忽然就萌生了退隐之心。再次登上钟楼时,他背对了富春江,远眺北面群山,喃喃自语出这样一段莫名其妙的话来:
那些日子,我住在山里,一个挂在半山的小村,高高低低差参着三五十户人家。灰蓝的瓦屋,方井似的四合头院子。四周是青翠的山峰,碧绿的树木。山上的风息了,外出的人回来了,哗啷哗啷的马车串铃声,飘在靛蓝靛蓝高远的天空里。晴空一鹤排云上,云淡风轻近午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是在中举后回乡呢?还是在中举前就回去呢?是要当李太白、陶渊明呢?还是要重拾祖业,默默无闻,在山中聊度日月呢?这实在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
在这种现实与理想前途的纠结中,柳子朱常常对了书本痴痴发呆。细心的嫂子看出了他在抱着满腹心事,这天中午吃饭时,便对他说:叔叔,你是不是身体不适呢?千万别累坏了自己,要不今天放上半天假,到江边转转,今晚就不去寺里了。正好小丹读《千家诗》,遇到些不解的地方,要请教于叔叔……。
嫂子的前半段话,柳子朱基本未进耳朵,但说到侄女小丹,他一下子清醒了。要小丹读书识字,是他的主意,兄长膝下只此一女,十分聪明伶俐,孩子四五岁时,他试着教她识字,没想到一教就会,他便让她背诗,记忆也出奇的好,柳子朱便拿了《千家诗》做她的课本,让她背过了,再一一地认字,初一十五清明端午等节日不去寺里时再给她讲解。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柳子朱却不这样看,虽然人生识字忧患始,但识字总比不识字的好。听到嫂子说到小丹的话遽然醒来,抬头看侄女时,侄女也正期待地盯着自己。忙说,好的,好的。小丹,叔叔晚上教你。
三
午饭后出城门时,一揖作下去,起身正欲走时,感到老兵在盯着他没提食盒的手看,便对老兵笑笑,却看到老兵温和的侄女一样期待的眼神,心里便有些迷糊,这样的眼神会是那威严老兵的吗?他期待着我的会是什么呢?
傍晚,夕阳就要衔山时,柳子朱从华藏寺出来,慢腾腾往城里走,走到老兵面前时,慢腾腾作下揖去,慢腾腾地起身抬头看那老兵时,看到的却是遮了眼睛的帽檐,老兵如平日一样,笔直了身子,笔直了手中的红缨大枪。柳子朱慢腾腾走开,心中的疑虑慢慢消除了。是我将侄女的眼神记得太死,他会有什么期待于我呢?笑话!
晚饭后,柳子朱在院里枇杷树下,与侄女议论着千家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分享那读书的妙处。侄女童稚的问话逗得他笑声不断,几日来胸中的雾霾在笑声中荡然无存。在嫂子柔声的催促中,侄女刚刚离开回屋去睡。院门呀然开处,一老仆模样的人悄然走了进来。那老仆深深一揖下去,悄声说:“先生,我家老爷备了好茶,欲请先生过舍下一叙,不知先生可肯赏脸?”
柳子朱吃了一惊,忙还了一揖说:“你我素昧平生,却不知尊老爷是谁?况此深夜……”
老仆直起身来,熹微月光中,柳子朱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忽然想到了那守门老兵。只听老仆仍压低了声音说:“我家老爷,先生每天都曾见的,先生去了便知。”听到这话,柳子朱明白了,便对着屋里说:“嫂子,有故人相邀,我去去就回,你和小丹先睡吧。不要等我。”
关好街门,跟在老仆身后,穿街过巷,迤逦来到一所宅院前。老仆停下步来,回头弯了腰,作出请的姿势,对柳子朱说:“先生,到了,请进。”
望着眼前颓败的富家高门,柳子朱怔在当地,直到老仆上台阶开了门,再次“请进”时,才讪讪地动了脚步。
一进大门,柳子朱又是一愣,门外颓败依旧,院内却花木扶疏,杂草全无,整齐洁净,透着富贵气息。是谁有如此神力,于人不知鬼不觉中,使这久废之宅焕然变貌呢?柳子朱不由肃然,绷紧了一颗惴惴的心。
进得二门,眼前又是一亮,只见上房大厅檐下两盏硕大灯笼透出猩红的烛光。厅中隔扇新糊窗纸被屋内烛光映得雪白。
走到厅前,老仆却未停步,带柳子朱转进角门,绕过“烟翠三秋色,波涛万古痕”的太湖石假山。假山后八角凉亭上,红烛高烧,石桌上几盘时鲜茶点,一套青瓷茶具,石墩上赫然端坐着的却正是换了便服的守门老兵。
这一下,柳子朱心中洞然,便如城门口一样,在亭外就遥遥地一揖下去。老兵慌忙起身让座。
坐下后,老仆沏了茶,便退去了。老兵端起茶杯,说声“请!”
知道了是谁,柳子朱那绷紧的心反倒坦然了,啜口茶后,正欲张口,老兵却抢在头里说:“想必先生早知我是谁了?”
“不敢,今日方才确实,以前只是揣测。”
“既是揣测,为何礼敬于我?”
“因你忠于职守,与众不同。”
老兵点点头,亲自操壶斟茶后又问:“你每天中午出入城门,可是在华藏寺用功?”
柳子朱摇摇手说:“惭愧,完成父兄遗命而已。”
“此话怎讲?”
“三科未中举,自知才薄力浅。只为今年秋闱一搏。”
“今年中了如何?”
“自然参加会试。”
“会试不中呢?”
“穷家薄依,如能中举足矣!哪敢奢望。”
“看来你对功名并不是很热衷?”
“热衷又能怎样?就比如年大将军……”说到这里,柳子朱自知失言,看眼老兵,涨红着脸将后面的话生生咽了回去。端起茶杯掩饰。
老兵似乎并不介意,微微一笑说:“看来你对年某还是有所了解的?”
柳子朱不敢造次了,字斟句酌说:“了解不敢说,道听途说而已。但我钦敬大将军为人。”
老兵脸上有了喜色,见柳子朱迟疑,便鼓励他说:“你听到些什么,说来听听。”
柳子朱略一踌躇,说:“大将军世宦之家,进士出身却带兵征讨,文武全才。进兵西藏,夜听疾风,便知宿鸟惊飞,痛歼林中偷袭之敌。征青海,预知前途泥泽,命军士各带草束木板,破蕃人所倚之险,直捣蕃巢,尽歼蕃酋。军法极严,一言甫出,部下必奉令唯谨。为两代圣上所倚重,威镇西北……”
老兵正听得入神,柳子朱却戛然而止。便问:“就这些?”
“这个?”柳子朱沉吟着说:“近来传闻,大将军被奸人构陷,一夜连降十八级。在下深为不平。不知可有此事?”
老兵脸上变色,霍然起身,却顺手提起茶壶,续水后,缓缓坐下,慨然长叹。
这一声长叹有如病虎之啸,穿林惊叶,在静夜中听来满溢悲凉。叹过之后,老兵忽然离座,对着柳子朱亦是深深一揖说:“年某夤夜请先生到此,正为此事相求,不知朱兄肯允否?”
听到老兵称他朱兄,柳子朱亦惊亦乍,慌忙站起也深深一揖后说:“大将军言重了,柳某不才,能为大将军效力,自是三生有幸。不过,大将军错了,在下柳子朱。柳下镇的柳,杨柳的柳。并非朱子柳。亦不敢与大将军称兄道弟。”
老兵难得一见地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挥挥手说:“请坐,请坐,先生不必紧张,坐下说话。”
柳子朱复又坐下后,老兵却敛了笑容说:“先生不必过谦,年某已非大将军,如今只是一守门老兵。且灭门之罪,就在旦夕之间。不是危急,也不会贸然请求先生。”
话已至此,柳子朱也不好再辩朱、柳,慨然说:“大将军请讲,只要在下能办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老兵微微一笑说:“赴汤蹈火倒也不必,年某托先生这件事呢,如果办得妥帖,是我送先生一个娇妻,半生富足;如果办得不妥帖呢,可就不光是赴汤蹈火所能尽的,恐怕要赴死灭门呢!”
柳子朱茫然道:“此话怎讲?莫非……?”
老兵眼光灼灼盯着他说:“先生且说。”
“大将军既说赠娇妻,又说灭门,莫非,莫非大将军有侍妾身怀六甲,欲托付在下?”
老兵一拍石桌道:“年某果然没看走眼,正是如此。先生可肯为年某做此牺牲?”
柳子朱淡然道:“大将军如此重托,在下自然国士相报。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在下与大将军素昧平生,不知道大将军为什么能以如此重事相托?”
老兵放松了神经,喟然长叹一声说:“实不相瞒,茫茫人海,年某一是已无可托之人,二是为你那每见一揖,知你是个能以生死相托之人。”
柳子朱肃然站起身来,对着老兵又是一揖,说:“在下谢过大将军知遇之恩。不过,大将军真就为那一揖吗?”
老兵亦肃然站起来还过礼说:“朱先生恕年某无礼。如此重事,当然并非只那一揖。先生的三代根基,年某都查过了。年某不但知道你姓朱不姓柳,还知道你这名字即为柳下之朱。你父兄所以将此名字赐你,且让你弃商从文,就是要在你手上恢复朱家之姓。而且我们今天所在之处,即为你朱家老宅。虽然朝廷已知当年柳下屠城是桩冤案,可你和你兄朱子丹从白际山中重返柳下后,仍然不敢以朱姓示人,只等你取得功名后再图恢复……”
朱子柳身上窜过一股寒意,随即镇定了说:“年大将军果然深谋远虑。”
老兵听出朱子柳讥讽之意,面现愧色,又长叹一声说:“事关年氏血脉存亡,不能不慎。年某出此下策,实属无奈,先生想能理解!”随即在座上握拳致谢。
朱子柳郑重道:“是在下情急失言了。其实听到帝出三江口童谣又起,朱某已经惶惶,近来传说又要屠城。朱某亦正拿着去留主意呢。此时恰逢大将军所托,岂非天意乎?不过,但凭朱某之力……”
“这个且请先生放心,年某已有周密安排。今上为人阴鸷刻毒,他又要置年某于死地,却又要让天下人相信他对年某仁至义尽,不是他要杀年某,而是年某该死。他是费尽心机,深文周纳,一步步逼年某就范。这就给了年某安排后事的运筹空隙。”
朱子柳慨然道:“在下一切听从大将军安排,只是得容我禀过家嫂,安置妥当。朱某生死事小……”
“这个不劳先生费心,年某既求于先生,就当保证先生家人安全与今后生活。”
“愿闻大概,不然在下心总不安。”
“死生大事,事不宜迟,先生既已答允,就请先生与小妾今晚动身。由年福陪你们到白际。路上自然有人保护。”
“然而,家嫂与侄女留在柳下,到底放心不下。还望大将军……”
“尊嫂与侄女自然要与你同回白际山中。只是得迟到几天。你们在前途等着,尊嫂到后,再回山中。那里亦有人安排。先生如今且给尊嫂留书一封,只说童谣事发,屠城在即。不得已连夜离开。让她迅速收拾好后随送书人上路会你……”
老兵既如此说,朱子柳知道只有服从的份了。年羹尧何等之人?有年冬天坐轿出府,正下大雪,随从官员扶轿而行,雪堆手上,指头都快冻掉了。年羹尧心生怜悯,说声“去手!”意思让他们收手,不用扶着轿杆了。随从官员理解为让他们去掉手,竟然都拔出佩刀,各自砍下了自己那只扶轿的手。
朱子柳嘴上不说,内心自然感到屈辱,不过当他看到年羹尧那怀着三个月身孕的五姨太时,屈辱马上烟消云散。脚步从未登过富贵之家的朱子柳,哪见过如此姝丽?而关键是年羹尧已经说了,这小妾从此就是他朱子柳的合法妻子。有如此娇妻陪伴终生,这是做梦也梦不到的美事,还屈辱个鸟?
其实此事已容不得他多想,老兵是霸王硬上弓,明显已早做了周密安排,你允也得允,不允也得允。你今晚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叫六儿的五姨太被年福引到亭子里见朱子柳时,已装束妥当,一件黑斗篷,提个沉重包袱。年福却带来一身富家公子哥儿的袍褂,让柳子朱在侧房里换下自己衣裤。门外车轿亦已安排停当。老兵亲自到北门开了城门,江边埠头上一艘小船等着。朱子柳等三人一上船,船马上就开。
四
七天后,朱子柳在淳安城外山上一座龙王庙里,等来了嫂子与侄女。
嫂子和侄女都穿着重孝,一见朱子柳,立时面如土色,张着口说不出话,半天才哭出声来。
站在旁边的年福淡淡地说:“朱先生,在柳下,柳子朱已经酒后不慎落水,淹死在富春江里了。你嫂子她们迟来,就是因为要料理柳子朱后事才耽搁的。”
这次是朱子柳张开嘴,半天说不上话来。心说,何必如此残忍,虽然事关机密,也用不着杀人殉葬呀?却不知是什么人代我遭此不测?
年福似乎猜到了朱子柳所想,便对嫂子说:“朱夫人,官府已侦知你们隐姓埋名之事。我家老爷为永绝后患,只好从死囚牢里挑了个与朱先生年龄相仿之人,穿了朱先生衣服,毁了面容,以醉酒溺水处理。为免嫌疑,不敢告诉夫人,让朱夫人受惊了。”
嫂子这才缓过神来,对朱子柳说:“真正吓死人了。我说你那送信的朋友为什么一发现尸体就抬来了棺材。三天刚过就要埋,一埋完没等我醒过神来,就催着上路。来了几个帮手,硬把我娘儿们塞进轿里,抬到江边。上船后却是一女仆陪着我们,我只说这下完了,我母女眼见是被卖到妓院了,看那女人,却又不像老鸨。那女仆只说她是淳安杨家的仆人。接我们到杨家的,其余却一概不知。只一路劝我放心。说她家老爷绝对不会亏待我们……”
嫂子还要絮絮说下去,年福却又催着起程了,朱子柳这时才忽然想起,走的那夜,老兵要他换衣还另有这样一层深意。不由对那老兵又生一份敬畏。
到白际山中后,朱子柳才知道所去并非他故居,过了他老家又百十里一个村子才停下来,老兵已让淳安那姓杨的乡绅在这里为他们买下了村中最大的宅院和附近四百亩田产,宅院已整修一新,房中一应器具齐全。朱子柳一个穷秀才一下子成了当地第一富户,从此衣食无忧了。
年富向朱子柳交代了房契地契,留下一沓当地银票后,便离开朱宅,向主人复命去了。临走对朱子柳说:“老爷吩咐,如果六儿生男,便让他姓生,生生不息的生。如生女就随便先生了。老爷如无恙,我便仍旧伺候老爷。老爷如遭不测,我亦难免横祸。一切便全拜托先生了。先生好自为之。”
年富走后,朱子柳立刻自己题字,让人做了块“白际生宅”的门匾挂在大门上。名字也改为生之柳。嫂子悄悄问起他回到白际还为何改姓后,他叹口气说:“为人守财尔!”
朱子柳在白际山中安居下来的第二天。柳下镇人在华藏寺外富春江港湾芦苇丛里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具浸泡得已面目不清的女尸。从那一身重孝和个头大小上,柳下镇人确信那就是刚死不久的柳子朱的嫂子和侄女。好心的柳下镇人将那两具女尸草草埋在了柳子朱的坟旁。
七八天后,柳下镇北门那个笔直了身子笔直了红缨大枪的守门老兵仿佛被初秋的炎阳蒸发,也如来时一般神秘地消失了。
不久,从京城传来消息,说曾任一等公、抚远大将军,杭州将军的年羹尧被赐自尽,一条白绫子结束了跋扈一生的性命。
二十年后,当“白际生家”长男中了安徽第四名举人,回乡娶亲成家,第二年赴京会试回来后,却发现家中只剩了新妇与管家以及男女仆役。生之柳将一应财产都交代了媳妇,自己带着寡嫂与妻子儿女都回百十里外的老家,做他名正言顺的朱子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