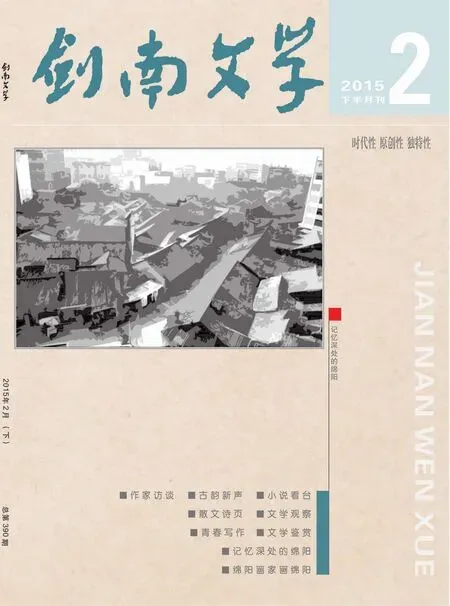文学与生命——作家冯小涓访谈
■孙 婧
题记:访谈那天,我见到了在朴素的外表下蕴藏着浓厚文化气息的作家冯小涓,但确切地说, 认识冯小涓, 是从她的作品开始。阅罢遣卷,我常常思索,在什么意义上,冯小涓的写作是一种生命的写作?我们如何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内部去发现她的独特性?她如何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的新的拓展者?只有当一种文字磨砺着我们的指尖,只有当一种语言砥砺着我们的内心,它才构成一种有生命的语言。在此,人们会发现这种不同的发声经历,会体会涌自心底的文学经验。
孙:作为作家,你写了很多,那么,对于你来说,写作是什么?
冯:对我来说,写作最初是人生历程上留下的心迹,斑斑点点、雪泥鴻爪一样的生命体验。也是外部世界留在内心的投影,是我对世界的观察、感受、追问和思考。随着写作量的增加,我现在觉得,写作就是重建一个世界, 一个带着自己眼光的独特世界。这个世界有外部的影子, 也有自我的影子。这个世界最大的优点是可以治愈外界的伤害,可以躲避时间的风雨,可以在另外的内心引起共鸣,而这个共鸣就是所谓的永生吧?
孙:文学离不开理论的视角,而理论的阐释中也充满文学性,一个作家的写作,多与早年阅读的知识谱系有很大关系,哪些阅读影响了你的创作?
冯:是的,作家大多是书虫,寂寞又美好的阅读时光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我喜欢诗性, 也喜欢神性。 最好的诗, 是神性的诗;而神性,充满了最为圆满的诗意。所以我喜欢阅读有诗意(美学意义上的诗学)的作品,不管是宗教、哲学还是文学书籍。我觉得我的很多思想问题是靠宗教和哲学书籍解决的。我仍然记得八十年代读到卡西尔的 《人论》时的感受,尤其是开篇讲到对人自身的探讨和认识, 启发我对生命意义进行思考。记得当时我才二十多岁,在四月温凉的夜晚,在一棵充满香气的大樟树旁,独自遥望繁星闪烁的星空。 “我对永恒宇宙的巨大沉默感到惶恐。”哲人的话在耳边回响。他的惶恐也是我的惶恐,我的沉默对应着宇宙更广大更深邃更恒久的沉默,星空闪烁着迷一般的幽光。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是多么渺小,又多么短暂,这种无法言说又没有答案的忧伤一直伴随很多年,使我的欢乐显得很稀薄,而忧伤却很浓稠。 文学不能解决我的心理问题,我只能在哲学和宗教书籍中寻求安慰。我喜欢帕斯卡尔、阿奎那、叔本华这样一些有宗教情怀和气质的哲学家,也喜欢禅诗和 《圣经》中的雅歌。2008 年5.12 特大地震以后,我更多地在佛教书籍中寻求安慰。对于文学书籍, 我喜欢阅读有文本意识的作家的作品,卡夫卡、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是我喜欢的四个作家, 尤其喜欢卡夫卡的作品, 因为他们使小说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使小说变得像魔术一样让人惊奇,同时也让阅读小说成为创造性的智力活动。
孙:在散文集《倔犟之眼》、 《幸福的底色》之外,你又创作了中短篇小说集 《在想像中完成》,长篇小说 《我是川军》,如何定义你的文学身份?是小说家还是散文家?
冯:怎样划分我都没意见。我喜欢散文也喜欢小说,还写了一些诗歌。我的文学之路是从诗歌开始的, 后来转向散文和小说。三种文学形式各有千秋,不能替代。我觉得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更博大更宽广,对一个作家的综合要求更高。长篇小说具有叙写复杂世界的优势, 对世界和人性的洞察更深透。散文,剖切生活的场景和断面,比小说更精致、唯美;诗的优势在于,捕捉风云变幻的内心,如捕风捉影,打捞无形,非才思敏捷、心灵丰沛者不能为也!
小说、诗歌、散文三种文学形式,对于我来说,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诗歌如同初恋情人,小说是明媒正娶的大婚,散文算是受宠的小妾。我的野心是,三种形式都要与我白头偕老。相比之下,投入小说的精力更多,特别是长篇小说,还有对小说理论的研究,这是非常耗时的工程。 散文的阅读和写作, 让人非常愉快; 而写诗完全是我的副业。
孙:你的作品,你最喜欢的是哪部?
冯:如同自己的孩子,我的作品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心血,我都喜欢。当写作持续了几十年以后, 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作品,我看到自己的内心伴随着写作活动不断成长。这就是写作的持久魅力,作品是对艰苦劳动者的报偿。对每一个作家而言,审视自己的全部作品会让人忧喜交加,就像农人收获的果实一样,有饱满的也有干瘪的。饱满固然可喜,但干瘪也是生命的一种状态,谁不对沙漠上的一棵草投以敬意呢?即使伟大的作家,也不可能收获的全是饱满果实。但相对而言,饱满的肯定会多一些。像卡夫卡这样对世界和自己充满怀疑的作家,在整理自己的作品时, 一定是用非常严厉的目光,就像父亲投向他的目光一样。所以他要友人烧毁他的全部作品。村上春树在翻译美国作家卡佛作品之后,认为卡佛的短篇小说 “至少有五六篇作品可以成为经典”。 我觉得村上春树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一个伟大的作家也有自己的局限,也只能对世界提供自己的体验、部分的真理和数量有限的经典。记得我曾喜欢国内某小说家和某散文家的作品, 阅读他们的全集后, 都有 “不过如此”的失望感。我是一个普通人,既没有卡夫卡锱铢必较的严格, 也没有村上春树的客观,但我还是会选出自己认为较好的作品。我喜欢自己的一些散文作品,也喜欢小说集 《在想像中完成》, 《我是川军》是目前为止投入精力最大的作品;至于有关地震的报告文学和纪实作品,是我倾注感情最多的作品。
孙:在某种意义上,生命也成了当代文学的一种精神资源,但真正能从文学与生命的关系上把握文学写作可能性的作品并不是很多。你是如何看待关于文学与生命的关系的?
冯:前些年,有学者在惊呼,文学死了。我觉得文学是生命的伴生物,应该伴随生命的始终。没有艺术的人生是有残缺的,没有文学的社会是贫乏的。我无法改变社会,只有坚守自己的信念。
孙: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你对生命有如此彻骨的体验,如此坚守自己的文学信念?
冯:刚参加工作时,我在一家医院普外科工作了五年,亲自送走了很多生命。没有一个人面对临终,是心甘情愿的。生命是一个可怜的存在,也应该是一个有可能寻求意义的存在。所以,宗教、哲学和文学艺术是人类伟大的发明,是对抗短暂和遗忘的精神力量。
孙:从医的那段经历是否帮助你建构了一种体察生命的视角?
冯: 是的, 那个视角深刻地影响了我。从人生的终点来反思生命,有利于我们思考人的一生应该怎样渡过,思考什么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思考人这个可怜而伟大的存在应该如何避免自己的弱小,又如何成就自己的伟大?
孙:生命为文学提供了直观的经验材料,我想这也涉及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面对生命,作家应该做些什么?如何平衡感知与意义之间的关系?
冯:作家关注的就是生命,关注生命过程中的欢乐与忧伤、矛盾与冲突、痛苦与彷徨、 孤独与无助。 作家在创造一个生命时,要像上帝一样充满仁慈和怜悯,因为在这个世间,每一个人都是无依无靠的,不管是高官还是平民、囚犯还是皇帝。孤独不只是一种情绪,而是生命的本质。这一点,是我在人临终的时候看到的,那种深刻的无助穿透了我的心。我体味着他们的无助,也体味着亲人的无助, 更体味着一个医务人员的无奈。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要用自己手中的笔去揭示不平、鞭挞丑恶、发现善良、歌颂美好、呼唤温暖。这就是文学的意义,让人类的精神得到慰藉。
在作品中,意义是能够被感知到的。文学的形象性让读者能够感知。作品中的意义,不是宗教教义一样的宣讲, 而是通过情节、场面、对话、心理展示等方式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感知的。比如小说的情节就是意义的富矿。没有对存在的探讨和发现,这样的小说只能叫故事。没有对意义的探求,写作是肤浅的。文学作品中的意义探求,也不是哲学似的论断;它是开放的、未完成的,蕴藏并需要读者参与创造的,意义永远在读者的创造中不断生成;所以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孙:文学是具有想象力的,它可以创造出人类自身无法驾驭的东西。你的语言自身的辐射力如 《铁皮,在风中悲吟》 《与万物面对》 《肉体.身体.天体》 《天和空》,影现了文学与生命个体存在的细微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文学在未来的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就当下的创作而言,你的作品与以往有哪些不同的变化?
冯:我一直在寻求文学语言的内在含量,希望自己的语言具有多重密度,体现汉语的形象性、模糊性和丰富性特点,既有具体指向更有能指空间。有时候,一个字就是一个坚挺的哨兵。或者像满园的草地上夹杂着无数的鲜花,让人惊奇、耐读。
你说的几篇文章是我的散文作品,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人类生命的大背景中来思考灾难、 人的身体、 人与寰宇的关系的作品。的确是想发现个体生命与外界的细微关联。我希望自己以后再多写一些这类的作品,也许能对生命的发现更细致更独特。
孙:能谈谈《我是川军》的故事吗?
冯: 《我是川军》是在一个真实故事的基础上提炼改写而成的。小说写的是四川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因为 “三丁抽一、五丁抽二” 的征兵条规, 而被迫离开家乡和恋人,投入抗日战场。第一次出川,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体验了战争的残酷。在一次指挥群众撤离时, 被离奇的大水冲散, 离开部队、九死一生才逃回家乡。正当他想着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时,征兵的人抓走了他的大哥。父母觉得大哥傻头傻脑,要他去顶替大哥当兵。这样,他再次离开家乡。他参加了远征军,在抗日战场转战。就在抗战胜利,他满心希望回到家乡的时刻,却被迫投入内战之中。在东北战场,他被解放军俘虏,经过改造,调转枪口打国民党军。就在即将迎来家乡解放、离老家越来越近的时候,他的梦想被抗美援朝的现实击碎。 在朝鲜战场,他在弹尽粮绝负伤昏迷时被俘。在美军战俘营,他与国民党特务进行抗争,但国民党特务在他全身刺上耻辱的反共标语,使他无颜回到故乡,被运到台湾,再次成为国民党军的一员。直到年老退役,他还是孤身一人。台海局势缓和,他才重返大陆探亲,并看望战友的家庭。就在他准备叶落归根回乡定居时,突发疾病去世,最终回来的是一颗思乡的魂。
孙: 你的文字渗透了人文主义的内涵,可我发现,它又与传统意义上的人文有所不同,你作品中的人文主义与传统的人文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冯: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是在人的框架内的批判与书写,而批判精神是 “五四”时期留下的新传统。人文主义的内涵在文学发展中不断丰富。通过这些年的翻译,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哲学、文学书籍都在影响着我们,成为新的人文传统。我喜欢看一些文学以外的书籍,这就丰富了我对世界的理解。我的作品中体现的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思想,而是当代的一些新发现。有一些作品是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通过当下视角的反映。比如 《狗生多艰》这篇作品,是佛家对 “有情众生”的悲悯,与柏格森生命意识的延伸,再利用小说情节展开的一篇新散文。之所以说它新,是它的意识和写作手法都新,为散文增添了新的元素。又如 《鱼和我生命中的四个小时》这篇作品,通过对鱼缸里的鱼的反观自照,突然灵光一现地发现了自己像鱼一样的命运。人与鱼,只有鱼缸的大小之别,呐喊最终变为沉寂。这里的人和鱼,非庄子笔下的人、鱼乐乎之辩;而是人、鱼互参、互证、互照的共同命运。在写法上,也跨越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有的编辑和评论家干脆就把它当做一篇小说。
孙:的确如此,在你的这些散文,如你提到的 《鱼和我生命中的四个小时》 《狗生多艰》,还包括像 《生命的依托》 《相思鸟》《孤单的狗》的等作品,在人之外的其他生命开始作为你思考和表述的对象。 《狗生多艰》所探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消解了传统意义上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思维模式,冲击了文学作品中固有的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念“人文”,这些被加以扩展的生命力量,形成了你作品 “后人文主义”的特色。文学的核心是泛审美,这种泛审美本身追求的就是心灵的超脱和心灵的圆满,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等等一些小说,就是将自然拟人化,将其作为寄托心灵的理想化神灵,而个人也在与自然的接触中获得心灵的历练,达到与自然的共鸣。长期以来,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人与自然二分的问题,你的作品给我们构筑了一种理论的视角,这应该是值得注意的。希望你能带给大家更多值得一读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