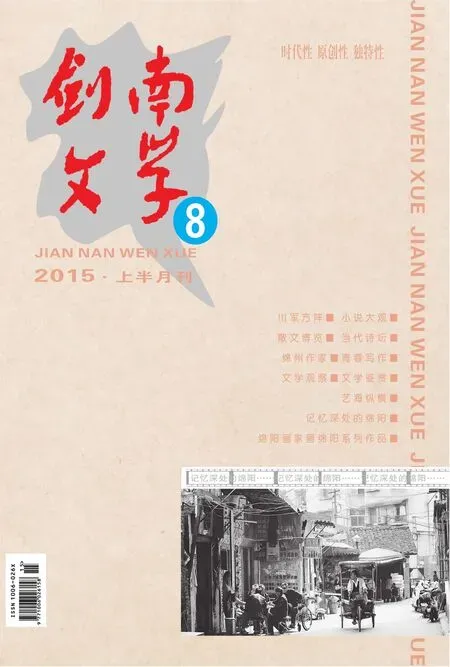沙玛阿普
■英布草心(彝族)
1
天色正走在越来越暗的路上。
沙玛寨下方低矮破陋的瓦板房上空时不时飘溢出互不谦让的吵架声。
你这个不孝子,长到十七岁就可以不听父亲的话了么?我过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哩!
我这不孝子不也是你造出来的?你造出来的不孝子不应该让你心寒么?我还要你的心结冰哩。
那是阿史木牛与阿史古体父子俩在吵架。阿史古体身材矮胖,声音却不矮胖。他厚着脸皮没大没小地与其父阿史木牛唇枪舌战。他们发出的吵架声在沙玛寨两块地之外都可以清晰地听到。
别人养儿我也养儿。别人养的儿是林中虎,我阿史木牛养的儿是家中狗,且还是一条不懂养育之恩的疯狗哩!天的眼睛长到哪里去了?
阿史木牛咆哮了起来。他的咆哮里夹带了苦涩的眼泪,给人一种阴森绝望的感觉。
你这个老不死的,还敢天啊地啊地诅咒我。天的眼睛长到哪里去了?天的眼睛长在我屁股上呢?要不,老不死的,我给你放个屁,也算是天给你唱首歌了!
阿史古体挪动着矮墩墩的身子,用他那双乌黑肮脏的手在阿史木牛面前夸张地比划着。在他的举动里,似乎有种想给阿史木牛一耳光的意向。
你这个不孝子,还想打老子是不是?老子今天不活了!你这个遭虎咬的……
阿史木牛一张烟黑的老脸上跳荡着坚韧不屈与无可奈何的光芒。
你们父子俩还真要开打是不是?当父亲的不像父亲,当儿子的也不像儿子。我看你们像两只被花椒涨了皮囊的癞蛤蟆。
莱莱史喜是个温顺勤劳的女人,她个子不高, 身材也不胖, 但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她为这个家付出得最多, 却一向少言寡语。当然,她也有突然发怒的时候。此刻,她发怒了。她夹在父子俩中间,双臂撑开着,把父子俩推在两边。
反正你们两个老不死的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明后天就坐班车到外面的大城市去打工挣大钱了的!
阿史古体气咻咻地退回火塘边,找了个半尺高的圆形的草垫子自顾自坐着。
你敢走?!你敢走我就打断你的腿!
阿史木牛两片老了的嘴皮子渐渐发乌、颤抖、哆哆嗦嗦起来。
看着你们父子俩这样,我还不如把自己撕了算了!
莱莱史喜一脸猪肝色。她一边吼一边用手使劲撕扯自己的胸襟。
沙玛阿普跟在我后面来了。
阿史木牛家的小儿子阿史古洛九岁半。他像一只小鸟,从半开着的木门外十分灵巧地飞进屋来。
沙玛阿普真来了?
一听说沙玛阿普来了,阿史木牛父子俩便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
沙玛阿普真来了吗?
莱莱史喜抚摸着小儿子两指宽的天菩萨,脸上生出激动。
真来了!
阿史古洛一双眼睛无比黑亮。他扑闪着天真的眼睫毛十分平静地回答。
火塘幽亮幽亮,静静悄悄的。
阿史木牛一家人也静静悄悄的。
他们一家围坐在火塘周围虔诚地等待沙玛阿普的到来。
一袋烟工夫后,一个坚实有力的脚步声在屋子前面深沟般坎坷不平的土路上响起了。
那就是沙玛阿普的脚步声。沙玛阿普人还没进得屋来, 其洪亮铿锵的声音却先进屋:
蒲公英的飘零,不一定是没有家的飘零……
2
阿史木牛一家子正一心一意研究蒲公英飘零的问题时,一个紧张且慌乱的叫喊声突然在屋背后的小林子里响起了。
哪个在喊?
阿史木牛勾着脑袋从狭小的木门里走出去,心里有点不高兴。
阿史大舅,我是木呷惹。
来人是居住在沙玛寨右边的阿尔拉且家的长子木呷惹。
原来是木呷惹呀,快进屋坐!
阿史木牛站在自家的院子中央向屋背后小林子前的木呷惹挥了挥手。
我是来找沙玛阿普的,我家二姐被人拐卖了。
木呷惹站在一块黑黑的大磐石上,一把粗大的天菩萨覆盖着一双扑闪扑闪的黑亮的大眼睛。他的声音颤巍巍的。
青天白日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咋会被拐卖了!
阿史木牛似乎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咋回事,但我家二姐确实两天两夜没有回家了。
木呷惹由于着急,吞吞吐吐的,说了半天,似乎也没说明白他二姐被拐卖的过程。
木呷惹啊,你不要慌张,不要心急!你二姐若真出了什么事,再慌张也没用啊!沙玛阿普在我家坐着哩,我叫他跟着你一起去就是!
阿史木牛给木呷惹说了些安慰的话,便勾着脑袋从狭小的木门进屋子去了。
木呷惹的母亲叫甲拉瓦则, 一年四季,总喜欢穿一身半旧的蓝黑相间的老式服装,中等身材,脸形长瘦,性格固执,且有时蛮不讲理。此刻,她听说自己含辛茹苦养育长大的二女儿被人拐卖了,便不顾左邻右舍苦口婆心地劝慰, “咚啊咚”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撕心裂肺地哭嚎。
傻子坐屋子,响雷掀房顶!我甲拉瓦则恨不得割了自己的肉自己吃了哟!我是林中的布谷鸟,我只会下蛋不会孵蛋哟……
你这个不长心不长眼的死婆娘烂婆娘,连自己的女儿都看不住, 在这里哭给鬼看么?你再哭的话看我不把你活活砍死,让你变成鬼去找你的不争气的二女儿去!
阿尔拉且明亮的太阳穴上两根手指粗的青筋暴突着,两只眼睛睁得圆鼓鼓的,像两个拳头那么大。
别拉我!你们都别拉我!我早就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一个要死了的人,还怕什么丢人?
甲拉瓦则听了阿尔拉且的训骂,变本加厉闹得更凶。 她的两个牙帮子咬得咯咯响,她的两只手交替撕扯自己的衣服。
你个烂婆娘,想死?你要跳崖还是上吊?你真敢死早死十回八回的了!
阿尔拉且从屋子一角捡了把烂了的扫帚高高地举过头顶向甲拉瓦则掷来。
你们不要拉他,让他把我活活打死!我只怕他雷声大雨点小,到头来连我一根毫毛都不敢动!
甲拉瓦则在左邻右舍中间探出个狰狞的面孔。
什么?真想死……
阿尔拉且扒开拉劝他的左邻右舍,再举高一把烂扫帚对准甲拉瓦则的脸狠狠地掷去。只听 “啪”的一声,扫帚落在了一个人的脸上,甲拉瓦则之外的另一个女人尖叫了起来。
你们不好好商量怎样去寻女儿,还有心思在这里干架!你们要干架平时不是多的是时间么?
中间拉劝的左邻右舍们拉下脸来嚷嚷。
你家咋回事?还真应了 “有劝架的就有冒包的”这句俗语,要死要活的你们俩口子闹个毬……
被扫帚打在脸上的,是寨子右边居住的拉巴阿以家的老婆阿支嫫。
我们来错了! 走, 我们干脆都回家去,看他家真能谁把谁打死?!
沙玛阿普来了!
左邻右舍们正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的时候,活泼可爱的木呷惹 “笃笃笃”地从外面跑进院子里来了。
石头长翅膀,如鹰天上飞。
沙玛阿普人没走进院子,神秘莫测的语言却又先撞进屋来。石头怎能长翅膀?石头怎能天上飞?沙玛阿普的谜底,可能与石头有关,也可能与石头无关。
3
彝族创世史诗 《勒俄特依》里面有这样一段远古的记载:恩体古仔家,开九大海子,淹地上人类。大水淹七天,人间万物灭。所罗阿菊山, 只剩狐狸大块地; 惹乎火吉山,只剩麂子大块地;沙玛莫获山,只剩竹林大块地。毋庸置疑,在彝族人民世代生活着的大山深处,沙玛莫获山自古以来就是实实在在的名山。
山青水秀、风光旖旎的沙玛寨就坐落在沙玛莫获山下一块凸出来的 “凸”字形的小山坡上。
沙玛寨子里的房舍也成 “凸”字形分布着。
沙玛寨的下方, 有一条山沟。 山沟里,有一条清清亮亮的叫吕古河的小河。一年四季,吕古河翻着洁白的浪花,唱着节奏缓慢的歌谣向西一直流淌。涉过吕古河去,对面却也是一座山。山叫什么名字,似乎也没有多少人记得了。人们记得的,在吕古河另一边的山的半腰上,有一个寨子,好像叫窝加寨子什么的。沙玛寨子里的人,只要涉过吕古河,爬过窝加寨子,就可以到达山的另一边。在山的另一边,只需走两袋烟工夫的山路,就可以看见一条凹凸不平、蜿蜒曲折的乡村公路;站在这条公路上,只稍等上半袋烟的工夫, 就可以等上一辆去A 市的班车。坐在去A 市的班车上,你尽可以唱一些你喜欢唱的歌,也可以尽情地欣赏车窗外的美丽风景。当然,你晕车或什么都不想看,也可以闭上眼睛静静地思想,养神什么的。到了A 市,有火车有飞机,只要你愿意或条件允许,去北京上海或英国美国都成。
那天,沙玛寨子里居住的阿史木牛家的大儿子阿史古体就是趁着天亮前的夜色涉过吕古河,爬过窝加寨子,走了两袋烟工夫的陡峭山路后,站在凹凸不平、蜿蜒曲折的山区公路上等了半袋烟的工夫,搭上一辆去A市的班车,一边尽情地欣赏着车窗外的美丽风景,一边深情款款地吼着他心爱的 《阿惹妞》走的。
阿史古体的歌声随着车子的颠簸,像颗粒饱满的金黄色豆子般撒了一路:
阿惹妞妞哟,
两个不爱的人不能装,
两个相爱的人情不断。
阿惹妞妞哟,
不想思念呀,
看到山腰上生长的相思树就思念了;
不想牵挂呀,
看到山顶上挺立的冷杉树就牵挂了。
阿惹妞妞哟,
只要可以与你在一起,
树叶当衣穿也暖和的哟,
石子当饭吃也香甜的哟……
在阿史古体深情款款的歌声中,似乎真有个美丽贤惠、善解人意的情妹妹在遥远的地方望穿秋水般等着他。阿史古体一路唱着,不停地唱着。后来,车子内的乘客们屏声息气, 车窗外的风景美丽依旧, 而阿史古体,自己把自己的两只眼睛都唱湿润了。
那一刻,沙玛寨子里阿史古体的父亲阿史木牛却不见天日般昏天黑地地诅咒自己的不孝之子:
神灵啊, 快去看看我家的儿子古体哟!我的那个挨千刀的儿子哟,我的那个遭雷打的儿子哟, 我的那个癞蛤蟆一样丑的儿子哟,我的那个虫豸一样低贱的儿子哟……
在阿史木牛家不远的一条道路边,莱莱史喜正站在一块方形的长满杂草的石包上。她披头散发、两眼血红。
土司恶就百姓逃,婆婆恶就媳妇逃,父亲恶就儿子逃。你这个万恶的阿史木牛,你这个遭鹰叼的阿史木牛,你这个遭竹尖插的阿史木牛,如果儿子回不来,我就一定不放过你!我要让你活着比死了还难受!
阿史木牛一听莱莱史喜的叫骂,心里面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
莱莱史喜啊, 所谓 “蛇崽像蛇嘴尖尖,蛙崽像蛙嘴扁扁”,说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你让儿子跑了,还理直气壮站在寨子中央来与我对骂,看我今晚不好好收拾收拾你!
由于是大清早,沙玛寨子还没有从自己的美丽梦境中清醒过来。
你这种无德无能的男人也配在晚上收拾我?! 晚上我不好好地收拾你就算你前世烧了高香了!
神灵啊,快睁开眼睛看看这种弯曲事实不要脸的女人吧!雷电啊,你咋就不亮出你的快刀劈死这种无德无心的女人呢?
莱莱史喜的辱骂触痛了阿史木牛一直以来隐隐的内伤与无奈, 他无助地咆哮了起来。
你要撕开自己的胸膛?你骗鬼去吧,你!你这个胆小多疑的男人,我早就看透你了!我嫁了你,可真是瞎了我的狗眼!
莱莱史喜如一个疯子般大笑了起来。
你……你这个恶婆娘!你还狗眼呢,你瞎眼还差不多……
静静的沙玛寨子终于苏醒了。
寨下方居住的米什支支站在自家的门框边,一边 “咯咯咯”地唤鸡喂食,一边小声地嘟囔。
大清早的,这一家子又咋个了?
他家呀,除了那个不争气的儿子阿史古体,还会有其他什么事哦!
米什支支家老婆躺在木床上半睡半醒地回答米什支支。
算了算了,没有磨石大的金子,没有耸进天的纠纷!你们俩口子吵来吵去有什么用?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一袋烟工夫后,好心的左邻右舍们来到寨子中间了。
不就是你家古体跑到山外去了吗?没事没事,现在又不是什么旧社会,不可能被人绑票或拐卖什么的。
小孩子不懂事,就像马驹子踩不实。你家古体在外面吃了些苦头后,肯定会回来的。那时候,你们俩就可以借机好好地教训开导他了。
俗话不是说,一个人一颗心,一只蚂蚁一条路,让他走走弯路也好,免得一天到晚与你们闹得不可开交。当他经历过什么是凛冽的寒风,就会珍惜温暖的春风了。
唉,理嘛,还不真是这个理……
天渐渐大亮,跑来劝解和做思想工作的人三三两两地多了起来。在人们的期盼与等待中,沙玛阿普又不负众望地来了。
一根木材水上漂, 要么就停靠在西岸,要么就停靠在东岸……
沙玛阿普站在正在劝解的众人后面提高嗓门呵呵大笑。
——运动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