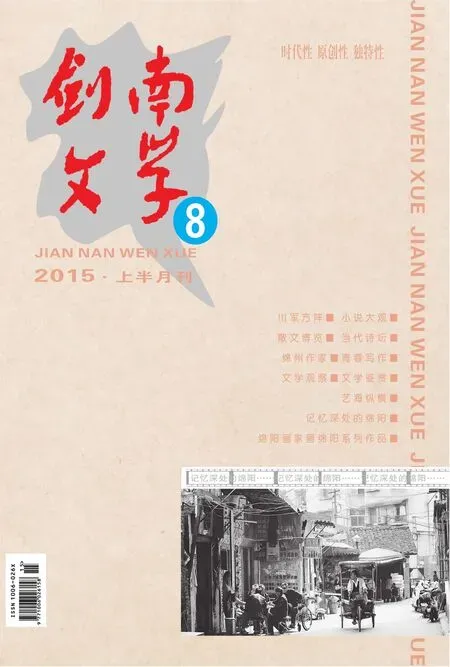乡土之恋,乡魂之泣
——莫言《白狗秋千架》的文学感染力
■陈智秀
乡土之恋,乡魂之泣
——莫言《白狗秋千架》的文学感染力
■陈智秀
莫言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以看似荒诞却合情合理的结局将感染力推向高潮,叙写了主人公暖的悲惨命运。本文从全文线索“白狗”,主要人物暖及其乡土主题等三方面评析该作品感染力的生发、支柱及延续。
《白狗秋千架》是一部写得美、写得实、写得巧的作品。它美,美在字里行间那缓慢流淌而出的娓娓叙述,既有“凉爽温和的东南风让人极舒服,让高粱梢头轻轻摇摆”的清新淡雅又不失“又想还是‘狗道’些”的活泼风趣,它将高密东北乡描画得惬意又安详,将乡村环境涂抹得素美而不浓艳;它实,实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外在刻画与细腻的内心雕琢,力求还原人物本来的真面目;它并不避讳某些俗词俗语的使用,“汗衫很快就湿了,紧贴在肥大下垂的乳房上”,“没结婚是金奶子,结了婚是银奶子,生了孩子是狗奶子”,这些词句恰到好处的出现反而更显作品的真实;它巧,巧在悬念隐现的小说情节,它虽并非一波三折,起伏跌宕,但“狗眼中的暗示”神秘而令人遐想。读罢后,会感到一股股莫名的情愫涌上心头。这种情愫萦绕于心,说不清,又道不明,却予人震撼之感,深沉之思。这便是《白狗秋千架》自身独有的感染力。
一、感染力的生发:狗之眼,狗之情
探寻这股感染力的生发之源,读者会遇见一只“全身皆白、只黑了两只前爪”的白狗。白狗虽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视点,它却成为比“我”更为称职的见证者。作为“我”和暖之外的第三者,白狗亲历了“我们”所共同发生的重要事件,如那段解放军进村,与蔡队长同住的日子,如那场因秋千架断裂而使暖致残的严重事故,还如重逢后“我”的那次探访暖家的经历。在这里,白狗已不是闻声便吠,遇人就咬的癞皮狗,也不是仅会看家守门、供人使唤的奴隶狗,更不是寝食无忧,与人玩耍的宠物狗。“狗眼里的神色遥远荒凉,含有一种模糊的暗示,这遥远荒凉的暗示唤起内心深处一种迷蒙的感受”,它不再作为普通的动物存在于小说中,而是幻化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有着人类情感特征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在“我”刚回到故土的时候“冷冷地瞅了我一眼”,有点恼怒于“我”至今才回来,然后又“激动不安地向来路跑来跑去”,无比兴奋于“我”终究还是回来了;这个“新生命”,在“我”拜访暖家的时候,“最先应了我的喊叫”,“安安稳稳地趴在眼下铺了干草的狗窝里,眯缝着狗眼,象征性地叫着”,仿佛是一个常常见面的老朋友打着不冷不热的招呼,因为它知道“我”一定会来;这个“新生命”,在“我”从暖家出来的时候,“站起来,向高粱地里走,一边走,一边频频回头鸣叫,好像是召唤我”,就像暖的一个知心密友。
这个富有情感,明白事理的白狗,促成了“我”和暖多年以后的再次重逢。它存在于两位主人公童年的回忆里;又存在于两人多年后的重逢中,以“媒人”的身份点燃了两位主人公旧年情愫:“我”刚到县城时便遇见了它,它把暖领到了“我”面前;在“我”即将离开暖家时,它引着“我”来到暖的身边。可以大胆地说,没有白狗,便无所谓故事的发展和结局,它是小说情节发展的独一线索,贯穿作品始终。在这里,“白狗”俨然成为作者创作的萌发点,成为该作品感染力的最初生发之地。
二、感染力的支柱:魂之泣,魂之诉
暖,是小说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她的悲惨命运致使我归乡前情绪起伏,是“我”难以打开的心结。在莫言笔下,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其命运的悲剧构成,是《白狗秋千架》中充满无穷感染力的重要支柱。
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确,在暖这个人物的身上,读者看到了命运之神的冷酷无情,不禁怜悯于,嗓音甜美、极有唱歌天赋的暖,因为家里穷,没有机会接受专业的训练,未能被挑到部队里去的无可奈何;不禁遗憾于,五官健全、相貌较好的暖,在一次与“我”相关的秋千断裂的事故中失去了一只眼睛,成为残疾人的不幸经历;不禁痛心于,“十几年前,她婷婷如一枝花,双目皎皎如星”,令蔡队长喜欢,使我心动的暖,如今却成为“要不是垂着头发,我是不大可能看出她是个女人的”,是一个乳房肥大下垂,拥有三个孩子,成日为养家糊口而过活的贫贱妇女;深切悲痛于,暖下嫁给“亲能把你亲死,揍能把你揍死”的哑巴,生出的三个儿子全长着一双 “土黄色小眼珠”,“脸显得很老相,额上都有抬头纹,下颚骨阔大结实”的小哑巴的悲惨遭遇;十足震撼于,暖不畏世俗眼光,放下女性的自尊乞求与“我”野合,期盼能生一个会说话的孩子的荒诞请求。
“这就是命,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乱想不中用”,生在黄土地上是命,瞎了一只眼睛是命,嫁给哑巴是命,生出三个小哑巴是命,这是暖的思想,可以看出,她是被残酷现实压迫的受害者,更是感慨命运不公的哭诉者。然而,在辽阔的黄土地上,仅有暖这样的一个悲剧发生么?诚然不是。在这悲剧的背后仍有无数个悲剧正在上演。读到小说的结局,读者不会再关注“我”是否真的同意了暖的请求,并与其野合,不再期待有关于“我”与暖野合过程的性的描写,不再追究莫言为何要以设置悬念的方式来处理小说的结尾。强烈的命运悲剧感已震撼了心灵,无穷思绪在脑海中萦绕,仿佛听见了无数的乡魂如怨如泣的哭诉着它们的苦,它们的痛,流淌着血色的眼泪。
三、感染力的延续:乡之恋,乡之怨
“高密东北乡”是莫言一贯创作的基地,其大部分作品都与“高密东北乡”密不可分。如果说,在小说中“穿走牵引”的白狗,是作品感染力的生发之源,那么,作品四处弥漫着的,“我”之于故乡那刻骨铭心的眷恋之情,便是支撑其感染力越生越烈的持续之力。
“我在农村滚了近二十年,自然晓得这高粱叶子是牛马的上等饲料,也知道褪掉晒米时高粱的老叶子,不大影响高粱的产量”,这种情,浮现在“我”望见故乡“高粱叶子”等熟悉事物时,所自然而然生出的段段清晰记忆里;“轻松,满足,是构成幸福的要素,对此,在逝去的岁月里,我是有体会的”,这种情,融入进了“我”对暖如今生活现状而产生的无限感慨中。
社会总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中演进,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而出现。于是,城市里开始崇尚时髦之风,但“故乡的人,却对我的牛仔裤投过鄙夷的目光”,“于是解释:处理货,三块六毛钱一条……,既然便宜,村里的人们也就原谅了我”。当我看见哑巴对与“我”的牛仔裤表现得愤怒的模样;当“我”感觉到和暖的对话无形之中变得艰难。这时,已成为大学教授的“我”,忽然深切感受到自己与曾亲切熟悉的黄土地上人与物间愈行愈远的距离。无独有偶,鲁迅的《故乡》与此有相似之处,在离乡后,鲁迅和“我”同样作为一个接受过正规教育,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回到故乡,那时对于故乡的生活、故乡的人民是如此的热爱和眷恋。然而,当鲁迅遇到麻木的闰土,当“我”因牛仔裤的事情被村民们另眼相待,终于发现了那道坚厚不可穿透的隔膜。至此,乡村与城市,传统化与现代化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所产生的紧张感,在作品中若隐若现。一种“怨”意渐而产生,之于故乡的“恋”情促使着“我”回归故里,这种对故乡的“怨”意却是“我”犹豫是否返乡一探的重要阻碍。
于“我”而言,当从城中返回乡下,感受着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碰撞,这期间趋于现代化的精神思想与之于传统化故乡难以割舍之情的关系,是难以处理的;在自身精神的“离乡”与“回乡”的分岔路间,作者左右徘徊,接受焦灼地现实考验和自省,却是无法果断抉择的。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内心与精神世界里纠缠,这种纠缠通过“我”与暖荒诞的结局显现,作品的感染力由此得以延续,震撼人心。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