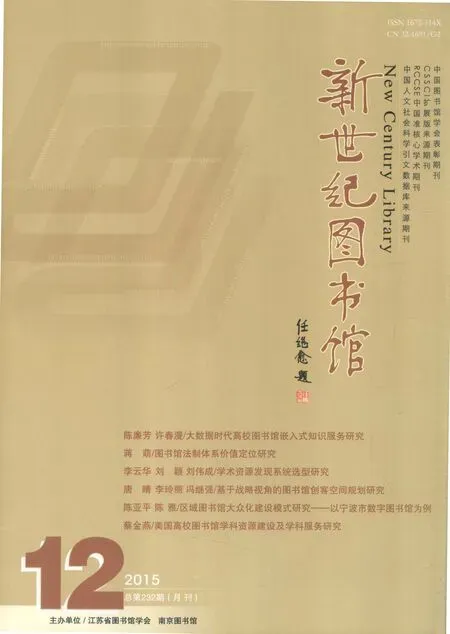方寸之间,东西之别
——从藏书票与藏书印看东西方书籍文化的异同
李晓源
方寸之间,东西之别
——从藏书票与藏书印看东西方书籍文化的异同
李晓源
藏书票与藏书印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作为藏书所有者的标记,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论文从藏书票和藏书印的功能演变,形式特点,使用规范以及产生原因等角度进行阐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西方书籍文化的不同取向与观念上的内在差别。
藏书票藏书印书籍文化藏书家
藏书票与藏书印都因藏书而生,与书籍和藏书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以赏心悦目的艺术造型带给人们一种美的享受,而且所表现的书籍文化也具有深远的人文意象。藏书票缩现了西方的历史文脉与人文情愫,而藏书印则印证了中国文化的特质与精神内核。
1 东西方藏书家的不同选择
同为爱书之人,为何西方的藏书家选择了藏书票而中国的文人墨客选择了藏书印呢?这主要与东、西方书籍的装帧形式有很大关系。西方的洋装书用纸坚硬厚重,表面粗糙滞涩,能够双面书写和印刷,并配以硬壳纸为封面。这种质地的纸不便于盖印章,却非常适合粘贴藏书票,就像在坚硬的墙壁上粘贴一幅精美的图画,既平整而又易于保存。而与之相反,中国的古籍以传统线装为装帧形式,讲究用纸柔、薄、绵、韧,阅读时常卷成轴状,便于把卷吟诵,如果贴上藏书票,既有碍于单手持卷,而且两种不同质地的纸张粘在一起,形态上格格不入,工艺上干戈难调。而印章和中国古籍的用纸与雕版刷印的工艺却是同出一辙,绵软的宣纸与钤下的朱泥呈现出一种工艺渊源上的默契与色彩配比上的鲜明。
2 藏书票、藏书印的功能及其演变
2.1 表示归属权
初始,藏书票和藏书印都是藏书者用以表示对于书籍的所有权。五百年前,德国人给自己的藏书加上一个写有“某某藏书”字样的纸签,以此表明书籍为谁所有,这便是最初的藏书票。藏书票上通常有拉丁语Ex libris,为“予以藏之”之义。1730年德国一家修道院的藏书票上有这样一句话:“我是维森布伦修道院的合法财产。注意!依法把我还给我的主人。”[1]以拟人的手法提醒人们这本书的归属权。无独有偶,在中国唐代,唐太宗曾自书“贞观”二字并命玉工刻成联珠印章[2],加盖在内府藏书之上,以示这些珍稀典籍为皇家藏有。历代文人墨客也会在自己的藏书上钤印姓氏、别号、书斋、堂名等藏书印章以示所有权。因此,有时一本流传久远的古籍善本,辗转易主,上面的印章少则几个,多则数十枚。从这些累累藏印之中便可以得知这本书的递藏序列,了解其潜在的庋藏历史,同时也成为鉴定此书版本源流,考证藏书者生平事迹的一条重要史证线索。
2.2 家族的荣誉与训诫
西方藏书票图案多以家族纹章徽志为主要内
容,是家族荣誉的象征。那时在欧洲人们非常讲究血统,纹章不仅反映了书籍第一代主人的身份,而且使书籍所有权在家族中作为遗产传承给下一代[3]。例如创作于1470年的《天使捧纹章》书票据考证就是勃兰登勃家族的纹章藏书票,台湾藏书票研究家吴兴文称它为“纹章藏书票的鼻祖”[4]237。在欧洲徽章是贵族的标志,有一整套严格的纹章制度,如果不了解纹章学常识,是很难知晓纹章式藏书票其中的含义。比如英国第一位宪政君王乔治五世的藏书票,以一头戴着王冠的狮子和挂着链子的独角兽共同捧着一面勋章的王室纹章为图案。勋章的左上和右下是三只狮,头向右、举起右前足行进,代表英格兰;右上狮以后腿撑地,全身跃立扬起前爪,代表苏格兰;左下是代表爱尔兰的竖琴,整体刚好构成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王国[5]。从这枚典型的纹章藏书票中,人们能够深切感受到英国王室至高无上的权力。以此可见最初的藏书票在社会上还是威信和身份的象征。
而中国的藏书家似乎更注重对子孙的训诫,希望自己收藏的书籍后人能够珍视。既有“传家永保”“子孙勿失”四字款的藏书章,也有字数较多,谆谆教诲子孙的藏书印。明代藏书家“汲古阁”主人毛晋,有一方56个字的大藏书印章,印文为“赵文敏于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卖,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屋,当念斯言,耻非其有,无宁舍旃”[6]10。又如清代藏书家王昶,其藏书印记云:“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极劳勖。愿后人,勤讲肄。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堕。如不材,敢弃置。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述庵传诫。”[7]216还有文字最多的藏书印,即明代王祖嫡录司马光诫子惜书的一段话,共计223字,此印文云:“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公晨夕取阅,……,汝为志之,信阳王氏四部堂识”。在这些藏书印的内容里,既有长辈对晚辈谆谆教导,也有对不屑子孙的谩骂威胁,从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藏书家对后世子孙的苦心与无奈。正如叶德辉先生所说“每叹子孙能知鬻书,犹胜于付之奚媵覆酱瓿褙鞋衬”[7]217。
2.3 个人的精神世界
18世纪之后,随着欧洲教育的普及和出版业的发展,藏书不再只是贵族和教堂的专属特权,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藏书。20世纪初,藏书票从贵族化转向平民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平民请设计家制作和使用藏书票已很普遍。藏书票的内容也开始从纹章型向图画型转变,不再只是家族财富和权势地位的象征,更多反映的是藏书者的兴趣与爱好,藏书票更趋向个性化,也更追求艺术的表现力。从单纯的风景人物、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等图案,到关于表现读书、书房的场景,还有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的画面,题材十分广泛。比如美国著名目录学家乔治·萨根特的藏书票中,不仅有票主平时使用的古书、卷纸和羽毛笔,还有自己家乡的老宅,将记忆中美妙的片段挽留在方寸之间[8]57。还有历史学家克里森将本人晚年的学者形象置于书票之上,背后的地球仪,摆满藏书的书架和桌面上零散的文献参考书,正是他一生“活到老学到老”的真实写照[8]58。至此藏书票和藏书印趋同于表达藏书家个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藏书家多以一些诗文名句作为印文,以此表现自己的志趣。如明代文学家许自昌的藏书印分别有“美人兮天一方”“吟诗一夜东方白”“半亩梅花”[9]。又如清初藏书家萧梦松,有一印曰:“杜门谢客,斋居一室,气味深美,山华野草,微风摇动,以此终日。”[10]何等的超然物外,飘逸洒脱!另有表达治学勤奋的励志藏书印,其文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需学也。非学无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怡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悲叹穷庐,将复何反也。”[11]更有比较极端的表达,如袁克文的“与身俱存亡”藏书印,有一种玉石俱焚的感觉,过于惨烈。倒是雍正皇帝的“为君难”,似更值得回味。
2.4 艺术品
随着人们对藏书票和藏书印的关注越来越多,藏书票和藏书印被抽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19世纪下半叶,藏书票迎来黄金时期,出现了许多艺术珍品,包括丢勒、霍加斯、马奈、毕维克、比亚兹莱、波纳尔、基尔希纳、马蒂斯、高更、科柯施卡、毕加索、埃舍尔、肯特等艺术家都曾参与创作。既有画家一幅幅手绘的作品,也有版画家创作的艺术品。特别是版画藏书票的种类繁多:根据制版工艺,有凸版(木块雕版印刷)、凹版(铜版印刷)、平版(胶印、石印)、漏版(丝网印刷);根据印刷色数,有单色印刷和双色、多色套印。精湛的绘画艺术和巧妙的设计理念使藏书票作为艺术品收藏的风尚开始在欧洲流行。1966年7月28日,由欧洲各国的藏书票爱好者成立了“国际藏书票协会联盟”,简称FISAE[4]238,现已发展到包括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等四十多个国家,会员上万人。尽管藏书票的艺术性越来越强,实用性逐渐衰退,但是与“书籍”“阅读”有关的创作素材仍然是藏书票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
在中国,藏书家对藏书印也十分讲究,经常会请一些制印名家为自己制印。如著名国画家、金石家陈师曾先后为鲁迅刻过“树人所藏”“俟堂”等5方印章[6]10。由于藏书印在印学中与经典文本息息相关,必须严谨周正、端庄雅致,可以发挥的空间有限,所以藏书印不仅要求内容富于深意,而且要求形状精巧别致,尺寸以不超过书籍行格为佳;笔画忌讳毛糙,笔体摒绝率意,整体要求呈现出珠圆玉润的典雅型视觉效果。例如,陈巨来所治的圆朱文印“上海图书馆藏”,笔体线条流畅,古风纯然,坚挺有力,灵动之气充满印面。陈巨来自己为书斋所治的满白文印“更生藤斋”,笔画丰硕,生字上部留红极宽,其余排布均匀,可谓“紧处密不透风,疏处宽可走马”。还有随性印,如宋代贾似道有印文为“悦生”的葫芦形藏书印。另有比较特殊的藏书肖像章,如袁克文有一枚,印面主体是袁氏潜心展读线装书的情景,上部是“皕宋书藏主人廿九岁小景”十一个篆书小字[12]。从宋代开始,许多鉴赏家搜集名家篆刻的精品印章,编印成册,集成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印谱,供大家研究、鉴赏和临摹。其中大量的闲章与肖形印在此就是作为“花押”或“藏书印”而存在的,例如: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养正楼钤印本《孙氏养正楼印存》,其中肖形印占了14枚,古器物形6枚,人物2枚。藏书印艺术性的体现由此从文字向图形转化。
3 藏书票、藏书印的表现形式
尽管藏书者使用藏书票和藏书印的目的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却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而且代表着两种人文气质。
首先,从“社会分工”上来看,藏书票多以图形语言来表达,利用的是版画艺术制作的工艺,多以私人委托专门艺术家为之定制而成。而藏书印多以文字形式来表达,运用的是篆刻艺术手法,虽然也有授意,他人定制的,但更为普遍的是藏书家本人设计制作的藏书印。因为中国的传统文人本身就有着书法家、学者、画家等多重文化身份,反映出近代西方学科的专业化与东方通才教育的差别性。
其次,从“媒介效应”上来讲,文字与绘画也呈现出不同的媒介效应。西方的藏书票所呈现的多为表象的图形语言,是具象的热媒介,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读者仅需要“观看”就会被蕴含的文化感受。与之相比,东方的藏书印所呈现的多为表意的文本语言,是抽象的冷媒介,有较强的参与力和深入感,读者需通过“思考”揣测印中的文化意境。
第三,从“心灵接受史”上来论,对于读者,藏书票的文化门槛较低,无需要有很高的文字、文学、文化修养就能感受其精神面貌;而藏书印的文化门槛较高,需要有很高的文字、文学、文化修养方能领会其精神内核。这是因为图像自身是历史记录中表达方式最直观的,而文字本身是保存文化的工具,其本性是最保守的[13]。
第四,从“符号学”上审视,图像语言为主的藏书票传达的是感性的“模糊信息”;文本语言为主的藏书印传达的是理性的“准确信息”。模糊信息的图像所具备的开放性正好是西方文明的特征,准确信息的文本所具备的闭合性正好是东方文化的特质。
最后,从“修辞学”上分析,虽然都有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的意境,但是西方藏书票的艺术特色是图文并茂、情景交融的,多以具象思维成就表达形式,与西方拉丁语系的表音文字在音画互动中构成修辞上的“蒙太奇效应”;而东方藏书印则多以文字为基础,将文字笔画的线条幻化于万千,构成朱白对比,以文为本,以义取象,展示出抽象形式之美,与东方象形文字在形意互见中构成修辞上的“互文效应”。两种文化基因在共同目的的驱使下构筑出别样的书籍文化景观。
4 藏书票、藏书印的使用
藏书票的规格通常在10~20cm2之间,一般浮贴于书皮或扉页上的右上角或中央。藏书票的尺寸大小与书籍之间的关系是有一定规律的。如果一部尺幅很大的书籍配一幅很小的藏书票,或者藏书票尺寸过大,占满整个扉页,显然都很不合适。藏书票的内容与艺术风格更需要与书籍相配,如果选取恰当,藏书票不仅对书籍起到装饰作用,更似为书籍打开了一扇小小的天窗,开辟出另一个神秘的时空,乐趣无穷。
另一方面,藏书印在书籍上钤印的位置也十分讲究。有钤于扉页著书人名下,或正文初页板框右上方天头处,或目录页下,也有钤于末页左上角或卷终结尾处。此外,在整个钤印过程中,印泥色明朱厚,纸张绵软细腻、技术严谨熟练,三者默契的结合,才能达到印面清晰端正的完美效果。如果藏书印本身明丽规整,位置选盖的恰到好处,不仅展示出书主人对书籍的恭敬之心和自身的文化底蕴,也是对书籍的一种装饰。
5 藏书票、藏书印的象征意义
藏书票和藏书印作为书籍所有者的标记,不仅成为书籍风雅的装饰,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西方文明下不同的书籍文化取向。藏书票的形式图文
并茂、风格多样,有的清新淡雅,有的寓意深刻,有的庄重大方,有的轻巧可爱,通过从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的古典哲学或诗歌中获取画像(例如法国高蹈派诗人及象征主义派诗人在其作品中的插图),或者利用主题双关及组合各种不同元素构成某种文化内涵,从而能够直观地反映书籍文化的内容。藏书票作为外在附着性、浮贴式的文化标记装饰之物,贴用时往往不全部贴死,而只在书票的上方点胶活贴,这种轻便灵活的做法,可以方便日后取下更换或是移用于别的书籍,可以多次使用。一本书籍在不同时段可以更换不同风格的藏书票,但同一时段却只能规约于一枚藏书票,折射出西方文化中开放、外向、直接、崇尚独立和自由的人文精神。
而藏书印是内在嵌入性、印记式的文化标记或铭志之物。虽然一枚印章可以反复钤用,然而一旦钤印之后,印文即与书籍融为一体,成为永久烙印,伴随书籍寿命始终而不容更改。后人收藏也只能在前任主人的藏书印上方空白处,次第盖上自己的印章,这种牢靠稳定的做法,可以让后人依照藏书印的次序,辨识出书籍传承的历史线索。另外,由于中国的文字属于象形文字,除了文字的内涵之外,字体本身也构成一种象征意义。藏书印通过字义与字形“互文”的方式来反映中国藏书家的一种价值观,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印章来铭属一本书籍,这与以不同的汉字字体来规约一种文义的文化现象相似。正如中国文化趋向于“和而不同”——意义相和而符号形态各异。中国文人每次用印都异常严谨审慎,要静读其书卷内容,玩味其印文字义,考究其字体形态,精审其印面大小,讲究其印泥色泽,然后才用印规定位,在重压之下钤留一枚铭文般的朱泥红印,这一系列颇具仪式感的身心状态,不仅对应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戏剧性体验,而且赋予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契约式体证,其中还包含了“一沙一世界,剎那即永恒”的宗教感悟,成为中国文人生活的一种写照,也代表了东方文化的内敛、自省、投入、中和及其含蓄之美。
6 余论
藏书票和藏书印虽然具有不同特点,但是都表达了藏书者对于书籍一份真挚的情感。这就像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虽然有很大差异,但是人们对知识的热爱与追求却是一样的。如果书籍是一座知识的殿堂,西方的藏书票就像是为这座殿堂镶嵌了一扇具有美丽风景的窗户,让爱书者的心灵与书内的风景相通相映;而中国的藏书印却是爱书人在庙堂之上奉入的虔敬贡品。用“礼仪性”融入庙堂,并化为庙堂中的一部分,让藏书者、传承者、爱书者、读书者皆能登堂入室,罗列其中,共瞻文化之盛。既构成薪火相传的烙印,也成为文脉相继的坐标。藏书票反映的是个人与作者的关联,而藏书印则反映出读者群与文本的融汇。基于文本内容,东西方有不同的文字属性,在语素上前者是外向型的发现,后者是内向型的重审。鉴于文脉载体,东西方有不同文人心绪,在语态上前者是游离性的船舶,后者是驻泊性的港口。历于文明进程,东西方有不同的文化使命,在语境上前者是通道式的窗口,后者是渐进式的地标。对此我们不应苛求于古人,反倒应该去理解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成因,只有充分理解东西方文人对待书籍各自的态度,才能更充分发掘书籍文化的魅力,才能更妥帖地服务于当下的阅读生活。
[1]江兆云.藏书票锁语[J].金融时代,2013(03):41-42.
[2]奚椿年.书趣[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93-95.
[3]马丁·霍普金森.藏书票的故事[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12.
[4]李艳萍,贾琨.浅析藏书票艺术的历史及当代发展[J].文艺研究,2012(05):237-238.
[5]吴兴文.我的藏书票之旅[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87.
[6]流云.名人藏书印章[N].江南时报,2009-01-11(10).
[7]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16-217.
[8]子安.藏书票之爱[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57-58.
[9]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674-677.
[10]范景中.藏书铭印记[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56.
[11]献洲.藏书章记趣[EB/OL].[2006-09-04].http://blog. 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594350&Post ID=6658785.
[12]王爱喜.中国传统私家藏书印[J].档案与建设,2002(04):48-49.
[13]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0.
李晓源西北大学图书馆馆员。陕西西安,710127。
Difference of the Book Culture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Ownership Stamp and Ownership Seal
Li Xiaoyuan
Ownership stamp and ownership seal reflect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but they are considered the book ownership of the mark and the same function.This paper introduces evolvement of function,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m, specification,origination of ownership stamp and ownership seal,which from one side reflected the book culture’s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and Westorientation and on the conceptof the inherent differences.
Ownership stamp.Ownership seal.Book culture.Bibliophile.
G256.1
2015-07-01编校:方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