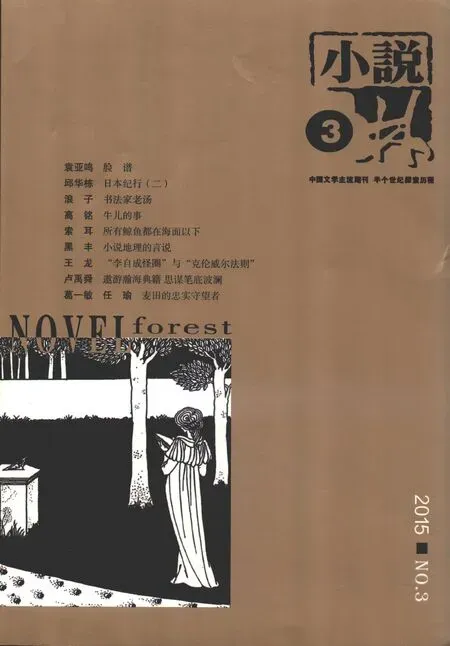黄金的生命
——写在纪念大鼻子离开二周年的日子里
◎袁亚鸣
黄金的生命
——写在纪念大鼻子离开二周年的日子里
◎袁亚鸣
《脸谱》是为大鼻子写的,写创作谈的时候,正好是大鼻子离开我们两周年的日子。
宁静的等待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尊重。对于生意或者自由的意志,都一样。北京时间19:13,黄金报价1199.72,离1200美金,还有一点点。
刚刚打球回来,就是这一点点儿,熬不住的平仓盘蜂拥杀出,陈大头山上的电话下来,我一个也没接到。来电话的时候我可能在扣球,杀得性起,什么球都能煞住。我们私募是全封闭的,四五个老友,几十年期货风雨洗礼后,见风使舵,钱“放”在一起,风险盈利共享。在山上的房子里轮流值班盯盘,这周是大头,下一周轮到我。不痛快一把上去,山上的球能把人闷死。大头在短信里说,平仓盘里百分之七八十是获利盘,他说平仓盘在八点前后简直太吓人了。一下子涌出来,铺天盖地。我见过那种阵势。那种杀出来的力量可以“秒杀”一切生命。震撼、麻木、感人。我想陈大头在那种气氛里还能出手平仓,换掉一半儿筹码,那是得益于多年来我们出入过死亡的门槛。倾家荡产,又瞬间家财万贯。不是从死人堆里爬进爬出,那一刻,吓也得被吓傻。
我坐在灯下,忽然觉得今天换我操盘我是不会抛了的。真的。我反复问自己,真的吗?在技术上我一直是一个激进分子,这种明显的机会我真的会放弃吗?
但这很可能不是真的。我现在这么想,原因是现在我身在局外。局外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宁静,可以没有责任,没有责任反能用最负责任的姿态去畅想、体会。直至体会到自由中最不自由的伪意志。
黄金也是生命。早在私募开始集合前,大鼻子就预言黄金要到1000美金。可惜他早在1400美元的那次大反弹里身败名裂,做空,没有挺过来。他出事后大家说他太贪了。他完全可以加入我们的组合,赚最开心和最友谊的钱。他干吗要到社会上去,做那种地下黄金公司的事呢?还有人说他有野心,等等。总之是不朋友了,或变得不朋友了。
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他一辈子期货人生,到头来还是没有弄懂生意,读懂生命,还有生命自由、微薄却顽强得可以无敌的意志。
二十年前,黄金不满两百美金的时候,大鼻子第一次来到新加坡。我对他说我一辈子会做黄金,他说你是猪,电解铜那么好,黄金那么慢,你做它干嘛?那一年,张百平在新加坡五矿,和他在一起的还有王勇。他们走过澳洲和智利,赚了整整一船铜。我做多黄金,亏得只剩下了最后几千块美金。1992年春节,我在大海里游泳,黄金跌到十七年最低点。一辈子就那一年没有回来过过年,不因为几近倾家荡产,更因为没有了再见江东父老的精神。
但我在海水里一直坚信着,坚信天不灭我。海水一度让我有逃避的念头,但我最后看见了黄金的召唤,选择了年轻时代最重要的那次等待。我相信我的等待,我相信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相知的生命。只要你能感受到,你就能坚守下去。我在海上漂流,任凭海浪把我推向何方。我要感谢大鼻子和老李。他们在那个时候给我的不是鲜花和安慰,而是借钱给我来抄底。整整九十万美金。我想唯有那一刻,大鼻子读懂了我的生命。五月份开始黄金三十个月的反弹,大鼻子和老李的钱让我等到了生命的爆发。我走出困境,获得数倍收益,收得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桶金。
我难忘我在最低谷时大鼻子在智利铜矿上对我说的话,一人头上一方天。他的天是铜,我的天就是黄金。既然是自己的天,就该坚守。既坚守,就该守高峰,也要守谷底。比如人在生病的低谷,就有可能一病不起了,但能不能起来与坚守无关。坚守是一种态度,在困难面前,坚持有时候还是阿Q式的,是一种只属于自己的精神胜利。但是这样的胜利很重要,没有客观标准,就是一种心态。也许在别人看来,那还是一种自己骗自己的儿戏。可是我读懂了大鼻子的话,他却在人生的航途里迷了航。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看到黄金的生命,抑或自己没有读懂自己的时候,就奋不顾身,贸然跳进黄金坑,结果轻易断送了黄金的自己。
他没有看到黄金的生命,也许连铜的生命也没有读到。他看到的是钱,钱的流动。钱的浪花墨黑的,但看上去鲜红。色差是眼睛的缘故,这样的差异或许会让人连钱的生命也无法看到。
大鼻子经抢救后醒过来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受过他帮助,挣到钱的人去找他,他们把花篮从病房走廊里一直摆到了楼梯口。再没人拿他们的钱为他们挣钱了。他们那一刻的焦虑,伤心钱的程度超过了对大鼻子的怜悯。即便在钱的世界里,感受生命其实远远不够。感受仅仅是生命的底线,我们还要在等待中敬重生命。对一个投资来说,我们要等待,等待生命宁静中的爆发。对一个病人来说,他需要的只是安静,而毋需我们期盼他好转的执拗。我们可以盼望病人好转,但请不要说出来。你没有权利喧哗。病房前我想起之前黄金在1400美元附近的反复折磨,它就是一个病人,这个时候大鼻子不买账,他去和黄金战斗,他非要黄金和他一样一起战斗。结果黄金死了,他也死了。而那时候,实际上他要做的仅仅只是等候。假如他真知道尊重自己的话,就该知道尊重生意和生命。要等到今天,他的每分钱都是十倍以上的收益。
说回《脸谱》,双奎不相信等待,他一直在奋进,在有形无形,各色各样的鞭子下毫无所惧,一往无前。双奎是写着诗前进的,但写诗并不意味着懂诗。最后,他被诗歌吞噬在了黑暗里。邪恶的不是黑暗,而是黑暗下的自己。
不懂得小说的生命属于自由,便不懂自己。而不懂得个体不属于大众生命正是那些自己都找不着北的“小说家”最难以摆脱的泥淖,才会有鸡零狗碎的“底层”故事,没有思辨的“现实主义”,消减了文学难度的功利写作。低俗的写作不但贬低文学,还嘲弄着时代和人性和那些说文学死了的人一样玷辱着文学、自由和生命,是一种担当的弃守,是时代的耻辱。当下的文学无疑是病了或被病了,但困局下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宁静的自我姿态。真的一定要为病人做点什么才安心的话,简单和宁静是最实在的。不要去为本来强盛的生命担心什么,更不要让自己的意志伪装成怜悯和祈祷去影响和改变生命,他属于他自己的轨迹。你可以低俗,但请不要冠以文学。你可以“文学”,但请不要说中国文学仅此一种。
我没有走进病房,在大鼻子最后的清醒时刻我离开了他。就像当年大鼻子借给我钱在黄金上翻本时一样。生意如此,我想小说也一样。在这个层面上,大鼻子理应获得值得文学和小说家纪念和敬重的意义。
说话间黄金已经回落了下来,1164.33,可见陈大头又为我们多赚了一把。可见等待也可以是一种行动。大头要不告诉我,就是默默的,可告诉了我,却一样,也是默默的。宁静有分别,等候的溪流才清晰生动地淌过喜怒哀乐,就像指尖跃动的琴键,清新流畅、黑白分明。每一种宁静的区别就在于,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行动,有他对生命的理解,不用我们去喧哗和干预。即便在自己生命的终点,他的生意或小说,一样闪动黄金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