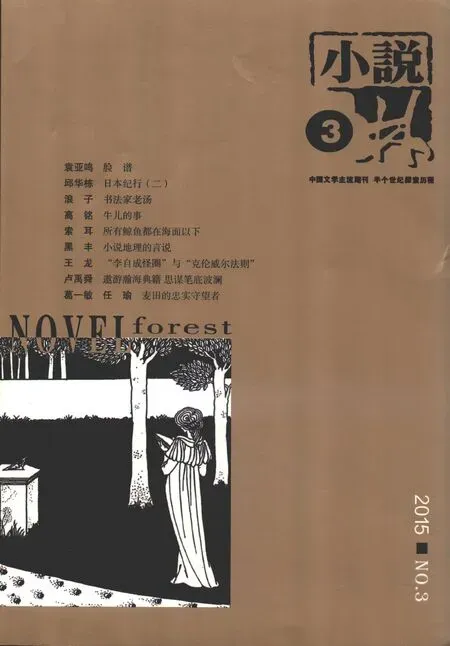隐藏的文学面孔
——评索耳的短篇小说《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
隐藏的文学面孔
——评索耳的短篇小说《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
或许不经意间,小说《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便令人信服地框定了一代文人的形象:他们现今五十岁上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度过人生与写作的双重活跃期。当然,同时又是“必须的”——在早前那个天真而狂热的“诗歌年代”还写过诗;在索耳的小说中,他们是叔叔和佩。
考虑到冷酷无情的时间流逝,合理公平的文学边缘化,上述这一群文人,应都已开始挂上日渐衰老的面容。但脸上的皱皮之下,隐藏着一张年青的文学面孔,所以偶尔还会在人前冒出几个文学表情。突如其来,往往令人错愕。先看看小说的结尾吧——佩和叔叔在婚礼上忽然念起当年写的诗,“他们的眼里已经没有别人了”。这些诗,让婚礼上的人们“不耐烦地走开了”。而在小说之外,我,一个大致与小说人物同龄的读者,停留在他们“真容”乍现的段落,感叹索耳写得有多么好。
佩和叔叔,他们暴露出了自己的那张文学面孔,若在当今现实生活中,这两人随即便得领受“老文青”之类的调侃或嘲弄了。但索耳却正色指认其为“鲸鱼”(不是吗?他说那些诗写在“幼鲸”之时)。在我看来,小说顿时便发生了奇妙的质变,成为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学言说。
文坛中人皆知,所谓“现当代文学史”有两种版本和制式,在“非公开”的那一版中,不同代际文人间的争斗与攻讦,有时如同一场微型文化战争。佩和叔叔这一代文人,对上一代文人呼喊过“PASS”的口号,不屑与嘲讽常作“投枪与匕首”使用……不同代际文人的分歧与区隔,肇因固然甚为复杂,有门派之争、观念之争,也有意气用事。然而,到了今日“我”登场写作之时,上述一切都被简化削平了(甚至没有一句吐槽)——索耳对于上代文人,只作冷静而审慎的言说,且不失敬意——在《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当中,闪过厄普代克、穆齐尓、卡夫卡、博尔赫斯……这些叔叔那代文人如数家珍的作家(亦为文学符号)大名。将他们穿插于小说中,是暗示写作者的文学师承出身,亦或在操作两代文人高格读品的隔空对接?索耳的同代写作者们往往乐于夸耀新型作文大赛优胜者的出身,多推崇二次元的审美趣味——这篇挟大“鲸鱼”登场的小说,相形之下,里外皆如此挥洒自如、从容不迫以及脱俗老到,的确令人惊艳不已。
小说从记忆开始。此时“我”的回忆,被伪装成了一个八岁男孩的单纯记忆,仿佛完全依凭彼时的生活经历写下。这篇小说的叙事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借鉴了侦探小说,后者总是在最后时刻才点明凶手,而该小说也在有意避免早早亮出佩的诗人身份。于是佩的四周,便没有了文学化的道具或氛围,陪伴他出场的,是一只被其烧烤售卖的穿山甲(四肢粗短,全身鳞甲,丑陋并令人生畏),且不可思议地昂贵至“五十元一串”。佩令人印象深刻,皆因作者别开生面的笔触,或许其中还有某种对诗人的敬畏之心——试想,若写的只是佩俗套般地售卖五毛一串的烤羊肉串,他无疑会迅速步入我们熟悉的“诗人-小丑”模式。之后,佩在小说中谈论“鲸鱼”、拯救鲸鱼,读来也并无突兀之感。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佩与令人生畏的动物同时出现,是自然的也是奇妙的意象。如同希腊神话中,天神的身旁常有猛兽相伴。这样,最后的一幕,便完全叩动了人心:佩尽管饱受长时间生活的压抑,还能在叔叔的婚礼上诗情爆发,因为真正诗人的体内,隐藏着巨大力量,像炸药一样等待点燃。
那么,另一位诗人,我的叔叔,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在世俗生活中,他是疏离的,却并不厌世。叔叔的内在性不在于他是诗人,而是拯救者,或替代的父亲。处理这个角色,索耳写其常态常性,带来一种在“我”成长的漫长时间中,叔叔的生活渐渐日常化,状态亦平稳的错觉。然而,横贯在《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整篇小说中的那种疏离感,却是由叔叔的平凡人生加以定义,又迅速弥漫开来的。小说写叔叔在婚礼前的若即若离,无所用心,此时他更关注仿佛不是去与他的新娘缔结夫妻之名实,而是再确认与“我”的那份深深的抚育之情。但这份感情,更接近于友谊。是某种因为文学的渗入而层次更为丰盈,却又难以名状的东西——“我”在小说情节中弑母,而非弑父,替代的父亲亦可被指认为“我”文学的父亲。于是在最后,当这位文学的父亲与诗同时降临时,也同样获得了“我”的再确认,接踵而来的便是喜悦、敬意,以及无尽温柔回忆。
《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写前代文人的文学行径笔墨俭省,点到为止,更多描述的是两代人生活与命运的交集;小说不是将文人的形象文学化,而是反其道而行,将其日常生活化。以其生活的面孔来遮掩文学的面孔,显然,这不是描写作家、诗人的惯常路数,所以,当最后的场景中一道生存的面纱被拂去,两条大“鲸鱼”浮上水面……文学的面孔变得生动而清晰,我们的掌声亦随之而响起。
海力洪,出版小说《药片的精神》《左和右》《夜泳》等多部,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执教于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