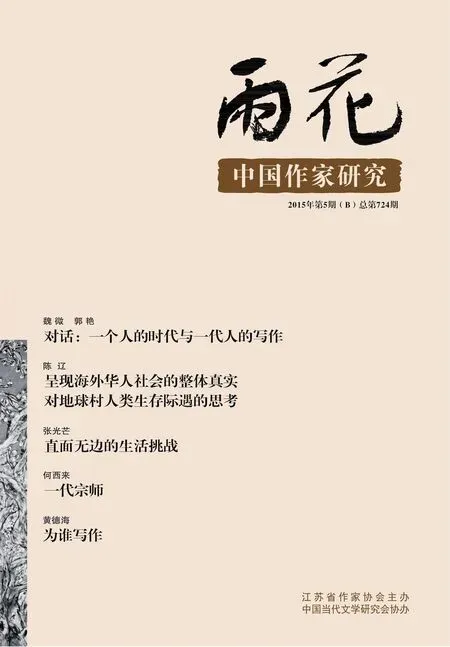创意写作的诗意如何可能
——中国高校写作工坊发展方向初探
■ 班易文
创意写作的诗意如何可能
——中国高校写作工坊发展方向初探
■ 班易文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创意写作系统已初具规模,美国的文学创作机制和环境随之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以爱荷华大学为代表的创意写作工坊,为“作家”和“写作”祛魅。写作工坊,这种发源于作家俱乐部传统,由沙龙等文学小团体演变而来的新模式,塑造了一个文学的新世界。从此,艺术和技术相连,由这种极其现代的文学理念出发,高校创意写作课程在设计之初便带有强烈的解决问题的意识,以求“创造性写作与高校专业性、学术性的教育联系起来,赋予创新与学术以联合的生命力”①(爱荷华大学,诺曼·福斯特语)。受益于这种联合的生命力的群体,既有参与到创意写作的学生,也有老师。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天分或兴趣的学生,由工坊找到了突破个人写作面临的种种技术问题;另一方面,伴随工坊模式而生的作家驻校模式,为一些愿意贡献于创意写作学科的小说家、诗人、艺术家们提供了职位和资源。而二者同时都能够突破个人写作的限制,找到面向市场,接受读者考验的直接路径。爱荷华作家工坊的成功,并不仅仅体现在这两方面,更重要的是由其培养出来的众多的作家作品所形成的交叉体系——其培养出的学生,进一步成为创意写作学科的教师,从而形成了创意写作的庞大系统。而高校在这一机制中,无疑承担着必不可少的平台功能。在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如火如荼之际,正应当反观美国写作工坊和创意写作发展经验,立足中国高校教育的特殊性,来探讨中国高校内的写作工坊如何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进行本土化的改变与设计。本文试图从工坊模式中的阅读(Reading)、写作(Writing)、反馈(Response)三个方面切入,这三点是创意写作工坊倡导的文学活动必要且基础的三个方面,同时也可以此为导向,构成创意写作课程体系所要建立的目标框架。
一、工坊引导下的形式阅读
作家工坊的明确目的就是培养作家,那么作家工坊所引导的阅读,自然就是让学生能够养成创造性阅读的习惯,以作家的思维去阅读。这种要求面临的首要的现实困境在于:读多少,读什么。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所处这个时代的人类造成了剧烈的影响,其阅读体验与阅读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2008年的美国NEA(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即国家艺术基金会)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大学生的阅读量令人堪忧,“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学生,在一周中,只花费一小时甚至不足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阅读活动”,②这与大学的竞争体制之下,学生面临就业等压力,专注于职业化的培训有关。在中国,大学生的阅读量同样不容乐观,新媒体的发展,使得学生在有限的闲暇时间,更愿意通过电子设备获得感官化、且互动性强的娱乐体验。新媒体带来的社交软件、游戏、影音娱乐,多少替代了传统书籍的地位。阅读领域本身也体现着媒介更新所带来的变化——现如今,学生们更加青睐搭载于移动终端的电子书,网络文学在文学市场的地位也逐步变得举足轻重。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学中的创意写作工坊应当倡导怎样富有独特性的阅读方式呢?首先,创意写作虽然强调培养创意思维之下的创造性阅读,但是仍旧是尊重和根治于文学研究批评阅读的传统的,正是这种尊重区分了接受创意写作教育的写作者和高校之外的自由写作者。在中国大学的传统的文学课堂上,学生接受的比较常规的“第一课”,就是抄写老师开出的书单。无论是学习批评,还是学习文学史,无论是学习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还是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都是如此。在创意写作工坊的课堂上恐怕也是如此。只不过阅读的书单包含的书目更加卷帙浩繁。笔者曾经为创意写作专业入学者列过一个基本阅读书单,其中不仅涉及文学作品,也包括哲学、历史方面的书籍。可以说这个书单是无限扩充的,最终由写作者自己列出个人化的书单,但其中经典文学作品必不可少。此外,大量的阅读必须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同时注重系统化、专题化,比如通俗小说阅读可以以小说类型为划分,以便加强以写作为导向的针对性阅读,旨在引导学生归纳类型叙事的成规,解决类型小说写作技巧的实际问题。
解决了读什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读。工坊阅读强调创造性地阅读,这是一种突破文学理论话语的阅读,同时也是一种打破作品权威的阅读。加里·霍金斯(Gary Hawkins)在谈到工坊制度的阅读课程时也特别指出,“事实是,今天的文学课程,越来越少地关注小说和诗歌的阅读,而越来越多地关注莫利斯·曼宁(Maurice Manning)所指的‘文学理论和伪政治话语’,他指出这种现象会导致‘无聊的、不言而喻的糟糕写作’。曼宁观察到,这种不幸的现实是‘当学生们来到工坊时,我们就知道他们已经丢失的:对于英语语言文学历史和传统的基本理解’。”③中国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研究生阶段,学生们学习使用各种批评“话语”,但是这些话语本身就带有政治倾向或者根本就是舶来品,长此以往,这样的文学教育模式便会造成学生丧失对中国语言文学传统的个人化理解,中文独特的审美意蕴便会消弭在“话语”的桎梏之下。此外就现当代文学教育而言,以中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为例,这些作品影响深远,其中不乏具有一定的艺术实验性的作品,但是学生的阅读应当从作品本身出发,而不是从文学史出发。忽视基本的叙事练习,一味追求风格甚至是片面地模仿大师风格,无疑是对叙事本身的不尊重,对文学传统的不尊重,这恰恰便是曼宁所言的糟糕的写作。
约翰·怀特海德、多萝西娅·布兰德、R·V·卡西尔、詹姆斯·福尔松等著名的创意写作研究者,在实践中形成了对于阅读方法的共识,那就是“像作家一样读书”。作家阅读,重视的不是文本的来源,而是关注文本是如何生成的,这就要考虑文本的构成形式。正如R·V·卡西尔阐明的那样,我们的读法区别于文学研究以及作品修辞形式的研究,他坚称所有的创意写作者都对文本是如何被制造出来感兴趣,对各部分如何组合成整体感兴趣,这意味着创意写作者承认这样的观点:“文本也许可以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生成”(Mayers,1994)。④因此,笔者认为,在创意写作工坊中,改写练习应当被推广,尤其针对小说这一题材,改写对象既可以是严肃文学作品,也可以是通俗文学作品,由此来对学生的写作能力进行一些基本的提升,例如改变叙事视角、叙事风格;改写情节走向、人物命运等等。毕竟工作坊的本意就是一堆工匠在一起,敲敲打打,而在创意写作视角下,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个故事表达了什么”,而是“这个故事是怎样表达的”。⑤
二、工坊氛围中的激励式写作
通过“像作家一样的阅读”,我们经由改写练习的方式,很自然地讨论到了工坊如何引导写作的问题,创意写作的工坊模式,虽然提倡积极地阅读和写作,但二者的界限是清晰的。这是指工坊写作和读者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作品面向市场需要考虑读者群即受众的问题,但是在工坊里,需要首先忘却条分缕析的写作规则,这也是和传统的作文教学所不同之处。也因而创意写作的潜能激发才至关重要。写作的前提,必须是写作者相信自己,突破心理障碍,认同自己的作家身份,然后想清楚作家的写作是一条艰难但是富有魔力的道路,通过练习自我施压,同时由工坊的领导者的激励与共同参与者的良性竞争带来一定的压力,比如最常见的限定写作时间的“速写式”写作练习。
一个完整成熟的写作工坊课程体系应该包括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两大类,前者包括短篇小说创作、中长篇小说创作、散文创作、诗歌写作、剧本写作,后者包括传记、论文写作、媒体写作、文案策划(又细分为广告文案、项目文案写作等等)等等。在笔者所在的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所开设的工坊课程中,已经囊括了虚构写作工坊和非虚构写作工坊二者。上海大学在富有特色的短学期制度之下,为时一个月的夏季实践性学期为创意写作工坊提供了学制上的保证。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中心与上海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创意写作夏令营,自2011年开始到去年(2014年)已经有四届了。这个写作夏令营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写作工坊,前三届参与者都是文学院的全体学生,而第四届伴随着上海大学通识教育和大类招生的改革,学生们选课的自由度更高,创意写作夏令营也开始面向全校各专业学生,只要报以兴趣和热情,都可以通过选课参与进来。如上文所述,工坊的有序进行,依赖于合理的分类。由上大的创意写作老师领队,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创作兴趣分为小说组、散文组、诗歌组、剧本组、文案组等几个小工坊,人数多的再细分小组,由创意写作中心的研究生作为助教带队,以保持每组成员十个以内,充分地保证工坊讨论的质量。工坊还邀请校外的著名作家作为写作导师,保证学生和作家有直接交流的机会,而作家们也会给予一些关于写作的讲座,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讲座,学者侧重于介绍自己的课题论文、研究领域的科研成果等,作家的讲座更为感性,就是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比如青年作家王若虚的讲座就介绍了他的成名作《马贼》的灵感由来,以亲身经验鼓励同学们描写熟悉的事物和日常事物,因为熟悉的事物联系着内心体验,日常事物写作同时又能够提高对日常的观察力;再如竹林老师的讲座就详细地叙述了她创作长篇小说的整个过程,甚至是遭遇的一些困难,真诚地告诉同学们写作是快乐的,但做作家却是要有毅力来克服种种困难的。这些经验无疑都为同学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之后校内老师的带队工作则更加细致,同学们会自由地讨论自己想选择的题材与体裁、内容与形式,互相评价,再由老师和助教提出建议。在第四届创意写作夏令营,老师们总结之前的经验,又加以创新。沿用之前线上、线下同步讨论的方式,线上利用互联网即时交流创作细节,线下则不断拓展空间,老师甚至会带领同学去名俗街、博物馆采风。在工坊课程中,学生们都会完成自己的作品,最后利用暑假时间,继续完善。最终,由学生自己校对、编辑、美化,做成精美的杂志。其中的优秀作品也有选送至校外著名期刊杂志发表的机会。可以说,这一过程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过程,而且还涉及了出版发行,使得工坊写作真正意义上成为完整的文学生产活动。
此外,上海大学的创意写作特色工坊还有剧本工坊,由葛红兵教授带领学生进行剧本的创作。工坊历时一学期(大约十周,每周一次),工坊领导者还有影视学院的老师,以及来自于影视制作公司的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专业指导者,所有参与者围坐在教室一同讨论,在前两周会定下基本人物设定,完成人物小传,之后两周分集创作,定下分集故事核,在之后三周讨论梗概,最后三周打磨剧本整体风格,在一门工坊课后,全体成员可以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可供直接投拍的网络剧剧本。
由上述的工坊教学的实际经验可见,创意写作专业的工坊是充分发掘个人潜力,激励个性发展的集体创作工坊,它打破了传统的写作是个人私密性的艺术活动的观念。在集体创作中完善作品,提高每一个参与者的写作技巧。在这个集体中,每一个人包括老师都是谦逊的,整体氛围是平等而自由的。中国基础教育往往以老师为权威,但是写作工坊更像是文学创作的“民主形式”,强调每个人的参与、讨论、相互激励。
“囚禁在创意写作的主观主义、表现主义牢笼中,唯一的法则就是事物的内在表现原则,就连最好的老师也必须承认自己有太多不知道的东西,也许只有彻底打破这个体系,才能够传授和习得文学知识。创意写作大概可以提供另外一种知识,告诉人们优秀的故事怎样构建人生的可能性;但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作为评价创作成就唯一标准的主观满意度,开始回应本体之外的、可能存在着他人的客观现实。”6这是梅尔斯对于创意写作专业内部改革的担忧:美国的创意写作工坊虽然表面上看发展迅猛,但实际上强调主观的个人表达,无法带来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价值系统,这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是十分难于有根本性的突破的,而年轻作家在其中最底层则是备受折磨。但在中国高校,情况恰恰相反,传统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权力十分强大,正需要创意写作工坊这种自由激励式的课程解放年轻写作者的天性。当然主观的诗意和创造力面对汹涌的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仍旧是脆弱的,但限制本身恰恰就是蕴藏无限能量的机会所在。
三、工坊打开的反馈空间
在上一段介绍上海大学的工坊课程倡导的写作方式中,创意写作的学科特征已然显而易见,那就是不仅仅强调写作这一行动,而且强调对于写作的反馈。在创意写作的视角之下,文学生产是一个有机动态的过程,其间的反馈从工坊内部而言,既发生在学生和老师之间,也发生在学生和学生之间,而学生或者老师本身有可能就已经具备作家、写作者身份,因此也不妨可将其看作是作家、写作者之间的讨论交流;从工坊的外部而言,工坊超越了一般大学课程的职能,是一个连接更多社会文化资源的有效平台,艺术家通过这个平台也可以面向读者和市场,在文艺市场的洗礼中不断保持创新的创作思维和积极进取的创作态度。
写作作为个人情感表达和诗意体验,首先必定是主观的,作家可以拥有权威和为自己保留的冥想空间,首先具有自足的内在王国,成为一个足够自信的国王,才能将丰沛的情感转化为故事、转化为一个由文字构成的具有异质性的世界。但是这个笔下王国诞生之后,其最终面临的是公共空间反馈的声音。普遍意义上说,任何的作品都期待被阅读和批评,卡夫卡交代朋友焚稿的佚事,多少散发着天才迷人而易逝的光晕,但是写作作为文化生产活动,少不了出版与发行的环节。甚至于网络文学和读者的互动模式,可以改变作者的创作思路,在创作过程中就产生了反馈带来的即时调整。
而创意写作的野心不仅仅在于文学作品的生产和作家的培养,更在于输出创意人才,支撑后工业时代的文化产业发展。在美国,就其文化输出的最大出口——好莱坞电影工业而言,就和创意写作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行业的巨擘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本身就是南加州大学的创意写作导师。现如今的中国高校和上世纪的美国高校一样,面对的是资本控制力空前强大的激变时代,全球化的发展也在逐步深入,作为文化大国,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将人文学科建设与社会文化产业紧密结合是必然的改革方向。上海大学建立“创意写作”学科在中国最初遭到的质疑之声,足以表明中文教育改革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在学生获得的学术“知识”无法适应社会需要,造成就业压力逐年增加的不良局面之后倒逼的。但随着2014年北京大学这一文学重镇,继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开设创意写作专业后,开始正式招收“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研究生,未来高校对于产业化运作模式的接受度将越来越高,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也会越来越系统化、机制化。
当然,在高校转型过程中,市场的主导作用会给人文精神带来不少威胁,我们不得不发问产业之外,那些“纯文学”怎么办?投射在工坊实践中,担忧即是过于重视“反馈”机制是否压制艺术中的“诗意”。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在足够成熟的产业思维关照下,“纯文学”也必将成为一种具有号召力的产品,它始终会拥有基数庞大且相对稳固的受众群体。而批评,也不会因为产业的发展而丧失应有的阵地,相反,可以通过这一过程更有力地回应文学作品、与创作者进行更有效的对话,甚至批评行为自身也可以成为一次富有冒险精神的创意写作体验。对此,劳伦斯·康拉德曾说,创意写作课的“核心内容”就是讨论学生的作品,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培养批评的勇气——“提高每个学生客观评价自己的作品,甚至自我批评的能力”,同时锻炼所有学生“将课堂评价当作自己作品的所引发的‘公众舆论’,而且要将批评者戳到的每一个痛处铭记于心”。7从这个角度说,工坊打开了一个新的批评空间,打通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甚至是来自于不同民族、国家的学生们,来自于社会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身份或职业的写作者们的讨论(当然这个民主化与民间化的过程将涉及高校以外的创意写作教育体系的建立以及更多的公共文化领域的实践,本文将不予赘述)。创意写作的兴起,其实也会带来高校之内“纯文学”批评复兴的希望,一方面,批评必须突破话语生产话语的困境,回归文本内部,而创意写作工坊引导的阅读恰恰就是进入文本的内部,甚至是讨论文本是如何生成的;另一方面,批评作为文学空间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反馈”,需要“在场”,需要直面正在创作的作品、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而不是或者仅仅是回溯文学史,写作工坊无疑提供着这样一种“在场”的可能性。
注 释:
① Norman Foerster,“The Study of Letters”,Literary Scholarship: Its Aims and Method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 ,p26-27.
② Burriesci, Matt. “NEA Report shows that Steep Decline in American Reading Skills will have Significant Long-Term Negative Effects on Society.” AWP Writer’sChronicle 40.40 (Feb. 2008): 1-2.
③ Dianne J. Donnelly:Establishing Creative Writing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2011,p110
④ Dianne J. Donnelly:Establishing Creative Writing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2011,p153
⑤ D·G·Myers:The Elephant Teach:Creative Writing since 188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⑥ D·G·Myers:The Elephant Teach:Creative Writing since 188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⑦ George Pierce Baker, Dramatic Techniqu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9), p.iv.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