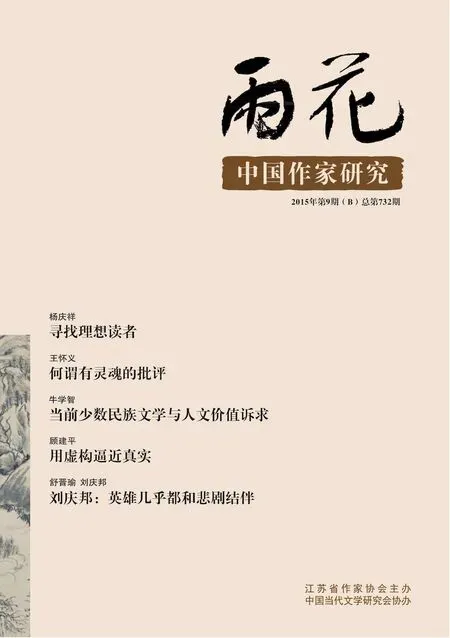记忆与历史的迷宫
——谈谈凸凹长篇小说《甑子场》
■叶开
记忆与历史的迷宫
——谈谈凸凹长篇小说《甑子场》
■叶开
面对深隐的历史迷藏,小说用何种角度去思考,去理解,去理清所有线索,让“历史”碎片复原成完整的叙事文本,是一名写作者面临的惯常难题。写作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寻找、阅读、消化相关资料,探访幸存者,受到激发,寻找一个特殊的线索——凸凹可能受到扣儿这个人物激发,脑袋里的一面墙上,突然长出一根藤,顺藤摸瓜,两边都是不可以忽视的事实之果实:一只瓜是单向叙事,两只瓜是双重叙事,四只瓜是多重叙事……围绕着扣儿的四个主要男人,与扣儿形成几个不同的叙事团,共同还原了一个“龙洛惨案”的可能真相——通常,历史类小说都要围绕着一个核心人物展开,如一个星图漩涡,所涉及的那些边缘,是叙事的边缘,以至于淡淡的无。
这里首先要谈到所谓历史和历史观念。
“历史”是被讲述出来的人与事。有些讲述可能逼近真相,有些偏离真相,有些歪曲真相——“真相”是另外一个要探讨的问题——因而有“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之类说法。对于四川、湖南、云贵等地的“剿匪”的认识,主要也是来源于“胜利者”,从胜利者的角度来重新思考那些已经沉寂了的事件。历史对于人性,有一种小说家的说法是:永远站在蛋的一边。蛋轻盈,丰沛,脆弱,硬度永远比不上石头。然而,蛋不是用来跟石头比硬度的。不过,中国总与众不同,更多人站在石头一边: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个中国,一个是世界。你懂的。
王朔好像写过一段有意思的对话:A谁敢惹我?B我敢!A哪,谁敢惹我们?立场的摇摆,和强者书写历史的立场,在这段对话中,昭昭然也。
不同立场,形成不同历史。不同叙述角度,生成不同文本。这些不同综合而成大部分我们对历史的整体认识,这所谓的整体认识,对于“原历史”来说也是局部的,片面的,你不可能在一次叙事中形成一个绝对准确而完整的“历史”。通过不同的叙事者、以不同的叙事角度还原“历史真相”,有可能出现某些“真相”——如美国和法国记者上世纪60年代写的《巴黎烧了吗》,也可能出现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所首先提出的“罗生门”——真相本身并不存在。
这与哲学困境有关。你必须承认不同叙事可能导致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结果。不同的屁股决定了不同的立场。黑泽明用“罗生门”揭示了人类认知和叙事真相的困境,同时也表达了人类认知的本质局限。通常来说,我们过于相信人类自己达到真理或真相的能力,我们以为综合所有能找到的资料,便能得出某种“真相蛋”般的结果。如,围绕在小说《甑子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里核心人物扣儿周边,有四个主要男人:鱼儿、安、禾、蛋,他们各代表人生中不同的态势,如同《易》里对未来世事的卦辞:“吉凶悔吝”——禾→吉,鱼儿→凶,安→悔,蛋→吝。
这四个男人代表的未来态势,决定了女主人公扣儿的一生遭遇:四分之一不到的幸福时光(包括与鱼儿的短暂的性与爱),与安的短暂婚姻幸福(以及六十年来每年一次零星地得到匿名者寄来的一封怪信所构成的暮年惆怅回忆)。扣儿的大部分人生(四分之三以上)由“凶悔吝”三者构成。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扣儿四分之三不幸人生的整体回顾,以六十年的时间跨度,作者试图还原“平叛剿匪”时代的疯狂人世间,以及可能有的平凡人生。
在长篇《甑子场》里,凸凹要还原“龙洛惨案”,就必须面对各种资料与不同叙述的谜团——作家写作过程是侦破过程。套用“罗生门”格式,“甑子场”是凸凹式多角度叙事——但“罗生门”最终否定真相,而凸凹试图还原真相。这是哲学观的差别,不是叙事的差别。
小说和电影在叙事上都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是历时性的,因此,无论你给出多少复杂的共时性虚拟空间,它都是历时性的——这是小说叙事的真正悖谬。莱辛在《拉奥孔》里分析了诗歌与雕塑的本质不同:诗歌是时间的艺术,雕塑是空间的艺术。现在我们可以说,一切叙事性文本都是时间性艺术,无论拟采用插入、倒叙、闪回还是其他什么神功,都不能违背这个事实。而雕塑和各种装置艺术(包括书法、绘画)则是共时性的艺术。历朝历代都有“野心家”企图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侵入别人的领地,例如近期最流行的科幻电影、诺兰大神的《星际穿越》等,但阴谋都没有得逞。凸凹的阴谋也没有得逞,虽然他在小说里不断回到某个断面:小说里有鱼儿和禾不断出没,他们死而复生,构成了小说中的叙事悬念,带来了繁复的危险和期待。
在小说《甑子场》里,凸凹兄不断设套,如龙洛那些心狠手辣的匪徒们(乌、鱼儿)一样,一会儿伏击外交官象,一会儿围攻运粮连队,一会儿挑衅龙洛镇黑老大安,而让我们这些读者成为打酱油者——鱼儿的“起死回生”,还有“禾”的略有些重复的“起死回生”,在扣儿的人生中,构成了一段紧凑的并行叙事主线。
但这些设伏,与小说中其他“碎片”一起,勾勒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图景,而不是破坏这种图景的完整性。如上所说,是“真相”,而不是“非真相”,在这层意义上看,凸凹兄不是先锋小说家,而是“伪先锋”小说家,他的小说思维是很传统的。很多批评家都曾经提及凸凹的“先锋叙事”。但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这种叙事停留在小说语言的皮层上——结构回环、事实拼贴,诗歌语言等。小说在语言上有不少闪光点,我记忆最深的一句是写安和扣儿结婚之后的甜蜜生活:一炮又一炮。六十岁老儿和二十岁嫩模有过一段相当不错的蜜月的描写,精炼而生动。“很黄很暴力”,但记忆深刻,但我觉得过于节制,并不满足。后来知道是编辑删改的,这是中国出版的秘密之一。至于匪徒们残杀外交官象及其护卫战士的场景,凸凹也不惜笔墨大加渲染,如挖掉副排长眼睛,砍掉他的脑袋,挂在树上等,营造一种血腥的场面。读过莫言长篇小说《檀香刑》的人,对其中用几十页、几万字篇幅描写“剐刑”和“檀香刑”的场面大概记忆深刻。相比之下,《甑子场》在渲染暴力方面(包括“涉黄”方面),仍比不上莫言,不够刺激,不能说够成功。凸凹兄的血腥场面读起来并不恐怖,可能是缺乏气氛渲染和场景铺垫的缘故。
长篇小说发展到现在,中外作家玩过各种形式和技巧,已经不堪再玩了,综合各种叙事手段,包括一些复古手法如典型人物塑造等,重新成为一种值得信赖的小说叙事方式。到了网络时代,“网络阅读”尤其“移动阅读”的新形态,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读者的审美和耐心。运用简练、短促的句子,塑造令人难忘的人物,提供精彩透彻的细节,铺陈引人入胜的悬念,就显得尤为必要。
当代法国作家写长篇小说,大多控制在10万字左右,老文艺青年崇拜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等不用说了,新小说派罗勃·格里耶的《橡皮》不用说了,今年新科诺奖者莫迪亚诺的《暗店街》、《星形广场》、《青春咖啡馆》等,还有2008年诺奖者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记》、《战争》等,都精炼短促非常。中国有特殊国情,还有特殊读者,时至今日,中国读者都爱读长篇章回体小说,网络上那些又长又赚钱的盗墓、穿越、修真不用说了,莫言也曾公开“叫嚣”说,长篇小说就是要长。完全是逆时代之潮流,螳臂当车的节奏。莫言之外,贾平凹、迟子建、阿来、王安忆等都写了大部头长篇小说。张炜老师更是放了一颗氢弹,由20部新旧长篇小说构成了长城般漫长的系列小说《你在高原》,一举创造了传统作家中几乎不可超越的吉尼斯纪录(但与网络作家比长短,那真是差太远了),甚至老牌先锋小说家余华也写了50万字的《兄弟》,格非写了70多万字的“江南三部曲”,以精短著称的苏童接连两部长篇《河岸》和《黄雀记》都20多万字,听说李洱兄在写50多万字的新长篇,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也有40多万字。这样的琳琅大长篇,构成了整个东方叙事的奇观,日本神人村上春树企图写个《18Q4》顽抗,结果发现势单力孤。
这意味着中国式叙事与世界主流叙事是脱钩的。不一定是坏事,也不一定是好事。我们的小说创作的强项在“宏大叙事”上,领导们推崇,主流批评家鼓吹,忠实读者热爱,时代性、历史性、政治性三位一体,让“大历史叙事”小说风靡一时,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开始,颇斩获了好几次茅盾文学奖。这样的“大历史”观成为中国式叙事主流,读得多了真是非常可厌。我个人觉得,中国式叙事的短板不在叙事上,不在结构上,而是在观念上。中国叙事在观念上,很传统,脱离了整个世界的潮流。但我们也不妨说,中国自有文学风流,不必事事迎合西方。这样的观念上的不合拍,乃至“落后”,使得中国叙事成为一种被边缘化的叙事,一种打着“宏大叙事”旗号的“小叙事”,有些汉学家批判中国作家叙事有问题,就是因为持这种立场所致。我们过分强调了“故事”和“故事性”,而对历史、对哲学、对现实,都放弃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我们的小说,则大多数停留在情感叙事和经历叙事的浅层,并浅尝辄止。
我读《甑子场》是断断续续的,无形中暗合了这部小说的叙事节奏。例如,我上一次放下小说送女儿上学,回家做饭,再拿起小说时,发现小说进入到了“现在”,叙事者“我”和一个不明身份的女生一起来采访老年扣儿婆婆,并且掺入了拆迁这类事儿。又发现,原来黑老大安的后面还暗藏了这么多的故事,他在被撤镇长被缴枪、回到安家大院之后,竟然发现国军地下行动负责人蔡、投降过解放军又摇摆不定的马、以及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鱼儿在桃花寺秘密聚会,带着一干哥老会信众来逼迫他高举反旗。
我看到的事实是,从乌开始的死亡,构成了小说中的阴沉背景:我军高官象,匪徒鱼儿,老“开明绅士”安,国军地下党领导菜,颇为脸谱化的报务员雪儿等,接连死亡,而铺叙了历史的底色。禾及扣儿活到了最后。禾被打成右派又官复原职,莫名其妙地写信给扣儿,试图讲述一个跨度60年的真相——谁知道呢?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禾一直在讲述一个谎言,是不是也有趣?
(作者单位:《收获》杂志社)
(责任编辑: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