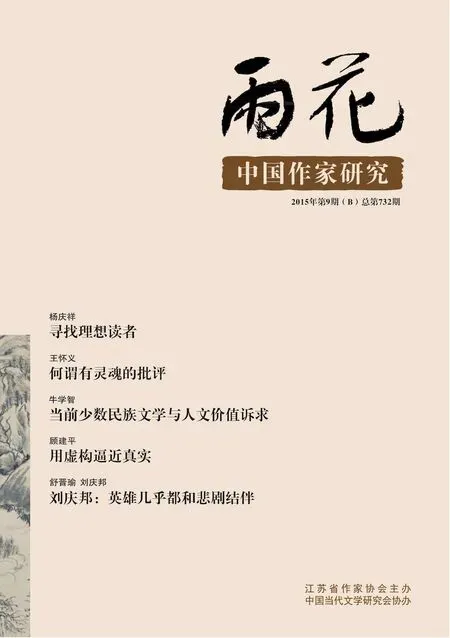悖谬一种:对“长篇崇拜”的非理性批评
■胡子龙
悖谬一种:对“长篇崇拜”的非理性批评
■胡子龙
近年来,对“长篇崇拜”的批评声音频频出现,渐渐形成了一种文学批评症候。在许多文学批评家的笔下,“长篇崇拜”被批驳得体无完肤,说什么正是很多作家的“长篇崇拜”,造成了长篇小说“唯我独尊”“一家独大”的局面,乃至出现了“体裁歧视”的不良后果,同时也把一段时间来尤其是眼下长篇小说质量普遍低、长篇小说创作不大如人意的现实,归结于一些作家们的“长篇崇拜”。
这些评论家所批评的“长篇崇拜”,其实应该是“长篇小说崇拜”。笔者的这篇小文姑且沿用他们批评中所用的“长篇崇拜”这个说法。
这些评论家对“长篇崇拜”的批评可以说是声色俱厉,“长篇崇拜”在他们的笔下成了“害人又害己”的“文学首恶”。但事实又如何呢?
首先,我们只要对中国长篇小说诞生以来各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就会清楚地看到,从来也没有因为长篇小说作家的“长篇崇拜”情结,出现长篇小说“唯我独尊”“一家独大”的局面,更没有造成“体裁歧视”的不良后果。
长篇小说在中国明清以来的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即便如此,在我看来也从来没有出现长篇小说“唯我独尊”“一家独大”,更没有造成“体裁歧视”。纵览明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史,长篇小说占文学主导地位的应该是明清两个朝代,多少年来让无数文学读者孜孜不倦欣赏阅读的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就问世于这两个朝代,故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说,尤其是《红楼梦》,问世几百年来,一直是一座后继文学人始终没能够成功超越的长篇小说高峰之作。但《“长篇崇拜”的原因及后果》一文所论,应该不是指向已经距离我们遥远的明清文学和作古几百年的明清作家,何况即便是明清,除了这几部被奉为经典的长篇小说和其他长篇小说外,也诞生了诸如以“三言二拍”、《聊斋志异》这样的经典短篇小说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若单以篇数论,抛开其他的中短篇不说,仅仅一部《聊斋志异》的篇数,就远远超过了明清长篇小说的数量,更何况同时期还有相当多的堪称优秀乃至经典的散文、辞赋、诗问世并传于后世。
到了现代,新文学运动蓬勃兴起,问世的长篇小说数量骤增,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作家创作和发表的长篇小说,数十倍于明清两朝的长篇小说,但长篇小说在现代文学中依然没有“唯我独尊”“一家独大”,没有出现任何程度的“体裁歧视”。稍微有点中国现代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时期,郁达夫、沙汀、艾芜、叶圣陶、赵树理、沈从文、萧红、冰心、许地山、钱钟书、聂绀弩、废名、张天翼、路翎等等创作发表的大量中短篇小说,与《子夜》、“激流三部曲”、《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围城》等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坛相映生辉,不分高下。特别是,鲁迅先生以《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在中外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在文学界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子夜》、“激流三部曲”、《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围城》等经典长篇。而且在盎然的现代文学之林中,除了小说,还有成千上万的散文和新诗、杂文、剧本,涌现出郭沫若、艾青、闻一多、冯志、戴望舒、徐志摩、臧克家、李广田、夏丏尊、曹禺、夏衍等大师级、大家级的诗人、散文家、剧作家。这些非小说的文学作品和创作出它们的作家,同样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熠熠生辉耀人眼目。这些作品,和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小说一道,并力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
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几年里中国文学的境况。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爆发的十七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和发表的数量的确很大,著名的就可以数出几十部,但这段时间里,《人民文学》《当代》《诗刊》等全国性文学刊物和各省市自治区文联作协主办的文学刊物,还有其他部门主办的文学性刊物,以及报纸副刊,非文学杂志的文学专栏,不也年复一年地正常编辑出版着,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诗、散文、杂文、剧本、报告文学,涌现出郭小川、邵燕祥、贺敬之、李瑛、公刘、流沙河、李季这样一些大家级别的中短篇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剧作家,留下了《百合花》《山地回忆》《驿路梨花》《龙须沟》等等无以数计至今依然脍炙人口的非长篇小说的优秀文学作品?一家家出版社不也大量出版了由新中国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杂文集?
十年文革是中国大陆文学的荒漠期,基本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问世。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问世,这个时期长篇小说“唯我独尊”“一家独大”“体裁歧视”就更无从谈起。“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中期,是中国大陆的文学热时期。然而在这个文学热时期,虽然也问世了《花园街五号》《冬天里的春天》《钟鼓楼》《沉重的翅膀》等数量可观的长篇小说,但影响最大的,却不是长篇小说,而是中短篇小说、诗和报告文学。可以说,在这个时段,任何一部长篇小说,都没有产生如短篇小说《班主任》《乡场上》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陈焕生进城》《高山下的花环》《人生》《人到中年》《黑骏马》《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那样广泛的影响,至于一些诗和报告文学,比如《小草在歌唱》、《周总理,你在哪里?》《歌德巴赫猜想》等等,同样让同时期的长篇小说望尘莫及。还有一点也可以应证当时的中短篇小说在小说上占有着压倒性优势,那就是小说发表产生巨大影响而改变成电影的,十有八九是中短篇小说——那个时候风靡全国的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红衣少女》《人生》《高山下的花环》《牧马人》《大墙下的红玉兰》等等影片,不就是由中短篇小说改编的?这个时期的长篇小说,无论怎么看,都属于逊色的一族。这个时期走红的作家,绝大多数是靠中短篇小说、诗和报告文学而走红的,专以长篇小说走红者寥寥。直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平凡的世界》《废都》等精彩亮相,才改变了长篇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尴尬处境。从20世纪90年代起,长篇小说的创作量和发表出版量确实是骤然增大了,特别新世纪以来,出现了莫言、贾平凹、刘志军、张炜、毕飞宇、阿来、麦家、余华、范稳等一大批以创作长篇小说为主打的作家,他们用推出的一部又一部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坛卷起一阵又一阵的飓风,让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坛显出了特别的亮色,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但这二十多年来,不同样也有严歌苓、刁斗、铁凝、徐则成、池莉、范小青、方方、姚鄂梅、罗伟章、苏童、须一瓜、刘庆邦、陈应松、滕肖澜、杨少恒、迟子建、阿成、聂鑫森、谈歌、夏天敏、张庆国、徐泽成、王祥夫、乔叶、胡学文、叶舟等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打的作家,李瑛、于坚、杰狄马加等以诗创作为主打的诗人,以及其他或以散文创作为主打或以诗歌创作为主打或以报告文学创作为主打的作家诗人,使中短篇小说、诗、散文、杂文、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创作继续呈蓬勃之势,各种文学体裁平分秋色。粗览一下新世纪里的文学作者,除报告文学作者队伍稍显衰落外,无论是中短篇小说作者、诗作者、散文作者、杂文作者,都要比长篇小说的作者多出去了许多!特别是诗作者,其数量几乎就是长篇小说作者的上百倍,数不胜数,创作的作品也是浩如烟海。大中城市自不必说了,就是随便一个县域内,都能聚起一个规模不小的诗创作群。又更何况,在现当代长篇小说作者中,你几乎就找不到清一色经营长篇小说的作家。他们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也根据各人的所好所长,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杂文、文学剧本、文学评论甚至纪实性文学。这样一种作者结构和作品结构,何来的长篇小说“唯我独尊”“一家独大”?又何来的“体裁歧视”?
这是从作家诗人的具体创作上来看的,转换视觉,从作为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文学刊物、报纸文学副刊、综合杂志文学专栏每年发表的浩如烟海的非长篇小说作品和出版社出版的数量数倍十数倍于长篇小说的诗集、散文集上,我们得到的,还是同样的结果。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详尽陈述。
其次,“长篇崇拜”没有错。“长篇崇拜”非但不应该受到批评指责,相反要给予热情的肯定褒扬。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历代许许多多作家的“长篇崇拜”情结,中国和世界就不可能产生那么多优秀的经典的长篇小说,中国和世界的文学成就将大打折扣。
前文说了,这些评论家所批评的“长篇崇拜”,其实应该是“长篇小说崇拜”。何谓“崇拜”?《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是:尊敬、钦佩。既然是尊敬、钦佩,毫无疑问包含了喜爱、热爱的意思。一个作家,尊敬、钦佩长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喜爱、热爱长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创作,即便是情有独钟,又何错之有?古今中外,不是也有更多的文学创作者,分别喜爱、热爱中短篇微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分别对这些体裁的创作情有独钟,有着不尽相同的体裁崇拜。如此多的文学创作者可以有“中短篇微篇崇拜”情结、“诗歌崇拜”情结、“散文崇拜”情结、“杂文崇拜”情结、“文学评论崇拜”情结,为数并不算太多的一部分文学创作者,怀有“长篇(小说)崇拜”情结,痴情于长篇小说创作,为什么就不可以了呢?为什么就要受到责备批评呢?而且更重要的是,千百年的文学创作实践告诉我们,正是文学作者们各自怀有的包括“长篇崇拜”在内的各种各样的体裁崇拜,单个的作家对某一种某两三种文学体裁深怀崇拜之情,以这份崇拜之情点燃自己在某个方面的文学创作才华,调动自己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知识积累,才源源不断地创作出各种体裁的优秀文学作品;各种体裁的优秀文学作品,汇成了层次分明浩浩荡荡的文学大森林。如同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一样,我从来也不相信,一个对长篇小说没有起码崇拜之情的作家,一个不喜爱不热爱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会自觉投入到长篇小说的创作实践中,会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创作出一部多部优秀特别是具有经典意义的长篇小说。更具体一点,雨果如果没有深厚的“长篇崇拜”情结,他能创作出《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悲惨世界》那样的经典长篇小说吗?巴金如果没有深厚的“长篇崇拜”情结,会创作出《家》《春》《秋》那样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长篇小说吗?莫言如果没有深厚的“长篇崇拜”情结,会创作出《丰乳肥臀》《蛙》《食草家族》《檀香刑》等十多部长篇小说,以至于终于折桂诺贝尔文学奖,填补了中国在诺贝尔文学奖上的百年空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家族中的莫言吗……而如果没有这些优秀的经典的长篇小说作品亮丽于中国文学之林世界文学之林,中国文学还是现在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吗?世界文学还是现在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吗?
由此可见,相比其他体裁的创作,在当今的文学环境中,长篇小说作者更应该得到包括评论家在内的人们的理解和尊敬;“长篇崇拜”非但不应该受到批评指责,相反要给予热情的肯定和褒扬。
但偏偏,我们的一些评论家对长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作家抱有偏见。这些偏见在眼下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横看竖看长篇小说不顺眼,横看竖看长篇小说作家不顺眼。在贬低长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作家、给“长篇崇拜”罗列种种莫须有的“罪状”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抬高其他体裁的作品和相关作家,特别是短篇小说作品和短篇小说作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短篇小说作家“致敬”。他们一会儿说,长篇小说因为篇幅长,容易掩盖缺陷藏污纳垢,欺骗读者的眼睛,因而不仅写起来容易,也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可,于是长篇小说创作成了某些懒惰型作家的首选。而短篇小说短小精悍的体裁特征,没有为偷懒的作家提供这方面的便利,因而是一种对作家的创作能力要求非常高的文学体裁,只有那些精品意识强烈的作家,才会钟情和专注于短篇小说创作。一会儿又说相比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给作者带来的经济回报非常低,如果没有对文学的真诚热爱,如果不是具备牺牲精神,如果不是淡名泊利,是无法坚持短篇小说创作的。殊不知,从创作的难度上讲,长篇小说对作家的要求一点也不比短篇小说低。但凡有文学常识特别是有过文学创作实践的人都知道,不同的文学体裁,由于它们的自身特点,各种体裁的特质化要求,每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创作上都有着难度,没有哪种体裁会写起来容易。要写出任何一种体裁的优秀篇章来,都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从作家的生活视野、素材积累、作品构建能力上来讲,长篇小说创作对作家的要求,比创作中短篇小说微篇小说对作家的要求要高出去许多,怎么可以说长篇小说创作是避重就轻呢?而从经济回报上讲,长篇小说创作不但不比短篇小说等短小作品丰厚,甚至不能和短篇小说等短小作品相比。作家创作了一个或一批短篇小说,只要不是质量太糟糕,全国那么多发表短篇小说的报刊,东方不亮西方亮,总可以找到发表的地方,然后获得一定数额的稿酬,尽管这稿酬一般不会很高。而长篇小说呢?中国就寥寥可数的那么几家使用长篇小说的刊物,如果不是大家名家,哪怕你写得再好,都几乎没有在刊物上发表的可能性。偶尔也有非著名作家无名作者在刊物上发表长篇小说的事,但几率比买彩票中五百万元千万元大奖还要低得多。交出版社出版吗?不错,有的作家,通过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就可以获得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成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可这样的长篇小说作家,整个中国大陆能数出多少个?绝大多数长篇小说作家出版长篇小说,要支付书号费,要支付编辑费装帧设计费,要支付纸张印刷费。几万块钱花出去,到手千把两千册书,有销路的,勉强收回成本。销路稍微好一些的,赚个几千万把元,但大多数是倒贴黄瓜二条。所谓发行,其实就是纯粹的赠阅,一些时候还要外加包装费邮寄费,经济物质高回报从何谈起?但即便这样,只要自己写的东西有人喜欢读,他们也发自内心地高兴,认为自己创造了社会价值,认为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了回报。可以说,长篇小说作家中的绝大多数,才是为长篇小说也是为文学为社会作着巨大的经济物质牺牲。可就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事实,这些文学评论家都看不到,或者说看到了装作没有看到。他们一边斥责长篇小说作家的“长篇崇拜”造成“体裁歧视”,一边又制造“体裁歧视”,而且是真正的“体裁歧视”。
至于说一段时间来尤其是眼下长篇小说创作不太如人意,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质量普遍低,一些甚至就是纯粹的文字垃圾,优秀长篇小说只占作家创作出来的长篇小说总数的一个很小比例,具有精品意义的长篇小说更是寥如晨星,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绝不是“长篇崇拜”惹的祸,正如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譬如诗歌散文,属于文字垃圾的不少,精品性作品只占很小的比例,经典意义的作品寥如晨星,不是“诗歌崇拜”、“散文崇拜”惹的祸一样。不但不是,相反,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不太如人意的状况,恰恰是长篇小说作者中的相当一部分没有“长篇崇拜”意识,严重匮乏“长篇崇拜”情结所致。在一段时间来特别是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队伍中,但凡没能创作出优秀长篇小说的作者,有很多是创作上的新手,尽管他们钟情于长篇小说,热爱长篇小说创作,把创作出优秀长篇小说作为自己的最大追求,也为此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和汗水,做了和正在做着艰辛努力,但他们这个阶段的素材积累、生活认知、人生经验、文学素养、美学素养等等,还不足以创作出优秀的长篇小说,捧出的作品与他们的原本诉求有着非常大的差距。除了这些作者外,还有两个类型的作者特别值得注意。一类是,不少创作能力本来比较强的长篇小说作家,浮躁心理作怪,在创作上耐不住寂寞,缺乏十年锻剑的严肃创作态度,盲目求多求快,甚至作家与作家存在着数量和速度上盲目攀比:比长篇小说书的厚度,比长篇小说问世的部数,比长篇小说问世的速度。由于只是强调长篇的部数、每部的厚度和推出的速度,理所当然地淡化了创作上的精品诉求,把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堕变成了粗制滥作的过程,原本能写出优秀长篇小说的他们,结果捧出的,是一部部粗糙之作、庸常之作、不堪卒读之作。另外一类是,很多作者甚至连小说的基本特征都没有搞懂,以为只要写进去一些人和事就是小说,以为只要以记流水账的方式不断铺陈生活琐事,使文字数量达到十几万字几十万字,就是长篇小说。于是出名心切的他们,把自己随意堆砌的没有任何小说特征甚至毫无文学意义可言的长文字,脸不红心不跳地以长篇小说的名义推出。这两种类型的长篇小说或者所谓“长篇小说”作者,毫无“长篇崇拜”可言,不是发自内心地喜爱、热爱长篇小说创作,而是把长篇小说作为获取虚名的一种手段,他们这是“虚名崇拜”,与“长篇崇拜”风马牛不相及。正是这些虚名崇拜者,严重伤害了长篇小说,糟蹋了长篇小说声誉。对这两个类型长篇小说或者所谓“长篇小说”作者,批评家是有足够的理由予以严厉批评和谴责的。但不能打错了屁股,不能让“长篇崇拜”和有“长篇崇拜”情结的作家替他们受过。
总之,作为一种个体性精神劳动,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体裁崇拜情结是正常的,不同的作家选择不同体裁从事文学创作也是正常的。因为正常,所以必须。文学评论家没有理由在体裁上和作家的创作选择上厚此薄彼,对某一种体裁和热衷于这种体裁的作家横加指责。唯如此,才能体现批评的公正,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获得文学的整体发展繁荣。一段时间来文学评论界对“长篇崇拜”非理性的批评指责,主观地武断地给“长篇崇拜”罗列种种“罪名”,让“长篇崇拜”蒙受不白之冤,让长篇小说作者不断受到来之文学批评界的指责、非难。这是一种“乱棒式”的批评——评论家捡一两根随意冠以某个名目的棒子,就劈头盖脸地朝着长篇小说作者和长篇小说打来,也不管打得有道理没道理。这种批评,非但解决不了长篇小说创作上客观存在的问题,相反制造了新的混乱,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造成了不可小视的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云南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汤娜)
——艺术体裁的修辞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