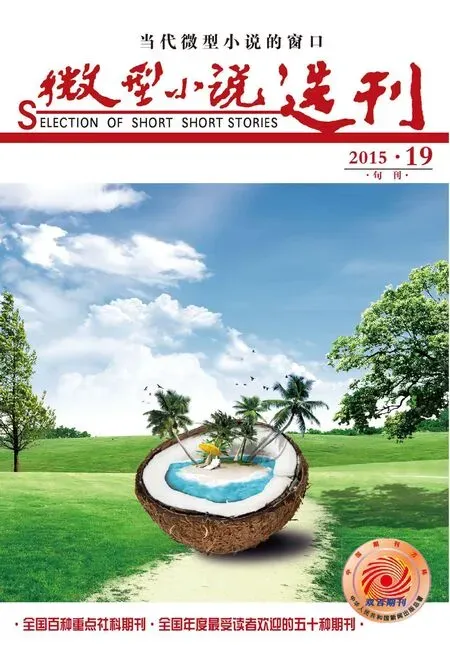疙瘩
□刘正权
疙瘩
□刘正权
蛤蟆打哇哇,四十五天吃疙瘩。
黑王寨第一声蛤蟆哇哇响起时,云秀大妈正在门外拿柴火。哇哇声吓了她一跳,跟着手像被蛇咬了似的往回一缩,柴火啪一声掉在地上,横七竖八在禾场上。
同时落在地上横七竖八的,是云秀大妈的心思。
西山脚下的太阳晃了一下,不见了,暮色就罩了下来。远远地,小叔子顺柱的咳嗽声一步步挪了过来,随着咳嗽声挪过来的,还有小叔子的脚步声。
这是小叔子顺柱第一次在傍黑把脚迈进她的院子呢,云秀心里慌了一下。自打男人顺友死后,小叔子二十年没在傍黑时走过她的家门了。
嫂子小叔,稀里糊涂。黑王寨虽有这样的戏言,但真临到自个头上,谁都会不由自主缩回头去的。
蛤蟆打哇哇了呢。顺柱没头没脑吭出这么一句话,然后拿眼盯着云秀。
云秀的脸一下子红得像块绸子布,眉眼低着,却不接话。
小叔子顺柱自顾自又补上一句,出新麦了,要吃面疙瘩了呢。
云秀顺了一下耳边的鬓发,嗔怪说,我又不是聋了瞎了,听不见也看不见啊。
顺柱一下子结巴起来,那,那你要记得啊。完了逃也似的跑了出去,像后面有鸡冠子蛇在追。云秀腿一软,就剩四十五天了,该怎么跟儿子张嘴呢?寡嫂跟光棍小叔子合家,好说不好听呢。
可想一想顺柱,二十年了,够难为他的,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年?当初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如今也成小老头了。夜色一点点浓了,蛤蟆声也一声声密了,云秀的心也一点点乱了。乱归乱,自己的承诺不能乱,云秀第二天一大早下了寨子,这么大的事,她得提前跟儿子通个气。
儿子接了电话,赶在麦收时回了趟家。虽说儿子眼下成了单位人,但寡娘的话还是听的,娘说新麦出来了,要给他做碗面疙瘩呢。想一想那些漂在碗里晶莹如白玉的面疙瘩,儿子的馋虫就往外钻。娘下的面疙瘩,均匀,全悬在汤水里,不冒头也不沉底,上面漂几片葱叶,要色有色要味有味。城里的面疙瘩不是没有,但总没娘用新麦面做出的香,亏还起了那么好听的名字—水上飘。
人可以在外面飘,但根是不能忘的。
儿子在单位请了假,为了寡娘,扣点奖金是值得的。
新面出来那天,云秀把厨房收拾干净了,又把自己拾掇齐整了,就开始和面。火架起来了,云秀探出头对儿子说,去把你叔叫来。
儿子跟叔亲,这点云秀晓得。小时候,小叔顺柱就是儿子的腿呢,上山下岭的从小学到初中,帮背书包帮着送粮食,一直到大学,还帮着送行李到车站。
合家,儿子应该没意见的。
小叔顺柱过来时,特意带了一瓶酒,吃新面是要喝酒的。面疙瘩就酒,越喝越有,好日子不就盼越过越有吗?
顺柱的胆子就是在酒的作用下才有的。喝到一半时,云秀把面疙瘩端上桌来,顺柱大着胆子一把抓住云秀的手说,忙了半天,你也坐下来喝一杯吧。
云秀急忙往回抽手,却抽不动,儿子的眼睛盯在两只手上。
云秀嘴一撇,喝醉了吧你?
顺柱说我才没醉呢,今儿当着孩子的面,你给我一个话吧。
什么话?儿子插了一句嘴。
合,一个家字没出口,顺柱脚被云秀狠狠踩了一下,顺柱疼得啊哟一声。
儿子问,叔你咋啦?
云秀接过话头,能咋呢?吃撑了呗,肚子疼呗。
顺柱见云秀脸色不对立马顺口说,我这是啊,乡巴佬不聚财,饭一饱屎出来。完了,装成要上厕所的样子捂着肚子跑了出去。
云秀一脸尴尬望着儿子,儿子是明眼人,这会儿却装糊涂,说叔要跟谁合家啊?
云秀半张着嘴,一时半会儿不晓得如何回答。
儿子不理云秀,继续说,不会是跟娘您吧,二十年您老熬过来了,还熬不过这二十天?儿子说的二十天是有深意的,他在城里买了房子,要把娘接进城呢。
还有二十天就要搬家呢。云秀的脸埋了下,蛤蟆的哇哇声也知趣地一点点消失。
儿子不看云秀了,站起身,说我要回城了,您把屋子料理干净,二十天后我来接您。
桌上的三碗面疙瘩就那么面面相觑立在那儿,有几个疙瘩在葱叶下探出头来,窥人隐私似的。
隐私,有吗?云秀叹口气,想起顺友去世时留下的话来,二十年后,孩子大了,你要记得为顺柱做一碗面疙瘩啊。在黑王寨,只有新婚的妻子才会给男人做新麦出来的第一碗面疙瘩呢。
顺柱的女人,是在粮荒时偷了队里的新麦给怀了娃的云秀做面疙瘩时被抓了现行,游街回来吊死的。有些事,是该让孩子知道的,顾不得孩子心里的疙瘩了。云秀站起身来,对儿子一端脸说,难得今儿个闲,娘讲个面疙瘩的故事给你听吧。
随着云秀的诉说,门外,蛤蟆的哇哇声又响了起来。顺柱老汉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一疙瘩一疙瘩砸在门槛上。
(原载《天池》2015年第7期湖北韩玉乐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