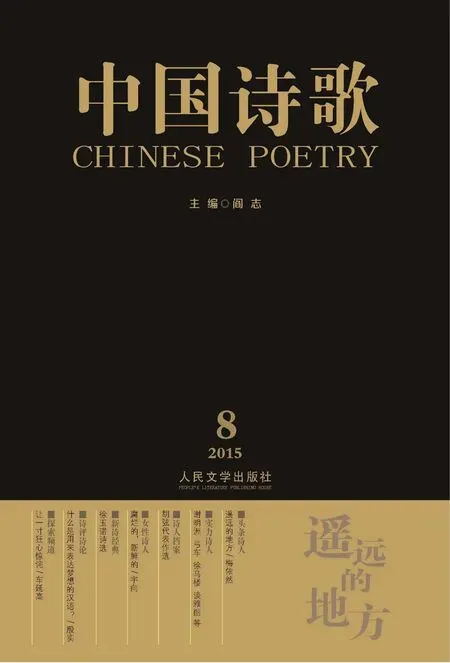遥远的地方
□梅依然
遥远的地方
□梅依然
朝圣者
“女人不在朝圣者道路上盛开,就将在睡床上枯萎”关键词:女性、生活、生命、尊严、希望、永恒
——一份女人手札
在这里,我们是自己的命运
我们只朝着一个高地走
珠穆朗玛峰、西藏只是象征
庙宇、喇嘛和格桑花也只是点缀
只有你和我——
你反映着我,我反映着你
我们反映了一个世界——
一个时代——
不漫长,但伟大
风吹得像大海和孩子的私语
啊,长长的风吹过高高的山岗
吹过宽广的河流
混合着田野的炊烟、我们的眼泪
以及黄昏的余晖
其实:
“一座花园般的孤独”
才是我们惟一的需要
——我们曾存在于此
仅此而已
遥远的地方
我仍然年轻
像一幅油画
一直生活在自我的框架里
在我一个人的故事里
我爱的人永远围坐在家的房子里
时光永远会在那里闪闪发光
但我始终渴望一个遥远的地方
而那里会有什么——
星空、瀑布、雪山、森林、草场、海洋……
我去过最远的地方
是和三个分别叫作叶子、花儿、流苏的年轻女人
穿越过喜马拉雅山
然后停驻在尼泊尔一条叫博卡拉的河流旁
“博卡拉——博卡拉——博卡拉”
“我是谁?我将到何处去?”
我听到了我骨头与骨头的歌唱
它们不断地呼喊着
鼓励我:向远方,向远方!
我不知道这条河流赋予其他人何种意义
可我确信
它就是我的老祖母身体里被割断的那条脐带
虽然早已埋进了历史破败的废墟
但一直在我沸腾的血的汁液里活着——
老祖母以我的名义如此活着
可是我活得还不够年轻、纯粹、认真
女儿,我要以你的名义再活一次
以你的眼睛重新观察这个世界
并再次爱上它
2.2 组织病理学改变 A组造模后,光镜下6h左右可见粘膜下层或固有层严重分离,肠绒毛腺体崩解分离、脱落缺失;12h部分肠绒毛上皮细胞开始修复,但轮廓不清;B组病理组织学改变较A组轻微,2h黏膜下层和肌层仅轻度水肿;6h粘膜下层或固有层轻中度分离,肠绒毛结构基本存在;12h修复明显。C组和D组肠绒毛完整,两组无明显不同。各组新生鼠肠组织损伤病理评分见表1。
哦,远方会有什么——
相信总会有一条河流将我和你带走
在一首诗歌的远处
2014年11月10日
我在日记上写下:
我的生活——
远离中东的冲突地带和乌克兰危机
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身体
正逐渐消失在我白色和黑色的日子堆砌的房子里
你呢,是否正处于自我的冲突地区,经营一个危机
而你渴望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
(你希望过上怎样的生活)
你是否戴着自己最喜爱的红色亚麻大披肩
坐在自己钟情的黄色的书桌前
读一本“关于女性如何生活”或是“心的岁月”的读物
用蓝色油漆涂刷的窗台上,那里
不时会有阳光的队列穿过女贞、桂树、苦楝的神经末梢
进驻你眼睛的隧洞和头脑的橱柜
你是否牵着女儿的手和爱人一起散步,感叹时光的消逝
你是否驾车陪伴母亲度过一段愉快的周末购物时间
这个冬日,不断从远处传来悲伤的消息:
难民营饥饿挨冻的人们、犹太人小镇上饮弹而亡的少女
被贩卖的妇女和孩子、孤独而死的留守老人
还有一些自杀者、冤死者、被杀者……
除了为这些不认识的人们感伤
献上我的祷告——我别无举措
而祷词也只是一种我为保护自己、安慰自己的辩护词
一如此刻,我如同一张明信片呆在家庭的邮箱等待寄出,收件人:我。
家族史
1
夏天仍在记忆里
那里有着鸟的合唱团的歌声
秋天却已过完
它的果实过于鼓胀、饱满而坠落
成为黄色土地的养料
而十一月,有着一张蛊惑人心的嘴唇“冷——冷——冷”
我开始怀念老祖母
她的手臂曾像黑章鱼一样搂抱我
陪伴我度过生命最初的冬天
2
我有一张地图
一条长长的河岸线
与充满悬念的爱相连
假如我旅行
会看到流浪的孩子和老人
我要庆幸而笑,他们不是我的亲人
旅途上,我也会哭泣
因为婚礼和葬礼总在不经意之地出现
3
我放弃成为父亲的部分
他活得恣意
保持孤独者的形态
从不为衰老的身体发愁
我也不会像母亲
她坚持有计划地活着
规律地出没在她自己的王国
为了粮食
4
我的躯体是盛放河流和爱情的印第安人陶罐
我要用弗里达的双手
忠实地记录一个女人的过去、现在
和“生命的愉快的尽头”
我有夏加尔的“三月的田野和小镇”
面对这个世界
我始终心怀敬意
5
女儿在闪着光的清晨的草地上奔跑欢笑
她那毛茸茸如鼹鼠般的旅程刚刚展开
将发生的故事
不久,我便会知道
但我不知道
我是否会成为我自己
为那未知的部分
而活着
经验主义
我善于放牧词语
它们像羊群散布在我易感伤的草场
渴望——总是不由自主、浑身颤抖
幸福——站在雨后彩虹的另一端微笑
痛苦——持久,可以感觉到我的存在
快乐——扇动一双天使的翅膀在瞳孔的尽头若隐若现
忧伤——常常发作,像一个容易感冒的病人
绝望——溺水者手中最后一根稻草
希望——悬崖绝壁上盛开的罂粟花
惊喜——一张好人的面孔
但是它们并不属于我
如同女儿不属于我一样
她像一颗秋日的葡萄脱离藤架
脱离了我的身体
进入另一条河流
其他的也不会属于我
只有这自杀者般的诗行属于我
我信任野雏菊的纯粹:站在田野里荒弃
有着一副端庄的忧郁症者模样
而我只属于未来和死亡
迁徙
按照“查无此人”的地址
退回到过去
这是我可以拥有你的方式
我又一次梦到一个大男孩
他是我消逝不见未有成形的儿子
是谁伤害了他
在厨房与谷仓的缝隙之处
是祖母“没有为自己而活”的遗迹
于是,我们以遗迹的方式存在
不规则的月光照耀着我们航行
退回到过去
我将会放任自己
像个无人领养的孤儿般生活
一点点星星之火
就能将自己点燃
可那样的生活
再也回不去
好时光
我咀嚼着一颗或两颗美国话梅
让甜和酸涩
同时挤占我的口腔和胃
潮湿的空气沿着开启的窗户进来
填满了我身边所有的空位
(我比别人缺少什么吗)
我眺望着窗外
一座高架桥
如一根精美的蛛丝
悬挂在河流之上
运送货物的列车
在那里慢慢爬动
不知道会驶往何处
雨水仍在远处的田野闪耀
那颤动的美
“像我们错过一次
还将继续错过的爱情”
我把思想投注其上
像一个亡命的赌徒
押上她的全部财产和运气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是新的一天
正在被我经历
纪念日
粮食,蜂蜜,阳光
柠檬水
今天,我们如此享用了
一天的时光
而遗憾从开始就有
光与影的线条
几乎完美
但并不无懈可击
水想补偿喷泉
当它从二十米高的地方坠落
破碎似乎可以预见
永恒替代短暂
这不属于放风筝的孩子的想象
他们在广场上奔跑嬉戏
那些所谓的意义也与他们无关
那精神与肉体的裂缝
渗出闪光的物质
——痛苦
是我们的普遍行为
灰色的雀鸟
从头顶飞来又飞走
黄昏降临
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狂吠,追逐着自己的影子
想想
无论哪种情形
取悦我们的往往
是我们自身
自愈者
黄昏
我们坐在山岗上
观看金色的光线如何
在田野的边界转换
树木绿色的海浪
在我们身边轻轻拍打
红雀鸟成群结队
从树林的另一边飞来
投入我们瞳孔的湖心
在那里溅起阵阵水花
我们依靠在一起
像两个稻草人
并不觉得贫穷与富有
在遗忘与记住之间
在过去和现在之间
一切事物看起来
都自得其乐
跟随回家的牛群
我们也起身
抖掉身上的草叶
仿佛抖落一个梦
将来——
无人知道
也不会有人看到我们离开
妥协的世界
悲剧
微笑着
他注视着人们
不管以前他经历过什么
现在他要解决的
是一个长长的假日
——他顺从地躺在床上
(对于这样的命运他曾挣扎过)
不需要花费任何精力
(他已将毕生全部耗尽)
就会到达目的地(他从没有制定过)——实践一个死人的责任与义务
人们专注地做着自己的事
偶尔看看他
又匆匆收回目光
为了让葬礼显得完美
并没有像日常那样去影响他
(还有什么可以影响一个死去的人呢)“现在我们是没有爷爷的孩子”
他们告诉她
“他还在那里呢”
她指着一块白墙壁上的黑镜框
(一个孩子又知道些什么呢)
——他面露微笑(除此外,他的一切都被掩盖)
注视着我们
只因我们如此愿望
喜剧
生命的尽头——
她完全没有觉察
肉体连接仪器
几条管线交叉缠绕着她
而呼吸急促如钟表
“一架活生生的机器”
一只眼睛紧闭
一只眼睛努力睁着
在静谧的房间
这样也是美的——
“我要等女儿回来,
给她做好吃的”
她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一生中
哪些是有意义的呢)
精神在此处打着结
——一件精美的礼物
要想尽办法送给所爱的人
“有”和“无”
我们如同旁观者
并不能给出好的建议或答案:
关于生命和爱
关于母亲和孩子
我们所知仍然甚微
倾诉
这是一只空空的肉体,一只朱红皮箱
躺在铺满水晶的阳光下
她需要一种持久而炽烈的痛苦来填满
一颗自由的心灵
需要燃烧成灰
需要一副风的形态
远处的田野里
已没有什么可值得信赖的植物
孤独
然而
我们无法控制:
比如——两辆迎面相撞的汽车
——一个女人衰老下垂的乳房
——我们越来越稀少的性生活
——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又结束于哪里
有一天,我们不再从睡梦中醒来
对这个世界说一声: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爱上你
进入一首诗的内部
当夜晚降临
我感觉到自己的内心
在某个地方停留
花坛中,一条蚯蚓借着雨水的力量
钻出泥土
它穿过石头的裂缝,偶尔驻足凝望
毫不在意前方是否有危险存在
——爬行或者凝望
随后,消失在一丛兰草下
不留下一丝痕迹
我感觉到
时间在我的血管中流淌
时缓,时急
甚至,我听得到它们的声音
汇入了一条河流
我享受这样的时刻
——我仿佛只在此活着:
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不知道下一刻自己要做什么
坦然接受,并任它悄然消失
失去的女人
“真正的死亡降临……”
我写下这样的文字留给后来的人
仿佛自己是那名先知
一切光线都不再被我的瞳孔吸收
我是如此之黑
黑得没有手指、没有头发
性感的嘴唇丧失了依附之地
再不能尖叫,再不能扭动
再不能触摸
层层空气重压着我
浑浊的雨水从我玫瑰的细缝中流淌
一切运动的元素逐渐变得冰冷
我的痛苦常常不合时宜地把我弄醒
让我怀念我的呻吟,我的尖叫
怀念我从没有做过的爱
我一直都在做噩梦
整日,我如此安眠于自我的墓地
而不必非要活得像个幸存者。
空白
午夜
我是否能够带着未成型的计划
驾车驶离小镇?
风已从山谷中撤退
明晃晃的车灯可以反映出一条
道路的晦暗不明
固定的线路
一开始便已设定
在一座婚姻的房子中
我们始终是缺少技艺的园丁
以为自己掌握了一切
而根源,正来自于我们对爱的渴望
如何学会控制自我的欲望
如何绕过绝望的雷区
而痛苦,多么适合于治疗
啊,我的思想停滞——
“我想……”
我已向我的时代透支过多
没有比月亮更好的理由
一个物体
为着圆满而照耀
来自古印度的黄金陶罐
倾倒出白银的汁液
凌晨两点
一个女人关在
自身不明意义的房子里
光的缝隙中
丛林、峡谷、海洋与花园之间
潮湿而闷热
鹅卵石小径如同一条眼镜王蛇
爬向另一片海滩
微妙:往往存在于
一个动物园里的两个物种
而遗留在沙滩的贝壳
为我们提供了特殊的美
粗糙而光滑
海浪退下又涨起
一次又一次
像我们褪色的激情
它要把整个大海洗劫一空
而我惟一的解释:
在之前或之后
都缺少一个男人赤裸的身体
想象与理解
我先安顿好躁动的四肢
而头脑迅速升温
像我日常做鸡蛋煎饼的平底锅
那里平常无奇
也不会产生痛苦
“滋滋”响的是油脂
和一块冒热气的饼
我要如何运用力量的词汇
将孤立无援的情感立于悬崖之上
精神紧绷,分为三种情形:
一种为欲望
另一种为压制欲望
第三种为压制欲望所承受的伤害
索德格朗的花园
尖顶式房屋
像一只无人驾驶的皮划艇
渐渐沉入黑暗的河流
也许它像我一样需要一个火炉
才能度过这个冬天最漫长的夜晚
在天空的天鹅绒床上
趴满了星星
“哪一颗是真正属于我的”
那旋转、闪亮的眼泪
正在进行自我裂变
它们失眠的方式
是让我们在噩梦中死亡一次
并再次活过来
寒冷的冬夜
女人热爱一个从身后贯穿自己的男人
除了睡觉
我们找不到更有趣的事情可做
荒原
这片荒原没有边界
如同一艘巨型货船
几根电线杆耸立在远处
像桅杆
风操纵着罗盘
我们可以去北美洲或南极洲
我坐在草地上
把手伸进野草和泥土相连的地方
那里并没有虫子出没
远处,一头黄牛在吃草
它骄傲的尾巴搅乱野草的水波
不远的地方
一对年轻夫妻在给孩子拍照
那女孩带着两只黑色水晶的眼睛
奔跑着格格的笑
以为整个世界都是属于她的
如我所知
上帝只会为我们准备一堆篝火
燃烧——熄灭
一部分人会等待星光
也许我会留下
也许会随着另一部分人
进入荒原的深处
我们是它一道莫名的伤口
被它容忍
女裁缝
她端坐于一堆色彩斑斓的布料中
双手温暖
和冰冷的缝纫机相遇
结合在一件衣服的成形之处
头微微低垂
眼睛专注固执
似乎她的一生
只与一件衣服发生关系:
布在机器上旋转
双手触碰到它
她以为就会触摸到他——
喉结颤动的脖子
粗壮的胳膊
光滑结实的胸膛
往下是平坦的肚腹
再往下——
再往下——
什么都没有
——一切戛然而止——
我给她安排了
最为忧伤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