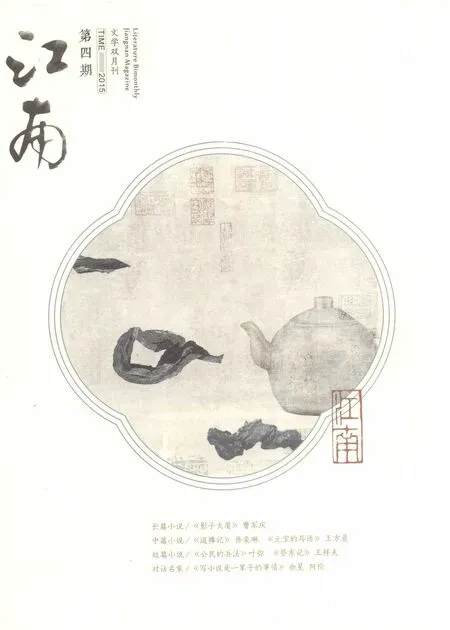写小说是一辈子的事情——对话徐星
□ 阿 伦
对话时间:2015年4月
对话人及对话整理:阿伦
一、我不喜欢大合唱
阿 伦:当年《无主题变奏》的发表,让您被称为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直到现在提起徐星,还是依然被称为先锋作家。那时您是否想过,把作家当成终身职业?
徐 星:没有,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职业作家。从出道到现在,一直就不是。我也不是什么作协会员之类的。我一直都是一个业余作家,现在我觉得我是一个业余的纪录片制作者。都是业余的,挺好的。我在边缘,有边缘的快感。
阿 伦:您认同评论家给您的先锋作家这个称号吗?
徐 星:所谓的评论家们,我对他们的评论是寄生在作家们身上混口饭吃的人。当时那个年代确实出名比较容易,什么都没有,电视都不多,你想想人们不看书干啥啊?所以有点儿怪声马上就会被听到,于是评论家们马上就闻到了饭味儿,赶快找概念的筐,往里面扔,争先恐后,这可不能落后,关系到吃饭。
阿 伦:也就是说,实际上您并不认同评论家对您的评论。
徐 星:我不看评论。先锋的意义是多重的。一般认为,所谓“先锋文学”是指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发起挑战的文学类型。我对自己的先锋性和“评论家”的定义有时有所不同。先锋,意味着你一个人孤独地奋力为之,甚至献身的某种局面。当大家习以为常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人记得你了。
阿 伦:能够感觉出,您是比较特立独行的。在您那个年代,能够自由散漫地生活,应该是一件挺酷、挺另类的事情吧?
徐 星:当时真的是惶惶不可终日。吃饭、医疗都没有保障,心理压力很大,但是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挺先锋的。结果,不出几年,社会上成批出现像我这样的人,下岗、离职成为普遍现象。
阿 伦:与您同时代的作家,大多写反思、写伤痕、写文革,因此文坛出现了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用个不恰当的比喻,那时所有人都吃西红柿,突然有一个人说我要吃土豆。您的那篇有些异类的成名作《无主题变奏》,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土豆吧。您是如何想到去写这篇作品的?
徐 星:就是因为西红柿吃腻了,看得太多了,跟我自己的文学理念相悖甚远。当时就是控诉,但其实都是挺概念化的。从反“文革”的高大全三突出变成了另外的三突出,没有从“文革”的套路里出来,我不满意。我觉得文学应该是有细节的,很敏感的,不是说塑造一个人物就是为了解释政策。当时看见这些东西很不满意,所以那好,我来尝试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我要唱就独唱,我不喜欢大合唱。别人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唱它干吗?
阿 伦:《无主题变奏》1985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试想,《无主题变奏》如果不放在当时的环境,是否还会一炮走红呢?
徐 星:我觉得完全不会。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里,人们刚刚从“文革”的泥沼里翻身出来,你只要发出一点和别人不一样的声音,很快会被注意到。今天我觉得已经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比如新闻,多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三两天就过去了,大家都不记得了,这跟当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当年文学的地位,我觉得也不正常,不应该是那样的,不应该是全国老百姓都要从文学里面找到政策、改革的信息。话说回来,今天的文学也没好到哪儿去,尽管从那种图解式的、概念化的东西里面产生了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不成熟的。如果我要接着说下去,你们杂志可能都没法刊登,但这确实是要求一种心灵上的自由、创作上的自由。
阿 伦:您有没有回过头去看自己的《无主题变奏》?
徐 星:我写的东西一般都不回头看。出版以后,每翻一点都会让自己觉得很羞愧,有点难为情。这是我写的吗?这么幼稚!为了避免这难为情,索性就不再去看。
二、反讽是弱者的强项
阿 伦:《剩下的都属于你》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取这个名字是想表达什么样的想法?
徐 星:这是一个不算太长的长篇小说,你用一天时间准能读完。小说是流浪汉题材,一般来说,流浪汉的期望值不会很高。流浪汉不会为了高官厚禄流浪,那么他们得到的也就是“剩下”的吧。
阿 伦: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徐 星:从1986年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作。当时没准备发表,计划是写一个比较长的长篇小说,但在那个时代,家里出了很多事,就被耽搁了。
阿 伦:我读这部小说的时候,非常明确的感到,这是一部绝对意义上的“在路上”作品。您也曾说过,非常喜欢在路上的感觉,游历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徐 星:在路上的意义在于,在路上你的感知触角全部打开。中国古人早就说过,“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古今中外那么多描写在路上的经典作品,它们无疑也会影响我。我个人非常喜欢流浪汉小说,《在路上》是这类作品之一。流浪不单单是一种生活方式,流浪还是为了和主流保持距离。你在主流之外,你才能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浊流,这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所说。
阿 伦:反讽是您这部作品的话语方式,您认为这部小说跟您以前的作品相比,有哪些变化?
徐 星:和我以前的小说相比较,可能这个小说更加尖锐,更加犀利。反讽是弱者唯一的强项,我是弱者。
阿 伦:为什么说自己是个弱者?
徐 星:因为无力改变自己,也不想改变自己。
阿 伦:我查资料看到,这本书在国外先出的是法文版。
徐 星:因为当时第一部分出版以后,我的法语翻译就已经开始翻译。后来她等了16年,我还没写完。她觉得就这些足够了,决定不再等下去了,所以就出了法文版。我因为自己的懒散,耽误了人家的工作,而且一耽误就是16年。
阿 伦:这部小说虽然成书于九十年代初,可是在今天看来,小说中描述的场景、人物、情感关系,放在今天依然不感到遥远。比如里面修皮鞋的女孩、年轻的姑娘、导演等等,内在状态没有任何改变,可否认为这是一部寓言小说?
徐 星:外在看起来,变化特别大,拆了那么多东西,建了那么多新的东西,真正的内在变化很难,得确立一种价值观,否则是没有办法产生什么大的变化,但是确立新价值观,是很艰难的事情。
阿 伦:像您刚刚所说,这部作品断断续续地写了很久。现在社会变化挺快的,《剩下的都属于你》中所要表达的思想,能否保证就是您真正想要表达的?
徐 星:我断断续续地写,对自己也比较不负责任,懒得改也懒得看。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对自己东西不太负责的人,比较随性。第二次出版,本来说好了,我校订一下,一直拖,后来我想算了,干脆就这样出版吧。第一部分在1989年都出过了。这是一部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当时我还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当时的语境,在今天看来在某些程度上可能已经时过境迁,另外我自己也渐渐苍老。对自己作品重新审视,有种种新的认识不足为奇。
阿 伦:您很早的时候就自己骑车,在大半个中国转,也喜欢坐着火车去各个地方。您提到过《在路上》这本书,说那种状态让您特别着迷。现在慢慢的年龄大了,那种让您着迷的在路上的状态,您还会持续下去吗?
徐 星:会持续。我现在还经常在想要出门之类的。我想训练两只大狗,做狗拉的车,然后就这样跟着狗走。狗的承重挺强的,像爱斯基摩人不都是狗拉雪橇吗。我脑子里有各种设计,这个车怎么轻便,怎么把狗套着,怎么把帐篷、衣物、随身带的东西、摄像机都放在这个车上,可能得找专业人士设计这个车。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不是挺好玩的吗?但我完成不了这个梦想,因为事太多,离不开。
阿 伦:您最近一次的远行是为了什么?
徐 星:去拍纪录片,走了十多天,辗转好几个地方。
阿 伦:能够看出来,您看着有些疲劳。
徐 星:对,昨天才回来。我推掉过很多采访,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
三、拍纪录片让我觉得幸福
阿 伦:您不光写小说,还拍纪录片,您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作家、导演,还是其他?
徐 星:我不给自己定位,这些都是别人给我定位的。我不是作协会员,也从来不参加会议,不参加评奖。有人说我是作家,有人说我是导演,对我来说都无所谓,这从来都不意味着什么。官方给我的定义是“三无”人员。当然,我的读者比较喜欢我,在他们心目中会觉得我是最好的作家。喜欢我拍的电影的人,可能我是最好的导演。别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通常说是自由职业者,而且还是混得不好的自由职业者,但也可以是作家、导演。
阿 伦:当初您为什么决定拍纪录片?这个工作是比较辛苦的。作家之中好像比较少有人去拍纪录片的。
徐 星:纪录片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文学。对我个人来说,纪录片是文学的另外一种载体。这个年代大家都叫它读图时代,都是手机、网络,要是巴尔扎克生活在现在的中国,他也会很绝望的,那种长篇大论的小说不会有人看了。我决定拍纪录片还有一个原因,我非常喜欢在路上,路上总能给我的生活提供新鲜感,拍片子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必须上路。我不拍事件,只拍人,这就跟文学有很多想通的地方。文学是用笔来写,我用镜头来做人物,就非常有趣,有挑战性,很好玩,非常享受。可能在外人看起来挺奇怪、挺辛苦的,跑来跑去的。最让别人不可理喻的是,它还是没有回报的事儿。但是拍纪录片让我觉得生活幸福,能够让我从中找到生存的意义。不做这些事情,我会不知道我要干吗。
阿 伦:您拍纪录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获奖什么的?
徐 星:获奖不获奖我没有兴趣,因为那是一个很繁琐的事儿,包括报名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拍纪录片更多的是享受,我很享受做这件事的过程,非常美。
阿 伦:就像您刚刚说的,纪录片是文学的另一种载体,拍纪录片让你觉得幸福,找到生存的意义,这些感受会不会反过来对您的文学创作有所帮助?
徐 星:目前我做了很多积累,也可以把它看做是文学素材。你看我拍的《文革编年史》就是一个很私人化的故事,要是写下来不就是一篇小说吗?一个悲剧故事,一个少年,为了一封情书,这一生就毁了。我现在拍的这个,也是一个“文革”时期的农村全景式的小说。其实差别就是用笔来写,还是用摄像机来表达。现在拍摄的手段很发达,变得越来越容易。作为一个写故事的人,可以尝试用一个新的手段,让文学创作更加丰满,更多样性。《剩下的都属于你》我当年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要是有现在这么成熟的视频技术,估计也不会选择笔。
阿 伦:《文革编年史》的名字挺大的,您为什么会特别关注那段时期?
徐 星:文革是我整个青春期的完成。我是1956年出生,1966年文革开始,1976年还没有真正的完,真正结束是在一九八十年代上旬。我的青春期在这十多年间完成,同时也是我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我自己解决了自己的怀疑、自己的不确定等等。对于任何人来说,如果你的生活里有一个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运动,一定也会很刺激你,你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所表达,这是很正常的行为。
阿 伦:您拍的那些人中应该有拒绝、不愿意接受拍摄的吧?
徐 星:有过,他们也有不愿意谈的。当然我在底层,我有一个跟他们打交道的经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交流方式,我能很快让他们对我放下戒心。
阿 伦:到现在您拍了几部纪录片。
徐 星:拍了五部。
阿 伦:能不能理解为你目前在做影片,算是地下电影?
徐 星:我自己也没法定义是地上还是地下。从严格意义上说,我拍的是作家电影。对我来说,这是文学的一个新载体。我既然拍了就想给别人看,就需要大家都能看到,但是不太可能,这里面有很多的障碍。
阿 伦:当一部纪录片拍完之后,您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徐 星:很高兴,它是我的一个作品,就像我写个小说写完了一样,会有成功喜悦的感觉。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怀胎十月,看到孩子出世的那种喜悦。
阿 伦:镜头语言和小说语言,目前您更喜欢哪个?
徐 星:写东西需要想、需要沉淀、需要时间,但视频手段很快、很直接,介入感很强,人跟世界、生活的直接对话,这样的交流目前很吸引我。
四、写小说是一辈子的事情
阿 伦:在大部分读者的眼里,您的身份还是作家。作为作家,您的作品数量并不是很多。与您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您是否觉得自己的产量较少?
徐 星:对,在欧洲参加图书节,记者采访我,说你作为一个作家,你认为自己的特点是什么。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是世界上写得最少的作家,他们报纸上就这么用了。其实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在1985年到1989年间,因为《无主题变奏》的呼声比较高,就把后来写的东西都淹没掉了。我还写过《城市的故事》、《饥饿的老鼠》,后来还写过什么殉道者,我都忘了。我真的是对自己的写东西是最不负责任的,一出去就不管了。无所谓,既然拿出去发表了,就不再管了。
阿 伦:中国的当代作家里面,有谁让您觉得是不错的?
徐 星:我觉得阎连科不错。年轻作家看得特别少,基本不怎么看。韩寒对我来说,不是文学,他确实在标准之下。还有郭敬明、安妮宝贝。我从来不觉得他们是文学,而是文学商业,也可以说是商业文学。不少青年作家出书,经常拿给我看,我挺多都很不满意。可能我眼高手低,但我确实挺看不上他们的。像韩寒、郭敬明我连看都不会看,觉得很造作,看不了。他们对语言没有感觉,离文学创作差十万八千里。
阿 伦:现在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各种信息狂轰乱炸,信息泛滥会不会降低您的感知能力?
徐 星: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确实会分散注意力。跟朋友吃饭,你会发现总有人用大量时间看手机。庞杂的信息给了人们逃跑的渠道,可以借此逃避思考。现在的逃避通道太多,多到无法面对自己的问题。我觉得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最好对这样的潮流要有所抵触,有自己的立场与姿态,才够得上“知识分子”这个词。但是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做不到。我可以吹牛说,他们都不如我。网络上,他们所塑造的那种形象都不吸引我,而且我也不屑,我没有时间去做那样的事。
阿 伦:我们常说文学的社会责任,是作家应该肩负的职责。对于文学的社会意义,您是怎么看的?
徐 星:我觉得文学的初衷在于自我表达。至于社会意义,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它会在社会上、在人群中产生认可和共鸣,这是文学的外在意义。
阿 伦:这么问可能不太礼貌,您现在主要是靠什么生活?
徐 星:没关系,在这儿没有什么礼貌不礼貌的,什么都可以问。生活,就是我给别人拍点广告,这儿挣点钱,那儿挣点钱,之后还有点稿费。有一些国外国内的稿费,不多,但是能活下去。
阿 伦:您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满意吗?我感觉您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
徐 星: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只要能活着,做自己高兴的事就可以了。要是生活有真谛的话,这不就是生活的真谛吗?对我而言,这就是生活的真谛。
阿 伦:您是否会感到焦虑和惶恐?
徐 星:没有,我一点都没有,这个确实离我很远,我体会不到那种焦虑,也体会不到那种压力。我是一个只要有温饱就没有什么更大梦想的人。要真有很多钱,我确实不知道该干吗,那会让很多事情变得复杂,会比别人更早白头吧。
阿 伦:过去有人采访您,问您对未来的憧憬,您说未来很迷茫,不确切,因为年轻,才50岁。现在您将近六十,临近知天命之年,心态上有没有变化?
徐 星:没有什么变化,也可以说我成熟得早,早就有了比较固定的认知。
阿 伦:您怕老吗?
徐 星:不怕老,老有什么可怕的。我连死都不怕,还怕老吗?
阿 伦:您现在所看到的世界和您年轻时看到的世界相比,您觉得变化大吗?
徐 星: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变化都是外在的。比如说经济发达了,技术水平提高了,高科技可能会带来一些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都是喜怒哀乐,生生死死。
阿 伦:您最不想写作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
徐 星:我不会在写不出的情况下,仅仅为了钱而写作。对于我来说,卖文为生比较耻辱,这仅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还有做些其他事情的能力。
阿 伦:您现在可以说是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写作素材,这些素材会一直放在那里吗?
徐 星:写小说是我一辈子的事情,迟早还会写。以后跑不动了,身体没这么好,精力没有这么旺盛了,我会启动这些素材,找到写小说的感觉。目前权衡的结果是我暂时放下笔,拿起摄像机。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老,既然有一个新手段,干吗不尝试一下?我写东西很慢,写的小说也非常有限。朋友说,穷成这样还不随便写点就发?但我做不到。瞎写有瞎写的才能,我的确没有那个才能。
阿 伦:非常感谢您向我们敞开心扉,聊了这么多。最后一个话题,最近您在写什么?您会给自己制订写作计划吗?
徐 星:不客气。我现在写也都是瞎写,不能算是文学写作,主要随感这些,就怕忘了,把它记一记。我没有一个写作计划,但是常常会有写作冲动,冲动完就过去了。
阿伦: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