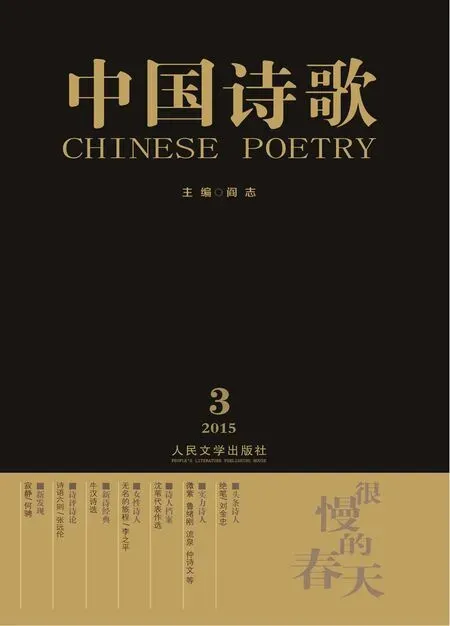悲 伤(外三首)
2015-11-15 00:33:15白鹤林
中国诗歌 2015年3期
白鹤林
整个早晨,一个老妇
在楼下。一直喊某个人的名字
我害怕这种声音,好像
一个人已经睡去,再也不会醒来
或者
根本不住在这里
深深地吸口气
在一张废纸上,我记下
这清晨的、措手不及的悲伤
恰到好处——致杰克·吉尔伯特
我不喜欢愚蠢的封面,也不喜欢
漂亮和煽情的句子。
我不是修辞主义者、偏执狂
和哗众取宠的口语派,
也不为了反对而反对去写博客。
我喜欢笨拙的人(他在外面快乐地种豆子)。
他总是追求少和隐秘。
好像诗人的工作不是写作,而是耕作。
而是谈话:恰到好处。
一个人的祖国
第一日。我看见母亲,在生日当天
衰老。在城东“老房子”酒楼
儿女们一桌,为她的生日和病体祝福
但谁能阻止生命,日渐虚弱的气息
第二日。我送别一位诗人,他驱车
而不是打马,奔赴雨中的剑门
他带着亲爱的妻子、兄弟和儿子
于诗歌和家庭之间,游刃有余过关
第三日。我听见婴儿,在另一个母体中
生长。“他或者她,该叫啥子名字?”
在建国门前的广场和百盛商场,小夫妇
为奶粉、名字和每日的开支,伤透脑筋
七日之秋。我的祖国一片繁忙
麻将的四川,钞票的广州,伟大的北京
一个人像一阵风一样,晃荡过
什么都降价的城市,和近郊热闹的乡村
明天。我还一定要赶在中秋之前
去乡下,给另外两位老人拜节。一个人
他从没干过什么大事,也不怎么惦记历史
但他一直这样认真地活着,在自己的祖国
先 知
他是阴沉的,像在地铁站口
遇见的肮脏占卜者
他是精于旁观的,像泄露的光
引证着局部的暗
他是偏颇的,像被蒙蔽的、残缺的文字
审判必然的死亡。在时间的快车上
他收买了时间,早定下预谋
把所有的无辜者
开往,一部电影的反面
猜你喜欢
文史杂志(2023年6期)2023-11-17 11:06:09
少年文艺·我爱写作文(2023年10期)2023-10-13 22:07:00
名作欣赏·学术版(2021年2期)2021-02-23 01:13:49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0年7期)2021-01-13 09:10:56
疯狂英语·初中天地(2019年12期)2020-01-04 02:46:50
环球时报(2019-12-05)2019-12-05 05:13:25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2期)2019-04-25 00:25:46
剑南文学(2018年6期)2018-11-22 04:20:23
少年文艺·开心阅读作文(2018年9期)2018-09-28 05:25:40
哲思(2017年8期)2017-11-01 11:56:58